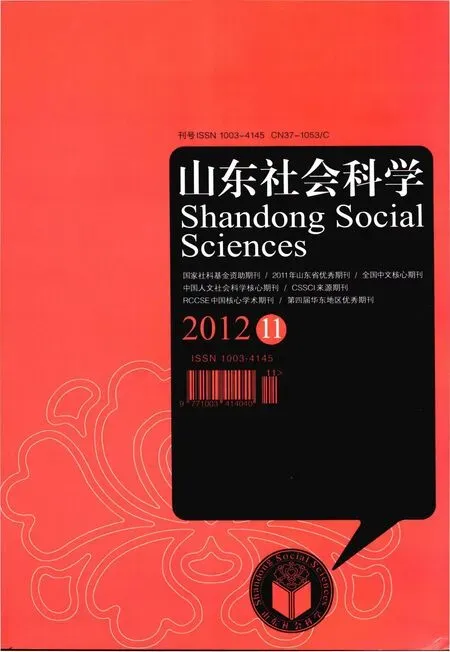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心同理同”说与“圣人”话语纠葛新诠
张向东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明末清初传教士携西方天文历算和水利、火炮等科学技术知识进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西方的天学知识和天学仪器远超中国,传教士籍此传播的地圆说、世界地图以及进行的历算推演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华夏中心说等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学者如何认识、应对这些冲击,并在这种认识和应对中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认知,也即是说,西学如何在接受者那里获得了观念基础,由此被建构起来,赢得了合法性并拥有合理性,是一个错综复杂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作为背景话语的“心同理同”说
明末清初所推崇的“心同理同”说,源于陆九渊的《杂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①[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73页。陆九渊的“心同理同”之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圣”。陆九渊强调,无论是千万世之前,还是千万世之后,只有“有圣人出”,才会“同此心同此理”,“古之圣贤,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也即是说,“心同理同”是以圣人之出和圣人之说为前提条件,舍此,则心同理同无所依托。二是“心”。把“吾心”与“宇宙”用“是”连接,强调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宇宙”(即时空)具有同等的价值,从而为二者的沟通提供依据。三是“异”。即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以千万世之前与千万世之后标识时间,以东西南北海标识空间),强调时空有差异,但真理却可以超越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心”和“理”具有普遍意义。四是“同”。即强调天下一理,“理之所在,安得不同”②[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73页。。
而就陆九渊“心同理同”说的思想渊源而言,笔者认为更可以远溯至孟子。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③《孟子·离娄下》。
曾经被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引用过的孟子的这段话,已经包含了陆九渊“心同理同”说中的圣人、时间、空间和天下一理(“其揆一也”)四个重要的思想要素,只是由于语境的不同,二者的表述各有侧重,孟子所侧重的是由圣人所建立起的道统,其后被李唐韩昌黎所倡导,至宋儒则奉为至论圭臬;而经过陆九渊阐发的“心同理同”说,由于更加侧重于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遍意义,则给明末清初的知识界提供了一个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知识和思想的观念基础。
朱维铮先生在《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中详细分析了利玛窦传教策略的确立与明末王学的关系,认为“利玛窦的传教路线,恰与王学由萌生到盛行的空间轨迹重合”,而利玛窦入华恰逢王学解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理论风行,宽容异教异学的人文环境为西学传播创造了条件。①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他进一步认为,“王学藐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②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那么,这种文化氛围究竟为何呢?笔者认为,从王阳明心学分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反动,阐发了新的“圣人说”。王阳明反对朱熹关于圣人集德性、才能与事功于一身,“做个圣贤千难万难”之说,认为只要人心纯乎天理而无私欲就是圣人,“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③[明]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在《大学问》篇中,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是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④[明]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这种人人可以成圣的“圣人观”和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人观”,蕴含了对传统“道统说”和“华夷之辨”的反对,对于西人西学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
其二,王阳明的心学,阐发了新的致知途径。王阳明说,程朱理学的大行,“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故“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⑤[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那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圣人之道又何见呢?“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⑥[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〇,《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这种不假外求,诉诸本心的心学,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也“不敢以为是也”。基于此,他进一步强调,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良知,都具有追求良知的道德意识,“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至李贽,则有不论贵贱贤愚,“天下无一人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之说。这对于作为外来者的西人西学而言,则提供了一种证明其学术地位的可能路径,即外夷亦可以为圣,西学亦可为真知。
其三,传教士与泰州学派、东林学派以及复社的交游,佐证了王学对西学的包容和接纳。作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李贽与利玛窦的交往,以及对利玛窦的评价,为学界所熟知。沈定平先生认为,利玛窦与李贽的交往,反映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西学与明末启蒙思想之间存在的某些可以相互沟通或契合之处,比如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对人人平等和爱人如己观念的宣扬,以及对交游士人的重视等等。⑦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9-461页。据黄一农先生考证,万历中叶至天启初年的进士和考官中,对西学西教持友善态度者,远超排拒之人。如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矫旨所颁的《东林党人榜》中,接洽与友善西人西教者包括:叶向高、魏大中、鹿善继、孙承宗、侯震旸、钱谦益、曹于汴、曾樱、崔景荣、郑鄤、李邦华、韩爌、朱大典、张问达、熊明遇等人,而除此之外的东林党人还包括,马世奇、史可法、张国维、黄淳耀、邹元标、冯琦、翁正春、侯峒曾、侯岐曾、李之藻、瞿式耜等人。而在被称为“小东林”的复社中,则拥有复社领军人物张溥以及魏学濂、熊人霖、韩霖、许之渐等一批西学拥趸。⑧参 见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第953页。李天纲先生的《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及续对此一问题亦有详细的梳理分析。他们或参与历法修订,或为西人著述作序,为西学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⑨徐 光台先生曾以熊明遇的《格致草》为分析对象,认为熊氏虽然没有脱离程朱理学对格致的理解来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但他明显对程朱历学持批判态度。见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学”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版,第235-258页。
正如朱维铮先生指出的,王学的诸种命题,“对正统理学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挑战。照王学的逻辑,必定走向撤除纲常名教的思想藩篱,包括所谓‘夷夏大防’在内。”⑩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也正因为此,明末清初士大夫中间,首先对利玛窦传播的欧洲学术和教义发生兴趣,乃至改宗天主教而不以为非的,有不少正是王学信徒,徐光启即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反之,在明末反教文本《破邪集》中收入攻击西士西说的文章,大部分作者都是以卫道士自居的朱学末流。
也许正是体悟到阳明心学的包容性,利玛窦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声称属于同一祖师爷的思想的各分支流派之间,尤其是在朱熹派与其对手王阳明派之间,神父却极力避免对两者持平等的态度:对王大师,对那种拒绝认知而求‘感知’导致的几近神秘主义的态度,利玛窦是宽容的;而对被贝尔纳——梅特尔神父过分简单地称作为‘朱熹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学说,他却加以批判。”①[法]艾田蒲(René Etiemble):《中国之欧洲》,许钧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242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晚明王学崇尚自得的传统和王阳明承认“涂之人皆可为禹”,导致承认陆九渊关于古今中外都可出圣人的推论,则可以作为明末士人接纳西学立足中国的直接理论基础。
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一个话语诠释的问题,即传教士到底如何看待东西方圣人之说。从以上我们的分析看到,西学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解决与中国道统和学统相契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一旦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方式予以诠释,就蕴含了东西海皆有圣人出的命题。但在耶稣会士的话语系统中,圣人却有着明确的概念限定,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词汇。
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多次使用“大西圣人”之说与孔孟之说相讨论,以证西说不诬。而对于西人如何称圣,他却明确表示了不同于中土之说,“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况称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诸侯得天下,虽不行一不义、不杀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国未谓之圣。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荣约处,仅称谓廉耳矣。其所谓圣者,乃其勤崇天主,卑谦自牧,然而其所言所为过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若有神功绝德,造化同用,不用药法,医不可医之病,复生既死之民,如此之类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来。敝国所称圣人者,率皆若此。”②[意]利玛窦:《天主实义》,《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第629-630页。
这样的表述,便将中西方圣人的标准完全两隔。按照利玛窦的标准,③之 所以称之为利玛窦的标准,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来华耶稣会士都将“圣人”作为一个需要严格界定的宗教词汇,比如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就曾说,“极西诸国,总名欧罗巴,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记。”圣人并非能通过自身的修养而达成,人之成圣,必自天主而来,因此在知识层面上讨论圣人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孔孟在西人看来均不能称为圣人,从而在逻辑上也就难以把东西海圣人之出作为中西学心同理同的前提。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传教士并不反对儒士教徒使用心同理同之说,但在圣人说上,却无法明确表示其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就造成了其后的传教士和儒士教徒一方面使用心同理同说作为西学立足合法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规避陆氏此说中的“圣人”要素,使其成为一种具有较高认同度的理论。
二、心同理同说的使用及身份标识意义
明末士人阐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说,用以作为接纳西学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冯应京1601年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所作的序文。这一篇幅不长的序文,表现出作者初次接触西说的新奇和愉悦,对于“心同理同”说并不加阐释,只是描述一种对于中西学问契合的直觉,他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在《山海舆地全图总序》中,他则试图表现这样一种思想,即中西之学彼此之间并无源流和师承关系,但各以圣人之学为本,“各以心之精神”增益知识,却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乃至达到“联万国为弟兄”的理想境地:
“圣人立极绥献,代天以仁万国,夫亦顺人心以利导,而吾徒顾瞻寰宇,效法前修,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薪火相传,何知其尽。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上帝为公父,联万国为弟兄,是乃绘此坤與之意与?”④[明]冯应京:《山海舆地全图总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冯应京与利玛窦、徐光启等人颇有交往,对于西方科学却并无深研。其对于中西学之关系论述,所反映出的当为明末学者特别是思想较为活跃的士人比较普遍的观点。⑤南师仲为程百二所编辑的《方舆胜略》作的序言中说,“盱眙公(冯应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那么,我们从其时学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此一学说怎样的发展轨迹呢?
李之藻是心同理同说的积极倡导者。1602年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序》中说,“(此图)别有南北半球之图,横割赤道,直以极星所当为中,而以东西上下为边,附刻左方。其式亦所创见,然考黄帝《素问》已有其义,……以天中为北,而以对之者为南,南北取诸天中,正取极星中天之义。昔儒以为最善言天,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与兹不信然乎?”①[明]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序》,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169页。
李之藻以其地图知识的素养和协助利玛窦绘制万国全图的经历,思考中西地图制作的异同,认为在知识层面上,西学与中学“意与暗契”,虽属不同进路却有相同的意旨。
在一年之后撰写的《天主实义重刻序》中,李之藻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同理同”说,认为西人的学术传统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但其心性实学、立教之言却与古儒之说契合。“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於正,至其检身事心,严翼匪懈,则世所谓皋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②[明]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版,第354、355-356页。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因作者与西学的初步接触,还停留在猜测的层面,那么,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李之藻已提出西人圣学的地位问题,明言西洋圣学自有道统。认为西人携来天文历法、测望、仪象、水法、医理乃至格物穷理等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深惟学问无穷,圣化无外,……遐方书籍,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但其言语文字绝不相同。”③[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不仅如此,在对西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李之藻还试图突破陆王的圣人说,从建立西学传播的合法性的角度,对心同理同给出更多的诠释。在《同文算指序》中,他认为,西人算学“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句股,开方测圆,旧法最难,新译弥捷。夫西方远人,安所窥龙马龟畴之秘、隶首商高之业,而十九符其用,书数共其宗,精之入委微,高之出意表,良亦心同理同,天地自然之数同欤?”④[明]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天学初函》,台北1965年影印版,第2782页。
在这里,他以数学知识为例,认为诸如三角形、圆形的计算,方程式的设立等方法,尽管中国早有旧法,却不如西人之法简洁实用,其原因恐不在于西人窃取中国古法,而在于“天地自然之数同”,也即是以对自然的研究为对象,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路径都可得出相同的结果,产生相同的理论。这样的论述,已经远远超出了为西学立足寻找理论依托的需要,而进入对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思考。⑤李 之藻此说是否对其后的梅文鼎造成影响,笔者未敢妄论,但我们确实从梅氏的《堑堵测量》卷二见到这样的说法,“东西共戴一天,即同此勾股测圆之法,当其心思所极,与理相符,虽在数万里,不容不合,亦其必然者矣。”见梅文鼎历算全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15页。
如果将这种思考与《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所讲的西学“言天文历数”而“我国昔贤未及者”十四事结合分析,或许可以认为,李之藻的着眼点和根本目的并非罗列中西历学的种种不同这样具体知识层面的问题,而是在尝试为西学的道统建立一个确切无疑的标准,那就是以“言所以然之理”为表现形式的严密的逻辑推理,“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原穷委,步步推明”,这与他所认为的儒者“两千年来推论无征,谩云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夫不议则论何以明,不论则存之奚据”⑥[明]李之藻:《译寰有诠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九四,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页。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为可贵的是,李之藻在对中西文化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独立综合创造精神”⑦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在《代疑编序》中,他的表述充满激情,认为对学理的辩难应当是“一翻新解,必一翻讨论;一翻异同,必一翻疑辩,然后真义理从此出焉。如石击而火出,玉砺而光显,皆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始虽若戾,终实相生,安见大异者之不为大同也。……其真同者,存为从前圣教之券,识东海、西海之皆同;真异者,留悟后进步之灯。”⑧[明]李之藻:《代疑篇序》,《天主教东传文献》,吴相湘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472-481页。此序徐宗泽误记为林起所做,刘耘华在《诠释的圆环》中已经指出。在《译寰有诠序》中,他进一步提出“人能无尽”思想,“原夫人察灵性,能推义理,故谓小天地。又谓人能参赞天地,天地设位而人成其能。试观古人所不知,今人能知;今人所未知,后人又或能知;新知不穷,固验人能无尽”。这种“人能无尽”的知识进化观,显示其思想的深刻,不仅在于对异质思想的准确把握,而且其把握的方式显示其已经站在儒学道统思想的框架之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超脱的态度。①关于知识的渐进性特点,徐光启在对历法的研究中亦有领悟。他说,“如时差等术,盖非一人一世之聪明所能揣测,必因千百年之积候,而后智者会通立法;若前无绪业,即守敬不能骤得之。”他甚至将这一理论作了过分的强调,进而否定了知识增长中的革命。“人虽上智,于未传之法,岂能自知。有而后尽心焉可矣。”见徐光启:《日食分数非多略陈义据以待候验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9页。
相对于给予西人圣人地位的李之藻而言,曾深受王学影响,倡导人之初“本与天为一耳”,“故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一也”,“率性之道,顺天之则,与天下大同谓圣人”②[明]徐光启:《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若何解》,《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09页。的徐光启,对于认同西人的独立道统并无理论上的障碍,事实上,他曾针对中国士人以“西儒所持论,古昔未闻也”之说作为拒斥西学论据的做法,强调“古人之前未有古人,孰能无创乎?天地万物皆创矣。”③[明]徐光启:《景教堂碑记》,《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1页。其中已经暗含了西人之说可为独创的可能。而通过对西方天文历法的研习,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言所以然之理”是西学不同于中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导致传统历法久废的重要原因。这种以能否“言所以然之理”为标准判断中西之学的优劣,明显呼应了李之藻对于西学的评判标准,同时以“泽火革”、“苟求其故”这样的古圣人之言,为西学独立的道统提出论证,显示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在徐光启思想中表现出深刻的复杂性。
在著名的《辨学章疏》中,徐光启以护教者的立场,将传教士称为“圣贤之徒”,“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④[明]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31页。其持论虽不免夸张虚言,但从《辨学章疏》之后朝野接纳西人治历而言,西人的学术传统,至少是在天文历法领域的知识传统,已经成为儒学道统必须直面的对象,是将其纳入道统,还是拒斥之为另类,已经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李之藻和徐光启对于“心同理同”说和“圣人说”态度的相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具有阳明心学这样共同的知识背景,那么同为儒士教徒的杨廷筠等人对待“心同理同”说的立场,则显示这一学说的高度“可适用性”和使用语境的复杂性。杨廷筠在代疑续篇中,完全从知识普遍性的角度论述此一问题,说,“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原自八荒我闼,而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不矜、不伐,更见大道为公。何必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将世间公共学问,认为一己私物,龊龊焉其不广也。”⑤[明]杨廷筠:《代疑续篇》,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北京大学2003年版,第249页。
李应试和瞿式穀给予西学不同的定位,却都使用了“心同理同”这样的论证方式。李应试在《刻两仪玄览图》中说,“然西方人声音文字与中土殊,殊而能同,盖心同理同,其学且周孔一辙,故贤公卿大夫目接而雅敬之云。”⑥[明]李应试:《刻两仪玄览图》,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相比较而言,瞿式穀显然更倾向于给予西学独立地位,他认为,“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⑦[明]瞿式穀:《职方外记小言》,《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第1300页。
相对于对西学有深入研究的儒士教徒而言,以普通士人身份入教的知识分子,对于“道统说”以及“圣人说”的表述更为大胆。收入《熙朝崇正集》的苏负英赠西教士诗,既有护教之论,又有浓厚的陆王心学味道,曰“吾师海外至,海道与云连。……直探周孔奥,高揭昊旻颠。同证此心理,修精即圣贤。”⑧[明]苏负英:《闽中诸公赠诗》,《熙朝崇正集》,《天主教东传文献》,吴相湘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677-678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收入了“上洋陶淑天懿氏”所作的“呈泰西孟师诗”,视西来教士为“圣人”,同时又力图证东西道统为一体,颇可作为教内士人对西海圣人说的立场,既不同于传教士本身的立场,又与教外士人有所差异,其关键点仍在“圣人”和“道统”。其诗曰,“向道西方有圣人,百年始得见来真。依稀道脉传孔孟,仿佛恩光烛汉秦。……诸方风俗千乡异,万国生灵一德同。愚贱私存尔我见,故教大道未流通。”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对“心同理同”说的认同,远远超出奉教士人的圈子,特别是与传教士们有较为密切交往的士大夫,普遍将其作为与西人交流并学习西学的正当性前提。如米嘉穗在为艾儒略的《西方答问》所写序文中写到:“学者每称象山先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说,然成见作主,旧闻塞胸,凡记载所不经,辄以诡异目之。……先圣、后圣不必同而道同,即东西海、南北海之圣人亦不必同而无不同矣。……岂天不爱道,不尽于尧舜周孔者而复孕其灵于西国欤?”⑩[明]米嘉穗:《西方答问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因此在他看来,那些视西学为诡异之端,并因此而拒斥的士大夫,实际上背离了先贤的教诲,为狭隘的成见所束缚。
教外士人如毕拱辰,参与了邓玉函译述《泰西人身说概》的润定,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秉持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说,且通过将西人关于人体构造的知识与中医相对照,认识到西学成就实有高出中学之处,认为“远西名士,……著有象纬舆图诸论,探原穷流,实千古来未发之旨。俾我华宗学人,终日戴天,今始知所以高;终日履地,今终知所以厚。昔人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惟西士当无愧色耳。”①[明]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三、会通超胜之型模与道统的关系:以徐光启为例
从“圣人说”角度诠释心同理同,更多的是从道统层面为西学建立合法性,而会通超胜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则更多着眼于具体操作层面的探讨。徐光启从对中西历法的比较中提出会通超胜思想,正显示他在具体科学知识层面上融通中西学知识,并最终实现学问之“大统”的抱负。他认为,中西历法各有所长,通过走“翻译→会通→超胜”之路,取西历之所长,并进而“融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就能建立“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远迈百王,垂贻永世”的圣朝巨典。对于会通超胜的模式及其意义,学界研究颇多,笔者尝试从徐光启对科学价值和功能的理解,认识其对会通超胜型模与道统关系的看法。
徐光启所认识的科学的价值和功能,可分析理解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开物成务的工具性功能。具体科学作为一种技艺的工具性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认知。程颐曾讲过:“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②[宋]程颐:《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二程集》,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9页。在程颐看来,科学是道学的附庸,是与禄利一般低贱的东西,为士所不齿。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中得到普遍的认同。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漠视,无疑是造成中国传统科技“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的重要原因。徐光启认为,“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二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③[明]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第79-80页、第79-80页。基于这种认识,徐光启重新给出了科学的工具性功能的定位。他引用《易经·系辞上》对于备制实物、创成器具的褒扬,以“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作为立论之据,指出:“我中夏自黄帝命隶首作算,以佐容成,至周大备。周公用之,列于学官以取士,宾兴贤能,而官使之。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谓之升堂入室,使数学可废,则周孔之教踳矣。”④[明]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第79-80页、第79-80页。他认为,作为具体科学的数学,本身就是儒家教育的内容,是知识分子“升堂入室”必备的能力,废弃象数学这样的科学知识,将其所具有的工具性功能视为低贱的技艺,则直接违背了圣人的训导,将会导致道统之不传。因此,虽然徐光启有时也称科学为“下学工夫”,但他认为“下学工夫,有理有事”,“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因此下学便具有了上达的功能,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从而得以确立。正如何俊在《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一书中所分析的,徐光启思想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肯定了开物成务的价值,而且在于他非常有意识地将具有开物成务这一功能的一个本来只具有工具性质的作为形而下学的科学提到与形而上学的道德性命相提并论的重要地位。”⑤[明]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第79-80页、第79-80页。
第二个层次是补益王化的文化性功能。在著名的《辨学章疏》一文中,徐光启对西学的文化性功能给出全面评价,认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皆“与儒家相合”。这种相合,使得以科学补益王化成为可能。自然,徐光启在这里更多的是从为天主教辩护的角度谈论西学,提出以耶补儒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西方科学具有的文化功能,正可以补中国传统文化“多虚浮而不可挪”的缺陷,从而使习学者祛除浮躁虚妄,成就健康道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和传播寄予厚望,认为,“此书有五不可学,躁心人不可学,粗心人不可学,满心人不可学,妒心人不可学,傲心人不可学。故学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⑥[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8页。
第三个层次是科学之为科学的学理性功能。徐光启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注重经验事实的记录和描述,而缺乏对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没有成为独立的学术。在《简平仪说序》中,他曾以历法为例阐述他的这一看法,认为杨子云、邵尧夫的历法都缺乏历理的支持,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直至郭守敬以推算精妙著称的历法,也没有真正改变“言理不言故”的历学传统,“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⑦[明]徐光启:《简平仪说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73页。
要补中国传统科学的不足,必须引进西方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就是要像利玛窦所传授的西学那样,“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象数之学亦皆溯源承流,根附叶著,上穷九天,旁该万事。”①[明]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且传之史册。”②[明]徐光启:《简平仪说序》,《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第74页。
就西学之补益学理而言,徐光启的“贵义”说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在《测量法义》中,他认为,利玛窦所传授的测量方法,与周髀、九章的勾股测望并没有技术层面上的不同,所不同的是,中国原有的测量之术,仅说明测量之法,却不能在义理的层面上给予说明,故西学之贵“亦贵其义也。”在其后的《测量异同》中,他进一步认为,“九章算法勾股篇中故有用表、用矩尺测量数条,与今译测量法义相较,其法略同。其义全缺,学者不能识其所繇。既具新论,以考旧文,如视掌矣。”③[明]徐光启:《测量异同绪言》,《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6页。以新法推求旧法,彰显新法补益之用,是“贵义”思想的真正目的所在,即为西学的立足赢得正当的地位。同样做于《测量法义》之后的《勾股义》,再以“贵义”为立论原点,明言西学之用,在于补益“自古迄今,无有言二法之所以然者”,更重要的是,在西学与“古者庖牺立周天历度”的古圣先贤之说之间建立补益关系,就更加超出了学理的层面,而向道统层面迈进一步。
李之藻积极响应传教士和徐光启之说,在一方面认为传教士传播的天主教(天学)“不诡六经之旨”④[明]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第1页。,另一方面认为西洋科学可补儒者之不足,而实现“天儒合一”。在《圆容较义》序中说,“第儒者不究其所以然,而异学顾恣诞于必不然,则有设两小儿之争,以为车盖近而盘盂远,苍凉远而探汤近者。”而在引进西学的实践中,李之藻也积极贯彻会通思想。《同文算指》的译著就是将中西算法的优点相融合的产物。在书中,他既吸取了中国传统算法中所缺少的“验算”,又将传统算术中的“方程术”、“带从开方法”补充到著作中。他认为,西算“加减乘除,总亦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圆,旧法最难,新译弥捷。”⑤[明]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第2781-2782页。
入清之后,西学中源说兴起,为西学建立道统地位的努力被学者放弃,但会通思想在具体知识层面被继承,显示其一方面不仅可以用于为心同理同说佐证,也可为西学中源说之用,另一方面,持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也不得不使用会通作为工具,则证明“西学中源”这一主观臆断的论题其实在学者那里从未达到理论上的圆满。
有“南王北薛”之称的王锡阐和薛凤祚分别代表了历法上中学传统的坚定维护者与西学的热情拥趸,但他们在会通话题上却表现出同样积极的态度。被梅文鼎称为“西学名家”的薛凤祚以三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了《历学会通》一书,认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⑥[清]薛凤祚:《历学会通·正集叙》,清康熙刻本,第619-620页。
王锡阐认为崇祯历书的编撰违背了“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的初衷,“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而会通的障碍,从学理上而言,在于“历理一也,而历数则有中与西之异。西人能言数中之理,不能言理之所以同。儒者每称理外之数,不能明数之所以异,此两者所以毕世而不相通耳。”⑦⑧⑨[清]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彭卫国、王原华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88页、第383页、第387页。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即是“兼采中西,去其疵颣,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⑧[清]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彭卫国、王原华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88页、第383页、第387页。,他的工作也被阮元誉为“究术数之微奥,補西人所不逮。”⑨[清]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彭卫国、王原华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88页、第383页、第387页。
会通思想发展到梅文鼎,就有了更为“宽容”的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以西学中源说为背景的。既然以“中源”解决了“道统”问题,那么自然可以大谈“去中西之见”。他在分析西法与《授时历》割浑圆的异同时说,“且夫数者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则弧三角之详明,郭图之简括,皆足以资探索而启深思,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其于古圣人创法流传之意庶几无负,而羲和之学无难再见于今日矣。”⑩[清]梅文鼎:《堑堵测量卷二》,见梅文鼎《历算全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16页。在历法和数学知识的会通上,他更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如将《几何摘要》、《九数存古》等书辑为《中西算学通》,利用中国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几何原本》中的许多命题,通过演算订正了《测量法义》中正二十面体体积与边长关系的错误等等,①参见陈卫平:《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2期。显示其时知识会通已经成为学者的自觉。②刘 钝认为,明末的会通说由于学者缺乏对传统天文、数学足够的了解,多半局限于一种政治策略,“真正认真地‘会通’中西之学,还是从梅文鼎这一代学者开始的。见刘钝:《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
四、结语
心同理同说在明末清初被反复诠释,是此一时期西学东渐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我们在这里追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的合理性是什么,它与西学传播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从以上对心同理同说的梳理,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
其一,从明末王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应看到其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陆王心学以致良知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更加注重道德修养的追求而忽视对外在世界的关照,“自然科学”始终未成为心学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梳理的,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为口号,心学的反道统论和“泛圣人论”为知识分子接受西学提供了话语空间,为西学在士人中传播提供了土壤。
其二,儒学道统是西学传播必须面对的藩篱。如果说利玛窦策略首先需要考量的是取得知识分子对其身份认同,那么进一步确立西学的地位,就是传教士为达致其宗教传播目的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儒士教徒和友教士人,都必须解决西学与儒学道统的关系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明末即是试图建立西学的独立道统,而具体的解决方式,则是通过对心同理同说和圣人说的诠释,以建立西学“能言所以然之理”的话语优势,使中西之学“各自抒一精彩”。如果说明末学术风气的相对自由使得话语权力的争夺并未显示激烈的冲突,心同理同说作为主流话语,为大批西学知识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那么清初历狱的话语争夺,主题便是道统、治统和学统,争论的结果,尽管最终西学在知识和技术层面获胜,但从作为底层话语的道统层面分析,西学却并未真正赢得话语权,反而是西学中源说占据了这一场域的话语支配地位。这不仅使得大批学者更倾向于到古圣先贤的故纸堆中寻真知,高层士大夫而精通西学者再未出现,客观上造成清初西学引进的规模远逊明末,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士作为西学传播者的生存空间大为受限,“宫廷专家”成为他们不得已而为自己选择的官方身份。
其三,在心同理同说语境下阐发的会通超胜说,显示出其时学界对西学的包容。徐光启首倡的“会通超胜”说,蕴含了中西学融合的宏大设想,明末学者试图不仅在具体知识层面上对西学进行会通,更试图为西学建立道统,使其获得学理上的合法性。入清之后,研习西学者在“西学中源说”的话语背景之下,放弃了为西学建立道统的努力,但会通中西始终是学者试图达致的境界,为他们继续深研西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尽管这种研究已经被严格限定于天文历算等知识形态之中。③即 便是在具体知识层面,学者对于会通仍须考量其道统因素,梅文鼎在《历学疑问》中,论述西历之必不可用的内容,首先是正朔之说,其原因就在于“若正朔之颁为国家礼乐刑政之所出,圣人之所定,万世之所遵行,此则其(西法)必不可用而不用者也,又何惑焉。”见《历学疑问》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九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页。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心同理同,在逻辑上的推演,一个结论就是中西学问并无高下区别,西方没有的,中国固然可以有,同样,中国没有的,西方也未必没有。而与之相关的东西海圣人说,更是对儒学道统地位的直接挑战。这样推演的进一步发展,就当是米嘉穗在《西方答问序》中说“以吾一身所偶及之见闻,概千百世无穷之见闻,不啻井蛙之一窥,萤光之一炤也。乃沾沾守其师说,而谓六合内外,尽可不论不议,此岂通论乎?”④[明]米嘉穗:《西方答问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