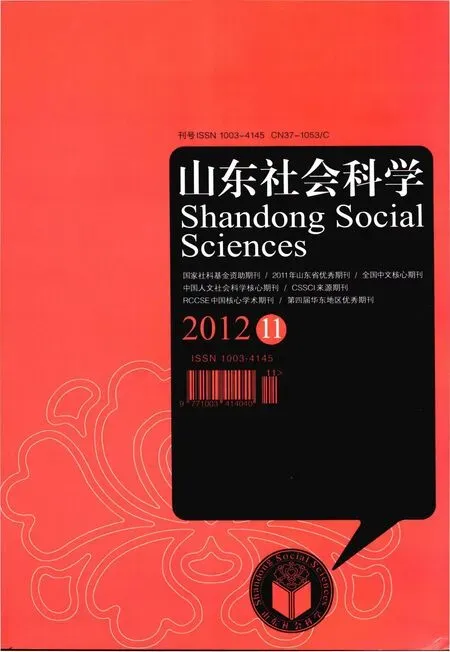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的再确认——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鲁迅阅读与接受
王中忱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一、日本的鲁迅接受史与中国新文学“走向世界”
首先想提起一件往事,尽管对于我来说那情景仍然鲜活生动如在眼前,但岁月流过7年之久,引发本文写作的契机性人物日本著名作家、学者加藤周一(1919—2008)已经成了故人。那是2005年3月2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应邀来北京讲学的加藤周一先生利用正式讲演前的空隙,在清华大学出席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当谈到他那些针砭时弊的文字在当下日本社会并不能被很多人理解甚至常常受到误解时,凝重的神色里明显地流露出孤寂和凄凉。沉默了片刻之后,他用深沉的语调吟诵了一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加藤周一先生是用日语诵读的,我记得当时担任翻译的L君愣了一下,随后才转过神来,译出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加藤周一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文学创作以外,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文学、文化与思想。他或许考虑到了座谈会的场合,考虑到了自己面对的中国听众,但他此时脱口诵出鲁迅诗句,却很明显不是有意准备的,而是他知识素养的自然流露。不知在场的其他朋友作何感想,对于我来说,这一细节确实触发了很多感慨,让我想到鲁迅和日本,想到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和接受,以及相关的中国新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
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1952—)曾多次写到,在日本,鲁迅“既是一个外国作家,同时也享受国民文学式的待遇”①参见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版,第286页;《新·鲁迅のすすめ》,日本放送协会2003年版,第101页。。在日语脉络中,藤井所说的“国民文学”具有怎样的含义呢?据日本权威的辞典《广辞苑》(岩波书店出版)解释,“国民文学”指的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使用本国语言独自创造出来的文学。是得到全体国民特别喜爱、引以为傲的文学”。按照这样的标准,仅就使用的书写语言而论,鲁迅的作品就不符合起码的条件,更不要说另外那个标准:让日本“全体国民”“引以为傲”了。藤井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谨慎地把“享受国民文学式的待遇”的鲁迅,限定在翻译成日文的鲁迅。据藤井考察,从20世纪初期的零星介绍,到鲁迅逝世第二年《大鲁迅全集》(全7卷,改造社1937)出版,再到二战以后各种各样的鲁迅作品日译本问世,在日本,鲁迅作品的翻译一直绵延相继。藤井特别提到,自1956年日本的教育出版社把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选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以后,其他一些出版社也相继仿效,到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1972年,日本5家垄断经营中学教科书的出版社,都在《国语》教科书亦即语文课本里选用了竹内好(1910—1977)翻译的《故乡》。也就是说,1972年以来,“这三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中学读过《故乡》。这样的作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是近似于国民作家的存在”①藤井省三:《新·鲁迅のすすめ》,日本放送协会2003年版,第119页。。
中学国语教科书当然不会是日本读者接触鲁迅的唯一途径,却无疑是一个显著标志,标志翻译成日文的鲁迅作品,已经作为经典,浸入了一般日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当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藤井省三确实指出了日本的鲁迅接受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当然可以说明鲁迅的影响巨大,甚至还可以此为例证,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如何“走向了世界”。但如果我们从藤井提示的现象,注意到经由翻译转换的鲁迅实际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语言脉络和阅读体制,从而去追问和探究,作为翻译文学,鲁迅的作品在另一种脉络里怎样被阅读和接受,与异国读者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也许比单纯陶醉于中国新文学的“世界影响”之类的佳话更具有学术生产性。
但是,迄今为止有关鲁迅在日本的阅读和接受史研究,大都集中在对鲁迅研究史的考察,这样的考察,自然主要是围绕着鲁迅作品的专业翻译者、研究者进行的,实际上忽略了专门家以外人数众多的一般读者。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一般读者,才是作为翻译文学的鲁迅的主要读者。当然,把鲁迅接受史的研究推进到一般读者层面并非易事,因为融化在这些读者的知识和修养中的文学,类似于水中之盐,没有明显的踪迹可寻,从这个层面讨论,也许需要另外一套方法,但诸如采访、问卷等手段更适于现状调查而很难应用于历史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把考察对象确定为一位特殊的读者:即曾经写过关于鲁迅的文章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Hotta Yoshie ,1918—1998)。
这自然因为堀田写下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追寻的线索,而他又主要是通过翻译来阅读鲁迅,在这一点上,和日本一般读者的距离远比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们更为接近;同时也因为,作为二战结束后以“国际作家”知名的堀田善卫始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抱有热切的关心,积极参与和推动亚非作家会议运动,并把自己的国际体验融入文学写作,以一批优秀作品影响了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在内的青年作家及众多日本读者。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很多日本读者是通过堀田的作品认识第三世界、认识中国的。而如同下面所引述的那样,堀田不止一次谈到,在其人生和文学写作道路上,鲁迅曾是他的坐标和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堀田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应该是鲁迅乃至中国新文学在日语脉络中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上一个有特色的个案。
二、堀田善卫:在由欧入亚的时刻与鲁迅相遇
1952年,堀田善卫以小说《广场的孤独》、《汉奸》获得第26届芥川文学奖,成为“战后派”文学中引人瞩目的存在。但是,堀田的文学活动其实开始得更早。他于1936年考入庆应义塾大学预科,专业本来是政治学,但兴趣却在文学,所以,进入本科后便从法学部转到了文学部,就读于法国文学系,并很快成为《荒地》、《山树》等诗歌杂志的同人。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堀田最倾心的是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兰波等象征主义诗人,以及巴尔扎克的小说、尼采的著作,同时,也读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总体说来,在这一时期,堀田和他周围的同人们都沉浸在欧洲文学、艺术和思想的氛围里②参见久保田芳太郎编:《堀田善衛年谱》,《昭和文学全集》第17卷,小学馆1989年版,第1113页。,和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关联,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景中接触到鲁迅的呢?在《鲁迅的墓》一文里,堀田说:
我热心阅读鲁迅,是在1942年冬到1943年秋季之间。为什么是在1942年冬到1943年秋季之间呢?因为那期间我生了病,被逐出军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通读了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①堀田善卫:《鲁迅の墓》,最初发表于《季刊·現代芸術·3》(1959年6月),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64页。
堀田的这段话说得比较简略,需要补充若干被省略的环节才能读得明白。以上引文中说到的1942年,在堀田的生活史上是一个转折,这年9月,他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而按照日本的学制,堀田的毕业时间本应在1943年3月,因为战争的需要,被提前了半年。若干年后,堀田还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是被国家强行赶出了校门。②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17-18页。同年10月,堀田就职于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一年以后,转到日本海军军令部欧洲军事情报临时调查部。在这个机构里,他被分配翻译法文的军事情报,如法国抵抗运动领导者利用英国BBC广播发往法国国内的信息,但因为不知密码,翻译过来也不知其意。用堀田的话说,他和一批文化人,当时做的都是这种毫无用处的愚蠢工作。
后来,在《难忘的断章·鲁迅的〈希望〉》(1961)一文里,堀田再次谈到和鲁迅作品的最初相遇,他说,他是在征召令到来之前的痛苦绝望时期,“偶然地买了《大鲁迅全集》读了起来”。最初读到鲁迅《野草》中的《希望》就在这一时期,亦即“1942年的冬季”。其实,在写于《鲁迅的墓》和《难忘的断章·鲁迅的〈希望〉》之前的《鲁迅的墓及其他》(1956)一文里,堀田把自己和鲁迅作品的相遇过程描述得更为具体,在此仅把其中的几段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1943年,夏季的一天,征召令解除,我走出富山陆军医院的大门。……
在征召令到来之前,我买了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只读了一两册。为什么学法国文学出身的我买了这么一大套全集?这是因为印在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上的作者的面部照片,那神情曾莫名地炙灼着我的头,给我留下了无法割舍的印象。
对于收在岩波文库版里的小说类作品,当时我几乎都不敢恭维,觉得写法笨拙。我觉得,比起写小说,虽然我不能确切知道那事情是什么,但作者似乎是一个有着堆积如山不得不做的事情的人,是一个不得不把小说作为那山一般堆积着的、必须去做的事情之一小部分的人,是一个担负着这样命运的人。
征召令解除,回到家里,我捧起了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③堀田善卫:《魯迅の墓その他》,初载于《文学》1956年10月号,转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36页。
需要注意,以上所引堀田谈论鲁迅的文章,都写于1950—1960年代,是作者对1940年代往事的回忆,其中不无记忆误差,我们依据这些文字考察堀田当年的思想状况,是要进行一些辨析的。首先,有关最初接触鲁迅作品的时间,堀田一直说是在“征召令”到来之前,但对这个最让他焦虑纠结的“征召令”的到来时间,却说得比较含混,有时笼统说是“在1942年冬到1943年秋季”④堀田善卫:《魯迅の墓》,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64页。,有时则明确地说是在“1943年2月”⑤参见堀田善卫:《美しきもの見し人は》,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03页。,但根据堀田在1940年代作为同人参与的《批评》杂志上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这个“征召令”到来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944年1月”⑥在 《批评》杂志第6卷第2号(1944年2月1日发行)署名山本的“后记”里写道:“堀田善卫应征”;同刊第6卷第4号(1944年4月1日发行)所载堀田善卫《西行(四)原高贵性(二)》一文末尾,附有作者所写短文《别离辞》,开头第一句便说:“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接到了征召令”。此文所记写作时间为“昭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另,同期《批评》还刊载了《堀田善衛君の応召を送る序》,都可证明堀田收到征召令是在1944年1月。。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判定堀田最初接触鲁迅著作的确切时间,但可以此为标志梳理出一个大概的线索:即堀田善卫最初接触鲁迅,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征召入伍的命令到来之前。他首先读到的是岩波书店版的《鲁迅选集》,这是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和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增田涉(1903—1977)共同翻译、193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随后,堀田又购买了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众所周知,增田涉1931年持佐藤春夫的介绍信到上海,通过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结识鲁迅后,即从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成为亲密的师徒。1935年增田和佐藤应岩波书店之邀译编《鲁迅选集》,曾得到鲁迅的认可和授权。⑦鲁 迅1934年12月2日《致增田涉》说:“《某氏集》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篇,请译出补进去”。信中所说“《某氏集》”,即指“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2-603页。增田后来说:“我觉得这个文库本对把鲁迅比较广泛地介绍到日本起到了作用,虽然记不准确,但大约10万册左右,我想那是卖了出去”⑧增田涉:《佐藤春夫と魯迅》,最初发表于1964年7月出版的《图书》杂志。。至于《大鲁迅全集》,则是在鲁迅逝世之后由改造社组织翻译的,共7卷,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至1937年出齐。藤井省三认为,《大鲁迅全集》出版之后,“在日本的读书界,鲁迅遂成为不能忘怀的名字”①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版,第288页。。如果考虑到其时正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日本读者出自各种不同目的竞相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改造社大规模出版鲁迅的作品,也可谓抓住了时机,当然,同时也为堀田善卫这样的后来读者阅读鲁迅提供了条件。
而堀田的关心之所以由法国及欧洲文学转向中国,转向鲁迅,无疑也和他当时的现实处境及精神状态有关。就此而言,在这几篇文章里不断出现的“征召”一词值得特别注意,这显然是引起堀田精神焦虑的最重要因素。堀田当然清楚,日本的国家权力之所以强行把青年学生提早赶出校门,目的并非是要把他们闲置在闲散的机构里,而是准备把他们送往战场。所谓“征召令”,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打断他的人生和文学写作的进程。堀田后来曾这样描述说:
战争早已开始,报纸上每天都是“势如破竹、战果赫赫”之类的标题。而我的心思全在诗歌、小说和评论的写作上。我有无限多的东西要写。
可是,尽管我一直想拼命地写下去,内心里萦回不去的却是这样的思绪:在写作完成之前,如果征兵通知来到,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人生,就都要半途而废了。周围的朋友们连续不断地被征召入伍,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和赫赫战果,都不能使我的绝望转换成希望。②堀 田善卫:《忘れえぬ断章 魯迅の〈希望〉》,初载于1961年7月17日《週刊読書人》,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53页。
不必说,在当时,日本军队的主要战场在中国,面对一个自己命定将要前往的地方,产生了解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对堀田来说,尽管这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本意,但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无疑是促成他的文学关心“由欧入亚”的重要背景。③据 堀田善卫回忆,他记得自己“最初接触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1941或1942年的时候”,首先读到的是小田岳夫根据茅盾小说《蚀》编译而成的《大过渡时代》。参见堀田善卫:《回想·作家茅盾》,初收《现代中国文学·2·茅盾》,河出书房1970年版。
三、堀田的早期文学评论与鲁迅的潜在影响
前面说到,堀田善卫读大学时就开始写诗,但他真正进入文坛,则是在走出大学校门加入《批评》杂志同人行列之后。《批评》杂志发刊于1939年8月,到1945年2月停办,总计印行56期。该杂志最初由山本健吉(1907—1988)、中村光夫(1911—1988)、吉田健一(1912—1977)等创办,堀田善卫自1943年开始参与,先后在该刊发表诗歌6首、评论和随笔5篇,其中论述日本中世著名和歌诗人、出家为僧的西行(1118—1190)的长篇论文《西行》,先后连载了5期④关 于堀田善卫在《批评》杂志上的文章,特别是堀田的“西行论”,曾嵘:《戦時下の堀田善衛についてー「批評」を中心にして》(大阪大学比较文学会编辑出版《阪大比较文学》第6号,2009年3月)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此时的堀田,主要是以文学评论家的面目出现的,其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评论文字里。查检堀田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到,他所谈论的,从日本的古典、现代作家到欧洲的文学艺术,所涉内容相当广泛,而弥漫在各篇文章中的,确实是一种苦闷绝望的情绪。在随笔《关于未来》的开篇,堀田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清晨,起身离开的时候,也许不会重新归来的念头便在朝阳的光线中穿梭漂浮。即使走在黄昏的归途,我觉得也不能充分理解“归途”一词所包含的所有意思。大致与此相同的,可以说还有“前进”。如果说自己在动,确实是在动,而周围也在一起运动。如果这样以为,这是真正的在动吗?
我的这种状态,似乎既不是漂泊,也不是停滞。不过,如果说是向前行进,确实可以感到激烈的向前;说是沉潜,则可以感受到一种纵深。倘若夸张一些说,甚至感觉到一种类似地球转动似的运动。⑤堀 田善卫:《未来について》,最初发表于《山河》1943年5月号,同月堀田也开始在《批评》发表作品,此文与《批评》所载堀田的文章属于同一系列。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07页。
不必说,这种进退不得、去归无定的悬空状态,既是堀田对自己当时生活处境的描述,也是他内心情绪的表露。在征召令随时可来,也就是随时可能被命令去赴死的严酷境况中,堀田没有试图以写作制造超然于现实的幻影,而是全力把自己被迫面对死亡时的紧张思索灌注于写作行为之中。堀田很诚实地表示:“在内心已经深怀确实而痛切的死的感受之时,所谓未来,以及现在,觉得都成了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甚至觉得所谓过去,也是混乱不清的。”⑥堀田善卫:《未来について》,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08页。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堀田自己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他不时陷入绝望和虚无,但又努力挣扎着振作。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说:“当死成为贴近身边的墙壁的时候,我们要竭尽全力度过每个生的瞬间”。而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堀田把艺术视为思考生与死问题的基石。他说:
我认为,在以死这一界限为前提的情形下,思考面向未来的生,不可能有比艺术更为可靠的基石。①堀田善卫:《未来について》,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09页。
作家、评论家中村真一郎(1918—1997)在阅读堀田早期的评论文字时特别注意到这句话,指出:在这里,“艺术是作为截断了有限之生的死的对抗物被提出来”②中村真一郎:《同时代者堀田善衛》,此文为《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的解说,见该书第380页。的。他认为,堀田在随笔《关于未来》里谈到了“当时对他而言最大的人生课题”,那就是“死和艺术”。中村说:“在平时,美、艺术是使生更为丰富的存在,但对于昭和十年以后年龄在二十岁的人来说,能够超克凸现到眼前的死——那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的——令人讨厌的死的,是艺术、美。”③中村真一郎:《同时代者堀田善衛》,此文为《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的解说,见该书第380页。
中村真一郎和堀田善卫同年出生,经历相仿且交往密切,他结合同时代人的经验所作的判断,表现出了特别的洞见,但我们还应该在中村的分析上更进一步,考察当时堀田所理解的艺术和美究竟意味着什么?翻检堀田早期的评论可以看到,他没有把美或艺术视为超然、静止、自律自足的存在。在《关于未来》一文里,堀田虽然认为艺术作品诞生之后,会脱离它的制作者而独立,但同时也指出,这只是在把作品作为主体考察时的解释,如果把作品的制作者也就是人作为主体予以考虑,则应该说,所谓作品的独立不过是其结果,作者和作品,其实处于一种“相互角逐搏斗”④参见堀田善卫:《未来について》,《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09-310页。的关系。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堀田的早期评论,并没有把作品和作者切割开来作封闭式分析,而是更关注作品的制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如在《海利根斯塔特遗书》一文中,堀田首先从贝多芬(1770—1827)遭遇听力减弱的困境入手提起话题,然后分析说,失聪并不是导致贝多芬精神危机的致命伤,而是促使他迈向“精神王国”更高阶段的契机;贝多芬因失聪而到海利根斯塔特修养时写下的“遗书”,表露的是对宿命的觉悟、内在激情的燃烧和朝向理想孤独地进行艺术创造的决心。堀田进而指出:贝多芬的“遗书”,是他遵从自己内心激情发出的“理想”宣言,是他对自己所爱的人、将要诀别的人的痛切致歉,是葬礼进行曲,是决然掉头而去的告别词。⑤参 见堀田善卫:《ハイリシュクットの遺書》,初载《批判》1943年10月号,撮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321-323页。另,所谓《海利根斯塔特遗书》,是贝多芬写给友人倾诉自己内心痛苦的信,在作曲家死后被发现,《大众音乐报》发表时称其为“遗嘱”。参见大卫·温·琼斯:《贝多芬画传》,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在同一篇文章里,堀田还由贝多芬谈到歌德(1749—1832),他认为,有人把歌德临终前的最后要求视为诗人的遗言,其实是不够确切的。歌德要求“再多一些光亮”,并非临终前的突然觉悟,而是这位伟大诗人毕生始终如一的追求。⑥参见堀田善卫:《ハイリシュクットの遺書》,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24-325页。
在早期的评论文字里,堀田曾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多次排列、分析欧洲文艺从古典派到浪漫派乃至现代派的谱系,他把古典主义音乐家巴赫(1685—1750)、亨德尔(1685—1759)、海顿(1732—1809)、莫扎特(1756—1791)、贝多芬等称为“伟大的血统”,认为“即使欧洲的末日来临,这些音乐也将像夕阳染红了的阿尔卑斯山那样巍然耸立”⑦堀田善卫:《ハイリシュクットの遺書》,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28页。。堀田特别指出了贝多芬与深受他影响的“正统浪漫派”的差异,认为与贝多芬相比,西欧的正统浪漫派表现出了更多的哀愁和没落,而浪漫派以后的现代音乐,则成了没有旋律的片段颤音⑧堀田善卫:《ハイリシュクットの遺書》,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27—328页。。对于文学,堀田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对19世纪末欧洲艺术中的“绝望之美”,对“20世纪前半的绝望感觉的文学”,都有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倾心于歌德对“光亮”的渴望,看重席勒(1759—1805)对“欢乐”的赞颂。⑨参见堀田善卫:《ハイリシュクットの遺書》,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25、328-329页。
概言之,在堀田的早期评论里,“绝望”、“绝望感觉”、“理想”、“光亮”等词语频繁出现,可知这是缠绕在作者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而其中所谓“理想”和“光亮”,又大都停留在抽象层面,缺少具体的内涵。在这样的脉络中,堀田对鲁迅的《野草》特别是其中的《希望》一文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尽管堀田的早期评论没有言及鲁迅,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但鲁迅的潜在影响无疑是存在的,所以他后来才不止一次地在回忆文章里提起。
前面已经引录过堀田此类回忆文字,在此可以再作补充的是,在《鲁迅的墓及其他》一文里堀田说过,当年他曾计划写作日本现代作家和鲁迅的比较论,所以把初读鲁迅的感受记在了笔记本上,而他后来在文章中对鲁迅面部神情的描述,就来自旧日的笔记:
总是在悲伤中夹杂着愤怒,愤怒里混合着忧伤,在怅惘中呐喊,呐喊中萦回着怅惘,深知人心内的无底深渊,彻底战斗一直到死。就是这样一张无法言说难以形容的面孔。望着鲁迅从鼻子两侧到嘴角两端的凹陷处,寒气凛然而至。具有如此悲惨而高贵面孔的人,一个世纪当中,并不会很多,或许最多也就是一个或两个。①堀田善卫:《魯迅の墓その他》,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37页。
在同一篇文章堀田还写到,和鲁迅头像一样震撼了他的还有《野草·希望》里的诗句,他从中感到了一种“绝望”的共鸣: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散文诗《希望》中的一句。这句诗,在此后的战争日子里,一直支持着我……
这样的诗句,尽管是鲁迅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里发现的,但也完全可以由此看出,鲁迅的内心是多么深刻的绝望。那时正迷恋绝望的我,从内心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②堀田善卫:《魯迅の墓その他》,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37页。
在《难忘的断章·鲁迅的〈希望〉》一文,堀田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和阅读《希望》的感受。他说,在《大鲁迅全集》里,自己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在那里,既存在着无论法国文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都不曾有的亲切,也存在着那两者之中同样没有的激烈。”③堀田善卫:《忘れえぬ断章 魯迅の〈希望〉》,引自《堀田善卫衛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54页。但堀田是否由此获得了摆脱内心绝望情绪的力量了呢?显然没有。在同一篇文章里,堀田说,这一时期,他曾接触到日本的反战人士,听到他们动员人民制止战争的主张,但在当时,“对这些庄严的反战的和革命的宣言,我并不相信。不是半信半疑,而是完全不信”。他引用鲁迅《野草·希望》中的话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④堀田善卫:《忘れえぬ断章 魯迅の〈希望〉》,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54页。
也就是说,此时的堀田,虽然从鲁迅作品中感受到了“亲切”、“激烈”、“血和铁”,同时,也对其中的“空虚”、“绝望”情绪深怀共鸣,甚至可能是后者对他更有吸引力,所以,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堀田才会认为《希望》中的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是激励的力量,同时也是“有毒”的,并说:“这有毒的言辞从战争期间到战后一直支撑着我,或者说是既使我成熟也让我堕落。”⑤堀田善卫:《忘れえぬ断章 魯迅の〈希望〉》,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54页。联系堀田此一时期有关欧洲文艺的评论,可以看到,这种情绪和认识,在当时堀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致的,他没有在事后的回忆里拔高自己,也没有夸大鲁迅影响的作用。而另外一个可证明堀田回忆文字诚实性的事件,是他后来去中国不久即专门拜谒了鲁迅的墓,时间在1945年6月,同行者有武田泰淳(1912—1976)、菊池租。那时堀田还没有在文章里直接谈到鲁迅,这一行为更显示了鲁迅在他心里所占的分量。
四、“上海物语”与鲁迅形象的意义
在此应该介绍堀田善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本来,堀田极有可能以从军士兵的身份“前往中国”,这也是让他最为焦虑的,但一个意外事件让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1944年2月堀田确曾应召入伍,但参加新兵训练的第十天便因胸部疾患住进了医院,且一住就是三个月,出院以后,对他的征召令解除,他的军人生活即告结束,又重新回到国际文化振兴会就职。⑥参 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21页;另见栗原幸夫:《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解題》,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86页。1945年3月,在亲历了美军飞机对东京的大轰炸之后,堀田决意离开日本本土。同月24日,搭乘通过关系获得座位的军用飞机抵达上海,在国际文化振兴会设在上海的资料室工作⑦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22页。;8月,在上海迎来日本的战败投降。
关于堀田在日本战败前决然离开本国的动机,在1952年2月25日祝贺他获得芥川文学奖的庆祝会上,他曾作过说明。这个庆祝会是由日本的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荒地》文学社共同举办的,堀田善卫作为获奖者发表致词说:今天有很多初次谋面或仅仅通过作品了解我的新朋友来参加庆祝会,按照常理,我应该介绍一下我的文学履历,不过,因为在别的地方我已经写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想还是应该讲讲那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决定奔赴仍处于战争之中的中国的动机,以及后来归国开始战后的工作这段期间的事情。接下来,堀田这样说:
十九年,当我被征召入伍而不久因病遣归的时候,我买了《鲁迅全集》,读了一遍。为什么买《鲁迅全集》,现在怎么也记不清了,总之,确实是买了,读了。而在全集中,确实收有散文诗《野草》,在其中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一句: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句诗,给处于战争绝望或者说是自暴自弃情绪之中的我以猛烈的一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这句诗对我的另一影响,是让我产生了前往中国的念头,我觉得绝非夸大其辞。①《堀田善衛全集》第一卷“解题”,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501页。
如前所述,堀田回忆自己经历的文字前后常有出入,如此次致词中说到在“(昭和)十九年”亦即1944年购买了《鲁迅全集》,就和他的另外几篇文章的说法不同。②参见堀田善卫:《魯迅の墓その他》、《魯迅の墓》、《忘れえぬ断章 魯迅の〈希望〉》。但这些细节上的出入不妨碍我们把握堀田与鲁迅的基本关系,从军队医院出来的堀田已经接触到鲁迅,并心有所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堀田说鲁迅《野草·希望》里的诗句,促使他“产生了前往中国的念头”,我们对此不能作过于简单的理解。首先应该看到,作为获奖庆祝会的致词,即使从礼节上,堀田也会考虑到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存在,有意提到与中国文学有关的话题。第二,从堀田在致词中所用的假设性修辞,可以看出他在谈鲁迅文章里的诗句的“另一影响”时,是在作事后追认,而非重述事前即已清晰存在的目的意识。第三,堀田在另外的场合谈到他在战争末期决意离开日本的动机,更多强调的是他亲眼目睹昭和天皇到轰炸后的现场视察,“臣民”们跪拜在废墟上谢罪的情景所引起的失望和愤怒。在当时的堀田内心,已经产生了“这究竟是谁的罪责”的疑问。③参见堀田善卫:《明月記私注》,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206-207页。第四,堀田还曾谈到他当时的目标,是想经由中国前往欧洲。④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21页。第五,也有堀田的好友认为,堀田离开日本,与他当时的家庭纠葛也有一定关系。⑤参见陈童君:《堀田善卫研究序说——从上海体验到〈祖国丧失〉》注(5),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论文,2010年。综合这些因素,可以看到,促使堀田离开日本奔赴上海的因素是多元的,“鲁迅影响”要放到多重纠结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才能准确评估其意义和作用。
同样还应该看到,到达上海以后,堀田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说,包括鲁迅在内的多种因素促使堀田从日本本土来到上海,是他挣脱绝望、希望有所作为的第一步,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如何认识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位置,选择怎样的生活,对于堀田而言,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虽然堀田滞留上海的时间仅仅一年零十个月,中间却经历了日本战败这样一个巨大的划时代变动,这使他对自己及环境的认识与判断变得更为严峻。从堀田后来的文章与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他确实不断把鲁迅作为自己思考的资源和坐标。而随着堀田思想的变化,他从鲁迅及其作品里感受到的意义也有所变化。
堀田初到上海时期,日本即将战败的气氛已经很明显,加之通货膨胀严重,使得他在任职机构几乎无事能做。⑥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26页。但当时的上海毕竟还被日本占领,属于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管辖区域,堀田所在的机构,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旗帜,但当时他们所谓的“国际”,无疑主要是在日本勾画的“大东亚”范围内,他们的活动,自然也要编组到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脉络里。对此,堀田虽然有所认识,但在一段时间内是颇为暧昧含混的,以至于他在战后不久为上海的《改造评论》撰文时,还特别强调自己是怀着诚意来从事中日民间文化事业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堀田还提到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在批判该会议作为日本帝国“官制”、“军制”的产物企图“把日本的侵略合理化”的行为同时,也不很委婉地认为,作为个人,一些文学家的内心里,也燃烧着想要拨正已经扭曲了中日关系、至少是文学领域的中日关系的悲壮愿望。但当时的管制太严酷了,是“绝对性的”,“即使是对中国的抗战文化抱有兴趣,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就意味着立刻‘入狱’。”行文至此,堀田引用了鲁迅,他说:“对于当时的我,鲁迅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支撑自己的力量之一。”⑦堀田善卫:《反省と希望》,初刊于《改造評論》创刊号,上海,1946年6月。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20页。
这应该是堀田在文章里第一次正式引用鲁迅,虽然没有详细谈到鲁迅在怎样的意义给了他启示和鼓励,却表明在堀田的文学世界里,鲁迅已经从潜在影响成为显性的存在。此后,堀田曾在等待遣返归国的日本侨民集聚区生活过一段时间,12月,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工作委员会留用,参与日语杂志《新生》的编辑及日语广播等工作。①参见红野谦介:《堀田善衛 上海日記·解題》,集英社2008年版,第344-345页。1946年12月,为担心卷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内部纷争而申请归国,翌年1月初回到日本。从1948年起,堀田陆续创作并发表了《波浪下》、《共犯者》、《被革命者》、《祖国丧失》等小说,题材和主旨皆取自他的上海经验,在战后的日本文坛呈现出异样色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海是二战以后堀田善卫作为小说家重新出发的起点,上海经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甚或决定了堀田文学写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音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堀田这一系列可称为“上海物语”的作品中,鲁迅形象作为情节的构成要素出现在小说里,这在日本的战后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
堀田的“上海物语”,既是各自独立的短篇,又在主题、情节上相互关联,特别是以《祖国丧失》为题汇为一集的作品,都以一位战后被留用在上海的日本知识分子杉先生的视点为叙述线索,描写在国共纷争中的背景下,一群中国青年为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而焦虑不安的状态。这组小说的最后一篇——《被革命者》(1950),在将要结尾的地方,借一个人物之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到底会不会成为中共的文化人呢?小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场面描写收束:
(杉先生)注意环视了一下四周,在大财阀宋氏家族气势威严的大墓附近,是鲁迅谦朴内敛的墓。烧制在白瓷上的肖像从鼻子向下缺了一块,那眼睛,闪着透彻的清醒和深厚的悲愁。②堀田善卫:《被革命者》,初刊《改造文芸》1950年1月号,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95页。
虽然只是以简练笔触勾勒出的场景,但放在一部系列小说的总结局之处,无疑蕴涵了作者的特殊用心。从叙事结构看,这一场景的出现也许有些突兀,但小说描述彷徨中路的知识分子在人生选择时刻,呈现出鲁迅的形象,应该不是作者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设计。在《祖国丧失》以后写作的长篇小说《历史》里,堀田又延续了同样的思考和叙述表现。《历史》仍然以战后中国的内战状态为背景,以各类知识分子聚分离合为主要内容,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叙述结构更为错综繁复,开篇化用《列子·汤问》篇的意象,这样写道:“中国天倾,倾向了西北。其结果,是地势低洼,斜向东南,每当秋季,水便溢出,向东南流淌。”显示出了史诗般的恢弘气势。但小说的叙述,仍然以留用在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视点为线索,其中再次出现了和鲁迅相关的情景:视点人物龟田在几位中国青年的聚会上作自我介绍,谈到自己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也谈到因为曾读过鲁迅的书,产生了对中国的关切。龟田有关鲁迅的话题引起在场青年的注意,特别是一位倾向进步的青年,特意沿着这个话题追问,但龟田的回答却让青年们失望,龟田明确说,当年他是把鲁迅有关“绝望”、“希望”的诗句,融进了带有赞同“大东亚共荣”色彩的诗篇。《历史》出现的这一场景,固然和作品的整体情节发展有关,因为在此场景之前,小说曾写到龟田发现中国青年简单地把日本曾经翻译过左翼文献的人物想象成反战人士,他认为这是误解,所以坦率地告诉中国青年,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知识界并不像中国青年善意想象的那样有效地组织过反战运动,“至少我自己不是那样组织里的一员,而是确实配合了(侵略)战争”③堀田善卫:《歴史》第一部第二篇《石を愛する男》,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35-36页。。很显然,这也是作者借助小说人物之口,对自己的思想所作的剖析和反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历史》里出现的这一细节,其实体现了堀田对鲁迅认识的深化和对鲁迅精神的继承。既严峻地批判社会现实,又严峻地剖析自己,在这一点上,堀田和鲁迅的精神是相通的。
五、鲁迅的启示:与异民族交涉的彻底性
从1948年到1950年代前期,堀田所写的“上海物语”系列,无疑都与他当年滞留上海的经验有关,带有某种回忆往事的味道。1956年,堀田善卫作为日本作家的代表赴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以后又成为亚非作家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文学活动和文学表现更具国际化色彩,其关心更多倾向第三世界,也萌生了重到中国看看的念头。值得注意的是,堀田是通过回忆鲁迅的文章表达这一愿望的。1956年10月发表的《鲁迅的墓及其他》一文,是堀田第一篇正面讲述自己阅读鲁迅经历的文章,他特别回忆到当年在上海寻访鲁迅墓地的过程,以及当时的感受:
鲁迅墓旁,是人所共知的宋子文、宋美龄的家族、也就是所谓宋氏家族的非常庞大的墓地。鲁迅的墓实在很卑微,连十字架也没有,但像在横浜的外国人墓地常见的那样,土葬之后立上一块细长的白色石头,在坟头的地方,立了一块像屏风似的,白色的石碑。只有这么一块东西。石头四周,杂草蓬乱地生长着。
但是,我的心因此而猛然一震。鲁迅的眼睛,那只眼睛,以沁入心扉般的视线,烛照到我的内心。
堀田特别说明,他之所以强调是鲁迅的“那只眼睛”,是因为当时看到墓碑上镶嵌的瓷质头像已经残破,“左眼也已残缺,只有右边的一只眼睛,从深处发出光芒,用似乎是微热而又锐利、直刺人心的目光凝视着我”。堀田这样描述鲁迅的目光:“亲切而冷酷,还可以用许多这样的反义词并列来形容的眼睛,似乎在述说着某种极为严峻重大的事情。是我很难清楚理解的,也许是不想让我清楚知道的重大事情……”按照此文的脉络,面对鲁迅的目光,堀田既有很多困惑不解,似乎也感觉到了一种召唤,所以,在文章结尾,他写道:“很想什么时候再去看看那墓地,还有那眼睛。鲁迅的眼睛,不仅牵连着日本、中国,还牵连着东方文化文学的整体。”①堀田善卫:《魯迅の墓その他》,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39-140页。
对照小说《被革命者》中出现的鲁迅墓地场面,可以看到,数年之后,堀田以随笔形式重提旧事,显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通过和鲁迅的目光想象性地重逢,提出了新的问题。此文发表于堀田去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筹备工作的前夕②亚 洲作家会议于1956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同年1月,堀田前往参与筹备。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54-55页。,他说想再去寻访鲁迅墓地,自然暗含着要去访问上海、访问中国的意思。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特别是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在冷战的格局中,日本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两国处于隔绝状态,堀田等日本作家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作家会议运动,是要遭遇很多阻力,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③据 堀田说,他去印度参与筹备亚洲作家会议,旅费和住宿费等就是日本笔会、文艺家协会和他本人支付的,当时川端康成、舟桥圣一和江户乱独步捐助较多。参见堀田善卫:《めぐりあい人びと》,集英社1993年版,第54页。在此过程中,堀田始终站在前列,并借此机会积极推动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的交流。1957年10月,堀田善卫获得重访中国机会,受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之邀,他和中野重治(1902—1979)、井上靖(1907—1991)等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并以此为契机写作了系列随笔,后以《在上海》为题结集出版。④堀 田善卫此部随笔集的作品从1958年起陆续在《世界》(岩波书店)等杂志发表,1959年7月以《上海にて》为题由筑摩书房(东京)印行单行本出版。
不必说,堀田之所以把他这部游记的主要场地设定在上海,和他当年的上海滞留经历有关,但从《在上海》可以看到,堀田并没有简单地抒发“旧地重游”的感慨,而是努力把自己的旧日经验,放在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巨变过程中,放在东西冷战与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背景下,重新咀嚼、审视,从而对中国以及日中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1935—)是堀田善卫的文学后辈,他对堀田的随笔集《在上海》极为推重,认为这是二战以后日本人所写关于中国的最好的书之一。⑤大江健三郎:《中国を経験する》,参见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筑摩书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215、229页。
《在上海》以对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方式展开叙述,其中,堀田比较集中思考和探究的是如何“与异民族交涉”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严峻的实践性课题,而对于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而言,要参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首要的前提是严峻地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在参与亚洲作家会议时,堀田对此已经有所感受⑥参 见堀田善卫:《胎動するアジア—第一回アジア作家会議に出席して—》,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439-440页。,到了《在上海》,堀田的反省意识更为自觉。而在堀田看来,从思想、文化深层追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首先应该清算“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特别是曾被大力鼓吹的所谓中日“同文同种”口号的虚妄性和欺瞒性。基于这样的考虑,堀田认为应该注意辨别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在《自杀的文学家和被杀的文学家》一文,堀田写道:“与其以文学的普遍性、理解的可能性为先导,不如逆道而行,从理解的困难,异质性、断绝程度之深刻……出发更为合适。”⑦堀田善卫:《自殺する文学者と殺される文学者》,引自《上海にて》,筑摩书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154页。《暴动与流行歌》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安娥(1905—1976)的《渔光曲》,堀田甚至用了很多笔墨逐句分析歌词,但在谈到自己无法理解该歌曲为何流行时,堀田却飞跃式地给出结论:“不能为所谓同文同种的虚妄口号迷惑,中国是外国,中国人民是外国人。”⑧堀田善卫:《暴動と流行歌》,引自《上海にて》,筑摩书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134页。
写作《在上海》时期的堀田善卫为何如此强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异质性?因为按照他的思路,这是破除“大东亚共荣”迷思的必要程序,只有先确认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然后才可以考虑怎样和不同的民族、文化进行交涉。也就是说,考虑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日本应重新确认二者的自我和他者身份。在这样的语境中,堀田重新提到了鲁迅,特别是鲁迅用日文写作、发表于《改造》杂志1936年4月号上的文章:《我要骗人》。
堀田认为,在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刻,在将去世之前,鲁迅接受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综合杂志《改造》的约稿,面对日本读者,鲁迅没有空泛地说一些友好的言辞,而是犀利地指出中日之间严峻对立的现实。犀利揭破当时日本宣扬的所谓“中日亲善”的虚伪性,毫不含糊地断言: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彼此之间还无法“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堀田认为,这表明“鲁迅与日本,鲁迅与异民族的交往,实际上也是非常彻底的”。他赞赏鲁迅的这种“彻底”精神,尤其对鲁迅文章末尾一句“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表示了深刻的共鸣,他说:“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在1936年还是今天,恐怕没有谁能够泰然自若地把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行读过去。这之间是“血”的历史,而经历了“血”的历史之后的今天,中国和日本甚至连正式的邦交还没有建立!”①堀田善卫:《鲁迅の墓》,引自《堀田善衛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65页。
很显然,堀田回顾历史,着眼点却在现在和未来。他不仅痛切反省日中之间“血”的历史,也对两国尚未建立“正式的邦交”的严酷隔绝感到痛心,由此可见,堀田强调与民族交涉的“彻底”精神,不仅是指要清晰确认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包含在此基础上跨过民族隔绝的深渊、进行更坚实的交流的热望。他访问中国,写文章介绍中国,从民间文化交流领域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无疑就是为实现此种愿望的努力。但堀田不赞成以廉价的乐观预测两国关系的前景,他说:“我们握手的手掌与手掌之间,浸染着血”②堀田善卫:《再び忘れることと·れられないことについて》,引自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筑摩書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60页。。甚至这样预言:“两国恢复邦交不容易,而邦交恢复以后也许还会更不容易”③堀田善卫:《上海にて·はじめに》,引自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筑摩书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12页。。大江健三郎为《在上海》单行本写“解说”文时,对堀田的这一预言给予了特别注意,认为这行文字是堀田“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④大江健三郎:《中国を経験する》,参见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筑摩书房ちくま文芸文库1995年版,第215、229页。。大江这里显然是借用了鲁迅的修辞,同时也以隐喻的方式对堀田与鲁迅的“彻底”精神之关系作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