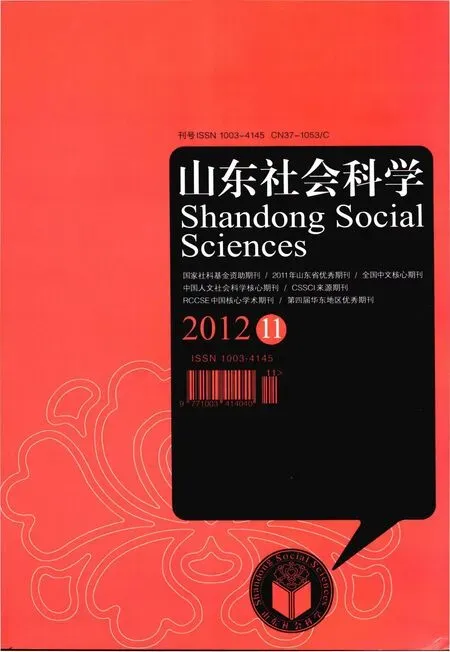革命话语阐释下的求真探索——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研究
孙宜山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作为中国革命史体系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运动发生伊始就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后更加强化和不容置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记录和阐释亦因此迥异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①对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鲁振祥的《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朱允兴的《五四运动史研究述评》、李宁和冯崇义的《建国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基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和脉络。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一员,华岗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颇具典型性。他力图用革命的话语还原五四运动的本来面目,探寻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这种努力以致用始,以致用终,但隐含于其中的求真趋向隐约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曾经的学术彷徨。
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华岗的历史研究,更确切地说中国革命史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致用目的。他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利工具。”②《社会发展史纲·自序》,《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虽然“历史科学工具论”不是华岗的发明和专利,但华岗至少在1940年代之前的学术研究中忠实地实践着这一理论。
在他最早评述五四运动的《今年“五四”纪念节对于青年学生之希望》一文中,华岗对五四运动仅作了不到300字的简单描述,而其中的“革命”一词却重复出现达6次之多。文章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在分析当时学生运动的形势以及鼓励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继续斗争,文中标语、口号一样的行文充满战斗的激情。“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这便是准备革命高潮的前提啊!”③少峰:《今年五四纪念节对于青年学生之希望》,《列宁青年》1929年第1卷第14期。这种革命呐喊压倒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整篇文章更像是一篇战斗檄文。
《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④《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于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出版后多次重印。文史资料出版社于1982年5月据1931年上海春耕书店版本,在订正了个别错字后,重新出版。是华岗在中国革命史领域的开拓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时间上仅晚于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①《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最早在1926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印行;1927年3月由广州国光书店出版单行本;同年6月即第二次印刷,至1929年仍在翻印出版。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下卷收入此书,个别地方略有删节。的革命史著,完全是华岗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创作的。他在该书自序中明确说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②《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自序》,《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求得这种历史辩证法的教训、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③《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绪言》,《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华岗创作《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只是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以有助于今后的革命事业,而基本上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学术意图。其中,作为大革命预演的五四运动显然也纯粹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被他加以叙述和分析,革命完全压倒了学术。
抗日战争期间,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抗日洪流中。写作《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④《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于1940年8月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后来也曾多次重印。1951年7月和1952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曾出增订本。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华岗意识到,非常有必要总结近百年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给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自序》,《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而这种“借镜和帮助”就是,“发扬我们民族在解放运动上的光荣历史传统,继承过去许多先烈的英勇斗争精神,警戒避免一些历史的错误和缺点”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绪论》,《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由《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扩充改写而成,其中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必然从属于抗日救亡这一最迫切的任务,而五四运动中抗日反帝的要素被华岗淋漓尽致地挖掘出来,以启迪当时的抗日事业。在该书的“五四运动”一章中,在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时,华岗直接点明这些教训是“五四运动对于目前抗战的教训”,以紧密配合当时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诸如,“五四运动所给予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发展群众运动,这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⑦《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五四运动》,《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5页。等评述,是在华岗此前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中所没有的,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现实色彩,使得史学在成为革命的武器后又成为救亡的武器。
在用革命话语叙述五四运动时,华岗采用了一种有别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注重历史事件发生背景、原因以及最终结果、影响的分析,而轻视对历史事件过程的描述。早在《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中,华岗就从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入手力图探求历史现象的真相和历史本质的真相。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他创建了“革命的原因——(革命的经过)——革命的影响”这一革命史研究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一开始并不成熟,但一旦架构完成就使华岗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并逐渐成为他用来研究革命史的常用和固定模式。华岗创建这种革命史研究模式源于他所信奉的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历史科学不仅要求,“应从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动中,从社会上由此产生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中,去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去寻找一切重要的历史事变之基本动因和决定的动力”;而且要求,“对于社会各阶级底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期底具体特点,都应作出确切而可用客观事实来检查的估计”⑧《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题记》,《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9页。。而对于五四运动,这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华岗以为,更“应分别作出确切而可用客观事实来检查的估计,找出它底历史意义和具体特点”⑨《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题记》,《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9页。。
在1930年至1940年这十年间,华岗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阐释始终只是为了现实的需要,或者为革命或者为救亡,事实上都是在自觉地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好的政治策略和革命策略提供足够的历史依据,以向世人宣传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换言之,他研究历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不是为求真,而是为致用。历史研究在华岗那里,是论证政治目标的手段,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领域,是进行理论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样说,既不意味着华岗主观上不愿意去求真,也不是说他的史学著作中没有求到真,而是说这一时期华岗已经具有了充分的致用自觉,但缺乏必要的求真自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心目中,用来致用的东西,本身就是历史之真,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就是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这样一种自信:一应用这一理论研究历史,不管理解的正确与否,也不问其他条件是否具备,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科学的,就是真的。这种对于致用的专注,导致了华岗对史料搜集、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的轻视和疏忽,以至于他这一时期的史著因长于义理短于考据而被人诟称为“宣言书”。
二
但这种情况在1941年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岗而言,这种变化就是,在继续强调致用的同时,开始推崇求真;在继续强调方法的同时,开始肯定和提高材料在治史过程中的相对地位。这种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从重论轻史到史论并重的转变,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共于1941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所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应当“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科学态度”,提倡搞“实学”,把科学当作“老老实实的学问”来搞。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801页。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本是乾嘉学派的治史口号,乾嘉学派的“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当时的史学家们来说,就是要像朴学家们那样去“求真”,就是要强化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因此求真倾向的强化,对材料的重视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整顿学风在史学界的开花结果。
1942年4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3周年,华岗发表了《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一文。单纯从题目看,与此前战斗檄文式的直白相比,文章显然多了一层冷静与朴实。文章探讨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革命,而是偏重于对历史、文化、学术的探讨,尤其是对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的一些关系问题的解释清楚、透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又颇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华岗对郭沫若以古喻今的简单比附提出了委婉批评。对于郭沫若在《屈原》中将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比作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并将屈原参与的那场变革称为二千年前的“五四运动”,华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只就意识形态变革的范围来比拟,绝不能抹杀或否认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所涵有的新因素与新意义”,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刻板的死籍,它将在流驶的段落中,刻出新的标志,把大动乱的起点、演变烙印出车辙的新痕迹。”③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群众》周刊1942年第7卷第8期。这意味着华岗已意识到,对历史的简单比附有时并不科学,严重时会歪曲历史,甚至直接抹杀历史的真实性。
抗战期间,华岗开始重视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论的探索,发表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文章。1946年,论文集《中国历史的翻案》的出版,标志着华岗史学思想的系统化,对其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华岗反复强调和阐释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④《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4页、第1382页。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华岗分析认为,这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即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华岗所说的历史观当然是指唯物史观;而对于方法论,华岗也有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辨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也如研究其他科学一样,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⑤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卷第2号。则是对重视史料所做出的恰当注解。
对于史料的重要性,华岗指出,无论作何种研究,材料的据有和检讨,都是必要的前提。因此,材料作为研究历史学的前提,自然也不能例外。“史料不够或不能自由运用,固无从着手研究”,但占有史料后的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对于研究历史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对于有了史料,而不能加以科学的检讨,即对于史料真伪和时代性,如不能检讨清楚,也和缺乏史料一样,甚至更危险。”⑥《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4页、第1382页。去伪存真和变伪为真,发掘历史真髓,考证辨伪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华岗强调,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同时对于不重视考证、研究历史却不在材料下功夫的情况,华岗的评价是:“根据抽象的理论,冰冻在许多符号公式上,拿它当做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①《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8页、第1383页、第1385页、第1386页。实际上,这是华岗对此前唯物史观派史学家重论轻史现象的一种反省和自我批评,这种反省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因为开始重材料、重考据,对于曾为文献辨伪作出贡献的乾嘉学派、“古史辨”派,及至王国维、董作宾等人,华岗也给予了适当肯定以至不吝褒奖:“有人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劳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不算过分的。”②《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8页、第1383页、第1385页、第1386页。
虽然如此,但对于考证学舍弃思想内容的字句钻研,华岗还是进行了批判,“他们自己称此为实学,实际乃是一种支离破碎之学,其结果是‘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③《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8页、第1383页、第1385页、第1386页。“中国近数百年来的历史考证学,确有相当成绩,但它缺少了活的神经,以至成了一种跛行学问。”为了改造这种瘸腿的学问,华岗提出,“应该注入必要的活的神经组织”,而这个活的神经,就是“汲取由近代新兴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综合起来具有客观真理的科学历史观”④《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8页、第1383页、第1385页、第1386页。,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有唯物史观作指导,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华岗设计了这样一种路径或方法:首先必须收集一切有关的历史材料与现实材料,再从具体事物的全面形态中,归纳有关的具体事物,加以精密的分析,考察并求得它们在发展中相互关联的枢纽;接着还要把其中所存在着的必然的现象和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和次要的现象分别清楚。而这种路径或方法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在华岗看来,能否收集一切有关的历史材料与现实材料就成了能否实事求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材料在华岗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预示着华岗治史方法的一大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他的《五四运动史》一书。
三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⑤该 文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合刊登载时,改为现名。一文,其中从性质、作用、影响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对五四运动做出了全面的阐述,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了毛泽东对五四运动评价这一新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有关五四运动的新的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华岗集中精力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中的“五四运动”一章扩写成了《五四运动史》一书,于1949年10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五四运动史》一书,与之前华岗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著述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上非常用力,扎实的材料支撑使得这部著作学术气息非常浓厚。
《五四运动史》所使用的材料的来源范围大大扩展了。之前,华岗研究五四运动所使用的材料非常有限,基本上局限在中共党史资料、苏联有关领导人的论述以及部分报刊的报道上。但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材料的来源、范围显著扩大,就其在书中使用的资料而言,报刊报道、回忆考实、条约协定、书牍信函、人物传记、全集选集、纪要专辑、文存文录等都成为华岗搜集资料的重要来源。⑥其中涉及的报刊有《商业月报》、《亚细亚日报》、《新青年》、《国民》、《新潮》、《每周评论》、《五七周刊》、《湘江评论》、《民国日报》、《乡导周报》、《中国青年》、《文萃》、《北京政治生活》、《大公报》、《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涉及的条约协定有《中英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巴黎和约》等,涉及的全集选集、文存文录有《列宁全集》、《列宁文选》、《总理全集》、《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瞿秋白文集》、《吴虞文录》、《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其他的资料还包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新约法》,《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朱尔典《使华回忆录》,陶菊隐《六君子传》,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白蕉《中华民国与袁世凯》,《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军务院考实》,蔡小舟、杨谅《五四》,《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专辑》,平心《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等十几种。为写作《五四运动史》,华岗在材料的搜集上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他把能见到的和五四运动有关的一手、二手材料搜罗、汇集起来,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充足、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
《五四运动史》对史料的整理、使用与观点、立场紧密配合,既不一味罗列材料,也不空发议论,而是有史有论、史论并重。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了中国民族工业以较好的发展机会时,华岗采用了上海总商会1929年出版的《商业月报》调查统计的一系列数据,甚至直接采用了数据列表的形式,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在一九零零年的时候,中国只有两家面粉厂,到一九一六年,居然增加到六十七家,到一九一八年更增加到八十六家。”“丝业方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的资本只有五万元左右,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则平均每年增加资本已达一百八十万元左右。”⑦《五四运动史》,《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页。类似于这样用数据来说明事实的地方,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多处出现。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华岗严谨认真的治史态度。
对有些材料,华岗不做任何处理,原汁原味摆出,给历史以真实、直观的展示;对有些材料,华岗则选取其核心部分,或精华部分,与其他材料相补充,以呈现历史的多样与复杂。为证明日本在1914年占领山东后对中国的进一步奴役与压迫,华岗将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全文照录,未做任何的修改与调整,目的就在于让国人明白,“这二十一条件是实实在在的亡国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华民族头颈上的绞索。”①《五四运动史》,《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3页。同样为了说明在巴黎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处理,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胜利,中国则完全失败,华岗把当时协约国对德和约中有关中国的第一百五十条至一百五十八条,原样照录,以供参证。为了客观、全面地叙述五四示威运动的经过和发展,华岗采用了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以互相补充和说明,不再全搬照抄。为说明《新青年》对青年人的启蒙作用,华岗引用了茅盾的《五四回忆》中的部分内容;为说明五四当天如火如荼的运动情势,华岗引用了曾亲历其事的沈尹默、李良骥的回忆;为了说明各地对五四运动的响应情况,华岗引用了邓颖超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从启蒙到发生再到发展,五四运动不同的阶段,通过不同人的回忆予以展示和说明,丰富的材料从不同层面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求真的治史倾向的强化、对材料前所未有的重视,说明了华岗这时正在走向史的自觉,并意味着他开始以一个史学家的身分、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来研究历史了。对对象负责、对历史真实负责的观念开始深入到华岗的头脑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支配他的研究实践。他这时也像那些史料考订派史学家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高扬求真,他这时也像那些职业历史学家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强调材料。这是一种值得欣喜而又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说明唯物史观派史学真正进入了以“求真”为目的境界,事实上致用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他们在观念上在朝“求真”这个方向运动,在“心向往之”,说明了像华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力图在致用和求真、方法和材料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他们必须真实地记录反映历史,而意识形态又要求他们必须为政治提供服务,于是纠结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扮演了双面人的角色。
在五四运动史领域,华岗的《五四运动史》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力作,在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论者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间,关于‘五四’运动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洪焕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等。同时,发表的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文也有数十篇。其中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做出全面论述的著作,当推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一书。”②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7页。时至今日,《五四运动史》仍然是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是研究五四运动必备的参考书之一。此书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华岗对致用和求真、方法和材料的关系作了相对得当的处理。
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华岗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辟之功。他的《五四运动史》等作品确立了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代表着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尽管目前华岗所创设的马克思主义的五四运动史模式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思和修正,但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学术史意义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另一方面,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成熟的轨迹是一致的。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到了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一系列的调整、变动,其一是唯物史观派史学开始举起求真的旗帜,史料考订学派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关注致用;其二是唯物史观派开始注重史料,注重考证,进而尊重史料学派。③参见王学典:《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第3期。华岗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一员,他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同样经历了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从重论轻史到史论并重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顺应时代、语境的外部变化而做出的相应调整,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学术理念、体系建设的新突破。可以说,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