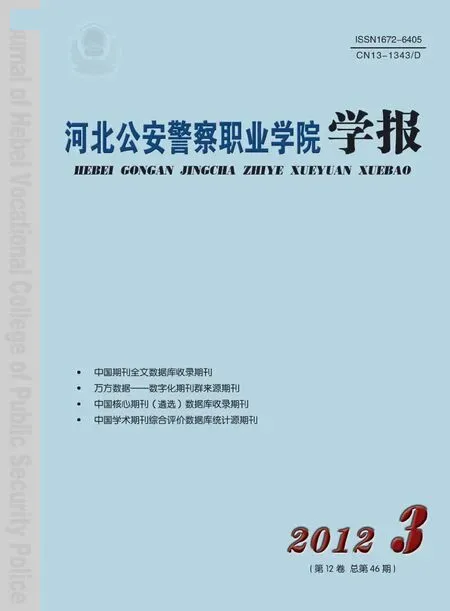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徐 苗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徐 苗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现阶段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如大村落家族衰微、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阶层分化等,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在社会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胁迫等非正当手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得以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黑恶势力;社会结构;社会整合
社会结构因素是诸多社会现象发生的重要诱因,犯罪最具时代特色,当然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社会结构原因是该类犯罪产生的重要因子。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寻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原因有利于将其与最广阔的社会变革背景联系起来,紧贴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社会结构理论概述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其普遍使用,但是并不存在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概念,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学者在实际应用这个概念时也十分的笼统和模糊。社会结构是犯罪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结构中的各要素都对犯罪产生作用,社会结构理论也是犯罪学的重要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要分析我国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产生的社会结构原因,就必须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结构的要素及组成有一个基本的界定。
社会学学者一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定义社会结构。如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社会结构是指存在于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也有学者并不局限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社会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即社会现象的结构分析,包括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和具象结构。所谓制度结构是指定义人们行为期望的文化或规范模式;关系结构是指行动者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独立性以及所占据的位置;具象结构铭刻于人类身体和思想中的习惯和机能,他们能使人们生产、再生产和改变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成为可能。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结构概念的表述不同,但是大多认为社会结构包括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等,概括起来社会结构诸要素核心表现为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结构最大的功能在于凭借规范、制度、文化的有机结合以保持秩序和力量的稳定与平衡,如果结构失衡就会导致力量对比不均衡,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犯罪就会产生。犯罪学中的社会结构主要关注那些导致犯罪或者越轨行为产生的结构性要素,如社会阶层结构、群体结构、组织结构、社区结构、制度结构、文化结构等。简言之,犯罪学中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意义上被组织起来,社会结构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前者关乎个体所属社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与物理属性,后者是指社会如何将个体分为不同等级,即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对犯罪的影响最受重视,但是如果将犯罪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来分析,社会结构诸要素都对犯罪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结构变迁引发农村黑恶势力滋生
农村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指农村中的不同行动主体围绕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农村社会结构中诸要素都是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转型还处于初始和过渡阶段,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与此相伴而行的是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失范与重建,系统震荡的危险与机遇,这一系列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变迁中演进。六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笔下“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十几年前苏力教授“送法下乡”的判断也与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尚未彻底改变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没有完全告别传统,远离乡土气息。这正如希尔斯所说,“一个社会与其过去的纽带关系不可能完全断裂,它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不能由政府的法令或旨在专门立法的公民 ‘运动’所创设”。因此,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表现为内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等各种力量的交锋,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特征。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实质是有组织犯罪,是一种力量的结构性整合,这从其内涵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是指,在农村一定区域或者行业活动,以帮伙形式为主体,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为主要手段,在较长时期内有组织地进行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公开欺压、残害群众,横行称霸一方,对抗基层政权组织,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特殊的群体性犯罪形态。由此可见,农村有组织犯罪是结构性矛盾激化的产物和表征,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聚合起来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采用暴力、恐怖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人群中实施非法控制的行为。正如有论者在解读当前我国农村的法律实践后指出,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陷入了结构混乱状态,种种因素导致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状态。社会转型急剧冲击农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内生权威式微,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进一步加剧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农村黑恶势力因此应运而生,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维持秩序的一股力量。
三、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社会结构剖析
由于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我国农村地区正处于社会不断分化、原有的社会整合力量逐渐弱化的阶段,而新的整合机制又尚未建立,因此就会产生结构上的矛盾。农村社会结构失衡为当前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提供了沃土,总体表现为农村社会整合能力不足以及控制能力的下降,具体表现为农村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现代新生的外来权威根基未稳。
1.大村落家族衰微,整合功能弱化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架构以土地为核心,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在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包括涉及自身相互之间及自身与土地之间两重关系在内的乡土关系,并因此派生出了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视。费孝通先生把这种深受地缘和血缘关系影响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称之为“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下会形成特有的伦理本位和乡村共同体,小社会大家族的凝聚力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国农村千年来赖以维持结构稳定的土地经济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计划生育制度的推行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使得传统的宗族力量大大削弱,血缘和地缘关系淡化,导致村落家族衰微或分化、瓦解成一个个小家庭,家族内部领导者权威丧失或者根本就没有领导者。在此局面下,各个小家庭各自为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淡漠,缺乏共同的联系纽带,当面临纠纷或者外在压力时,村落家族的调解与干预不再是一种有效的化解机制和依靠力量,同时也很难出现整个家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情形,家族原有的生存、维护、保护的正功能正在逐步弱化。
但是随着整个大宗族、大村落家族的瓦解,农村社会分别呈现出了以宗族、小亲族、联合家庭、户族、村民组、核心家庭等不同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尤其是核心家庭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影响重大。然而,核心家庭等类似家庭的复兴在整合农村社会中与基层政府往往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其负功能更为显著,表现为利用家族势力, 群体抵抗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或与其他村落体在争夺资源方面进行武力械斗。这无疑是一种结构性矛盾,核心家庭失去了大村落家族的制衡,单个的原子家庭又无法与之对抗,而农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又有核心家庭介入的实际需要,长此以往核心家庭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靠暴力,有组织的从事非法活动的黑恶势力。
由此可见,大家族、宗族势力的衰微使农村社会难以被整合成一个整体,而核心家庭的异军突起则进一步分割、瓦解了这个整体,那种大家族内部统一解决纠纷的局面不复存在,混乱失序和力量的斗争成为核心家庭本位下的农村社会关系主旋律。
2.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经济情感基础流失
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应该是地缘群体,但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农业社会决定了村落的稳定性、封闭性、内聚性,人们一直被束缚在土地上,同一宗族血缘关系的人聚居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传统村落是地缘、血缘、业缘关系的综合体,正因为有这三个强大的纽带才有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村落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所产生的规范效应和认同权威,其血缘共同体价值逐渐衰落。传统村落共同体土地是经济基础,决定了地缘和业缘,而血缘则是乡村社会整合的文化情感源泉。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村落共同体迅速走向解体,生产力的发展将人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富余的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非农业收入,维持村落共同体存在的土地经济不再是主要的经济形式。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随之带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批青壮年涌向城镇,农村只剩下老年妇女和儿童留守,村落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和愿意苦心经营的家园,人们对村落的情感认同和忠诚感不复存在,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成为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必然。
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后果是带来人们情感和认知的漂浮无根状态,人们直接缺乏面对面的充分交流与互动,道德约束和情感联系的社会控制力量下降,无法满足人们找寻确定性的需要,这无疑会是不安全的隐患之一。社会学的研究表明,面对面日常互动与非面对面互动的效果完全不同,熟悉的人群中产生的道德约束与情感联系的强度与性质也完全不同于陌生人群,人群越是熟悉个体满足与认同感越是有比较效度。由此,随着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人们之间的互动减少,信任降低,文化上的手足之清淡漠,联系纽带的丧失必然会产一系列的失序行为。
随着社会结构变迁,村民的行为在经济和道德两个层面上失去了相应的约束,村落共同体的意识与观念不再强烈,内生权威衰落到不能定纷止争,于是村民不得不寻求其他的纠纷解决办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谁行事霸道,谁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谁不要脸面,谁就在农村事务中处于有利地位,其他村民却无可奈何,这样无形中助推暴力蛮狠文化的大行其事,最终发展成为农村黑恶势力。事实上,如果内生权威式微,国家权威有无法有效整合农村时,人们在处理纠纷时就会产生依靠黑恶势力的内在需求。这种不正常现象慢慢会内化成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加上黑恶势力在农村经济资源控制与配置上的优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黑恶势力的滋生与不断发展壮大。
3.社会阶层分化,激发阶层功能和收入分配合法性矛盾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处在最底层的农民通过绅士与国家发生联系,国家——绅士——农民三者在乡村中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稳定的社会生态,国家权力一般不直接扩展延伸到村庄,因此不存在国家与村落的二元对立,社会阶层划分也相对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阶级划分当作改造农村的出发点, 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共产主义以前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阶级划分极大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乡村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破坏了村庄的内聚力。阶级划分增加了国家的直接影响, 扫除了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力之上的权威, 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由于阶层划分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政治色彩,往往会产生仇恨和身份歧视,极大的破坏了乡村社会原有的阶层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能够自主参与市场竞争,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逐渐有了明显差距。有学者认为经过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的社会剧烈变革,农村社会基本形成了七大社会阶层,分别是管理干部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类白领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民工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贫弱阶层。由于阶层分化造成人们地位的不平等,农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会激化这一结构性矛盾,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现象在今日之中国乡村社会十分普遍,这必然会引发人们对阶层功能合法性和收入分配合法性的质疑。
这种结构上的矛盾会引发人们的心态失衡以及对既有利益者的不满,这为农村黑恶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沃土,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在正当致富不能奏效之时就会纠结在一起,利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抢夺资源发展成为黑恶势力。相反处于较好社会阶层的家庭或者农村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竞争中的有利局面,也会认识到组织集团的重要性,会运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由红转黑”,成为危害农村发展的黑恶势力。
4.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弱化、蜕变,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近年来越来越强调通过国家政权建设加强对农村的改变与控制,以加快现代化进程,国家政权的强力进入迅速瓦解了农村社会原有的力量平衡格局,在新旧权力交替时期势必会造成农村社会制约和调控机制的相对弱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经济,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合作社制度。生产队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也保证了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农村最底层,国家对农村的控制能力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体制寿终正寝,农村社会管理陷入短时期的权力真空状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降低。
随后我国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探索建立村民自治,加强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和控制,但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多种因素致使其未能将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整合。基层政权正在远离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没有贴近社会的利益,他们日益成为既脱离了原来的行政监督,同时又未受到任何社会监督,相对独立的、内聚紧密的资源垄断集团。之所以出现基层政权游离与国家社会是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基层政权合法性来自上一级政府的授权,而非由人民选举难以受到来自人民的有效监督。权利最容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基层专权极易与本土宗亲、家族势力结合,利用公共权利欺下瞒上,独断专权。基层政权腐败一方面有损国家权威,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下降,国家政策执行力减弱,使农村社会整体处于失序状态,许多黑恶势力乘机通过贿选进入基层政权;另一方面腐败与农村黑恶势力的勾结、纵容甚至直接为其提供合法外衣,合法纠纷解决机制失灵致农民转而求助于农村黑恶势力来解决纠纷。
由于国家力量不足以将农村纳入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因此只能下发权力,推行村民自治来建立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威。但是,村民自治与基层政权之间并未建立良性互动。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与乡镇一级政府在管理范围和权限上划分不明,对许多涉及村民需要履行义务的事项,村民自治组织无力、无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而对关涉公民重大利益的事项,比如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等,村民自治组织缺乏相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撑只能无为而治。因此,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村民自治也未能成功整合农村社会。
由于国家力量的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制度不健全和法律执行乏力。正如有论者所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整个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从静态转向动态,新旧体制、新旧观念在转换中相互“冲撞”、“磨合”,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达到相对或完全稳定的状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农村旧制度失去原有功能,而新制度尚不完备。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某些制度,诸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防队、治保会等结构名存实亡,人们发生纠纷时没有强有力的机构来化解。新建立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比如农村集贸市场管理制度等,由于认识不足,经验缺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漏洞,这些都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另外,法律这一公共产品在农民纠纷解决中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法律不能定纷止争,由于人们法律意识不强以及黑恶势力凭借暴力、弄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产生的错误导向,人们对法律的信赖严重不足。
四、农村社会结构引起黑恶势力滋生的犯罪学解读
犯罪作为人类社会的梦魇,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犯罪是犯罪者个人实施的,因此早期的犯罪学家较为注重找寻犯罪的个人原因,从犯罪生物学和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犯罪产生的根源。事实上,犯罪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任何犯罪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及其不公对理解犯罪的根源具有重大价值,如今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世纪,犯罪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就指出社会结构因素对犯罪的影响远远超出个人因素,他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自此以后,犯罪学家认识到社会结构对犯罪的影响,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进入20世纪,美国芝加哥犯罪学派在探究犯罪发生的社会结构原因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时期产生了社会解组理论、失范理论、社会纽带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美国犯罪学家重视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所取得的成果。
社会结构反映一个社会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意义上的组合状况,比如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分配以及个体乃至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被组织起来的方式对于犯罪的发生和控制意义重大。良好稳定的社会结构能控制犯罪,但社会结构构成不科学以及变迁中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会诱发犯罪。强烈的集体意识以及牢固的社会连结能够限制个人冲动和防止失序,任何社会结构要素的弱化都会使社会不稳定并导致失序。在快速的社会变迁时期,传统意义上控制我们行为和态度的规范不再明确,面对新环境人们会变得无所适从,失范和低度的社会整合两种结构性条件会导致犯罪。
我国农村正经历的激烈社会变迁,比如村落家族衰微,农村共同体走向崩溃,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基层政权组织的弱化、蜕变等都极大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改变或者重组必然会改变原有的社会联系纽带,打破原来的权威秩序体系,并因此削弱了传统的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控制减弱必然会引起社会失范,现阶段农村社会各阶层成员行为方式各异,彼此对立矛盾,价值观、道德观偏离,人们不同程度地感到迷茫和困惑,由于缺乏统一协调的社会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状态。人们对传统文化目标、社会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丧失了信心,对新的设计纷呈的目标和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道德规范又难以选择和适从,从而最终造成社会成员文化目标、价值观念、道德法律规范取向上的危机。面对利益分配不公和利益冲突,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与日俱增,愤怒和挫折感强烈,在社会失范的大背景下,人们不能指望从政府以及司法制度获得帮助,因此会采用暴力或者借助黑恶势力来保护自己,暴力亚文化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规范作用。正是由于我国农村传统社会的道德权威和行为规范失去作用,新的社会规范和调整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农村社会结构矛盾激化,社会解组、规范和社会纽带崩溃给了农村黑恶势力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可乘之机。
在社会失范和低度社会整合情形下,农村黑恶势力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在内在权威式微,外在秩序力量尚未建立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是一种强大的武器,疯狂的群体暴力压制着善良百姓的反抗欲望,作恶称霸,恃强凌弱,百姓敢怒不敢言。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有效性进一步强化暴力亚文化,引发更多的小混混效仿,为农村黑恶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和组织文化基础。农村黑恶势力通过重金贿赂基层政府党政干部和司法人员,建立保护伞,不断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以达到支配农村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资源的目的。农村黑恶势力能够凭借暴力以黑护商,以商养黑,黑商互促控制农村经济资源,甚至通过贿选等方式掌握农村基层政权,利用官方资源来谋求自身发展,这无不是农村社会结构混乱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1](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9.
[2]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
[3](美)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M].秦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4]张一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J].社会学研究,2006,(6).
[5]曾贇.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有组织犯罪生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5).
[6](美)E·希尔新.论传统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92:440.
[7]王智民.当前中国农民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168.
[8]董磊明等.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9]周晓红.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5).
[10]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存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11]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1).
[12]董磊明等.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13](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67.
[14](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488.
[15]李全生.农村社会分层结构与民生政策选择[J].农业经济,2012,(6).
[16]张静.基层政权——农村制度诸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89.
[17]康树华.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组织的弱化、蜕变(下)[J].辽宁警专学报,2005,(4).
[18]郭颖慧.论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犯罪的关系[J].现代法学,1993,(4).
Structural Causes of the Criminal and Vicious Groups in Rural Areas at the Present
Xu Mi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The breeding of criminal and vicious groups at this stage is rooted in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Due to rapid social changes,the authority of the decline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endogenous,such as the decline of large village families,the collaps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has failed to establish,which result in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entire rural community in a anomie and low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state.In this context,relying on non-legitimate means of violence,coercion,criminal and vicious groups in rural areas has a natural advantage in the race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resources and thus it's able to breed and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criminal and vicious groups in rural areas;social structure;social integration
D917
A
1672-6405(2012)03-0031-05
徐苗(1986-),男,湖北建始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2012-08-13
王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