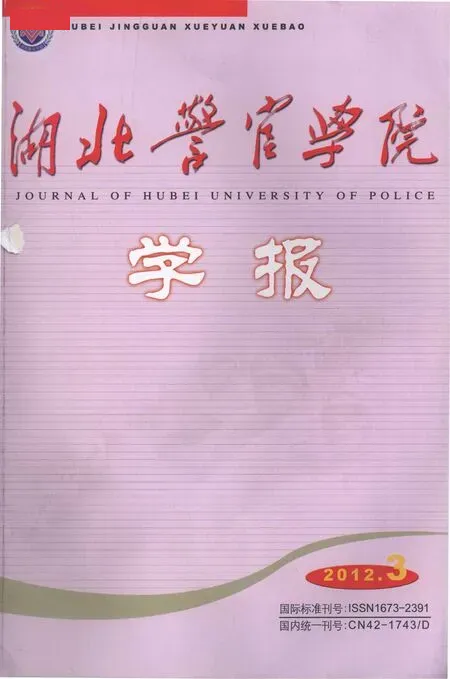正当防卫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张 进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4)
正当防卫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张 进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4)
从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根据和构成要件出发,结合具体案情,分析被绑架者杀人行为的正当防卫符合性,并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其他阻却性事由。
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紧迫性;有责性阻却事由
一、争议问题
本案案情复杂冗长,为便于分析,本文将根据案情发展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其存在的刑法问题进行分析。
(一)第一阶段
民警A与甲共谋,绑架B及其女友C,由甲、乙、丙负责关押,A等人向B的亲属提出赎金30万元。本阶段的案情相对清晰,民警A与甲、乙、丙共同绑架B和C,并由甲、乙、丙负责关押。四人的行为客观上符合采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视具体案情而定)劫持或控制他人,使被害人处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的情形,主观上四人具有侵犯B和C的行动自由的故意,亦具有利用被绑架人的亲属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的意思[1],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已构成绑架罪的既遂。
(二)第二阶段
A向甲提出得到30万元后杀死B,但甲反对,由此产生矛盾,后甲与乙谈论此事,乙对甲说:“B跟我说过,如果放掉他,他同意给我们60万元。”(因为B知道A要杀自己)。于是,甲、乙、丙共谋利用机会杀 A,甲、乙、丙、B、C 共同杀死A,B、C被放出,并交钱给甲等人及窝藏A的手枪。此为本案的第二阶段,本文的分析重点即在此阶段,争论的焦点问题:B和C针对A的侵害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或者特殊正当防卫?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从A、甲、乙、丙四人实施绑架行为起,B和C的人身法益即持续受到A等四人的不法侵害,此时B和C即享有对侵害者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A具有杀死被绑架者B的意图。那么,当B获知A意图要杀死自己时,B对A的反击行为的限度应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定?是否可以认定此时 A的绑架行为已经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甚至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
其次,若B和C的行为不成立正当防卫,B、C杀死A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B、C的上述侵害行为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违法性或有责性阻却事由?
二、理论分析
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款分别规定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阻却违法性的根据
关于正当防卫的阻却违法性根据,刑法理论上存在多种看法。放任行为说认为,正当防卫行为,乃因一法益与他法益不能两立,且其事情处于急迫,不及收官署之援助,故任听当事人自理援助,与紧急避险行为无异;法律与社会利益说认为,不法侵害行为含有反社会性,此种反社会性之行为,人人皆得加以防御,借以保全社会之共同福利,故扑灭此项反社会性,自不在应禁之列,即应视为权利行为;义务说认为,根据宪法要求,每个公民都有维护公共利益不受非法行为侵害的义务,而正当防卫则是履行这种义务的体现;法益衡量说认为,如果法益侵害行为的实施是为了保护另外价值更高的法益,则该行为就是正当的,这种观点中又可以分为保护法益欠缺说和优越法益说。[2]
放任行为说认为正当防卫属于紧急行为,正如欧洲中世纪教会法中的一句格言:紧急时无法律。但该说并未虑及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自救行为的区别,并不能很好地揭示正当防卫的本质。法律与社会利益说认为正当防卫是一种权利行为,值得采纳,但该说过于强调行为的社会性,在对防卫人具体行为的分析中略显无力。义务说根据宪法将正当防卫视作每个公民的义务,这种说法混淆了宪法义务与刑法意义上义务的区别,如果采义务说,受害人未能采取针对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受到侵害,将被视为未履行义务,这在法理层面是说不通的。利益衡量说中的保护法益欠缺说认为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受到否定,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不法侵害者基本人权的保护,正如刑法格言所说,“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3]
笔者赞同法益衡量说中的优越法益说。正当防卫制度作为刑法总则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其设置目的也应当是保护法益免受不法侵害。基于此,正当防卫作为一种在侵害者与被侵害者法益冲突下的针对前者法益的损害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满足了保护更优越法益的正当化条件,而为法律所允许,从而阻却了该行为的违法性。
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根据虽然并不直接构成其成立要件,但作为这种行为的实质,支配着其成立要件的取舍。在B、C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认定上,笔者认为,此时对构成要件的逐一认定,应结合相应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从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根据出发予以判定。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1.一般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存在四要件说和五要件说。四要件说包括:不法侵害的存在;紧迫性;防卫对象;防卫限度。五要件说则增加了防卫意识。持五要件说的学者认为,五要件说“不仅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而且较好地、准确地反映了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4]
正如我国刑法学界通说所主张的,犯罪的成立应当满足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当主观方面或者客观方面不满足时,应当排除犯罪的可能性。按照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符合前述四要件但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例如偶然防卫,也应该阻却违法。尽管我们不必纠结于此种行为的具体分类,但可以确定的是,上述行为并不构成对法益的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
四要件说是更具理论和实践说服力的正当防卫成立要件说。本文将根据四要件说,结合本案的实际发展过程分析B和C所针对A的侵害行为,判定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2.特殊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关于特殊正当防卫,有学者称之为“无限度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5]。其实,结合特殊正当防卫的具体条文分析,将其冠以“无限”的称谓是不当且危险的,这种理解“潜藏着在防卫过程中催化新的不法的严重危险”。根据刑法条文,特殊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不设防卫限度。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正当防卫之行为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人身伤亡。
在一般正当防卫中,防卫者针对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在特殊正当防卫中,在面对人身安全的法益遭受严重侵害时,防卫人针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法益进行防卫,根据法益衡量说的观点,仍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的。因此,特殊正当防卫仍然是一般正当防卫的一种情形,而不是与之相斥的另一种刑事法律制度。
据此,笔者将根据正当防卫的一般原理分析本案,而不拘泥于特殊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事实上,根据一般正当防卫与特殊正当防卫的原理对B和C的行为进行分析,亦应当得出一致的结论。
(三)B、C行为的正当防卫符合性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包括:不法侵害的存在;紧迫性;防卫对象;防卫限度。
本案首先可以确定,A伙同甲、乙、丙等三人绑架B和C,并以此向其亲属要求赎金,构成绑架罪,在此过程中,B和C的人身自由始终受到A等人的剥夺,因此,不法侵害的存在确定无疑。另外,B和C的打击行为确是针对A,亦符合防卫针对不法侵害者的要件。存在疑问的是,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即A的侵害行为是否具有紧迫性,以及B和C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上述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A的绑架行为无疑处于持续之中,因此A的不法侵害的紧迫性确定无疑,但如案情所述,在本案的第一阶段,A等人对B和C实施的绑架行为尚未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因此,如果说B和C的打击行为以A在第一阶段的不法侵害行为为前提,那么很明显,其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另一方面,A成功实施绑架行为后,在持续剥夺被绑架人人身自由的过程中,由于担心B被放出后指认自己的罪行,产生了杀害被绑架人B的意图,同时B和C获知了A的杀人意图。结合这一事实,如果认为A的不法侵害在整体上已经具有紧迫性,那么,B和C的防卫行为就可以认为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从而符合正当防卫的规定。因此,分析B和C行为的焦点即在于:A所实施的不法侵害,是否具有严重危及B和C的人身安全的紧迫性?
1.不法侵害紧迫性的认定
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侵害现场说、直接面临说、着手说和综合说。从实质上来说,当被害者的法益处于紧迫危险时,即可对侵害者进行防卫。不法侵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判断不法侵害的开始,采取形式上的单一标准是无法满足普适性的,只有从案件的具体事实出发,对受害者所遭遇的危险作具体的分析,才能够合理地判定正当防卫开始的时间,避免错误认定为事前或者事后防卫。基于此,笔者赞同综合说,即通常情况下,应以具体犯罪行为的开始作为正当防卫的起点,但如果不法侵害威胁十分明显、紧迫,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此时被害者可以对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因此,唯有结合案件具体进展,客观地分析被害者法益受到侵害的危险程度,才能对不法侵害紧迫性作出合理认定。
2.民警A的不法侵害的紧迫性
首先,如何认定A的不法侵害的性质?
从A、甲、乙、丙四人实施绑架行为起,B和C的人身安全即持续受到A等四人的不法侵害,此时可以确定A等人的侵害行为构成绑架罪,但从案情描述来看,A等人的侵害行为尚未严重危及B和C的人身安全,只是限制了B和C的人身自由。后来,A向甲提出,得到30万元后杀死B(因为B认识A),但甲坚决反对(甲也认识B),为此,A与甲发生矛盾。这表明,A已经具有杀死被绑架者B的意图。
其次,确定了A的不法侵害的性质以后,如何判断这一不法侵害危及受害者法益的程度?
如果按照着手说的观点,A仅仅是具有故意杀人的犯意,其行为未得到同伙的认同,且并未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此时B所针对A进行的防卫行为,既可以认定为不符合正当防卫在时间上的要求,亦可以认为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明显超过正当防卫所允许的限度,所以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要件。但着手说存在固有的缺陷,本文采综合说,对侵害行为紧迫性的认定,应从案件事实出发,具体分析:(1)A的严重危及B和C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2)A的上述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
(1)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民警A伙同他人对B和C绑架既遂,A向其同伙提出杀害B(B认识A),其意图已为B所获悉。此后,B、C与甲等人共谋,在A进入其关押地点后杀死了A。由于A具有民警身份且配有枪支,并与甲同谋实施绑架,其无疑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B和C的人身自由已处于A的控制(间接控制)之下,人身安全亦为A所掌握,此后,A明确流露杀害B的犯意,且为B所知,但因同伙甲阻拦而未进行。如果根据A“尚未着手实施杀人行为”,否定紧迫性,对B、C存在明显不公。B和A认识,这就意味着,A当然地认识到,在获取赎金后放走B和C,A的罪行必然受到B的指证,A的这一想法也必然为B所认识。换言之,由于A在绑架中处于主要地位,持有枪支,并已经完全掌握了B和C的人身安全,如果认定B和C必须等到 A开始着手进行杀人行为时才可进行相应限度的正当防卫,那么B和C基本不可能进行正当防卫。所以,应当认为此时具有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
(2)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如果行为已经结束同样不符合紧迫性要件。B和C在遭到A的绑架,获知A意图杀死自己后,即享有进行相应限度的正当防卫权,此时A已经对B和C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紧迫的侵害危险,该正当防卫权利应当认定为特殊正当防卫权利。如果这一防卫行为造成A的伤亡,亦处于正当防卫的合理限度之内,因而不承担刑事责任。那么,A对B、C的严重人身安全威胁何时结束呢?根据案情所述,A到关押B和C的现场后,甲、乙、丙制住A,甲将刀递给B,让B刺杀A;B持刀向A的心脏刺了几刀,从而杀死了A。在判定A的严重危及B和C的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当A被甲、乙、丙等三人制住时,A已经无可能再对B和C的人身安全进行侵害,A对B和C的人身法益的不法侵害已经不具有紧迫性,B杀死A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紧迫性构成要件。因此,A严重危及B和C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确然存在紧迫性,但该紧迫性在A为甲、乙、丙所制住之时便已结束。但对C而言,其并未实施杀人行为,且其之前协助甲、乙、丙等人针对A的侵害行为,并不违反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要求,因而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
(四)B行为的有责性阻却事由分析
B的防卫行为不满足不法侵害紧迫性这一时间要求,不能成立正当防卫,那么,是否一定要追究B的刑事责任呢?从案情看,B的故意杀人行为可能存在不得已的情况,还应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分析:在当时的特定情形之下,B杀死A的行为是否存在无法选择或者不可抗拒的情形?
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6]
当甲、乙、丙制服A之后,A已经丧失对B和C继续进行不法侵害的可能,此时B的行为就不符合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如果认为B和C在当时情势之下,客观上乃是不得已而作出杀人行为,从而否定其行为有责性的成立,则需要证明:B此时不具有作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进而适用《刑法》第16条的规定。
B是否可以选择不执行杀死A的行为?如果B不杀死A,B是否一定受到甲等人的杀害?由于“只有杀了A,才可以放掉B,因而可以得到60万元,否则A可能杀害甲、乙、丙及B与C”,在已经制住A之后,甲、乙、丙杀死A已属必然,但如案情所述,甲等人与B并不互相认识,也不主张杀死B。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甲等三人并不会因为B不执行杀死A的行为,而选择将A、B、C三人一同杀死。基于上述分析,B杀死A的行为,不可认定为《刑法》第16条“不可抗拒”的情形,因而其有责性成立。
可以看到,B杀死A的实行时间在A丧失侵害能力之后,不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从案情的具体实施出发,亦可判断其行为并非缺乏期待可能性。如果 B仅仅是在制服 A之前的阶段为甲、乙、丙等人的行为提供了帮助,在本案的特殊案情之下,其行为将符合正当防卫;但由于其在制服A之后仍然执行杀人行为,因而符合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成立犯罪。
三、结论
本案中,A的绑架行为、甲、乙、丙的绑架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以及B窝藏枪支的行为比较容易认定,但B和C在本案中“反杀”A的行为,其性质则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一方面,对于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应当坚持法益危险的紧迫性这一实质标准,从具体情况出发分析防卫人的行为,进而得出C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另一方面,在认定B的杀人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下,进一步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此也应当以具体的行为为基准,结合案情进展,最终得出B的相应行为不具备有责性阻却事由进而成立犯罪的结论。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66.
[2]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28.
[3][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 97:96.
[4]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1.
[5]赵秉志,赫兴旺.论刑法典总则的改革和发展[J].中国法学,1997(2).
[6]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30.
DF6
A
1673―2391(2012)03―0115―03
2011—12—10
张进,清华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