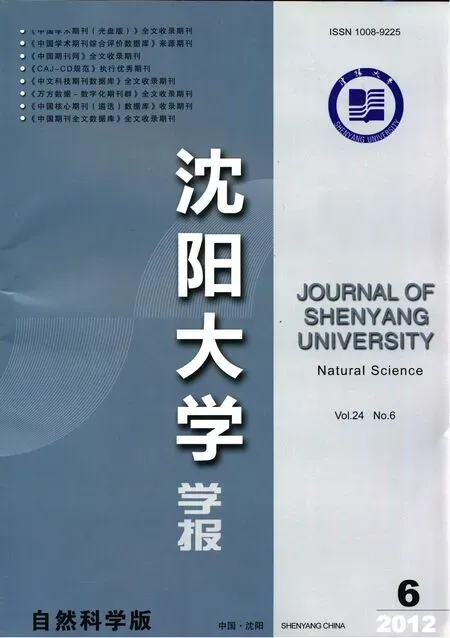民族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傅钱余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民族文学理论”的提出
所谓民族文学理论,简而言之,“即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艺术追求、文本特性及特征的理论及批评方法。”[1]这一理论的提出,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我国是多民族一体的国家,除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并不相同。同样,各个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各具特色、自有芳华。历史地看,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文学传统,既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作家文学传统,比如满族、蒙古族、壮族、藏族等民族较早就产生了自己的作家文学。如果说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整体而言不够兴盛,那么现代以来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则突飞猛进。特别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大量涌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如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满族作家郭雪波、赵玫,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席慕容,彝族作家阿库乌雾、吉狄马加,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叶梅,等等。逐步繁荣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呼唤着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进一步深入。其二,目前国内文学研究对各民族间文学的差异重视并不够,研究思路通常是试图创建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期待着其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样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独有特征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比如,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推论文学的差异是一个常见的逻辑,然而,文化差异又是如何形成了文学的差异,文学是如何体现自己的民族精神等需要深入的问题通常是语焉不详。
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体形式为例:刘俐俐教授曾考察了彝族作家阿库乌雾的“人类学散文”写作,发现“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本,从文本形态来说,以民间口头文学和民族文学传统文本为其重要创作资源,口头文学和民族传统文学的叙事、描写乃至议论等表达方式,以及篇章结构,不只是作为技巧,而且作为思维方式被自然而然地继承和采用,从而形成文学人类学文本融诗意和哲理为一体,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充沛的文学性表达。”[2]刘俐俐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也曾指出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作品,在文体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征,它是介于文人创作和民间口头创作之间的过渡形态文本[1]。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文体特殊性不是偶然现象,但目前对此的研究却相对欠缺,更别说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了。
乌热尔图是用汉语进行写作的,可想而知,那些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的作家,其文体与通常所言的文体范型当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因此,发现少数民族小说文体的特异性及其根源、意义,就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实际上,不仅仅在文体方面少数民族小说具有特点,在诸如叙事、审美意蕴、意象隐喻等各个方面,少数民族小说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需要被发现、被挖掘,并加以仔细辨析、研究和探讨的。
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各个民族间文学的差异性,但整体来说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学者直言:“当代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不足,不是个别性的问题,而是全面表现于宏观理论研究和整体把握研究与微观具体批评上。”[3]相对而言,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具体作家作品批评和族别文学研究还是有较大起色的,但宏观的、整体的、深层次的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还明显羸弱。
基于此,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在《“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一文中,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建设以“美人之美”为宗旨的、不同于普适性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学理论”。该理论宗旨的提法源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方针,“它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超越了‘各是其是’‘各美其美’阶段所达到的一个高度,是‘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理想得到实现的基础,也是我们对于民族文化体认乃至选择的立场和姿态。”[4]质言之,“各美其美”因其可能具有的自我民族本位意识、狭隘民族主义而将其他民族他者化,各民族之间不能达到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因此这种狭隘的民族观不利于各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美人之美”即是要站在各民族文化平等、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立场下实现各民族文化间的深度交流,同时,在这样的宏阔视野中,也能发现“各美其美”视野下容易忽视的本民族文化的局限和不足。那么,就学术研究者来看,必然就要求一种文化平等对话的基本态度,尊重他者经验,倡导多元、差异的价值立场。
二、民族文学理论的存在形态及建设方式
然而,民族文学理论的提出也有其理论上的困境:既然普适性文学理论漠视了差异性,那基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文学理论以何种形态存在?如果说民族文学理论囊括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那又何尝不是从一种普适性走到另一种普适性;如果民族文学理论是关于汉族之外的各单个民族的文学现象的理论形态,则需要回答民族文学理论和个别民族的文学研究或者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区别何在?它如何从个别研究走向理论表述?因此,民族文学理论是不是一个伪命题?面对这一质疑,民族文学理论该如何作答?对民族文学理论的进一步说明有助于消除以上的诘难.首先,既然民族文学理论题以“民族文学”,其对象必然是全部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理论”相对的是以往主要基于汉族作家作品,忽视少数民族作家独创性、特异性和不可规约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不可否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举是比较通常的做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被描述为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权力话语与非权力话语。在反驳这个观点的简单化、片面性之前,必须将之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从而策略性地将少数民族整体化。如果说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共性,那么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极有可能会体现出某种相同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是文学内容、价值内涵或者表意方式,等等,但它必然不同于汉族作家的创作。因此,以此为研究起点和基石,进而进行理论的总结、归纳和阐释,就成为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个范畴。
但是,正如前所述,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各具特色,实际上并不是同质化的,可能上述的共性也各有其不同的根源,这也就构成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二个范畴。这个层次中民族文学理论首先关注的是个案,包括各个民族的独特表达方式,寻找此表达方式的根源,进而和其他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进行比较,从而推进民族文学研究。可以看出,这个层次中民族文学理论包括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区域文学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式。那么,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区域文学研究还是不是“理论”?一方面,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区域文学研究是理论产生的方式和过程;另一方面,理论的存在也不排斥个案分析和比较。这正是要强调的第三点,即对“理论”的理解。在《文学理论入门》首章中,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对“何为理论?”这个问题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一反给“理论”一词下定义的做法,而是对理论的特点进行了描述,他总结了以下四点:①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②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些什么。③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④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5]。
民族文学理论的“理论”正是基于此意义上的理解,而跨学科性、开放性(动态性)、批判性、自反性是其核心理念。简言之,理论不是一套死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理论是暂时的、片面的,因此理论才需要不断地充实、更新;同时,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提出新问题,促进对问题的思考,“是分析和推测”。民族文学理论是开放的、动态的,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场”,在这个“场”中不同学科的方法可以得到借鉴,因此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民族文学理论追求的不是二元对立,不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而是强调多元,强调差异。最后,理论和方法既是一体的,也是有区别的。民族文学理论虽然立足于多学科的视野,借鉴多学科的方法,但其对象始终是民族文学,得出的研究成果归属于民族文学理论。笔者曾以空间为切入点,分别讨论了残雪和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作品。虽然角度和方法是相同的,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残雪的作品更重视对个人精神空间的挖掘,力图以“少数孤独者”的顽强抗争来唤醒“沉沦于世俗、束缚于现实”的多数人[6];而叶梅的小说植根于土家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族群精神空间,饱含了作者在多元文化时代对本民族命运的关怀与思考[7]。
质言之,理论总结离不开个案分析,个案分析又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无法将民族文学理论与具体作家作品研究、族别文学研究割裂开来。民族文学理论必然是“理论”与“批评”的结合,是一般与特殊的双向互动。民族文学理论是多层次的、立体化的理论形态。
粗略地看,理论的产生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从理论到理论,这主要是一种思辨的、推导性的理论生产方式,比如黑格尔的《美学》主要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其二是从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出发,通过总结、归纳最后形成理论,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便是通过对普鲁斯特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的细致考究、条分缕析,从而得出了关于文学叙事的一些规律。民族文学理论将范围设定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民族文学理论推崇第二种理论生产方式,从具体问题出发,得出有所“指”的理论。从具体的文本出发,首先能避免民族性和作家个性的混淆,辨析出哪些特征是作家的个人风格,哪些特征是其民族个性,从而不至于发现了某个特点便不加区别地认为是民族特性;其次,要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真正的独创性,必须从文本出发,仅仅站在文化差异的高台“推导”文学的差异,并不能得出有价值的成果,可能性和实际现象可能完全不相合,因此需要深入文本细致探讨。
正如刘俐俐教授所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如何创新?不能依据文学理论原有思路,必须重新提问题,可是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目前尚不清晰。基于此,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形成跨学科视野,汲取相关学科资源,从中获得启发,提出超越原有文学理论,具有较高创新程度的问题。”[8]要提出有价值、有创见的新问题,就不能囿于传统的学科限制,那样无疑是画地为牢。而是要立足于文学学科,采取宏阔的学术视野,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从而让民族文学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也正是目前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格局下研究民族文学,无法避免多民族文化关系问题。如何看待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在民族文学研究界,仍然存在一种不良的研究倾向,即在大汉族文化优越态度下,带着有色眼镜以“主流眼光”“巡视”民族文学。这并不是说民族身份必然决定价值选择。许多汉族学者也能放下姿态,平等地看待民族文化,相反有些少数民族学者却有意无意盲目认同所谓主流价值。其次,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将文化与文学生搬硬套循环互证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不乏一些新颖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往往忘记了一个“如何”的问题。换言之,推论民族文学具有民族特色是很容易的,但文学是如何体现民族精神的这一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这提醒我们深入研究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的转换环节。
总而言之,民族文学理论聚焦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以“美人之美”为宗旨,以跨学科的、开放的、动态的视野挑战普适性文学理论,注重多元性、差异性和不可规约性。民族文学理论有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既要把握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要注重各民族文学间的差异。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性是其主要出发点;同时,民族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要求研究者立足于文学学科,以宏阔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在这块尚待耕耘的土地中,研究者还须采取更为切实的态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从而让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刘俐俐.“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J].文艺理论研究,2010(1):61-62.
[2]刘俐俐.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81.
[3]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8):157.
[4]刘俐俐.“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5):45.
[5]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6.
[6]傅钱余.空间、意象与残雪小说边疆[J].沈阳大学学报,2011(6):77.
[7]傅钱余.梯玛信仰与叶梅的小说世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26-130.
[8]刘俐俐.我的学术选择及反思[J].粤海风,201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