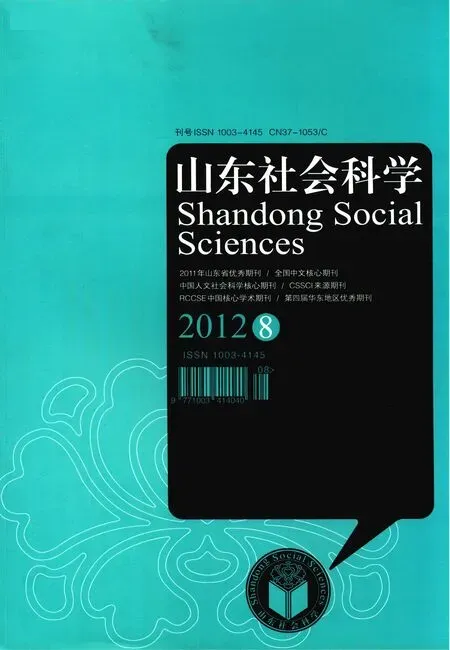论债(务)与责任的关系
---兼谈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问题
郭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论债(务)与责任的关系
---兼谈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问题
郭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传统大陆民法在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上坚持权利---义务两位一体的结构,在立法中并未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得以区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应该设立债法总则,在债与侵权责任关系上实现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兼顾的转变.
债;责任;本位义务;变生义务;债法总则
债法总则的存废是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学界对于债法总则设立与否的争论日趋激烈.①学界对于是否设立债法总则存在两种观点:一为肯定说,具体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政法论丛》2003年第1期;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柳经纬:《我国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二为否定说,具体参见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覃有土、麻昌华:《我国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存废》,《法学》2003年第5期;许中缘:《合同的概念与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清华法学》2010年第1期.据笔者考察,学界的探讨主要从体系化、功能性以及债与责任的关系的视角进行论证.然而,学界尚未完全厘清债与责任的关系问题,给得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带来无尽的困扰.本文通过对传统大陆法系债(务)与责任的关系进行解读,将其与我国立法中的规定进行比较,分析两种不同的路径.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债法总则设计的不同主张,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对我国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有所裨益.
一、传统民法中债(务)与责任的关系
罗马法上的债的观念并未区别债务与责任,而是由债务与责任结合成为债务观念.责任常伴随债务而生,二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②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该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法上的救济最终都可归结为财产利益,即无论是财产的损害,抑或是肢体、名誉和信用的损害,均可最终归结为金钱赔偿.由于债的标的最终统一于财产利益,不履行给付义务应负的责任是财产赔偿,原债务的给付和因承担责任的给付似乎没有区别,因而在观念上也不分债务与责任.③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德国在普通法时代仍延续了罗马法的思维,不区分债(务)与责任.但由于受到日耳曼法的影响,债务与责任的区别观念日益明确.在日耳曼法中,债(务)为法的当为,不含有强制性因素,而责任则是指在债务人当为给付而未为或不完全为给付时,债权人有权强制债务人履行.诚然,日耳曼法虽然提出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分问题,近代各国在法学理论上对于债(务)和责任亦作出了区分,但是,其立法模式无不遵循罗马法传统,在民法典体例上视债与责任为统一体.无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抑或是其他继受法国模式或德国模式的各国民法典,均将侵权法置于债的体系之中,均未厘清债与责任的区别.例如,《法国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被置于第四编"非因约定而发生的债"之下;《德国民法典》于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第二十七节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内容;《日本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则被规定在了法典债权编的第五章之中;《阿根廷民法典》虽然在体系结构上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大相径庭,但其第二卷"民事关系中的对人权"实际上就是有关债的规定,而"不适法行为"和"产生于非侵权行为之不适法行为的债"也毫无疑问地被规定在了该卷之中.
在传统民法中,之所以将契约、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置于债法体系之中,究其缘由,乃在于法律效果的形式相同性.具体来说,上述各种法律事实,在形式上均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特定行为(给付).此种特定人间得请求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即属于债的关系.①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在这种形式相同性中,蕴含了债的同一性理念,即各种不同的给付义务在得不到履行时,都可以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在罗马法中,损害赔偿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恢复原状;第二,金钱赔偿.继受了罗马法的《德国民法典》于第249条规定了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方式.而且,在恢复原状不能时,金钱赔偿成为了最终的救济手段.从德国民法典的条文看,义务和责任的概念也没有严格区分."损害赔偿"一词在德国民法典中有时指损害赔偿义务,有时指损害赔偿责任.②魏振瀛:"《〈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由此可见,正是在债的同一性理论的支撑下,传统民法并未对债(务)与责任进行区分,侵权法也就理所当然地置于债法的体系之中.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债(务)与责任关系的路径.在传统民法中,债(务)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债的概念包含债权和债务,而债务本身就包含了债务与责任.通过将责任视为债的担保,运用隐藏在债务背后的责任的概念,将债务与诉权和自力救济联系起来,形成了权利---义务两位一体的结构,进而构建起具有逻辑性的民事权利救济体系.可以说,传统大陆法系民法的这种立法模式是成功的,在该模式中,债与责任的关系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二、我国民法中债与责任的关系
有经济学学者将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并将博弈规则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从国外借鉴的正式规则即使是良好的,如果本土的的非正式规则仍然力量强大且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原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导致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无法奏效.③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这一理论研究框架对我国民法研究亦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即若引进的民事法律规则与我国的本土法律文化及其所形成民事法律的体系或制度相冲突,将会极大地制约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发生了转变.我国《民法通则》第六章规定了民事责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体例,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民事立法深受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立法者认为,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提高民事责任的地位,将有利于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中,义务与责任不分.经长期研究和发展,提出了民事责任是法律关系的第四要素的观点,于是《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作为独立一章加以规定.这是民法理论发展的成果,也是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④刘士国:《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质言之,我国《民法通则》存在着权利---救济的逻辑路径.王利明教授曾准确地指出,民法不仅仅是一部权利法,而且各项权利具有充分的保障机制,整个民法就是按权利和权利保障机制建立起来的体系.⑤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082,访问于2010年11月7日.李开国教授亦将义务分为本位义务和变生义务,认为本位义务是指相对于权利人的原本权利而发生的义务,变生义务是指因不履行本位义务而发生的义务,变生义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民事责任.⑥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刘保玉教授持不同的见解,其认为,义务与责任的关系应该坚持"三段论",即原本义务(本位义务)---后发义务(变生义务)---责任.而义务与责任的分界线在于裁判文书生效与否.具体参见刘保玉,周彬彬:《民事责任与义务的界分问题再思考》,《法学论丛》2009年第4期.笔者认为,上述见解的思路颇为缜密,义务与责任的关系在此得到了清晰而具有逻辑性的梳理.但是,在我国目前民事理论的体系中,这种见解略显超前,与我国自《民法通则》以来的立法传统不尽一致.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基础请求权和派生请求权.⑦庄海丽:《请求权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可以看出,与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不同,我国民事立法在处理债(务)与责任的关系问题上遵循了另一条逻辑路径,即权利、义务和责任三位一体的立法模式.通过将债务与责任区分,直接运用责任的概念将债务与诉权和自力救济联系起来,形成了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进而构建具有逻辑性的民事权利救济体系.
实际上,在我国权利、义务和责任三位一体的立法模式下,债(务)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已经转化为义务与责任的关系.无怪乎我国《民法通则》将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与侵权的民事责任共同置于第六章民事责任部分.根据前文李开国教授关于本位义务和变生义务的论述,笔者认为,法律关系亦可分为本位性法律关系和变生性法律关系.前者是指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包括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对于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根据义务主体特定与否又可分为绝对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人格权、物权和知识产权等)和相对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债权);后者是指权利责任型法律关系,即责任.由于债具有财产性,也即相对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具有财产性,由此而产生的权利责任型法律关系亦具有财产性.但并不是任何绝对权利义务型法律关系都具有财产性,例如人格权就不具有财产性,由此产生的权利责任型法律关系亦未必全都具有财产性.①关晓铭:《从自然权利到正义规则:洛克与休谟财产权利之比较》,《求索》2011年第1期,第85-87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条路径仅仅是立法技术的不同,并无优劣之分.我们也很难看出第一条路径在隶属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遇到根本性的挑战.②在欧洲范围内,存在着统一债法的运动.冯.巴尔教授主张把契约外的责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事项来处理,但是,纵使这样,其仍然是在债的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并未脱离债与责任融合的路径.具体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侵权责任问题---罗马法渊源解读》,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5550,访问于2010年11月8日.对于选择的方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最重要的是法学家应该站在一定高度上运用法学思维方式以及对社会观念的把握,来选择一种能够适合本国国情并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③桑德罗.斯奇巴尼:《侵权责任问题---罗马法渊源解读》,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 25550,访问于2010年11月8日.
当然,在债(务)与责任分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延续《民法通则》的模式,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同归于一章(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继《民法通则》之后制定的《合同法》已经将违约责任置于合同法体系当中,这一点在学界和实务界已经取得了普遍认同.其次,在民事责任领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适用的"归责原则"并不相同,若将它们勉强"拉拢"在一起,难免产生规则适用上的困难.④此处之所以在归责原则上加注引号,乃在于学者之间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将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规定为无过错责任,不是依据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的分类而分别确定归责原则,而是按照责任方式确定归责原则,不符合归责原则的起源、根据.但是,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是责任还是债的问题上去了,涉及到侵权责任是否独立成编的问题上去了.总之,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产生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具体参见魏振瀛:《物权的民法保护方法---是侵权责任,还是物权请求权?(二)》,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3286,访问于2010年10月9日.
对于因侵犯人格权和物权等绝对权而产生的责任,诸如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应该如何安排它们在民法典体系中的位置呢?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可采取如下几种方案:方案一: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人格权编等中不规定相关权利保护的内容,将侵犯上述权利而产生的责任同归于侵权责任编;方案二: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人格权编等中只规定除损害赔偿之外的其他责任形式,而在侵权责任编中只规定损害赔偿责任;方案三: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人格权编等中规定相关权利保护的内容,又在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上述内容.就第一种方案而言,其使整个民法典的体系采取了较为彻底的"总---分---总"的立法模式,具有形式上的美感.但是,其亦可能遭受到如下质疑:诸多责任承担方式的"归责原则"不尽一致,统归于侵权责任编难免会产生适用上的龃龉.就第三种方案而言,难免给人以责任承担方式"遍地开花"的感觉,于法典的体系性方面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案值得赞同,具体设计如下:首先,人格权编所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其次,在物权编规定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最后,在侵权责任编仅规定损害赔偿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如此设计的理由在于:第一,该种设计解决了各种责任方式适用不同"归责原则"的难题.如果将其统归于侵权责任编,势必需要另行规定其适用的"归责原则",而将除损害赔偿之外的其他责任承担方式规定在相应的部分,自然不会产生这种问题;第二,虽然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诸责任承担方式应该属于责任的范畴,但是,学界已然对其属于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抑或是责任争论不休.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来说,该设计可以缓解上述争论;第三,鉴于上述各种责任方式(损害赔偿除外)均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现代社会的法律不可能强制责任人的人身,若其不履行相应义务,最终都会落脚于损害赔偿上来,故在侵权责任编规定损害赔偿,在人格权编和物权编规定的责任方式得不到履行时,可以运用损害赔偿的方式来衡平受害人的损害.可见,通过这种递推式的设计,形成了体系上的逻辑性.当然,采用此种设计,应该说明上述诸责任承担方式与损害赔偿是竞合的关系.此处的竞合关系是指在责任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如受害人仍有损失,得请求损害赔偿.
三、我国债法总则设计的不同路径
(一)我国应该设立债法总则
2002年10月制定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并未规定债法总则.根据参与立法人员的介绍,如果搞债法总则,最大的问题是债法总则的内容有相当部分要和合同法的一般规定重复.草案有合同法的一般规定,有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以后再进一步完善有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规定.这样,债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这次虽然没有把债法总则独立成编,但是债的最基本规定,包括债的发生原因、债的效力等,先写在民法总则的民事权利一章中.①王利明:《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几个问题》,《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应当看到,现行《合同法》超越自己的范围去规定本属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则、代理规则和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则,是因为《民法通则》的规定太简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制定民法典,就应当按照法律逻辑和体系的要求,将现行《合同法》中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定回归于"债权总则编",属于民法总则的内容回归于"总则编",将剔除了属于"债权总则"内容和属于民法总则内容后的合同法作为民法典的"合同编".怎么能够因《合同法》规定了"债权总则"的内容而取消"债权总则编"呢?②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也有学者从债法总则效用的角度否定债法总则的设立,认为债法总则应该是为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法提供共同适用的规则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法总则在合同之外的领域的适用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如关于债的抵销,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因故意侵权而生之债禁止抵销,再如出现新问题而侵权行为法中未有明确条文规制时,债法总则也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③覃有土,麻昌华:《我国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存废》,《法学》2003年第5期.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因故意侵权而生之债禁止抵销",乃是指债务人不得为之,并未限制债权人对该权利的行使.④参见《德国民法典》第393条、台湾地区民法第339条.就"债法总则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的论点而言,实属对债法总则的误解,债法总则的内容是在概括具体制度的共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来就不应该承担创制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既然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作为损害赔偿之债重点的侵权行为从债法中分离之后,债法总则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怀疑.⑤许中缘:《合同的概念与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清华法学》2010年第1期.诚然,侵权行为从债法中分离之后,整个债法的体系表面上看似出现了"危机".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厘清损害赔偿的性质属于责任范畴,并不能剥离其与债法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对于债(务)与责任分离的可行性及其优势已经作过大量论述,此处不再赘言.⑥具体参见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 37082,访问于2010年11月11日.就债与侵权责任中损害赔偿的关系而言,基于债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法总则中相关规定仍可以适用于损害赔偿.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指出,有关债权的规定可以准用于请求权.⑦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在此,笔者提出债与侵权责任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区分与联系的论点.所谓债的形式主义,是指大陆法系以给付为纽带,将传统民法上的四种"债"---契约、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侵权行为---组合起来的形式,其亦反映了传统大陆民法债(务)与责任融合的体例.而债的实质主义,是指债与责任的分离,承认债与责任实质上的区别.而债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联系或曰兼顾是指,在承认债与责任分离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债的形式主义,对责任中以损害赔偿为形式的部分准予适用债法总则.
另外,债法总则存在的价值还在于其对民法体系其他部分的作用上.有学者指出,德国民法典之所以将债法置于总则之后,物权、亲属和继承之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债权总则的规范对物权关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义务具有效力.⑧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在此,抛开德国民法中债法位置安排的争论,仅就债法总则对于其他诸编的效力而言,上述学者的观点十分中肯.虽然德国民法坚持债与责任合一的体例,但是,如前文所言,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认知,有学者指出,身份法有向财产法趋同的趋势,适用总则的内容并无障碍.①李霞:《民法亲属编三题》,《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55页.其他诸编中有关金钱赔偿的内容仍可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而且,类推下去,债法总则对于基于法律规定的金钱给付,如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一方的补偿请求权、第42条规定的一方的适当帮助请求权以及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亦具有适用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我国学者所提出的"非典型之债"的问题.②具体参见柳经纬:《从非典型之债看债法总则的设立》,《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1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柳经纬:《非典型之债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二)我国债法总则设计的不同主张
梁慧星教授认为,设立"债权总则编"以统率"合同编"和"侵权编",进一步完善"债权"法律制度,为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和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法制基础.③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8页.其主持编纂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三编(第20章至第26章)即为债法总则,具体内容包括通则、债的原因、债的种类、债的履行、债的保全、债的变更与移转、债的消灭.
王利明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六编(第1章至第6章)为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债的发生、债的类型、债的保全、债的转让、债的消灭.其认为,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当然,有关债权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④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当然,债法总则的设计与整个债法体系的结构是不能分开的,可以说,债法体系的构建直接决定了债法总则的体系设计和内容安排.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明确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的前提下,关于债法体系的具体安排可以考虑三种模式:一是如德日意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那样,专设债法一编,将债法的全部内容规定在债法编;二是如俄罗斯等国那样,分设两编:一编规定除了合同以外的债的内容,包括债的一般规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一编规定合同;三是鉴于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的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过于简约,不能适应侵权法的发展,需要增加条文,也可以考虑梁慧星教授提出的三编制构想,即分设三编,分别规定债法总则、合同和侵权行为,编制上前后相接,由此构成统一的债法体系.⑤柳经纬:《我国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12页.薛军认为,考虑到维持传统债法体系、采用总则-分则立法技术和变革传统债法内部结构这几重目标,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债法编的结构可作如下设计:第X编:债法总则,包括第1章:债的一般规定;第2章:合同之债的一般规定;第3章:侵权行为之债的一般规定;第4章:无因管理之债;第5章:不当得利之债.第X+1编:债法分则;第1章:各种合同;第2章:各种侵权行为.⑥薛军:《论未来中国民法典债法编的结构设计》,《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第56页.
(三)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对债法总则设计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法典体系的设计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问题的关键是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体系安排.一方面,我国《民法通则》已经确立了责任法单独成编,且该种模式的实践效应也已经得到肯定;另一方面,学界大多数学者也支持这种模式.可见,采用这种模式,并不是说要否定传统大陆民法所采方式的价值,仅仅是出于延续我国立法传统的考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我国债法总则的具体安排进行探讨,只是希望厘清关于设立债法总则问题的一些认识误区.通过分析学者们的主张,笔者发现,关于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学界有同一性说和分离说.就同一性说内部而言,又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维持传统大陆民法的体例;另一种则主张将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持同一性说观点的学者多主张设立债法总则.就分离说而言,一种主张认为,既然债的概念的中心是契约,且我国《合同法》中已经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规定,应当简化债法总则的内容;另一种主张则认为,既然债(务)与责任已然分离,那么,传统债的体系将被肢解,债法总则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就值得商榷了.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上述争议看似与债与责任的关系直接相关,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债的财产性问题认识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若债不具有财产性,那么债与责任同一性的观点即可成立,不管侵权行为是否独立成编,其均属于债的范畴,债法总则的设立也就是当然之理;若债具有财产性,那么债与责任应当分离,侵权责任法应当独立成编.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后,债法总则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就受到怀疑.
然而,债的财产性与债法总则的设立真的如此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吗?答案是否定的.该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债法总则的各项规定能否适用于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损害赔偿这几种责任承担方式(尤其是损害赔偿).如上文所言,应当将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几种责任承担方式相应地规定在物权编和人格权编中,而在侵权责任编中单独规定损害赔偿这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上文述及的关于债与侵权责任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区分与联系的观点表明,债(务)与责任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债为请求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请求权都是债.在债与责任分离的前提下,权利人要求责任人承担责任时,也是以请求权为纽带.所以,在请求权这一纽带的作用下,存在债法总则的规定适用于侵权责任中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至于侵权责任中的其他责任形式,由于其具有较浓厚的人身属性色彩,在当今法律观念下,似乎不能直接适用债法总则.只有在其他责任形式因得不到履行而转为损害赔偿时,才存在适用的余地.由此,我们应该实现债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形式主义向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兼顾的转变,在承认债与责任分离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债的形式主义,设立债法总则,责任中以损害赔偿为形式的部分准予适用债法总则.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
D923.3
A
1003-4145[2012]08-0072-05
2012-05-12
郭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刘保玉教授主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科研基金项目"中国民法典的体系设计和制度创新"(YWF-10-06-015)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