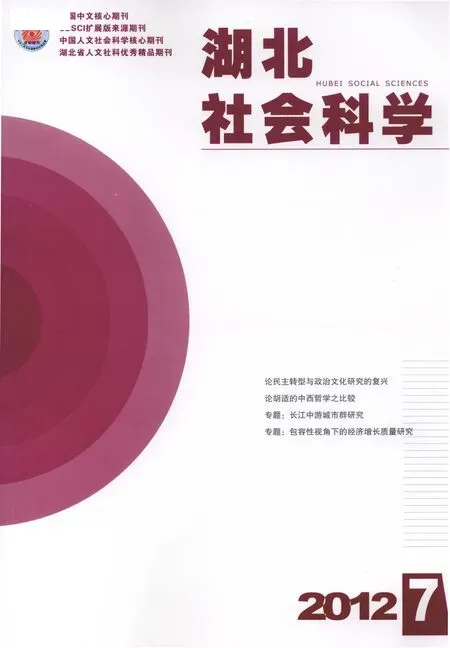杜甫“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臣”、“仙”解读
——兼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处之念
李博昊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中文系,广东 珠海 519041)
杜甫“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臣”、“仙”解读
——兼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处之念
李博昊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中文系,广东 珠海 519041)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谈及李白时用了“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语,一般认为“臣”为人称指代词,“仙”是对李白神韵的展现,此实为一种解读上的偏误,阻碍了对作者创作心理的探究。杜甫所用的“臣”和“仙”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其中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与“处”之间挣扎与徘徊的矛盾心理。
杜甫;臣;仙;解读;出处观念
一
杜甫曾在其《饮中八仙歌》中描绘李白醉饮的状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此四句被广为传诵,然对于其中“臣”字的所指,各家诗注中均未有详解。在古汉语中,“臣”主要有如下几个意思:1.君主时代官吏和百姓的统称。如《孟子·万章下》中“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2.古人表示谦卑的自称。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官吏对君主的自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杜甫“自称臣是酒中仙”中的“臣”若取“官吏对君主的自称”之意,则似与后文之“仙”不甚相符。“仙”本即超尘脱俗,不受人间万物所羁绊,又怎甘为王之吏,向王称臣,更何况杜甫创作此诗的时候的李白早已经被赐金放还?若取“古人表示谦卑的自称”之意亦不完全合理,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诗句之中很少流露出对君王的谦卑之心,且此时的他已非皇帝的官吏,称臣与之个性不合。因此,诗中的“臣”若是从李白的角度来阐释,有“百姓”之意。
李白天宝三载离开长安,《新唐书·李白传》记,“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狂放不羁的李白终究没有抵挡住小人的诋毁,远离了朝廷。李白虽然傲岸,却并非超现实的人物,此时的他,感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饱含“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忧愤,但他又以“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来安慰自己,表达出“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于酒中归隐的心态。这既是一种逃避,同时也带有一种抗争的勇气。“李白在长安受到谗谤而被玄宗疏远,‘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敞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李阳冰《革堂集序》,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连当时的‘朝列’都对李白的真实心情有所理解,作诗‘言公之不得意’,难道在数年以前曾与离京后的李白交游甚且相知甚深的杜甫反倒会对李白“浪迹纵洒,以自昏秽”的动机毫无觉察?”[1](p80)程千帆在其《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一文中也谈到,《饮中八仙歌》并非是反映盛唐诗人共有的“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而是展现了当时意欲有所作为却被迫无所作为,不得已而沉湎于醉乡的“饮中八仙”的情态。杜甫面对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怀着错愕与怅惋的心情,睁着一双醒眼客观地记录了八个醉人的病态。[2]“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现,而且杜甫对此是有所理解的”,[1](p79)他们“借酒浇愁的状态,恰恰表达了在唐代社会从强盛转向衰弱、唐王朝的政治开始腐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表现……尽管这八个醉汉当时喝得醉醺醺的,尽管他们心中有忧愁,有愤懑,有牢骚,但是他们并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变迁,也没有像杜甫这样非常清醒地观察社会。而杜甫与他们不同,杜甫进入长安以后就开始清醒地观察社会,他以这种心态、这种眼光来看待李白等人,来分析他们,所以这八个人的醉醺醺的状态是在一个清醒的诗人的眼光中反映出来”[3](p155-156)
在杜甫看来,李白沉醉酒乡,实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于人世间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尧舜,看不起孔丘,是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他说他不能‘摧眉折腰’事奉权贵,是因为自己‘不得开心颜’。”[4](p36)故其沉醉于酒乡,在酒中养“仙”之气,虽为市井酒徒,却具有着仙家超凡的气质。“仙”是杜甫对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理想破灭后,意欲做隐士神仙的出世心态的较为准确的揣摩,李白“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同柳永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异形而同质。
二
文学作品往往折射出创作者内心最细腻的情感,杜甫虽然是在描摹李白的醉态,但已在不自觉中渗入了个人的主观意识。这一“臣”一“仙”不仅是杜甫对于李白的理解,其中亦流露出杜甫的某种隐幽心绪。对于杜甫而言,“臣”即是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官吏,这是杜甫内心社会责任感的投影,而“仙”则是他心底出世愿望的反映。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可从此诗的创作时间和李杜之间的交游入手。
关于《饮中八仙歌》创作时间,“最早出现的杜甫年谱就是“九家注”中引的蔡兴宗谱,认为这首诗是天宝五载写的,也就是746年,杜甫到长安的第一年,那一年杜甫35岁。编得最晚的是梁权道谱,见于黄鹤本,也就是黄鹤的编年,他认为是天宝十五载,也就是756年,那一年杜甫45岁。浦起龙是编在中间,他认为是在天宝五载到天宝十三载这一段时期内写的,不能确定是哪一年。现代的学者有两种编年:一种是四川省文史馆编的杜甫年谱,该年谱认为是天宝三载,比较早,744年就写了;一种是已故的杜诗专家萧涤非先生的看法,萧涤非先生说是到长安的头一二年,大概是天宝五载或天宝六载,也就是杜甫进入长安的前两年……萧涤非的说法现在已经为大多数的杜甫研究者以及杜诗注家所采用,大多数人都认为萧涤非的编年是对的,就是杜甫到长安的头一两年。”[3](p139)陈贻欣也认为“这诗最早也必作于天宝五载四月以后”,[5](p137)程千帆则认为,“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应该往后推一些,它不可能是杜甫刚到长安时写的。杜甫刚到长安时还有雄心壮志,还没有遭受生活的折磨,经济上也还没有捉襟见肘,他还不会有这样的认识。这首诗一定是杜甫在长安过了几年以后写的,因为在长安生活了几年以后,杜甫的生活越来越困顿,个人前途已经无望,他也逐渐观察到大唐王朝的各种社会弊端,觉得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暗了,盛世快要过去,动乱快要来了。在这个时候,杜甫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来。”[3](p156)但“杜甫这首《饮中八仙歌》不管是在天宝五载还是稍晚一些时候写的,反正他写这首诗时已经与李白有过交游。”[3](p152)
杜甫与李白在公元744年相遇,在李白身上,杜甫“看见了游侠,他也亲自去求仙访道。这在他的一生里是一段插曲。也许正因为他这时的生活没有出路,同时对于社会的现实也还缺乏认识,他在他送给李白的第一首诗里便有一大套道家的术语,而且还和李白约定一起到梁州(开封)宋州一带去采折瑶草。他随即和李白渡过浪涛汹涌的黄河,到了王屋山。这座山在山西阳城和河南济源的中间,当时是一个道家的圣地。他们走到山上的小有清虚洞天,去参拜道士华盖君,可是到了那里,华盖君已经死去。”[4](p38)后来二人短暂分别,公元745年再次相遇,此时杜甫写下了《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曾“五岳寻仙不辞远”,然求仙之理想终究未成,杜甫此作既表达出对于李白求仙不得的遗憾,亦含有自身未遇仙家的惆怅,“飞扬跋扈为谁雄”在伤李白之时,同样有着深深的自伤。后“他和李白—起走入东蒙山访问道士董炼师和元逸人;他们白天携手同行,醉时共被酣睡……他们有时走出兖州的北门,到荒陂漫野中寻访他们共同的友人范隐士,在那里任情谈笑……”[4](p43)这是杜甫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欢畅时光,虽然兖州分别后二人再也未曾相见,但“一往情深的杜甫,后来无论是在长安的书斋,或在秦州的客舍,或是在成都和夔州,都有思念李白的诗写出来,而且思念的情绪一次比一次迫切……”[4](p44)这种思念,不仅是对一段自由生活的追忆,更是对李白潇洒人格的追慕。李白在酒中寻找到了心灵上的些许宁静,“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杜甫未能达到李白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与李白一同求仙访道之举,其《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均表达出对于官场勾心斗角生活的厌倦,对于李白潇洒追仙之举的羡慕。
但作为一个出生在世业儒学的家庭之中的封建士子,杜甫从小即怀有济苍生的远大抱负。在杜甫与李白交游之时,他已对唐王朝的政治情况充满了忧虑,其晚年写有《昔游》,其中有言“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表达出对安禄山、对东北边境形势的担忧。虽然他对朝廷的统治现状多有不满,愤懑忧郁,但他所受到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使他终究不能完全如李白一般在酒中寻得片刻之安宁,“臣”是杜甫的社会角色,是他一生内心中永远无法摆脱的责任与使命。而“仙”或是他在无力承受外界令人极度失望的社会环境之时,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一个愿望。
杜甫曾写下“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晨溪向虚駃,归径行已昨。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虽悲鬒发变,未忧筋力弱。扶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追忆当年访华盖君而不得的场景,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惆怅。他深深体会到身陷官场囹圄的痛苦,对于能舍弃世间一切的人,他饱含敬佩。杜甫作有《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巢父此去意欲求仙访道,对此,杜甫充满了羡慕之情却无法效仿。因此,杜甫也常耽溺于酒,郭沫若曾在《李白与杜甫》中对于李杜饮酒之作做了统计,在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多首中,言饮酒的共有三百多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说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以上数字似乎表明杜甫更愿意沉醉在酒中以忘却世事的纷繁,做李白式的“酒中仙”成为他潜在的一种意识。然较之李白,杜甫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更为深沉,对朝廷称臣的心态更为虔诚,求仙的愿望也更为强烈,出世与避世相互纠结的心态亦显得格外复杂。或许对他来说,在酒中求仙都是一种人生奢求。
三
杜甫的心态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在仕或隐两种生命形态之间的艰难抉择。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子》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在封建社会,士子们的命运就如东方朔《答客难》中所说的那样,“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然东方朔尚可在用与不用之间寻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史记·滑稽列传》载:“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而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种隐于朝的心态是后世许多文人在进与退中所选择的一种折中的生活方式,白居易有《中隐》诗,言“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同样表达了在出处间寻求平衡的心态。但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说的“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或许说明朝隐的方式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理想破灭的落寞心绪,对于一些不满社会现状的耿介知识分子来说,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朝隐亦为难以承受之痛。因此,陶渊明所创造的桃花源才成为了后世文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归宿,虽然他们内心深处清楚桃花源的虚幻性,但他们宁愿相信桃花源的存在,那是他们在遭受生活打压后最后的心灵港湾。纵然在世上寻不到真正的桃花源,他们仍愿意找寻一方类似的土地。韩愈有《送李愿归盘谷序》,其中倾吐了他劳苦奔波十余年而始终不受重用的愤慨,对于李愿“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生活方式充满了羡慕之心,感慨“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愿“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但韩愈少即有读书经世之志,这种家国理想最终超越了他追寻个人内心安定的一己之怀,他始终没有走下天子之堂而成为田舍之郎。虽然“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纵然前有上蔡之犬与华亭之鹤的悲剧,也不能阻止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国为民而前进的脚步。屈原有“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王逸曾言“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神明,而为谗邪所蔽,进退不可,惟博采众善以自处而已。”然“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其纵有“去国远游”、“独善其身”之念,但内心深处的责任感终究让他为国而殒身。贾谊感慨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社会环境中,他用“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这种心隐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然洒脱而超然的外在之下,是他内心的颠沛与迷惘,他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前途渺茫而忧虑,恬静的文字中流淌着深沉的悲怆。这或许说明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讲,真隐只是不可求的一种人生理想。
“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是杜甫一生难以割舍的一种情愫。对他而言,效命国家始终是最高的人生理想。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在他的身上不能得到真正的实践,“朝隐”的生活方式亦不能满足他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定位,他更不能舍下苍生安心去找寻桃花源。杜甫内心所背负的社会责任感与个人独立人格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其精神世界之中,在其颂扬李白的“臣”与“仙”两个字之中得到了体现,透过这简单的文字,一个情感丰富而细腻的杜工部清晰地呈现在了后世读者的眼前,而他的身上,正凸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与良心。
[1]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J].中国社会科学,1984,(5).
[3]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冯至.杜甫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5]陈贻欣.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I207.22
A
1003-8477(2012)07-0129-03
李博昊(1982—),女,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基金资助项目。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百人工程”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