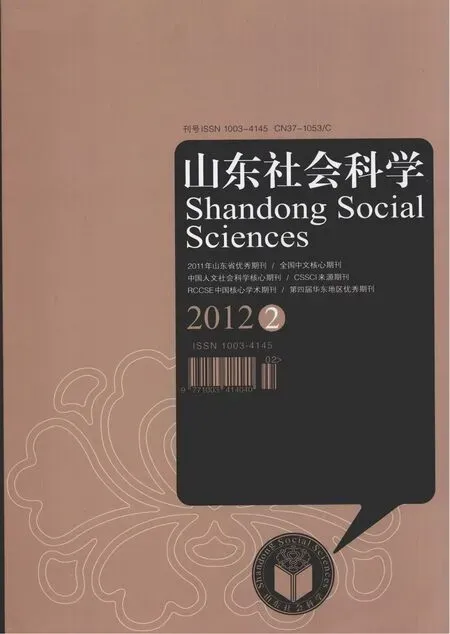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的冲突与融合
——以几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
孙俊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的冲突与融合
——以几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
孙俊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现代化一方面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它与构建我们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又往往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造成了知识分子心理上的两种焦虑:现代化的焦虑与民族认同的焦虑。这两方面在不同题材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概括说,作家在改革文学中更多地表达了现代化的焦虑,并呈现出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认识趋向;而乡村小说更多地附加了民族认同的情感。这使改革与乡村的文学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现代化;民族认同;改革文学;乡村小说
现代化和民族认同问题是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命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追根溯源,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从精神层面来看,可以说它凸显了知识分子心理上这样的两种焦虑:现代化的焦虑和民族认同的焦虑。一方面,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相比自身落后的状况和危机,认识到现代化的迫切性,更明确地将工业经济的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现代化与构建我们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又往往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民族认同感必然来自于在共同的民族历史中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其中主要是儒家文化,它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风俗习性等在几千年的承传过程中早已沉潜为我们的无意识,内化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民族精神的体认,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它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俞祖华:《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也正基于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的焦点,其他一切文化与文化史问题的讨论都是以这一问题为中轴而展开的”②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作家们以其创作参与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此,我们通过几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识,既可以看到伴随现代化进程作家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可见出由于文化立场的不同,作家以不同的题材空间承载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
一、改革进程中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
最突出地表现了现代化在中国新时期的进程及其带来的美好前景的莫过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几部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无论《沉重的翅膀》、《都市风流》、《骚动之秋》、《抉择》还是《英雄时代》、《湖光山色》,它们都与社会生活同步,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和必然性。其中,《沉重的翅膀》和《英雄时代》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文本。这种代表性就在于它们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和态度,映现了作家在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促进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深刻关联认识的不断深化。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中国进行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建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家以磅礴的激情写出了改革初始新与旧、文明与愚昧、改革与守旧、解放与僵化的种种冲突,在根本上演绎的是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阻滞力。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书写的则是党的十五大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此时,市场经济尚未健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国企亏损,下岗,贫富差距,私营经济成为富有活力的一支力量,其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它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对于现代化的补益作用。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除了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也必然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现代化的精神基石,这是《英雄时代》中表现出的文化取向。《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和《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代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他们矢志不渝的目标。由于处于不同的改革阶段,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特色表现在,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与情感伦理困境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沉重的翅膀》中,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摆脱贫困、吃大锅饭的状态是彼时最紧迫的任务。作品通过“小”字辈的激情与活力,通过老一辈如李瑞林等人的思想转变展现了现代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历史必然性。郑子云作为“改革派的一个亡命徒”,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传统文化惰性造成的反对改革的僵化、守旧的观念,如小说中所说的“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对田守诚等人的深刻影响,他为保权、保位子,处心积虑,小心翼翼,无所作为,不敢作为,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形成的反改革的“圈子”,他们视支持改革的人为异类而加以排挤。作为现代化代表的郑子云,作家在描写他与反改革派进行斗争时,也写出了他自身承袭的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负,以及这种重负对他精神造成的戕害和痛苦。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上。他虽然是个现代化的先锋,却没有勇气挣脱与妻子夏竹筠的没有爱的婚姻,只能维持着虚无的“模范家庭”的称号。虽然在小说中,作家也着力表现了郑子云的忧患意识、担当意识,写了普通工人、群众之间的友爱互助等传统优秀品质,但在根本上,作品所倾力揭示的,依然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那种深重的阻滞力量,甚至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的优秀品质时,也很难说从理性上意识到了它们和传统文化有什么关联。
时代发展到90年代后期,《英雄时代》中史天雄在其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已经不必去承受传统婚姻伦理的枷锁。小说中的主要矛盾冲突来自于他和陆承伟之间,这是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奉献的精神、仁爱的精神为精神基石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陆承伟最后的自我救赎则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皈依。
在史天雄所探索的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成为他所秉持的重要精神价值。首先,史天雄本人是一个极富儒家文化精神品质的人。他和郑子云一样具有忧患意识、担当意识、责任意识。王传志说他“身在江湖,心系庙堂”的话语里虽然透着一丝凉意,却也是对史天雄的一种恳切评价。“国家利益”是他一切行为的准则,无论是初始的想挽救红太阳集团、加盟“都得利”,还是最终听从党的安排去领导合并后的红太阳和天宇,他从未考虑丝毫个人的得失。史天雄所领导的“都得利”集团,作为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板,也是充满了仁爱精神的团体。它最初的创立就是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个再就业的机会,在这个集团里,不仅全体员工真心地为抗洪救灾捐款,而且作为个人,还有王小丽、杨世光、江榕、毛小妹等人充满纯朴“仁义”精神的作为。“都得利”体现着一种集体的精神、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正如它的经营理念:“与全市人民共渡难关”。如果说,这就是史天雄所探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具有的现代精神品质,那么这种现代精神品质是不是可以称为儒家文化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呢?
这种精神品质在《英雄时代》中可以说是作家有意加以表现的,这从史天雄对陆承业与陆承伟的不同态度即可见出。史天雄虽然对陆承业的顽固、刚愎自负以及家企同构观念进行了批判,却借梅丰之口对他以国有资产为重、不推卸责任的国家意识、奉献意识表达了敬意。而作为史天雄主要的对手,陆承伟可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代表。陆承伟曾在美国哈佛工商学院读MBA,受到西方的教育,回国后投身商界,“在美国学到了务实精神”,也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英雄时代》中展示了陆承伟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化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如个人利益至上、金钱至上造成的道德堕落、自私自利、无国家意识,为私利挖社会主义墙角。这种现代化与史天雄所领导的“都得利”集团的价值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更显示出对传统文化中优秀价值品质的认同,也是对构成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的认同。
从《沉重的翅膀》到《英雄时代》,从单纯的现代化建设到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勾画出改革者筚路蓝缕、不断探索的改革实践,既是现实的社会发展,也传递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再认识。
二、乡村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流连和困惑
总体来看,在改革文学中,现代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沉重的翅膀》等80年代的改革题材的小说中。这与当时文化启蒙者二元思维的影响有关,也就是把传统与现代作为两个对立的因素,西方现代的是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中国传统的则是保守的,应该否定。改革文学中所设置的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这种二元思维的制约下形成的。改革文学是以现代化作为总体价值旨归,以之观照传统文化,取我所需,而一切阻碍现代化发展的都被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抛弃。他们的主人公精神灵魂的力量足够强大、信仰足够坚定,在现代化生活所展现的五光十色之中才不会自我迷失。郑子云和史天雄及其他改革领导人物从来没有过犹疑、徘徊,没有过灵魂的上下求索,他们所做的只是站在现代化的基点上,认准了方向,向前、向前。然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现代化在带给人丰富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使人感受到目迷五色的炫惑,传统的维系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四分五裂,丧失终极意义,连同我们的民族认同的迷惑。于是,我们又到历史中去追寻、去挖掘,在现实中仔细辨认那些构筑我们精神心灵的根系。乡土、乡村或者民间成为灵魂漂泊的最后锚地。
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便是这样的两个文本。《白鹿原》问世于1993年,我们当然无法忘怀此时文化界对于传统文化的各种再认识、再思考的成果。“与‘寻根’文学一样,它也体现了发掘传统资源以探求民族精神、重续文化命脉的努力:而与‘寻根’文学否定‘中原规范’的倾向不同,它要寻求的恰恰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规范’中隐藏的生命活力。”①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秦腔》是贾平凹有感于自己无奈的离根体验,曾经魂牵梦绕的淳朴的故乡的人与事、风土人情在现代化风卷残叶般的进程中都已难觅其踪,通过对传统乡土文化衰落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艺术把握为传统文化谱写的一曲挽歌。
如果叙事视角部分地决定了作家对于事件的态度和认识,讲故事的方式也暗含了对故事的阐释,那么,我们近乎可以说,改革文学是以现代化的视角来书写的社会进程,因此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阻滞因素,而现代化是光明与美好的一种现实许诺。《白鹿原》和《秦腔》则更多地倾向于传统文化的角度,书写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挤压下的衰落、困惑以及它顽强的生命力。由于这种角度的不同、文化立场的不同,《白鹿原》与《秦腔》所看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呈现出与改革文学中不同的另一番情景。对农业文明中的传统伦理感情、对人际关系中脉脉含情的一面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对于现代化,虽然理性上认识到它的必然趋势,却更多地倾向于它所带来的弊端的书写。
《白鹿原》和《秦腔》都书写了儒家文化传统所濡染的精神人格魅力。
《白鹿原》中贯穿始终并集聚了作家最多情感的人物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传统在民间民众中的体现者,是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真诚地信仰并恪守儒家的行为规范准则。他以传统宗法制度治理白鹿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三纲五常”组织家族世俗生活、规范行为、凝聚人心、解决争端,担负起为家族谋利益的责任。考察白嘉轩一生所为,修祠堂,办学堂,为防白狼筑堡墙,刻《乡约》,策动“交农”,率众求雨,“刺刷”小娥和孝文,修镇妖塔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多次以德报怨营救“仇人”(黑娃、鹿子霖及闹农协时曾伤害过他的那些人等),体现了儒家文化传统中重义轻利、仁爱谦恭、注重修身治家等传统道德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力量使“白的一身,仿佛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的象征,他的顽健表明,封建社会维系几千年之秘密,就在于有像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的支撑”②雷达:《一九九三年的“长篇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作家对于白嘉轩无疑倾注了深厚的爱敬感情。其他如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黑娃对传统文化的皈依等都表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倾心。
同样,《秦腔》通过引生的视角与讲述也表达了贾平凹对儒家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夏天义、夏天智及白雪等人的向往和爱。夏天义和夏天智是引生最为尊敬的两个人,他们身上有着白嘉轩和朱先生的影子。他们都是执著于传统耕读文化的人,夏天义对土地的热爱最突出地表现了传统耕读文化中人与土地的关系。虽然在夏天义和夏天智身上多了现代社会的因素。如夏天义把党、集体、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夏天智也已不可能是私塾先生或者如朱先生置周围的纷争于身外,而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这种外在的现代因素并没有改变他们在内在的思想情感、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文化特征。他们注重自身德性的完善,对于村人都表现出一种“仁义”之心:如夏天义的清廉自守、热心村务,夏天智以其德望热心解决邻里家庭纠纷、乐善好施、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学、对病中的秦安给予关心与安慰。同时,他们还极为注重家庭伦理关系。夏天义与夏天智几个兄弟妯娌之间一直其乐融融、相互帮扶,呈现着传统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都是传统耕读文化所孕育的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理在现代乡村无序的底色上显得尤为可亲与珍贵,而引生对于白雪的痴爱更是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那种精神皈依。
如果说《白鹿原》有意识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的生命活力的话,那么《秦腔》中“矛盾和痛苦”、“迷惘和辛酸”的复杂情感,则来自于贾平凹对传统人伦情理和人格的流连,看到了它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记忆中的陈迹。作者看到现代化在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带给乡村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在丢弃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东西。在引生所述说的清风街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吃喝拉撒睡中,几乎没有使人快慰的事,被人看做“十全十美”的婚姻中,有的只是不和谐、隔膜、争吵,最后分手;唯一的新生,带来的却并非欢欣而是痛苦;能够记起一年中发生的五大“恶”的案件,却没有述说一件喜乐之事。这种对事件的选择本身就已表明了对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然而,无论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具有怎样使人敬慕或赞扬的品质,具有怎样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它却始终处于历史现代化进程的边缘状态,没有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无论是闹农协、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还是中国内战,所有这些历史的大事件对于白嘉轩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所采取的都是一种“反身而诚求于己”的内敛、冷眼旁观的姿态。甚至他也从未产生朱先生那样的抗日情绪。他惩罚异己的方式更多地是将他们驱逐出去,却不能够审时度势,使自身更具包容性。那么它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历史进程中又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如果它并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那就必然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如雷达所说:“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①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同样的困惑也表现在《秦腔》之中。“人是土命,土地是不亏人的,只要你下了功夫肯定会回报的”,但这种回报却没能使人摆脱贫穷,夏天义对现代化的拒绝与阻碍行为遭到了子孙辈的抱怨。当庆金只能卖血给父亲治病、瞎瞎因无钱上交税款被抓走时,夏天义的几个儿子之间为了赡养老人而不断发生的矛盾争吵、锱铢必较,也许并非完全是道德的滑坡,更是缘于经济的贫困。极度的贫困使人心胸狭隘、情感变异。夏天义与夏天智的“仁义”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那么,“实”与“足”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丰富却并没有必然地附带着人情物理的美好,却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欲望的无限膨胀……如同年三十的团聚这一最具家族认同之感的传统风俗,在后辈眼中也已失去了意义一样,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冲击着传统文化,消弥着民族认同的根基。
这种困惑矛盾正是由于作家无法找到解决现代化与民族认同之间矛盾的一种外在表现。
三、两种题材小说不同的文化承载
改革小说中的现代化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所表现的改革是激情的、振奋的、向上的,是全民投入的。在其中,大多数主人公都充满了一种内心的躁动,很少有对日常生活琐事的精雕细刻和品味。这种躁动是一种时代的情绪,驱使他们去把握机遇、拼搏进取,最大限度实现生命的价值,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因为改革正是民族强大的社会需求,可以说,改革小说最为充分地表现了作家的也是民族的现代化的焦虑。
而现代化焦虑和民族认同的焦虑必然内在地纠缠在一起。现代化依凭其强势的西方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它的对话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西方文化以及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映照出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端,一方面又对形成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传统伦理道德、固有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人为中心的启蒙理性在重现人的价值、尊严之时,也给人的精神信仰带来了危机,追求物质的享受给人带来舒适也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拜金主义使社会道德堕落,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欲望都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不能不问:构建我们精神、情感、心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该何去何从。贾平凹说:“在社会巨变时期,城市如果出现不好的东西,我还能回到家乡去,那里好像是一块净土,但现在我不能回去了,回去后发现农村里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城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这种现状,就让人想回家,却回不去了”。①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化的对话》,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之感,正是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面前无可挽回的衰落造成自我身份迷失的表现。
我们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有着天然的本质的联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中国”的概念随着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的出版,成为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性质的一种经典概括。乡土不仅指向几千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农业本位思想和家族意识外化的精神坐标。在这片广褒的乡土上,诞生了中国古老而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天人合一、农业本位、家族意识、仁义礼智信……它的核心观念对于整合社会秩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下来。它曾经是我们的骄傲,曾几何时,又被看做现代化的羁縻负累。而乡土,作为诞生古老文明的母亲,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却始终具有“原乡”的性质,是割不断的根、摆不脱的梦魅。正如白嘉轩所说:“无论是谁,只要生在原上,他就得返回原上来。”尽管白孝文认为:“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回来是另外一码事”,回来即意味着“原”在心底的存在,因为它所携带的文化是人们身份认同的凭依,它不仅使人更深地认识自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认识到自身的归属——民族与国家。
正是因为这种乡土所孕育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是灵魂的“锚地”,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据,作家将民族认同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突出地表现在乡土文学叙事之中。
我们在《白鹿原》与《秦腔》中看到了这种冲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更借少数民族的山林文化,以山林文化与现代化相对照,以年届九旬、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讲述,更为明显地表现了现代化和民族认同的双重焦虑。对这个民族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和反思。众多的死亡故事,严寒、瘟疫、猛兽侵害下举步唯艰的传统生活方式,舒缓而深情的讲述、偏执的固守之间的矛盾张力彰显的是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民族认同的需求之间难以两全的价值评价悬置,为了民族更好地生存,需要进行现代化,而现代化却使传统民族文化更趋式微,依莲娜徘徊往返于城市与山林之间、痛苦与迷惘地游走于现代与民族文化之间、最终导致自杀的悲剧更显示了这种双重焦虑的无法偏至。
在潜在的现代化坐标中,作家对乡村所代表的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追慕、批判或者哀悼,是民族认同的精神需要,更是作家在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对本民族特性的反思和对其优质一面的弘扬,承担着“旧邦”如何更好地“维新”的现实思考。“旧邦维新”暗合了民族认同与现代化的融合。
当白嘉轩充满信心地宣称:“无论是谁,只要生在原上,他就得返回原上来。”他又怎么可能意识到孝文的返回更是一种反叛者的挑战呢。当孝文成了社会的主角,运用计谋将早已皈依儒家传统、立志“学为好人”的黑娃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并枪决时,白嘉轩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与文化人格也被现代化宣判了死刑。而代表儒家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朱先生与逃离封建家庭进行革命的白灵同样都是白鹿精灵的启示,是否又表现了作家认为只有将传统儒家的优质因素与现代化的优秀品质相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代表幸福、祥和的白鹿精魂呢?夏风与白雪所生的女孩具有先天的残疾,必须经过大的手术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人,也让人想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因素能够被现代化吸收、融合从而产生一个现代的“宁馨儿”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夏天义和夏天智死去了,传统文化似乎已随着它的代表人物的死去而土崩瓦解,但毁灭也意味着新生。引生等待夏风回来,这又使人生出了一种期望。当夏风再次归来概括自己父辈一生的是非功过,无疑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对传统的父辈更多一些“温情的敬意”,更多地体认到父辈身上闪光的品格,体认到自己与脚下这块土地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永远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
I206
A
1003-4145[2012]02-0089-05
2011-11-30
孙俊杰(1973—),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