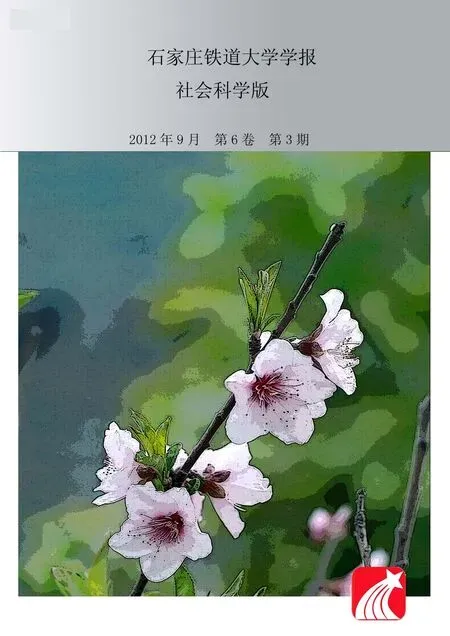沈从文与聂绀弩“评议鲁迅”探微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256603)
一、“评议鲁迅”始终
抗战开始后,沈从文颠沛流离到昆明,受聘西南联大。因为讲授“习作”课的需要,他对五四以来的很多作家进行了评点。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上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对周氏兄弟的为人与为文进行了比较。就为人来说,他认为,周作人“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鲁迅则“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就为文来说,他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 ;鲁迅的杂文“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从一直坚守的京派文学观念出发,即使周作人已经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正式“落水”,沈从文依然如此盛赞他的为人和为文,可见其为人的执拗迂腐。这让读者已经很难接受了,再加上他鲜明的贬抑鲁迅的倾向,引起尊崇鲁迅的读者的反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在桂林的聂绀弩就是其中之一,读了沈从文的文章后,他写了《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注:刊1940年12月1日的《野草》月刊)。沈从文对鲁迅及其杂文的看法,聂绀弩是非常反对的。但他的反驳方式很鲁迅化,不是自己条分缕析逐一议论评述,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段落,以鲁迅之矛予以反击,呈现出他特有的俏皮风格。
譬如针对沈从文所说的鲁迅的“憎恨”,聂绀弩先引用了鲁迅1935年针对沈从文而写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1]然后议论说:“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何以如此?他认为,“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荡开笔墨:“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所当爱。”[2]63-66
文章最后,聂绀弩概括说:“我们常常说: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史。”[2]66-67交代了鲁迅文章的写作背景,摆明了鲁迅“骂世”、“冷嘲”、“憎恨”的现实基础。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聂绀弩的这段话,是理解鲁迅的“骂世”、“冷嘲”和“憎恨”的钥匙。
聂绀弩的文章,沈从文也许当时并没有看到。但是,1947年11月,鲁迅逝世11周年之际,沈从文以他特有的小说家的敏感对鲁迅做了新的阐释,对鲁迅的文学史贡献从古籍整理、杂文、小说3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评价。他认为,鲁迅“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能把握大处”;鲁迅的杂文,“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就小说而言,他认为,鲁迅是乡土文学的领路者,使“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20年文学主流。”[3]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鲁迅杂文“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的认识,恰恰照应了聂绀弩的文字。更难得的是,至于鲁迅的为人,当时许多人以为他“偏狭”,沈从文却在说他“愤激”、“骂世”的同时,又洞察了其“诚恳”和“素朴无华”的一面。这是沈从文超越自我情绪、超越一般读者的深刻见解。
二、沈从文抑鲁扬周的原因
鲁迅与沈从文相差不到20岁,沈从文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是1925年,鲁迅去世是1936年,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见面的。但,他们竟然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有很深的过节。这根源于一场误会。
1925年的4月,在北平走投无路的丁玲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鲁迅相信了当时正在他家的孙伏园(注:一说荆有麟)的判断,以为是休芸芸(注:即沈从文)冒名女性给他写信,很生气。之后,他在给钱玄同的信里,以挖苦的口吻提到沈从文。1928年初丁玲走红文坛后,鲁迅知道了真相,曾说,真有丁玲这么一个人,我还真错怪了她。事实上,鲁迅错怪的不是丁玲,而是沈从文。但他没有就此向沈从文道歉或者是表示一种遗憾。
沈从文与鲁迅关系不睦,与政治思想、艺术观念的不同有关,更与这次误解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有关。因为这对于年轻的沈从文来说是非常巨大地打击,所以在以后的文章里,他不止一次提及这个事情。比如1931年胡也频遇难,他写了《记胡也频》。在谈到这件事情说,我们三个人(注:指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当时的字迹比较一样,其中丁玲给一个叫做自以为聪明的人写了一封信,而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还以为是我写的。[4]
正因如此,新文学作家中,沈从文评论最多的就是鲁迅,篇幅最大,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最为复杂。吴投文先生认为,对逝世前的鲁迅,沈从文一直是平视的,虽然他的年龄小鲁迅很多,走上文坛的时间也晚很多。不过,他具有批评家与读者的双重角色。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对文学家鲁迅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包括其早期诗歌创作)持基本肯定态度,眼光独具而又不失公允。作为一般读者的沈从文,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和作为战士的鲁迅的杂文创作和人格气度持基本否定态度,常见尖刻的嘲笑与辛辣的讽刺。[5]75
也就是说,呈现在沈从文视域中的是一个分裂扭曲和充满矛盾的鲁迅形象,所以如此,是因为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是从他特有的标举独立与纯正的文艺观出发的。这使他能敏锐准确地把握鲁迅作品,尤其是小说与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复杂的审美意蕴,也使他厌弃鲁迅在杂文中显现的斗士型的人格气度和思想锋芒,从而消解了鲁迅惯有的现实战斗精神。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妥的。因为“完整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乃至战士同时出现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5]75
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使沈从文对鲁迅有了更深的成见。鲁迅编《小说二集》,在序言里面提到乡土文学,也把沈从文归为乡土文学作家,但是他没有选沈从文的哪怕一篇作品。而1935年的沈从文已经名满天下了,前一年发表的《边城》使他成为了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设想一经提出,沈从文就认为这是“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并说将这部书介绍给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6]
没有选沈从文的作品,主要原因恐怕是鲁迅不认同沈从文的作品。但是,两个人的矛盾影响了选本编选的可能是存在的。1935年11月,沈从文写了《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书评,没有谈及自己的作品是否应该入选,但认为鲁迅的选本“有抑彼扬此处”,“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特别点明未选入王统照等几人的作品,对沉钟社、莽原社的评价过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共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和郑伯奇编选。茅盾编的《小说一集》,收文学研究会29名作家的58篇作品,其中有王统照的《遗音》《一栏之隔》《技术》《车中》4篇。因此,沈从文指责鲁迅没有选入王统照的作品该是纰漏,但他所说的“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7]却不能不说是事实。鲁迅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情的激进主义者,所以他在《小说二集》中选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33名作家的62篇作品,大多都是缓缓道来,在不经意间把对社会的憎恶注入读者的体内,具有冷静中富于激情的特点。其中,浅草——沉钟社有8个作家的作品被选入,是选入作品最多的文学团体。
我们不能怀疑鲁迅的公正,但他选的作品,许多已被研究者淡忘,沈从文的作品却越来越被大家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鲁迅编选的原则、标准和方式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疑问。去世之前,在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鲁迅曾将沈从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作家”之列。“最好作家”之一的作品却没有体现在编选的作品里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鲁迅去世以后,沈从文对他的看法逐渐有了变化。于是有了《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的周氏兄弟比较,有了1947年的《学鲁迅》。这是沈从文第一次非常客观的评价他所认识的鲁迅的成功和伟大,虽然还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
与对鲁迅不同,沈从文对周作人是由衷的钦敬,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如“秋水”般的性格,甚至巴金在小说《沉落》中对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有所影射,沈从文就认为巴金火气太大,“过分偏持,不能容物”,与之通过几封长信为周作人辩护。
日常言行中如此,文学创作中亦然。沈从文反对闲适、幽默的小品文,但又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大登周作人的小品文,并为之叫好。1934年,沈从文的《论冯文炳》对周作人最得意的弟子废名进行了评论。文章开头,沈从文就对周作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概括: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8]96进而认为周作人的所有文字,无论是小品、散文诗、介绍评论,还是翻译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腊故事,与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学,都能“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上来,那么非常贴近人们的情感。”并预言他的文章,“因为文体的美丽,最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仍然不会容易使世人忘却,而成为历史的一种原型,那是无疑的” 。[8]96
沈从文自视甚高,很少激赏人。如此推崇周作人,是因为他与周作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更是因为周作人为人宽容、谦和,在平淡中至情尽礼、超然淡泊、节制内敛、与世无争,被崇拜陶渊明的京派诸人,包括沈从文,认为是“活着的陶渊明”。
三、聂绀弩维护鲁迅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积极宣传抗日,聂绀弩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的监狱里关押了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并于1933年7月回到上海,旋即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了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一员。第二年 3月,他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分歧日深,所以报上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便创办了该报副刊“动向”,任主编,并请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叶紫任助编,使之很快成为了继《申报·自由谈》之后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的又一块重要阵地,在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鲁迅的赏识和器重,两人书信交往频繁不说,仅1934年鲁迅就曾两次邀约聂氏夫妇在梁园吃饭。
聂绀弩主编《动向》期间,鲁迅在该刊先后发表了23篇杂文,包括《拿来主义》、《骂杀与捧杀》等名篇。1936年初,聂绀弩和胡风等创办文学杂志《海燕》,鲁迅继续给予最大的支持,亲自题写了刊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出关》和《“题未定”草(六至七)》,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3篇文章。为了支持《动向》,鲁迅除了自己不断撰稿外,还推荐了颇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徐诗荃的杂文。
鲁迅器重、支持聂绀弩,聂绀弩则非常敬仰尊崇鲁迅。“两个口号”论争期间,聂绀弩最早表态拥护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鲁迅犀利深刻的杂文,聂绀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后来回忆说,鲁迅的“杂文至少很难再有了。然而这并不排斥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后辈景仰他,学习他,学习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杂文,乃至模仿他的笔调之类。我就是学习乃至仿效鲁迅杂文的一个。”他还说,我“这样一个人,虽然曾经爱好、学习、甚至模仿鲁迅的杂文,但无论内容和形式,其不会相像,毫无是处,相隔十万八千里,那是十分自然的。”[9]
鲁迅影响了聂绀弩的创作,更影响了聂绀弩的精神气质。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后来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难怪当时的人们誉其为“鲁迅派”了。夏衍曾说:“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他写杂文不拘一格,不陷于一个程式,绝对不八股,真是多彩多姿。”[1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后,聂绀弩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琐碎而危险的工作中,并和胡风、巴金等16人为他们尊敬的鲁迅先生启灵、安葬、送棺、抬棺入穴。在悲痛与操劳中,聂绀弩还写下了悼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表达了失去领路人的深沉忧伤与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后来黄源编辑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时,将该诗放在了首页。40多年后,钟敬文还说:“恕我狂妄,我始终认为在数量不少的追悼鲁翁的诗篇中,它是值得反复吟诵的一篇。”[11]
除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聂绀弩当时还写有散文《关于哀悼鲁迅先生》,记述鲁迅丧葬的盛况。此后,他还陆陆续续写过许多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聂绀弩已经78岁了,还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撰写了总题为《为鲁迅先生百岁诞辰而歌》的10题21首诗歌。
令人感叹的是,对于“评议鲁迅”的辩驳,聂绀弩“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之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12]他曾如许称赞沈从文:“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13]而在谈到朋友喜欢自己的作品不尽一致时,沈从文把聂绀弩列在了很熟悉的朋友之列,他说:“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14]
参考文献:
[1]鲁迅.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M]//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88.
[2]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M]//绀弩杂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66-67.
[3]沈从文.学鲁迅[M]//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33.
[4]沈从文.记胡也频[M]//沈从文文集(第9卷·散文).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69.
[5]吴投文.沈从文论鲁迅:在疏离与接受之间[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1):71-75.
[6]沈从文. 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M]//沈从文文集(第12卷·文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73.
[7]沈从文.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M]//沈从文文集(第12卷·文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87-188.
[8]沈从文.论冯文炳[M]//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9]聂绀弩.聂绀弩杂文集·序[M]//聂绀弩杂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1995:2.
[10]夏衍. 聂绀弩还活着——代序[M]//聂绀弩还活着.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
[11]钟敬文. 悼念绀弩同志[M]//沧海潮音. 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2:412.
[12]汪曾祺. 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M]//沈从文.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1.
[13]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EB/OL].[2011-07-15]. http://www.housebook.com.cn/.
[14]杨建民.沈从文评议鲁迅与聂绀弩的辩驳[EB/OL].[2011-07-15].http://www.eywedu.com/Bolanqunshu/blqs2008/blqs20080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