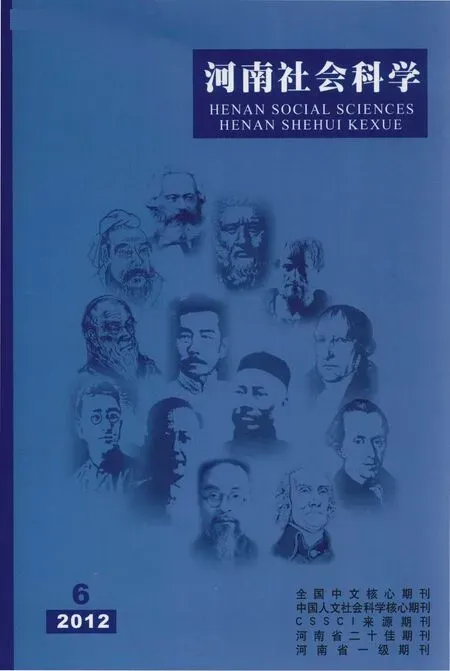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横向考察
——兼及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研究
时锦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横向考察
——兼及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研究
时锦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经历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变异学研究的学科方法。国内学者多从纵向的角度考察这些学派与学科方法的更迭变化,忽视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横向研究。横向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凸显的是比较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性,这是对学科发展过程的深一层把握。从横向看,中西方比较文学在建构学科理论时存在着两个误区:过分注重学派建构与文学真理的诉求;学派固守疆域,文学真理压制了文学他化的灵性。中国学派提出了变异学研究,虽然也有学派疆域与真理残留的尾巴,但它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局限,是国内比较文学有代表性的学科理论之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比较文学学派;文学真理;中国学派;变异学
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始于19世纪,100多年来,中西方比较文学经历了以学派为特征的三个阶段,曹顺庆认为:“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1]曹顺庆虽然从纵向上考察了比较文学发展历程,并指出了比较文学“涟漪式”发展特点,但是这种纵向考察忽视了比较文学横向上的学科共性。笔者认为,中西方一百多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从纵向上看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再到中国学派,而从横向上看则是比较文学学派建构的冲动与追求文学规律的欲望。比较文学学派建构的冲动使得现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多以学派面目出现,追求文学真理的欲望则使文学的比较成为文学归纳的狭隘化操作。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过程的这两种倾向影响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学科建构,也束缚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中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发、跨文化研究、和而不同研究与变异学研究等学科理论,这些学科理论体现了中国学者积极融会中西文化以求建构有世界影响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努力,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努力不仅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而且反映了中国学者力求创新的文化自觉意识。
一、学派建构: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论争
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和学派建构纠缠在一起。法国学者首创比较文学学科,打着“影响研究”的旗帜占地为王,在已有学科园地中画定疆域。美国学者紧跟其后,在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地中重新洗牌,形成了以“平行研究”为特色的学派。中国学者也不甘落后,从学科建制开始就着力论证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力求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阵地。比较文学学派的建构既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蕴涵着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化民族身份的焦虑心理,其中的复杂性显然不是一种心平气和、冷静客观的纯文学研究。从学科的发展看,学派的建立意味着学派的死亡。学派画定疆域,为学科建制金汤城池,违背了比较的会通性,从而将比较文学拖进僵化的泥淖。
法国学派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影响研究”。梵·第根、卡雷、基亚等老一代比较文学家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义,从理论上确定了影响研究的学理依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艾金伯勒、布鲁奈尔、比梭瓦和卢梭紧承其后,在美国学派的攻击声中完善影响研究的学科理论,继续守卫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学科疆域。影响研究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入手,以接收、放送和媒介为考察对象,形成了渊源学、舆誉学和媒介学三大子学科,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证成果。但是,文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实证的也是审美的。法国学派在自立门户以后也给比较文学研究戴上了枷锁。美国学者雷马克批评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说:“有不少关于影响研究的论文过于注重追溯影响的来源,而未足够重视这样一些问题:保存下来的是些什么?去掉的又是些什么?原始材料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同化?结果又如何?如果按这类问题去进行,影响研究就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能增进我们对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2]雷马克对影响研究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他一方面揭示了影响研究注重实证在学理上的不通融,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影响研究在注重实证的时候忽视了实证之外的文学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学派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总是为了突出学派的独立性而对文学研究的其他要素视而不见。法国学派突出了文学的外在性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内在性研究。内在性研究是美国当代新批评所热衷的批评方法,法国学派对此方法的忽视当然遭到美国学者的反对。
美国学者韦勒克以新批评的眼光看出了法国学派的不足,公开而系统地批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韦勒克认为,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等人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了19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3],方法论的错误导致比较文学成为一潭死水。韦勒克的批评撕开了法国学派的门户堡垒,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雷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将比较文学从注重事实关系转入到了类比、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平行研究解除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疆域,将比较文学从实证研究、事实联系之中解放了出来。但是,美国学者解除了法国学派的疆域又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在文学比较的过程中推崇文学的科学客观性而忽略了文本意义的历史性。曹顺庆总结美国学派说:“比较文学美国学派迥别于法国学派的地方有一点就是要求达到一种真正科学的客观性,即要求比较文学家尽量排斥自己的文化‘成见’的干扰。……总之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以二元对立的本质/现象允诺要为人类文学知识提供一种坚实的基础,但它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牺牲了文学的历史性、牺牲了理解的历史性、牺牲了意义的历史性。”[4]这是学派建构的悖论。美国学派批评了法国学派外在研究的历史性,强调了文学研究过程中的真理诉求,但是这种文学真理的诉求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又是一个理论的想象。因此,雷马克等美国学者无力回应当代哲学特别是来自解构主义的批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又陷入了理论困境。
中国学者在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又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学科设想。首提中国学派的是台湾学者。据考证,1971年台湾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构想,1972年李达三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为中国学派确定命名①,之后经由台湾学者陈鹏翔、古添洪和大陆学者季羡林、杨周翰、乐黛云、曹顺庆等人的不断推进,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终于为中国学派抢下了滩头阵地,中国学派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构想逐渐成型。乐黛云教授针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大胆预测:“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5]中国学派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为根基,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特别是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力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能够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质因子,又能够以中国文化补缺西方文化。因此,中国学派的立足点正如台湾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学派是“求异”的学派。求同也好,求异也罢,这些都是黑格尔同异思想的表现,都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将存在当做存在者的现成性研究。当然,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还有超越学术研究的民族自强心理。王向远认为:“比较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纯学术现象,一种学院现象。而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就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形成。”[6]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不是纯学术现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建构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相关,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派的建构只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分疆划域,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高端境界。学派封疆画界的结果是比较文学学派的三分天下,刘象愚说:“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原先的欧洲和北美双雄并列的形态逐渐淡出,以东方为主的世界其余地区的比较文学崛起,形成了大体上三分天下的局面。”[7]三分天下的比较文学并不能说明比较文学已经高枕无忧,实际上,比较文学学派林立带来了更多的遮蔽。法国学派寻找文学国际交流的事实联系,推崇“某某在某国”的研究范式,标举了实证的方法,但是,“某某在某国”其实就是某某与某国文化的同一,以“同”为出发点看影响研究,容易演化为中心主义的傲慢。法国学派由此被指责为充满着欧洲中心主义。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的疆域,形成了“A与B”的研究范式,实质上A与B的比较还是一种类同性的比较。当研究者在回答A与B为何能够比较时,A与B“类”的确定还是只看到文学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中国学派将比较的疆域推广到了东方,突出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这里边包含着中国学者的文化自尊与焦虑,还没有从深处突破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局限。中国文化能否代表东方文化成为学派的主导姑且不论,在全球化过程中强调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只是学者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文化焦虑心理。刘象愚总结了比较文学三分天下后说:“在全球化的版图中,比较文学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未来走向如何,似乎只能看今后的发展和演化而定。”[7]
二、真理追求:比较文学研究的求真幻想
寻求文学发展之共同规律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动力。追求真理并将自己的理论标榜为规律是西方逻各斯中心的主流,这种倾向在19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中达到了高峰,俨然成为文学研究的最高价值标准。随着西学东渐,这一倾向也影响并支配了中国的治学秩序。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阐发自己的比较文学观念时很容易集结在真理追求的阵营之中,缺乏对真理进行一番反思。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绪论中说:“我们要借助于各民族诗学的比较,探寻世界文学更普遍的规律,将对各国各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都会做出突出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8]这一通过比较探求真理的表述是国内比较诗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然而,19世纪的真理追求受到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叛,透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阿多诺的“碎片”思想和德里达、福柯、布德里亚等人的后现代扫描,我们可以看清真理所蕴涵的僵化、器化倾向扼杀着文学灵动、起伏和会通的本性。
真理只是击败时间的幻想。真理与时间的一维性相互纠缠,以超越时间的相对性为旨归,但是,真理作为话语的表述,本身就是话语主体的表述行为,这种表述行为生存在时间之中,脱离不了主体存在的有限性。因此,问题在于,谁能够确认自己的表述就代表着永恒呢?又有谁能够超越于自己的有限性而使自己的话语在无限时空中永存呢?美国学者库恩是看穿了真理永恒的这种假象,他针对真理的永恒提出了范式的构想。常规科学只是话语表述的集合体,表述能否成为范式,关键还看范式所在时空中话语主体相互之间的论争、检验和接受。库恩的范式理论无疑将科学拖进了具体时空,指认了真理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事实。真理无法超越时空,强调真理的永恒只是知识生产者的集体幻象。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所归纳的“文学真理”能够永恒存在。
真理容易成为权力压制的工具。真理含有独尊的霸道,要求其他的知识行为追随它,指定实践行为服从它。真理对知识行为和实践行为的这种先行要求容易使自己跨越话语表述的园地,演化成为学术权力和社会权力争斗的工具。学术界以把握真理标榜,抱窝成立学派,排斥异己,压制反对的声音。政治斗争也容易以真理为旗号,利用“真理”的影响打压其他的抗衡力量。法国学者福柯针对真理的这种霸道提出了“权力话语”这一概念,点出了话语以真理为借口与世俗权力纠缠的真相。以真理标榜正是学派存在的深层根源,也是学派分疆划域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比较文学研究将研究的终极追求寄托在真理身上,虽然脱离了学派建构的僵化,但是,寻求所谓的客观真理距离文学本根尚有一段距离。
真理需要存在论的澄清。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真理进行了存在论的澄清,这种澄清将真理的本质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缘始于揭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的体验、表象是物的肖似,并不就是中世纪、19世纪认识论所解读的认识与实在的符合。海德格尔退回到逻各斯的源头,退回到判断过程和判断内容的区分,重新展示了“符合”的原初意义:符合具有如……那样的关系性质。“这就是说,它在它的自我同一性中存在着,一如它在命题中所展示、所揭示的那样存在着”[9]。如此看来,真理并没有19世纪认识论所高举的纯粹客观性。真理所具有的客观只是存在者所看到的。“一命题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中说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让人看见’存在者”[9]。揭示活动是在世的一种方式,真理现象最缘始的基础还是生存论存在论,是此在的“寻视着操劳或甚至逗留着观望的操劳”。此在在世界中自然有着对存在者的揭示活动,真理“如……那样”的整体结构包含着此在的在世。由此看来,真理并没有超越时空的特权,真理在世界中,与同时在世的此在构成了物我同一。海德格尔将真理拖进在世界中的结构,破解了真理的超越性,还原出一个和我们的在世生存息息相关的真理现象。
真理/客观规律一直是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津津乐道的话题。强调文学研究的规律性与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逃避现实的借口。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是此在的操劳,是人的完善。海德格尔说:“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真理追求恰恰忽视了人的这种本己的可能性。丢失了人最本己的可能性的文学研究怎么可能成为文学研究的高端境界呢?
三、变异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新世纪探索
比较文学研究不能着眼于固守门派,不能寄托于真理追求,那么比较文学又应该如何确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当代比较文学界热衷于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国际社会如果承认中国学派,那么这个“中国学派”就必须从本根处为国际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法国学派为国际比较文学贡献了影响研究,美国学派为比较文学贡献了平行研究,这些学派各有自己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基础。当代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和整合与建构研究,这些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吸收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方法还缺乏中国文化的民族基础。曹顺庆认为:“中国文论话语要实现现代性重建,就要在坚守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言说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和融会西方文论的精髓,才不会让西方文论话语成为中国文论意义建构的方式,达到本土与他者的良好结合,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10]中国文论话语现代性建构需要中西文化会通,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也需要这种会通。会通中西方文化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方向,这种发展方向被曹顺庆、严绍等当代学者总结为变异学。变异学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当代中国跨文明研究的一种自觉性的理论建构。
变异学首先由曹顺庆正式提出。曹顺庆2006年在《复旦学报》刊发了《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该文一开始就提出,“将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是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现状、文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以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的”[11]。变异学概念突破了以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求同的理论基础,要求从异质文化的立场研究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这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变异学研究的四个方面: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的形象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和文化变异学研究。这四个层面的变异学研究有助于破除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心主义。曹顺庆认为:“此前,比较文学侧重在不同文化与文明中寻找共同规律,以促进世界各文明圈的对话与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以增进文学的发展,而变异学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学科跨越性的基本特征,并聚焦于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这不仅有助于发现人类文化的互补性,而且为找到通往真理的不同途径提供了可能。变异学的研究对象跨越了中西文化体系界限,在方法上则是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结合,这也体现了比较文学在坚持自身学科特色的前提下,试图融合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努力。”[12]可见,以曹顺庆为核心的四川比较文学研究群体提出变异学的研究有其现实依据和理论根据。从求同到变异,中国学派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实在不断推进,尽管变异学还残留一些问题,但它已经注意到了比较文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种转变超越了学派固守疆域的局限,更加契合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观念。栾栋教授认为,文学本无疆域,文学之疆域是分工与私有的痛苦产物。文学有疆域并非文学的禀性,“从终极处透视,文学是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而是与天地气息通感的人类文化原生态,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的精气神,是与社会正负价值切磋磨合的非自我中心话语。这几种本根性的文学禀性注定了它与疆域论者的重大差异”[13]。文学变异学突破求同,着眼于差异,是近年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讨的一个深化与推进。
变异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能找到学理基础,这就是乐黛云教授所提倡的比较文学“和而不同”的观念。乐黛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这种重视“不同”的思维可以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原则,乐黛云说:“‘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14]乐黛云对“和而不同”的阐发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突破。和而不同重视差异,同时又超越了纯粹差异性的多元主义。当代的多元主义文化思潮强调文化发展的和平共处,这是对19世纪、20世纪前期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达尔文社会理论的突破,这种突破于西方学者来说是一种苦修,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而不同”在多元文化平等共处的基础上,提倡“和”在基础上形成新的事物,更为深入地论述了文化和平共处的意义与追求。世界文化和平共处是前提,而其目的还是落实于文化的融会创新,只有“和”而没有创新,文化不能发展更新,而没有“和”,世界失却了和平的环境,人类文化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论述也是变异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曹顺庆在提出变异学后对变异学的发展前景也有过疑问:“不同文明之间没有影响关系的文本该如何比较,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问题,也即比较文学跨文化/文明比较的‘瓶颈问题’该如何解决?”[4]如果拘泥于文学比较的事实联系,拘泥于文学比较的规律性,变异学中的可比性问题就是一个无法回应的难题,但是如果从“和而不同”的角度看,比较的目的不是规律,不是跨国别文学之间的事实关系,而是寻求文化之间的会通创新,那么可比性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具有综合能力的主体手里,跨文化之异质性熔铸成了具有创新性的文明成果。
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力求推进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认为,100多年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史,并且作为一种文学视野渗透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比较文学在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领域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对这一学科认识的深化其实是国际性研究视野的相应扩展,同时也是努力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发出具有中国特色声音的尝试,尽管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平等对话的过程还很漫长,但这将是中国学者不断努力的目标。
注释:
①关于谁最早提出中国学派的命名,学术界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本处采取孟昭毅教授的观点。详细论述可见孟昭毅教授所著《比较文学通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中国比较文学,2001,(3):1—17.
[2]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A].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于永昌.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5]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王向远.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刘象愚.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0]曹顺庆.迈向比较文学第三阶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1]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79—114.
[12]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1.
[13]栾栋.文学的疆域[N].光明日报,2003-03-05(9).
[14]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I0
A
1007-905X(2012)06-0084-04
2011-12-25
时锦瑞(1963— ),女,河南长葛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