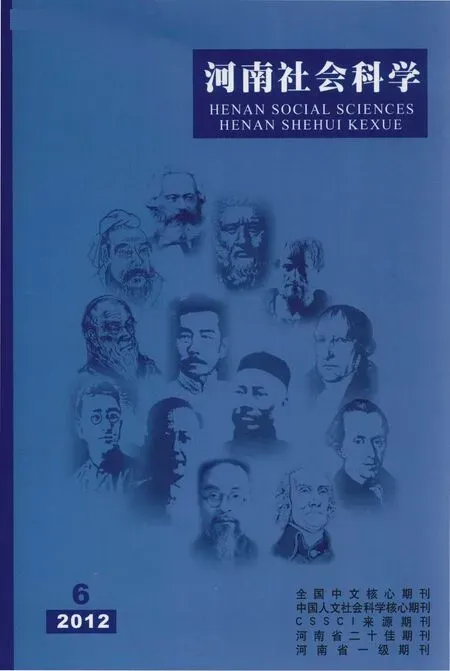论禁止“过度刑罚”
——以美国宪法判例与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朱玉霞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88)
论禁止“过度刑罚”
——以美国宪法判例与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朱玉霞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88)
自20世纪初,美国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和学说,不仅将“过度刑罚”诠释为宪法所禁止的酷刑的一种展开形态,而且还为其确立了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判断标准以及一整套严密精致的认定方法。这种理论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到中国的语境之下,但无论是对我国禁止酷刑理论研究的深化还是对我国刑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均不无借鉴意义。
酷刑;过度刑罚;正当标准
从世界范围来看,禁止酷刑的观念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问题,迄今我国刑事法学界以及宪法学界几乎尚无人论涉,乃至留下了空白。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宪法学的视角的出发,涉入刑事法学的理论和实践,间中以美国宪法判例和学说为中心,对“过度刑罚”的理论渊源、认定标准以及认定方法予以探究分析,最终反观中国问题,从中国立场出发,对该理论的借鉴意义予以思考和评价。
一、传统的酷刑观
关于酷刑的定义①,各种的理论学说向来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法学的领域,探究关于酷刑的法学意义上的概念,其内涵的表述则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可知:酷刑是一种为了施与惩罚、获取口供或信息,或为了施虐的快乐,而给人的身体或心理造成的剧烈痛苦;在旧的刑法里,在司法准许和监督下,与对人的调查或审查相联系,通过采取拉肢刑架、刑车或其他器械,对个人施加暴力的肉体痛苦,作为逼取供认或迫使其揭发同谋的方法②。应该说,这个定义具有权威性,也反映了法学领域中有关酷刑概念的传统见解③。
当然,法学意义上的酷刑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形态。这是由于在判断某一个刑罚是否属于酷刑时,总是难以避免涉及哲学、伦理、社会以及文化意义上的评价和考量,而且这种评价和考量的依据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不同的国家并随着不同的时代,而拥有不同的内容、特征和意义,为此,酷刑概念本身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历史概念。诚如美国学者摩尔教授所言,酷刑“是只能依据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系来理解的一种社会现象”④。
二、过度刑罚的认定标准:“演进的正当标准”
当今的美国学者认为宪法上所禁止的“残忍的和不寻常的刑罚”,在逻辑上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它包含了一部分可以被认做是过度的刑罚,譬如,对轻微的盗窃的行为实行终身监禁,这是一种过度的不合比例的惩罚,也可被视为一种“残忍的”和“不寻常”的惩罚。质言之,即使“过度的”与“残忍的”、“不寻常的”有不同的内涵,但这并不妨碍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子集,或者与后者形成被包容的关系⑤。但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禁止过度刑罚的观点也曾一度受到质疑。在2003年的Ewing一案⑥中,斯卡利大法官和托马斯大法官就在其法庭意见中表示,他们深深怀疑过度刑罚也是酷刑的论断。斯卡利大法官认为,立法者知道如何适当地使用“过度”这个词,就像在禁止过度罚金条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中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个词语一样。他认为,根据立法者的本意,认为“过度”具有与“残忍”和“不寻常”相同的内涵的观点未免失之草率。此外,有些学者也持类似的怀疑态度,认为在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和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中,立法者在拟订禁止残忍和不寻常的刑罚的条款时,恐怕并没有考虑过使用比例原则对刑罚权给予限制⑦。
一方面,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的质疑观点均采用了一种严格的解释方法。但是,正如康拉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只能依据18世纪立宪者使用的概念和含义对宪法进行解释,那么,这简直无异于将宪法制成木乃伊存放于陵墓之中供人瞻仰,如此宪法的唯一用处就是成为社会变革的障碍⑧。而实际上,自从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时代以来,这种观点已经不是联邦最高法院所遵循的规则了。立法者的本意自然可以为宪法解释提供一种向导,然而,从一系列的有关第八修正案的司法判例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实仍然不难发现,在立法者关于何为“残忍的和不寻常”的立法原意的基础之上,司法实践已经走出更远。
另一方面,在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之中,也只有斯卡利大法官和托马斯大法官否认“过度刑罚”的概念以及宪法上禁止酷刑的条款所蕴涵的比例性原则,而且,他们的观点也很难符合自Weems案⑨以来的判例精神。肯尼迪大法官就曾宣称:“比例原则的制约存在于宪法第八修正案已经80年了。”⑩质言之,不合比例的过度刑罚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的和不寻常的刑罚”这一观念,无论在美国的理论上还是在美国的实践上均已被普遍接受。
基于“演进的正当标准”,“过度刑罚”概念的内涵颇为明晰,而不像传统的“酷刑”概念那样,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残忍的和不寻常的”这样的术语的伦理理解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其三项具体的“客观性指标”,使得过度刑罚的认定标准进一步得以细密化。
三、过度刑罚的认定方法:比例衡量的方法
如上所述,随着宪法判例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宪法理论,即认为:(1)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酷刑,其中也包含了禁止“过度刑罚”;(2)所谓“过度刑罚”,指的是任意加之于人的不必要的痛苦,或者犯罪的严重性与所科处的刑罚的严厉性不成比例的刑罚⑪;(3)而某一项刑罚是否属于“过度刑罚”,应依据当前的“演进中的正当标准”进行判断,其中主要是依据立法状况、陪审团态度以及宪法判例等综合因素进行考量分析⑫。
那么,在具体个案之中,究竟应该如何认定某项刑罚属于“过度刑罚”呢?有关宪法判例明确指出,如果某种刑罚属于以下两种情形之中的任何一种,即可认定为“过度刑罚”:一是无助于实现刑罚的合理目的,纯属盲目且无谓地制造痛苦和折磨;二是罪轻刑重,严重失衡⑬。这里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是上述两种情形之中的第二种。应该说,美国联邦法院在认定这种情形即罪刑失衡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归纳出了一套较为精致也较具可操作性的步骤,即具有三段式(three-step process)结构的比例衡量方法:
在某个具体个案中,要判断某项刑事判决是否与被告所指控的罪行达成合理的比例,具体可分为如下三个步骤:(1)首先对本案中罪行的严重性与刑罚的严厉性进行衡量,二者须符合比例原则。这个步骤可被看做内部的衡量。(2)将本案中的罪行与判处相同刑罚的其他不同罪行相衡量,看本案中的罪行是更严重还是更轻微,如果罪行更轻微却被科以同样严厉的刑罚,这个刑罚即是不合比例的过度刑罚。(3)与相同罪行被判的不同处罚相衡量,看本案中的处罚是更具有严厉性或者更不具有严厉性,如果该处罚更具有严厉性,即是过度刑罚。当然,这里还会派生另外一种比较的情形,即与更严重的罪行所科以的刑罚相比,若该刑罚却更为严厉,自然也属于过度刑罚。以上第二、第三个步骤均是属于外部的衡量。上述整个三段式的衡量比较步骤,可简单归结如下:
1.本罪:罪行↔刑罚
2.相同刑罚的不同罪行:罪行↔罪行⇒更轻者为过度刑罚
3.相同罪行的不同刑罚:刑罚↔刑罚⇒更重者为过度刑罚
四、余论:基于中国立场的思考
美国的过度刑罚理论的提出,相对地扩大了酷刑概念的内涵和范围,并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把过度刑罚的适用纳入禁止酷刑原则的审查范围,这对于推动刑罚制度的改善,促进刑罚制度的理性化、合理化、文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却未必可以完全照抄照搬到中国的实践之中。然而,美国式的“过度刑罚”理论,对于我国的法理论与实践而言,也非全然没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这个理论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对于我们颇有裨益。
(一)理论意义
上述有关禁止“过度刑罚”理论的确立,表明了在当今的美国,酷刑的概念已从一个刑事法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宪法概念,已从一个内涵单一的传统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了“过度刑罚”这样的复合概念,并已从一个主要依赖价值判断来界定的抽象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明晰的判断标准和认定方法的具体概念。但与此不同,酷刑的概念在我国仍相当于传统的概念,大多数刑事法学者主张接受《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中关于酷刑的定义,即“‘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但这个酷刑的定义仅仅是对酷刑行为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仍然无法回答一个行为被认定为酷刑,其本质依据是什么;该定义自称是“宣示”而非穷尽,其实范围仍然是有限的、自闭的,至少无法从中推导出过度刑罚也是酷刑的论点。由于酷刑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其中蕴涵着文化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更替和进步,社会对酷刑的观念和认识会有很大不同,因此,比照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的法治国家的规范性条文,采取一个类似的开放式的酷刑定义,并参酌其判断标准和方法,对于我国禁止酷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实践意义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上没有禁止酷刑的条款,不可能直接将禁止过度刑罚的内涵纳入其中,但尽管如此,在一定意义上,禁止过度刑罚的理论本身也具有独立的意义,对推进我国刑罚制度的合理化和人性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至少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抵制“重刑”政策。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重刑主义传统,古时就有“刑乱世、用重典”的主张,目的是通过严苛的法律惩治犯罪,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自1983年以来我国所进行的三次刑事“严打”活动,即是这种重刑主义政策的承继和延续,并导致了普遍意义上的重刑化⑭。但诚如两百多年前贝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⑮。目前,重刑政策在我国也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和批评。而禁止过度刑罚的理论,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法律允许的刑罚方式,因罪刑不均衡导致过分严厉之时,即为过度刑罚,在美国甚至被确定为属于宪法上所禁止的酷刑。而从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来看,这种宪法学上的思考路径和论证方法,对于限制刑罚权的滥用颇为有效。而且,把“严打”这种刑事政策纳入实定法的框架内尤其是宪法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为反思重刑主义提供有力的依据。
其二,有助于建立合理的量刑具体化结构体系。实现罪刑均衡,也是我国刑事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规范自由裁量权和实现罪刑均衡,2010年10月,我国最高法院就曾颁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量刑规范化的试点工作。然而,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应如何实现罪刑该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美国最早开始实行量刑指南制度。我国学者也认为,虽然美国的量刑指南招致诸多批评⑯,但是其促进量刑标准具体化的做法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主张我国刑罚裁量制度的改革,有必要适当参考、借鉴美国联邦和州的量刑指南,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既有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量刑标准⑰。具体而言,美国各州的量刑委员会根据量刑惯例所确定的“量刑格”为量刑准则,法官在量刑时必须严格按照量刑格给罪犯打分,最终确定罪犯应受的处罚,其目的也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罪刑相当。而量刑格所依据的原理以及采用的方法,其中一部分正是暗合了禁止过度刑罚理论中使用三段式的衡量步骤去判断刑罚是否与罪行均衡的过程。而且,无论怎样设计量刑格,总有一个最高刑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这个适用过程则必然伴随着最高刑是否属于酷刑或者过度刑罚的判断和甄别。总之,借鉴禁止过度刑罚的理论,尤其是参酌其中的过度刑罚的认定标准和具体的衡量方法,对于在我国刑事制度中建立合理的量刑具体化结构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宪法所禁止的酷刑,所以首先排除了施虐的个人行为,同样的理由也可排除某些具有残酷特征的宗教行为。
②参见 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Publishing Co.Fifth Edition pp.1335—1336。
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主要是把酷刑限制在刑事调查过程中,与各国禁止酷刑的理论中所确定的酷刑含义相比,已经是太过狭窄了。这种有关酷刑的观点被视为狭义的概念,包含了如下限制:其一,酷刑行为人的身份应为特定的国家机关或在此特定国家机关工作的公职人员。所谓“特定”,通常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工作人员而非任何国家机关人员或者任何公职人员。其二,酷刑须与刑事司法程序有关或者该酷刑行为须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其三,遭受酷刑的对象应为特定人,通常指刑事被告人、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在押人员。其四,该种刑罚是否为合法性惩罚对酷刑犯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五,就各国历史看,酷刑没有公认的认定标准,当代社会仍无普遍认同的酷刑标准。参见陈云生:《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④转引邱兴隆主编:《比较刑罚(第1卷 死刑专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⑤ 参 见 Youngjae Lee,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against Excessive Punishment,Virginia Law Review, Vol.91,No.3.(May,2005),P680。
⑥参见Ewing v.California,538 U.S.11,31(2003)。
⑦参见Nancy J.King & Susan R.Klein,Essential Elements,54 Vanderbilt Law Review,1467,1517。
⑧[美]欧内斯特·范·登·哈格、约翰·P 康拉德:《死刑论辩》,方鹏,吕亚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⑨参见Weems v.United States,217 U.S.349(1910)。
⑩参见Harmelin v.Michiganm,501 U.S.957(1991)。
⑪参见Gregg v.Georgia,428 U.S.153(1976)。
⑫参见Atkins v Virginia,536 U.S.206(2002)。
⑬参见Coker v.Georgia,433 U.S.584(1977)。
⑭在1983年“严打”以后,在刑事立法上通过颁布单行刑法,使死刑罪名从1979年《刑法》的28个增加到1997年《刑法》的68个,增幅达2/3左右。随着死刑罪名的增加,各种常见罪的刑罚普遍趋重。参见陈兴良:《刑罚改革论纲》,《法学家》2006年第1期。
⑮[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⑯实际上,量刑指南从制定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方的批评,美国司法界认为量刑指南太不确定;很可能不合乎宪法,难以施行,与现有的司法实践相比过于严厉,甚至使用量刑指南后,反而导致了比无量刑指南时更大的差异性。由于面临多方批评,美国的量刑指南从制定之日起,就处于不断的修改之中。
⑰赵秉志:《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论纲》,《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D9
A
1007-905X(2012)06-0017-03
2011-10-28
朱玉霞(1976— ),女,河南周口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韩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