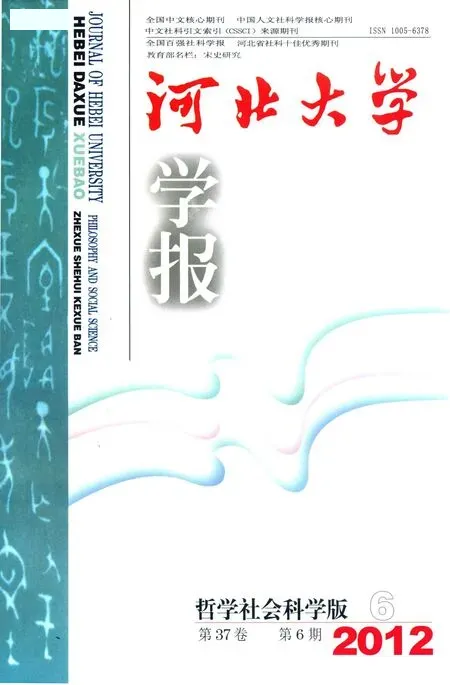中国志怪传奇在日本近世怪异文学中的形变——以《伽婢子》为例
吴 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引 言
在日本文学用语中,有一个词汇叫“翻案小说”。所谓“翻案小说”(an adapted story)是一种“借用外国作品的内容,将风土人情、人名地名等按照本国习俗进行改编的文学体裁”[1],即翻改小说。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出现了大量以中国明清文言、白话小说为底本改写的翻改小说。特别是改写自明代传奇《剪灯新话》和清代“用传奇法,而以志怪”[2]的《聊斋志异》的作品在翻改小说中所占比例极大,形成了日本近世(前近代)文学的一大重要特征。
早自中古时期开始,神鬼妖怪故事就成为日本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而这些题材在进入近世时期后,其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这其中,缘自中国小说的影响不可忽视。正如日本学者太刀川清所言,“研究近世怪异小说通常要以宽延时期(1748~1751)为界点来划分前后。儒学者都贺庭钟的《古今奇谈英草纸》①江户时期的读本小说。五卷本。1749年刊。改写自《古今小说》《今古奇观》和《警世通言》等中国白话小说,被称为读本小说的鼻祖。(1749年刊)的出现,显示出怪异小说开始受到中国通俗文学越来越大的影响”[3]。因此,通常以为,日本近世的怪异小说基本源自对中国志怪传奇的翻改和仿效。知名作品如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②江户时期的读本小说。1776年刊。由九部中、短篇构成。主要源自《古今小说》《剪灯新话》《醒世恒言》《古今说海》《五杂俎》等中国典籍。和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③长篇传奇小说。其中怪异荒诞的情节多改写自《搜神记》《水浒传》等中国典籍。等等。
其中以江户前期的假名草子作家浅井了意的《伽婢子》(1666年)最具代表性和创造性,《伽婢子》被称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的鼻祖。在《伽婢子》之后,又出现了追随其后的《新御伽婢子》(1683年)、《御前御伽婢子》(1702年)、《拾遗伽婢子》(1704年)等伽婢子系列怪谈集,足见《伽婢子》的影响之大。可以说《伽婢子》的诞生,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的创作开启了新的模式。
《伽婢子》由13卷68篇构成,其中大多出自中国典籍。45篇出自《五朝小说》;16篇出自《剪灯新话》;2篇出自《剪灯余话》;2篇出自朝鲜的《金鳌新话》;余下3篇为作者原创。《剪灯新话》共计4卷20篇,而《伽婢子》就改写了其中16篇之多,由此可见该作品对《剪灯新话》的借用最为集中。因此在日本学界,与《伽婢子》的相关研究大多着眼于该作品与其主要出典原著《剪灯新话》的比较,例如藤井乙男的《中国小说的翻译(剪灯新话和伽婢子)》①藤井乙男:《江户文学研究》内外出版社,1921年。、麻生矶次的《怪异小说的影响》②麻生矶次:《江户文学和中国文学》三省堂,1972年。等先学的理论为解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迄今为止,多数研究仍滞留于《剪灯新话》的研究范围内,显现了古典文学研究固有的一种惯性局限。本文选取《伽婢子》中两则改编自其他中国小说的故事(卷二的《狐妖》和卷十二的《早梅花妖精》),试对《伽婢子》与《剪灯新话》之外的其他中国传奇小说之间的关系做一考察。
关于日本近世翻案小说的过往研究课题大多偏重于典故研究,即对典据的考证,出典论倾向较为明显。而原著在改编中产生的形变往往被忽略,对改编自身的技巧与创造性也鲜有涉及。其实,以《伽婢子》为例,作者借用原著的构思与情节另辟蹊径,将单一的故事复杂化、一元的线索多元化的例子并不在少数,使读者对照原著读来,常有脱胎换骨之感。本文以先学业绩为基础,以探讨《伽婢子》的“个性”为目的,使用文本对照分析的方法,将在以下探讨中国志怪传奇在日本近世怪异文学中如何发生形变、《伽婢子》作者如何在继承原著的基础之上,拓展创作空间,发挥独自的想象力,使作品在依附于原著的同时又独立于原著,成为具有一定“个性”的翻改作品。
一
《伽婢子》卷二的《狐妖》改编自明代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卷三中的《胡媚娘传》。中国的传奇小说发端于六朝志怪,成熟于唐宋传奇,而明代的传奇小说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诚然,《剪灯余话》的影响力远不及它的模仿对象《剪灯新话》,其成就也难与后世的《聊斋志异》相提并论,但是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相较于之前以及同期的传奇作品都已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同类文言小说继承和发展的对象。《胡媚娘传》是一则典型的异类姻缘故事,其中的胡媚娘——狐精形象多为后世作品模仿。故事讲述河南省新郑县的驿卒黄兴偶遇戴骷髅拜月化为妙龄少女的狐精(胡媚娘),以为奇货可居,遂起歹意领回家中,将其卖给了素行非端的进士萧裕为妾。萧裕倾囊而出,如获至宝携带还乡。初始胡媚娘伪装甚好,贤德可人,然而未及一年,萧裕却日渐枯槁、行为颠倒。后被道士尹憺然识破,做法将狐狸霹死,现其原型。而黄兴在发了横财后早已逃之夭夭。《狐妖》基本承袭了《胡媚娘传》的故事结构,看似是《胡媚娘传》的忠实翻版,然而,于细微处便可见作者的再创作功力。特别是小说前半部一改普通翻改作品“中规中矩”的性格,显露了翻改者希图改头换面的“恣意”与有意识的突破。
在此试循故事的情节发展,就小说前半部的“开篇人物”“狐精变身”“身世倾诉”三个章段将《胡媚娘传》③李昌祺撰,周夷校注:《剪灯新话》附《剪灯余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狐妖》④江本裕校注:《伽婢子》,平凡社,1987年。本稿中出现的所有日本原著引用部分均为笔者翻译。做一对比。
原作在开篇处对人物的介绍极为简单,“黄兴者,新郑驿卒也”。对始作俑者黄兴,只以寥寥数字便交代完毕。从中只可看到人物的身份和所居地。相较之下,《狐妖》中的割竹小弥太(即原作中的黄兴)的人物形象则显得厚实丰满,除了必须铺陈的基础要素之外,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也为情节的发展做了合理的铺垫。
在江洲武佐有个旅店主名叫割竹小弥太,原本住在甲贺。此人喜欢相扑且力高胆壮。平时招待路经此地的过往客人,专心经营自家的小旅店。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小弥太不仅喜欢相扑,还力大无比、气高胆壮,使得小弥太其后在路遇狐精戴骷髅变身人形时能毫无惧色并大胆领回家中。对这个“始作俑者”的设计描写,两作品略有不同。首先是身份的差异。黄兴是河南新郑县驿站的差役,而小弥太却是经营旅店的业主。这种差异使得小弥太在路遇狐精之初并未急于利用狐精来脱贫致富。而黄兴的狡黠和贪财自始便暴露无遗,见狐精变身娇媚女子,顿觉“此奇货可居”,一番巧言令狐精视他若“再生之父母”。在选中行为不端的进士萧裕做“主顾”后,立即告知妻子“吾贫行可脱矣”,并“数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见之”,演出了一场“父卖女”的好戏。如此,黄兴自始便将狐妖作为“奇货”储备而最终如愿得以出手。而小弥太虽亲眼得见狐精变身的全过程,并明知狐精是在诳骗自己,却无做他想,而是顺势领狐精回家做了下女。之后,虽在对狐精一见钟情的石田市令助(即原作中的萧裕)面前谎称“赫赫有名的诸侯们都有意娶我家婢女,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没有把她嫁给任何一个达官显贵。如果有谁能让我日后生活无忧,嫁她出去倒也无妨”,但作者并未在小弥太亲自导演这出“主卖仆”的闹剧上多蘸笔墨,而是顺其自然地让小弥太最终获得了和黄兴同样的收益。这里的“刻意的主观谋划”与“顺便的客观行为”表面上虽然体现的是相异的人物性格,实则反映的却是中日两国“妖怪文化”的不同。中国自古就有戏弄鬼怪换取钱财的故事。《搜神记》中的《定伯卖鬼》讲述的就是南阳人宋定伯在年少时夜行遇鬼,施巧计将鬼骗至集市卖掉,得钱1 500文的故事。作者在故事的结尾处称“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4]112,石崇是西晋时人,为荆州刺史,劫掠客商成为巨富,生活奢糜。与贵戚王恺攀比斗富,以富可敌国而名闻天下。有这个石崇佐证,可见卖鬼的传说在中国流传之广。而日本的古书记事中却难见买卖鬼魅妖怪的传说记载,人们对妖怪更多的是怀有畏怖甚至是畏敬之念,在神道文化中,鬼怪也被视为众神之一。因此也难怪浅井了意在改写《胡媚娘传》时对原作的取舍了。
在“狐精变身”的描写中,《狐妖》也显现出异于原作的特征。原作中的“狐精顶戴骷髅”早在《搜神记·僧志亥》中便有如下记载:
至绛州城东十里 ,夜宿于墓林下。月明如昼,忽见一野狐,于林下将枯骨骷髅安头上,便摇之 ,落者弃却。如此三四度,摇之不落,乃取草叶装束于身体,逡巡化为一女子 ,眉目如画,世间无比,着素衣。于行路立犹未定,忽闻东北上有鞍马行声,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听[4]129。
唐代中期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僧晏通》中的“因举锡杖扣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5]描述的也是狐妖被击中,所戴骷髅头落地现原形逃窜的情形。
《宋高僧传》卷二四《唐沙门志玄传》则这样再现这个传说:“月色如昼,见一狐从林下将髑髅置于首,摇之落者不顾,不落者戴之。更取艿草堕叶,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娇娆女子。”[6]
南宋诗人陆游更吟诵过“野狐出林作百态,击下髑髅渠自怍”[7]的诗句。
这些文献记载的内容大同小异,都表述了狐精化身曼妙女子的过程。其中的几点要素不可或缺,即明月夜和骷髅头,而戴骷髅头并摇之不落成为变身成功与否的关键条件。这也印证了荀子说过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所谓“有辨”,这里即指拥有能思维的头脑。这里的狐精戴上死人的骷髅头,意为拥有了人的思想。这里的“辨”亦指“辩”。在中国的志怪传奇中,狐狸作为鬼魅怪异的灵兽,比起其他动物来除了具有幻化超能、妖惑人心等特性,还历来给人以聪明思辨的印象。如《任氏传》中的任氏、《阅微草堂笔记》中罗生在古冢投书乞赐得来的艳婢、宁波吴生所遇狐女等等,无一不能言善辩、出口成章,其辩才着实可圈点,个个堪称“思想家”。如《宁波吴生》中,吴生与一狐女时常幽会却依旧出入青楼,于是狐女幻化成其心仪的各色女子取悦吴生,但吴生仍觉“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于是如此开导好色吴生:
“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倾耳。中间两美相合,成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8]
一席话使吴“洒然有悟。后数年,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由此也可见狐狸的辩才非同一般。当然,这无非是作者借狐狸之口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狐狸所充当的角色却显现了狐狸在人们心中思维敏捷、睿智思辨的形象。
狐精戴骷髅于头顶拜月变身一节在原作《胡媚娘传》中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一狐拾人骷髅。戴之向月拜。俄化为女子。年十六七。绝有姿色。
而这一过程在浅井了意的笔下却是浓墨重彩。
道旁窜出一只狐狸,将死人的骷髅头置于脑顶,直立上身,面北揖拜,骷髅头随即落地。狐狸拾起骷髅戴上又做揖拜,照落不误,再拾起再戴,戴之再落,如此这般重复了竟有七、八回之多。终于骷髅头稳稳地戴在了狐狸脑顶,狐狸面朝北方揖拜了竟近百回。在一旁暗自观察已久的小弥太颇感不可思议,疑惑间只见那狐狸早已变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亭亭玉立,仪态万方。顾盼间风情万种,倾国倾城。
从这样入微的描写中可见狐精化人实属不易。对原作中的狐狸拜月,笔者以为在这里可以做以下解释,即月属阴,自古中国就有女拜月男祭灶的习俗。狐精既然要化身女子,自然要拜。另外,民间一直有月老为媒的说法,既然狐狸幻化美女意在结缘,就更加没有不拜的道理。而原作中的“向月拜”在《狐妖》中被改写成“面北揖拜”,这里的面北揖拜即拜北斗,北斗即北斗七星。这里的拜北斗和拜月应具同一意义。道教将七星崇奉为七位星神,以为祈禳北斗,可以化解灾厄,保命求生。狐精拜北斗为骷髅延命,最终还是要使骷髅起死回生,达到附人体的目的。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也有“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的文字。因此,较之原作,《狐妖》中让狐精拜北斗似更有依据。
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父调官陕西。适被盗。于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财物为之一空。独奴伏深草得存。残喘至此。今孤苦一身无所依托。将投水而死。
《狐妖》中的狐精也同样不堪贼寇劫掠烧杀之苦:
我是此地以北的余五郡人。此前木下藤吉郎大将欲攻占山本山城,在余五郡烧杀掳掠,我的父兄战死沙场。母亲惊吓成病,卧床不起。贼军将家中财宝洗劫一空,母亲厉声痛斥,惨遭乱贼斩杀。我惊恐万分躲在草丛中才得以逃命,残喘至今,成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儿。现在无处可去,一心只想投河自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浅井了意把日本战国时期武将织田信长进攻小谷城的史实融入其中,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为单纯的怪异小说打上了时代烙印。小谷城是日本五大山城之一,也是战国时期的诸侯浅井氏的居城,以戍防坚固著称。元龟三年(1572年),织田信长发起对小谷城的进攻,其后在连续4年的动乱中,小谷城最终陷落。对这个著名历史事件的借用,给故事平添了时代的色彩,使怪异小说具有了现实性。
整体看来,比起《胡媚娘传》《狐妖》的人物形象略显丰满,叙事也稍见细致。在忠实于原作风格的基础上,《狐妖》突出了自己的个性,可以看出在不影响题材主干的前提下,作者尽量于细节处对故事加以润色,在叙景、叙情、叙事上都显现出作者的文字功力。
二
如果说《狐妖》只是对原作的精雕细琢的话,《早梅花妖精》对原作的改编则显得大刀阔斧、气势恢宏。《伽婢子》卷十二的《早梅花妖精》改写自唐传奇小说《龙城录》中的《赵师雄醉憩梅花下》,《龙城录》旧题柳宗元撰,其真伪历来是学界争议之所在。这里暂且不做考证。原作《赵师雄醉憩梅花下》讲述的是隋开皇年间,一名为赵师雄的人迁官罗浮。天寒日暮,他在半醉半醒间将车马停在松林间酒肆旁歇息。见一淡妆素服美女前来迎接。暮色已深,残雪映月,二人相与欢笑。于是敲开酒肆,讨酒数杯共饮,稍后有一绿衣童子载歌载舞。不久赵师雄醉卧懵然,只觉得天寒地冷。天色将明,赵师雄起身一看,原来身在一棵大梅花树下,树上翠鸟啾鸣,赵师雄惆怅不已。
这是一则人与梅精相恋的异类姻缘故事。异类姻缘故事作为民间传说的一大类型,泛指人与异类之间的婚恋,而异类中最常见的是动物精的化身,植物成精的记述虽不多,却也散见于中国的古书中。如东晋祖台之所著《志怪》中就有以下传说:
此时,由于d1点、d2点均接地,相当于在两个接地点间短接。根据欧姆定理,电压220V、电阻为零,电流无穷大,电源开关跳闸、熔断器熔断,如开关跳闸及熔断器熔断失败,还可能烧损电源及电缆绝缘等,非常危险。而该回路中的负荷1至负荷4,由于两侧电压均为零,没有电流流过。
蹇保至檀丘坞上北楼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黄练单衣、白袷,将入人炬火上楼。保惧,藏壁中。须臾,有二婢上,使婢迎一女子上,与白袷人入帐中宿。未明,白袷人辄先去。如是四五宿。後向晨,白袷人才去,保因入帐中,持女子问:“向去者谁?”答曰:“桐侯郎,道东庙树是也。”至暮鼓二中,桐郎来,保乃斫取之,缚着楼柱。明日视之,形如人,长三尺馀。槛送诣丞相,渡江未半,风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风波乃息[9]77。
老树经年成怪,这里的“桐郎”实为梧桐树的化身。
《异苑》中《赤苋魅》讲述的是鲜卑女怀顺诉其姑女被赤苋幻化的妖怪所魅惑的故事: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侍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9]131。
苋是一类草本植物,赤苋为其中一种。在古代人眼中,不仅动物,山川草木、森罗万象皆有神灵宿于其中。以上两则讲述的均为植物精化身人类男女兴妖作怪之事。
虽同为植物精,比起以上两则,《赵师雄醉憩梅花下》中的梅精就显得只见灵气、不见妖气了。原作文字精炼、情节简单,虽然没有诗情却也不无画意,比如对景色的描写“残雪对月色微明”宛若一幅风景画,对梅精的描写“淡妆素服……芳香袭人”又像一卷仕女图。
然而这一切在浅井了意的笔下,被改写成既有画意又富诗情的一篇名符其实的诗情画意之作。《早梅花妖精》以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武田信玄和村上义清之间的争霸战为时代背景,讲述主人公武士埴科文次(即原作中的赵师雄)是个感风吟月的重情之人,习武的闲暇仍不忘吟诗作歌。战乱时节也常在战斗间歇即兴赋诗,深得将士喜爱。一日出征前听闻信州伊奈郡开善寺的梅花开得茂盛,当晚携仆役一人在夜色中循梅香来到开善寺,身在梅林中不禁吟诵起来,一首汉诗咏罢,月下寒梅激发诗兴,不禁复吟和歌一首。歌罢见一绝色女子携一婢女也站在月下作歌咏梅。二人相互倾慕,于是文次命仆役寻酒家坐屋檐下与女子交杯换盏,二人作歌对答,你唱我和,情深意切,共度良宵。文次在微醉中昏昏睡去。天色微明,文次醒来发现自己醉卧梅树下,从衣袖上残留的梅香猜出昨夜遇到了梅精。想到崔护的“人面桃花”一诗不禁惆怅不已。回到营地,依旧难忘女子模样,文次怅然若失无限伤感。至暮色降临愈发怀恋,悲从中来而泪流不止。文次对女子思慕过度,痛觉世事无常。次日,文次战死沙场。
虽然同样是巧遇梅精的故事,但是原作篇中基本没有涉及到“梅”,只于篇末以“乃在大梅树下”点题。而《早梅花妖精》却以梅花开篇:
在信浓国伊奈郡有个开善寺,那里年年盛开早梅花,寺院里的梅树为稀世古木,远近闻名。每年冬至前后开始绽放,梅花凌寒独自开满枝头,香飘四溢,芬芳澄明无比。远乡近邻的人们探访而来,每日会聚于此,一解梅花风情。
接下来的大段文字依旧与寺中梅花相关,作者对梅花的描述为其后梅精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主人公埴科文次被塑造成文武双全、才情兼备的风雅之士:
文次是一个待人宽厚、古道热肠之人。在习武的余暇,对吟诗作歌仍留恋难舍,即使在出征途中,于触景生情之处也不忘作歌表达思绪,令诸军武士感佩。如此优雅之士获众口交赞。
这一形象塑造不仅使主人公显得丰满真实,也为丰富故事的内涵增添了话题。
对梅精的赞誉作者也不吝笔墨:
芳龄二十,身着白色小袄衬红梅色长裙,佳人之绝色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举止娴雅,更疑似天人临世。
故事背景一如《狐妖》的设计,将历史事件进行真实再现:
时值甲州的武田、信州的村上两家争战天下,双方摆好阵势蓄势待发,准备决一死战。
这里的武田、村上两族的争斗指的是甲越之战,把历史人物揉进并不复杂的情节,读来临场感强烈。
文中汉诗和和歌的插入堪称对翻改小说的一次革命。如前所述,原作虽然文字简洁,故事短小精悍,但其唯美意境却不容忽略。《早梅花妖精》运用诗赋将这种意境进一步加以升华,拓展了审美的广度和深度。文中共插入5首和歌、2首汉诗。主人公初入梅林,所吟苏东坡的一首“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便开启了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暮色寒梅,暗香疏影,令人感觉连寺内钟声都扬起梅花的香气。于是主人公一首“寺梅映暮色,花香袭晚钟”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而梅精面对年年岁岁盛开的梅花,看新蕊思旧影,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庭上梅枝挂旧影,遥思昔日嗅陈香”。接下来文次与梅精唱和:
文次:落梅衣袖留香,痴梦空遗枕上。梅精:夜枕落梅寝憩,晨起香漫霓裳。
二人两情相悦,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进而创造出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唱和的效果增加了作品的抒情性。这两首歌有如下意向,即衣袖、梦境、梅花和梅香,这些意向共同构成了一幅融情于境的画面,虚实相生,情景交融。诚如明代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所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可见作者在此处的添笔恰到好处。当文次醒来发现女子不见,空留梅香时,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仍旧笑春风”正体现了主人公的凄清迷茫。文次最后吟诵了一首“梅香浸衣袖,夕来落春雨”,以春雨比喻自己的眼泪,意指每当夜幕降临,都会泪洒残留着梅香的衣袖。衬托了《早梅花妖精》的悲凉感。
比起原作,《早梅花妖精》的人物塑像、情境描写、背景衬托、情节构成都更加完整,其文学性和现实性都值得肯定。作为一部翻改小说,可以说《赵师雄醉憩梅花下》为其提供了一个题材纲要。而改编者对提纲恰恰做到了充分领会和合理发展。如在原作中,梅精登场后,“师雄喜之与之语”,改编者将这寥寥数字改写成文次与梅精二人初相识的精彩片段:
文次听罢女子的咏叹,煞是好奇。不禁走近女子,牵其衣袖调侃道:“与今夜月色争辉的不只这寺中梅花,还有佳人你的绰约身姿啊”。女子对文次的举动丝毫未感讶异,而是沉着应答:“我踏梅香而来,方才是对月有感而发。倒是于暮色中能邂逅您这般风雅之士,才令人心情愉悦呢”……
以上文字既有神态、动作描写,又插入对话,以主人公初遇梅精时的恬淡闲适与文末怅然战死沙场的结局相对照,这种有意铺陈足见作者“讲故事”的功力。
结 语
以上列举了《伽婢子》中改写自中国小说的《狐妖》和《早梅花妖精》二篇。通过对比分析,作为翻改小说,比起原作,两作品都显示出各自的特性,在文学性和现实性上都实现了超越。如果说《狐妖》中部分翻改于原作的平淡叙述基本没有脱离原作之框架的话,那么《早梅花妖精》一篇,则体现出中国出典与日本文学传统的契合,可以称它为几乎接近但不依附于原作的另一版本的原创作品。从中也可看出浅井了意在改编时有意摒弃怪异小说惯有的记录性、力求生动性的创作技法以及一个作家强烈的创作意识。
“伽婢子”的日文词义为丝绢做的偶人娃娃,这种白绢作衣、黑线作发的绢偶人在日本民间被当做幼儿的辟邪之物,被认为具有驱灾除煞的功能。对于以此物命名该书的缘由,《伽婢子》的作者在序文中做出了如下解释:“该书不为硕学之人明目洗耳,只为教化幼童改邪心、赴正道”。可见该书具有明显的训诫意图,与中国志怪传奇所体现的宗教、伦理思想一脉相承。日本江户时期,谈论鬼魅妖怪、殊方异物的风气盛行,人们崇尚谈论魑魅魍魉。荒诞离奇的中国志怪传奇恰好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志怪传奇题材的翻改小说应运而生,翻改骤然成风。中国的志怪传奇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影响既深且广,然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的志怪传奇在翻改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形变。这些翻改小说既保持了中国志怪传奇的怪异性,又融入了日本本土的民俗风情,可谓中国古典与日本文化的完美结合。
[1]矶田光一.新潮日本文学词典[M].东京:新潮社,1988:15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76.
[3]太刀川清.百物语怪谈集成[M].东京:国书刊行会,1987:7.
[4]干宝.搜神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0:112.
[5]太平广记引集异记.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46-147.
[6]赞宁,范祥雍.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89.
[7]陆游诗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6:58.
[8]曹月堂,周美昌.评注阅微草堂笔记选[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253.
[9]前野直彬.六朝唐宋小说选[M].东京:平凡社,1968:77.
[10]唐志远.六朝《异物志》与文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74-79.
[11]勾艳军.日本近世戏作小说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J].日本问题研究,2012(2):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