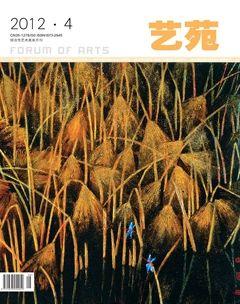二胡艺术形成的“催化剂”: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
李祖胜
【摘要】本文从文化学的视角,通过探寻刘天华与其成长的江南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现正是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并立志革新国乐,从而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形成。
【关键词】 二胡;江南;外因在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将二胡搬上独奏舞台从而形成二胡艺术之前,二胡一直是在江南(指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流行的民间乐器。由于江南地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等方面具备的优越性,自明清以来,在江南商品经济的带动下,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事业、民俗活动、各种音乐艺术品种等等的繁荣,为二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至民国初年,江南民间二胡不仅具备了宽阔的音域、良好的乐器音质音色,而且也具有丰富的左右手演奏技法,这是同时代的其它胡琴类弓弦乐器无法比拟的,它为二胡艺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合力的结果,如果说江南社会在明清以来的各种文化因素是导致二胡艺术形成的内因,那么,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引起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沧桑巨变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也引发中国音乐人士的国乐革新之思,这成为了二胡艺术形成的外部诱因。
在二胡艺术形成的20世纪初,江南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及音乐文化变革转型的先行、枢纽地区,是中西文化共存之所在。中西音乐文化长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并存,为彼此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机会,音乐文化变迁成为一种必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或是个人内心在接受了他种类型文化后在文化观念上的排斥与认同,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变迁,文化变迁由人来完成。具有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和技法的现代二胡独奏艺术就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变迁出来的“一条新路”。引领这一文化变迁的人正是刘天华。刘天华之所以能引领这一文化变迁,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江南地区正处于中西音乐文化并存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中西音乐文化并存使他得以接触和学习中西两种音乐文化,强势的西方音乐文化的不断刺激引起刘天华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从而催生了现代二胡独奏艺术。所以说,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是二胡艺术形成的“催化剂”。
一、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而西学东渐的第一站就是江南重镇——上海。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曾将西学第一次传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人徐光启、杭州人李之藻为首的“西学派”。此后,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成了西学的主要传播群体。上海作为西学的传播中心,对二胡艺术形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航线的中心点,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北可通过东海或运河连通黄河地区,交通十分便利。并有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作它的贴身腹地。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条件把上海推向中国近代化的最前沿。1842年在南京江面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对外的开放和外贸的扩大,江南的商品经济开始融入到国际市场之中,如棉纺织业这种制作工序比较简单的行业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洋纱洋布价格十分便宜,致使土布日益被排挤,苏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已成普遍现象,“而土布之销数日绌,小民生计维艰”[1]7。为了谋求生计,江南农村大批的劳动力涌入上海,各地的商帮也纷纷涌入上海经商。上海在中西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由于江南各地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在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江南各地出现起了一批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而增强了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品流通。正是这种商品流通以及往返于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人、民工所携带的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信息,促使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整体。所以,1912年,当刘天华在读的常州府中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课时,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也融入到前往上海打工的潮流当中,刘天华才有机会在上海的“开明剧社”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洋音乐。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入,诸多学者认为主要通过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和学堂乐歌这三个途径[2]17。在这三个方面,江南地区比同时代的中国其它地区更为普遍和深入。西方教会学校具有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以及音乐、体育、美术等多学科综合教育功能。这类学校大都面向社会,接纳非教徒子女入学,因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是很深的。据统计,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而江南因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和领先的经济、文化地位,教会学校亦不在少数。在上海,像徐汇公学、裨文女塾、女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等等,都是西方传教士在旧上海创办的知名学堂。教会学校开展的宗教歌咏活动开启了中国人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大门。当然,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的三种途径中,最让刘天华受益的是后两者。
新制学堂的广泛建立和乐歌课的开设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历来都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江南地区,各级各类公办与私办的新式学堂不断涌现,并且大多數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都开设有音乐课。刘天华之父——江阴秀才刘宝珊在19世纪末就开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历史刚刚跨入20世纪,刘宝珊就与当地知名人士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了新式的翰墨林小学,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早的。刘天华1903年入学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英语、数学、博物、体操、美术、音乐等新式课程。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洋学堂”。新兴的西式教育和学唱学堂乐歌的经历对幼小的刘天华在音乐观念上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刘天华的西方音乐思维的经历则是他在常州五中学习铜管乐的两年。
军乐队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外国人在英美租界创办了一个上海公共管乐队。清末民初,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在中国还不是十分普遍,但相比较而言,江南的军乐队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江南的许多中学堂都成立了军乐队。据《中国军乐队谈》一文记载,至该文发表的1917年,在江南存在的相当著名的军乐队就有:上海工部局军乐队、上海土山湾军乐队、苏州东吴大学军乐队、上海南洋公学军乐队、常州第五中学(即常州府中学堂)军乐队等。[3]190-1911909年,刘天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学校就已经有了一个规格不错的军乐队。他“参加了校中的军乐队,把乐队中所有的乐器都学会了,特别是对铜管乐器更有莫大的兴趣,因此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对铜管乐的掌握已达到校内首屈一指的程度”[4]35。1915年他从上海回来,执教于母校时,由他指导的军乐队已经能演奏“威武雄壮的《马赛曲》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俄罗斯进行曲》,还有《第六号进行曲》、《第七号进行曲》以及各种序曲、优美动听的小夜曲等”[4]72有相当演奏难度的乐曲。在学习和指导西洋管乐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音乐迥然不同的西洋管乐的音乐风格、创作手法对刘天华在后来进行的国乐改进和音乐创作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1912年,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在熟人的推荐下,刘天华加入到“开明剧社”的乐队,担任小号手,有时还给乐队编曲。“开明剧社”乐队是一个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混编的乐队,钢琴、提琴等各种西洋管弦乐器应有尽有,这使得第一次来上海的刘天华大开眼界。刘天华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西方音乐。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万国音乐队(即上海公共乐队)学习,并利用一切机会,钻研音乐理论,学习多种西洋管弦乐器,尤以铜管乐进步最快,而钢琴和小提琴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的(1)。当时的上海,西洋管弦乐、小提琴演奏家的演出已不少见,刘天华又在西洋乐队中工作。在对小提琴及整个西方音乐文化耳濡目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中,使他得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音乐,从学习乐器到掌握西方音乐的音乐风格、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等方面,比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管乐时显然更加深入和全面。通过小学、中学和在上海期间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接触与学习,刘天华对西方音乐从演奏技巧到音乐理念的把握已经相当精到。
当然,刘天华尽管从小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但他毕竟出生在民间音乐传统十分浓厚,滩簧、十番锣鼓、江南丝竹等民间音乐盛行的江阴。江阴城内的孔庙和涌塔庵,每逢春秋祭祀,僧家佛事,都是钟鼓、丝竹之声不断,庙会、集日各类民间音乐云集。刘天华从小就可听到邻居汪阿大用笛子和二胡演奏五更调、梅花三弄、孟姜女等民歌小调和江南丝竹器乐曲[4]27,擅长演奏笛子和二胡等乐器的涌塔庵彻尘小和尚跟刘天华从小也是形影不离,一起吹笛、拉琴玩音乐。从出生之日开始就置身于各种民间音乐熏陶当中的刘天华依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虽然从小也学习了西方音乐,却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了作为传统中国人在音乐文化方面具有的“民族性”。他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扬弃和汲取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的养分。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多依附于各种稳态的民俗,民俗内涵成为音乐的主要表现内容。而作为经受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刘天华需要用音乐来表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的忧患情绪、思想以及个人的前途、人生意义。中国传统音乐的民俗性音乐内涵不足以表现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的情感内涵。通过学习西方音乐,刘天华知道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的原创性理念和技法能帮他实现这一音乐表现的愿望。但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劉天华身上积淀的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所以,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充满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趣味。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类型在他内心的碰撞,使他改变了江南丝竹通过改编和加花变奏等方式来创新乐曲的创作观念以及民俗性音乐内涵,这种创作观念的改变却并没有舍弃的是,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五声性音调以及咿呀如语的滑音奏法等民族性音乐特征。
1914年,刘天华从上海回到江阴,拜师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学习二胡和琵琶,1915年刘天华便开始创作他的二胡处女作——《病中吟》。《病中吟》全曲的原创性和三部性构思体现出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而源自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旋法则又充分体现出乐曲的“民族性”。
从刘天华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是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具备了创造新型二胡音乐文化的能力。
二、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中西音乐并存的强烈反差促使刘天华立志革新国乐
诚然,中西并存的江南音乐文化环境虽然能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但如果刘天华对中西音乐没有主观的学习兴趣和目的,也不会如此努力。应该说,从小学到中学,刘天华学习西方音乐还仅凭个人兴趣,毕竟此时的刘天华还未成年。1912年,经受过辛亥革命洗礼的刘天华跟随其兄刘半农到上海谋生,当时的上海崇洋之风盛行,坐洋车、穿洋服、欣赏西洋音乐等等都成为上海人最时髦的生活习惯。西洋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比,已经在人们的娱乐生活当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传统音乐处于十分萧条的状况。笔者认为,刘天华正是在上海耳闻目睹了中西音乐文化在市民音乐生活中如此悬殊的不同待遇,感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音乐文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强烈对比反差,接触了各种立志改进国乐的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后,引发对国乐前途的思索,从而开始了他不遗余力地改进国乐的漫漫征途,而二胡成为了他改进国乐的突破口。
清末民初,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体系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下逐渐开始瓦解,开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不求社会发展、但求社会稳定的封建统治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不需要鼓舞国民进取精神,而是被希望具有能化解阶级矛盾的“中和之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直没有走上专业化创作的道路,而在民间自生自灭,具有浓重的民俗性、地域性、自娱性特征。而西方音乐文化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专业化创作的道路,经过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至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西方音乐文化已经饱含着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属性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然比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更适于中国近现代广泛掀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就需要一种以宣扬资产阶级积极进取、追求民主与自由为精神内涵的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出现。因此,到20世纪初,国乐革新很快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又有江南能深入接触西洋音乐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而成为了国乐革新的主要实践群体。立志“改进国乐”的刘天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而是众多国乐革新者中的一员。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各种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等不断涌现,出现了周少梅、郑觐文、卫仲乐、汪昱庭、张萍舟、王巽之、程午嘉、李廷松等一大批国乐革新的积极实践者。在刘天华1922年离开江南前往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之前,江南的国乐革新早已酝酿成星火燎原之势。
那么,刘天华为何要以二胡为国乐革新的突破口呢?这来自于与二胡同为弓弦乐器并形成强烈对比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小提琴传入中国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侨居上海的西洋人为了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将小提琴带入了他们的新居住地,并运用于他们的娱乐活动中。当时的戏院演出是“华人”与“西人”都可欣赏的,中国人欣赏小提琴音乐是常见的事情。
至20世纪初,上海开始出现西洋管弦乐队,乐队中的提琴类乐器已经相当完备。如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原本是一支铜管乐队,1907年被扩大为管弦乐队。乐队不仅演出仪式音乐,还经常单独举行定期音乐会。从1911年的音乐会节目单,可以知道当时乐队的编制情况为:第一小提琴四把、第二小提琴四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二把、低音大提琴二把、长笛二支、双簧管二支、单簧管二支、大管二支、小号二支、长号二支、打击乐一人,共计30人[5]97。乐队成员都是外国人。作为一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弦乐组的乐器编制是比较齐全的。随着小提琴音乐在上海的影响逐渐扩大,也逐渐有中国人开始学习小提琴。如学堂乐歌的先驱者之一——曾志忞,其夫人曹汝锦女士在1901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高寿田也于1903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1907年曾志忞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式的“上海贫儿院”,并在其中特别设立了一个“音乐部”,高寿田就任该部主任。在高寿田和曹汝锦的帮助和直接参与教学下,曾志忞在学习音乐的贫儿中选出约四十人组织了一个西洋管弦乐队,也是第一个全由中国人任演奏员的西洋乐队。弦乐组是西洋管弦乐队中需要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所以,在这个乐队中,学习和演奏提琴的乐队成员应该不下20人,这对推广西方提琴音乐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提琴音乐在上海的逐渐广泛传播,1912年,当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时,刘天华才得以接触和学习小提琴。
当时的小提琴早已是西方音乐的“弦乐之王”,而中国的二胡类胡琴乐器虽然是“环视国内皮黄、梆子、高腔、滩簧、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那一种离得了它”[6]?却仍被认为其“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正是這一中一西两件弓弦乐器的不同命运,使得刘天华决定以二胡为突破口来革新国乐。
刘天华的胞弟——二胡教育家刘北茂先生也认为,刘天华是在上海“开明剧社”时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的,他谈到:“刘天华在1927年8月1日给《国乐改进社》撰写的《我对本社的计划》一文中曾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头脑中蕴藏了恐怕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见《国乐改进社成立刊》)天华先生于1912年至1914年在上海‘开明剧社工作,距离上面所说的时间正好是‘不止十年。故上面一段话,正好可以印证他在上海‘开明剧社时已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4]54笔者对刘北茂先生的观点是非常认同的,对于“垂绝的国乐”的体会,只有在洋乐盛行,国乐萧条的上海才能体会得最为深切。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江阴,1915年他就开始了二胡曲《病中吟》的创作,就是说此时的刘天华已经开始了改进国乐的征途。《病中吟》全新的西方音乐创作理念,显然跟他在上海的工作和学习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说,如果没有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刘天华就看不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与西方音乐文化较量中的孱弱无力,他就不会想到要革新国乐,因而就不具备有二胡艺术形成的充备的外部诱因,中国弓弦乐器地位的提升恐怕至少退后数年。反言之,正是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成就了刘天华,成就了二胡艺术。
二胡经过江南的戏曲、曲艺、吹打乐、丝竹乐等江南音乐文化的历史熏陶,经过历代江南艺人的继承和发展,积累着能形成二胡艺术的内在潜质。到清末民初,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江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地位,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了中西音乐并存的文化环境,中西音乐文化的强烈反差引发以江南人为主体的国乐革新者之思,刘天华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得以学贯中西,并以二胡为突破口来改进国乐,二胡艺术才得以形成。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对二胡艺术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注释:
(1)此段内容主要参见刘北茂《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中“上海之行”一节,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版。
参考文献:
[1]朱寿明.东华续录[M].光绪,一四九.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3]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刘北茂.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5]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M].彭谨,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6]刘天华.《月夜》说明[J].音乐杂志,一卷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