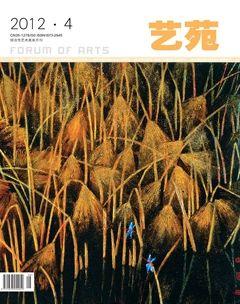《朱子语类》“乐”论诠释学美学初探
刘基玫 邹其昌
【摘要】本文主要对《朱子语类·乐》部分的礼学诠释学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索,包括朱子乐论诠释学美学基本结构及其重要觀点等。“乐”历来属于“礼学”的内在组成部分,礼乐合一是华夏文化和华夏美学的核心。《朱子语类》“乐”论诠释学美学是朱子礼学诠释学美学的核心内涵。
【关键词】 朱子礼学诠释学美学;《朱子语类》;乐论朱子乐律学思想不只是展示在其自己著述或编撰的文献之中,更活跃于平日交谈之中。因此,朱子乐律学文献中《朱子语类·乐》(1)具有重要的美学研究价值。“乐”论较为鲜活地展示了朱子与其门人畅谈乐律学问题的场景,并成为了研究宋代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源。《朱子语类》“乐”论所涉及的音乐问题很广泛,其中包括朱子的基本礼乐观,更包括朱子对乐律、乐教、乐礼、俗乐、外来音乐等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去研究。
一、《朱子语类》“乐”论美学体系概述
《朱子语类》“乐”论中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朱子“乐论”美学体系建构要素问题。那么朱子“乐论”美学体系建构要素有哪些呢?通过考察梳理,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关于音乐的审美标准问题,朱子反复申言“中声为定”的理论:朱子在讨论乐律与古尺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
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季通尝截小竹吹之,可验。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牛鸣盎中”,谓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笑云:“如此议论,又却似在乐不在德也。”(2)
音律如尖塔样,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惟五声者中声也。
(二)关于中国传统乐律问题,朱子重新阐述“三分损益”理论。关于“三分损益”理论,《管子·地员篇第五十八》中指出:“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史记·律书》、《通典》等著作中进一步阐发。朱子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因论乐律,云:“尺以三分为增减,盖上生下生,三分损一益一。故须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厘,一厘分九丝,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杰录云:‘律管只以九寸为准,则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损一,如破竹矣。其制作,《通典》亦略备,《史记·律书》、《汉·律历志》所载亦详。范蜀公与温公都枉了相争,只《通典》亦未尝看。蜀公之言(2336页)既疏,温公又在下。”
(三)关于律吕规律问题,朱子反复争辩“还相为宫”理论:《礼记·礼运》中曾记载过“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的命题,后世乐律学家都曾做过很多研究和阐释。其中孔颖达汇集了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加以说明。朱子对此也进行过讨论。如:《朱子语类》曰:
乐律:自黄钟至中吕皆属阳,自蕤宾至应钟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
自黄钟至中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钟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关于“钟律”,《仪礼经传通解·钟律第二十二》中引述了朱子与其门人蔡元定共同创作的“律吕相生图”:[1]486
《礼记注疏》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处,分明。
旋宫:且如大吕为宫,则大吕用黄钟八十一之数,而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又用林钟五十四之数,而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其余皆然。
问:“先生所论乐,今考之,若以黄钟为宫,便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林钟为征,南吕(2337页)为羽,应钟为变宫。若以大吕为宫,便是夹钟为商,中吕为角,林钟为变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黄钟为变宫。其余则旋相为宫,周而复始。若言相生之法,则以律生吕,便是下生;以吕生律,则为上生。自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本当下生,今却复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相生之道,至是穷矣,遂复变而上生黄钟之宫。再生之黄钟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余。然黄钟君象也,非诸宫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复用,所用只再生之变者。就再生之变又缺其半,所谓缺其半者,盖若大吕为宫,黄钟为变宫时,黄钟管最长,所以只得用其半声。而余宫亦皆仿此。”曰:“然。”又曰:“宫、商、角、征、羽与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征、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去声。相连接处。”
“‘旋相为宫,若到应钟为宫,则下四声都当低去,所以有半声,亦谓之‘子声,近时所谓清声是也。大率乐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声不得过宫声。然近时却有四清声,方响十六个,十二个是律吕,四片是四清声。古来十二律却都有半声。所谓‘半声者,如蕤宾之管当用六寸,却只用三寸。虽用三寸,声却只是大吕,但愈重浊耳。”又问声气之元。曰:“律历家最重这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差,向下都差。”饶本云:“因论乐,云:‘黄钟之律最长,应钟之律最短,长者声浊,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为君,商为臣。乐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如今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四清声,清声是减一律之半。如应钟为宫,其声最短而清。或蕤宾为之商,则是商声高似宫声,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宾律减半为清声以应之,虽然减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应也。此是通典载此一项。又云:‘乐声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乐中上声,便是郑卫。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当王朴造乐,闻其声太急,便令减下一律,其声遂平。徽宗朝作大晟乐,其声一声低似一声,故其音缓。又云:‘贤君大概属意于雅乐,所以仁宗晚年极力要理会雅乐,终未理会得。”
律递相为宫,到末后宫声极清,则臣民之声反重,故作折半之声;然止于四者,以为臣民不可大于君也。事物大于君不妨。五声分为十二律,添三分,减三分,至十二而止。后世又增其四,取四清声。
关于朱子乐律学思想来源,大致有《管子》、《史记·乐律》、《汉书》、《隋书》、《通典》,《注疏》、王朴以及近世诸公如范蜀公、司马温公、沈括、蔡元定等。
二、《朱子语类》“乐”论中俗乐问题
“俗乐”问题,在朱子时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朱子的态度和基本精神是“礼乐随俗”,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和于“中声”,以维护正统礼乐观念。《朱子语类》中有很多的讨论。如:
今朝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乐府做,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
“詹卿家令乐家以俗乐谱吹《风》《雅》篇章。初闻吹《二南》诗,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都不成模样。”因言:“古者《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乐律》中所载《十二诗谱》,乃赵子敬所传,云是唐开元间乡饮酒所歌也。但却以黄钟清为宫,此便不可。盖黄钟管九寸,最长。若以黄钟为宫,则余律皆顺,若以其他律为宫,便有相陵处。今且只以黄钟言之,自第九宫后四宫,则后为角,或为羽,或为商,或为征。若以为角,则是民陵其君矣;若以为商,则是臣陵其君矣。征为事,羽为物,皆可类推。《乐记》曰:“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故制黄钟四清声用之。清声短其律之半,是黄钟清长四寸半也。若后四宫用黄钟为角、征、商、羽,则以四清声代之,不可用黄钟本律,以避陵慢。故《汉志》有云:“黄钟不复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声,若遇相陵,则以清声避之,不然则否。惟是黄钟则不复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续笔谈》说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则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说:“古人亦有时用黄钟清为宫,前说未是。”
赵子敬送至《小雅》乐歌,以黄钟清为宫,此便非古。清者,半声也。唐末丧乱,乐人散亡,礼坏乐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声。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声,又有变声六。谓如黄钟为宫,则他律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不用黄钟之正聲,而用其子声。故《汉书》云“黄钟不与他律为役”者,此也。若用清声为宫,则本声轻清而高,余声重浊而下,《礼书》中删去乃是。乐律,《通典》中盖说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马公李照辈,元不曾看,徒自如此争辨也。《汉书》所载甚详,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载甚略,然都是要紧处。新修《礼书》中乐律补篇,以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一分为九,一厘为九毫,一毫为九丝。
俗乐中无征声,盖没安排处;及无黄钟等四浊声。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宫某宫云。今乐起处差一位。
洛阳有带花刘使,名几,于俗乐甚明,盖晓音律者。范蜀公徒论钟律,其实不晓,但守死法。若以应钟为宫,则君民事物皆乱矣。司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于《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说得分晓。《史记·律书》说律数亦好。此盖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般,更无安排。但数到穷处,又须变而生之,却生变律。
问乐。曰:“古声只是和,后来多以悲恨为佳。温公与范蜀公,胡安定与阮逸李照争辩,其实都自理会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说得极分明,盖此书在唐犹有传者,至唐末遂失其传。王朴当五代之末杜撰得个乐如此。当时有几钟名为‘哑钟,不曾击得,盖是八十四调。朴调其声,令一一击之。其实那个哑底却是。古人制此不击,以避宫声。若一例皆击,便有陵节之患。《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唐人俗舞谓之‘打令,其状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记不得。盖招则邀之之意,摇则摇手呼唤之意,送者送酒之意。旧尝见深村父老为余言,其祖父尝为之收得谱子。曰:‘兵火失去。舞时皆裹幞头,列坐饮酒,少刻起舞。有四句号云:‘送摇招摇,三方一圆,分成四片,得在摇前。人多不知,皆以为哑谜。”汉卿云:“张滋约斋亦是张家好子弟。”曰:“见君举说,其人大晓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处,见其教乐,又以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只用《太常谱》。然亦只做得今乐,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只以某调终之,如《关雎》‘关字合作无射调,结尾亦著作无射声应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钟调,结尾亦著作黄钟声应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则是清声调,末亦以清声调结之;如‘五月斯螽动股,‘二之日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浊声,黄钟调,末以浊声结之。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征、羽,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征、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
戊己土,“律中黄钟之宫”。詹卿以为阳生于子,至午而尽,到未又生出一黄钟。这个只可说话,某思量得不是恁地。盖似些元亨利贞。黄钟略略似个“干”字,宫是在“中”字中间,又似“是非”在“恻隐”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征,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说宫声。如京房律准十三弦,中一弦为黄钟不动,十二弦便拄起应十二月。[2]2238-2239
三、《朱子语类》“乐”论中的外来音乐问题
朱子考察音乐还特别关注外来音乐问题。中华音乐的发展应该是长期内外交流与传播发展的结果。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高度繁荣,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越来越广泛与深入。朱子在考察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外来音乐进行过探讨。在此,我们可以略举几例加以阐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涉及到外来文化因素的事物,在命名上常常有一定的标识。如《营造法式》中大量关于外来的文化事件大多在原名称前使用“海”,“海石榴华”。也有用“胡”字的,如“胡人”、“胡服”、“胡乐”、“胡萝卜”、“胡琴”等。
关于“胡乐”问题,《朱子语类》中曾有一段记载叙述过朱子的观点:
今之乐,皆胡乐也。虽古之郑卫,亦不可见矣。今《关雎》《鹿鸣》等诗,亦有人播之歌曲。然听之与俗乐无异,不知古乐如何。古之宫调与今之宫调无异,但恐古者用浊声处多,今乐用清声处多。季通谓今俗乐,黄钟及夹钟清,如此则争四律,不见得如何。《般涉调》者,胡乐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齐闻《韶》”,据季札观乐,鲁亦有之,何必在齐而闻之也?又,夫子见小儿徐行恭谨,曰:“《韶乐》作矣!”
此处记载显示,朱子认为,当今(宋代)的音乐主流是外来音乐(今之乐,皆胡乐也)。究其原因,朱子从音乐的基本规律入手进行探讨,认为当时流行的音乐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乐律标准,也就是完全不符合传统古乐的基本规律。即使用古代所谓“郑卫”之乐的标准来衡量,也很难找到其依据,就更不用说古代的雅乐标准了。所以他说:“虽古之郑卫,亦不可见矣。”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古乐新奏、“雅俗合流”等现象。如“今《关雎》《鹿鸣》等诗,亦有人播之歌曲。然听之与俗乐无异,不知古乐如何。古之宫调与今之宫调无异,但恐古者用浊声处多,今乐用清声处多。季通谓今俗乐,黄钟及夹钟清,如此则争四律,不见得如何。”还有《般涉调》这样的外来乐名。朱子也谈及了孔子时代的《韶乐》就已有广泛的音乐交流与传播现象。
除了有特别的表示之外,外来事物也有直接用音译的方式來表示。如《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子谈论“苏祗婆”的外来音乐:
南北之乱,中华雅乐中绝。隋文帝时,郑译得之于苏祗婆。苏祗婆乃自西域传来,故知律吕乃天地自然之声气,非人之所能为。译请用旋宫,何妥耻其不能,遂止用黄钟一均。事见《隋志》。因言,佛与吾道不合者,盖道乃无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乐律,则有数器,所以合也。
此处我们更加明确地了解到,中国古代所谓的本土音乐(中华雅乐)受到最大的一次冲击,是在南北朝。这就是朱子所说的“南北之乱,中华雅乐中绝”。“绝”字,说明外来音乐在中华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传统之“雅乐”已经到了“绝灭”之境地。
朱子讨论了隋文帝时期的外来音乐“苏袛婆”风格。据朱子考证,“苏袛婆”传自于西域,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种外来音乐也自然进行了“民族化”过程,大胆地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并按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如“黄钟”等进行改造和融合,获得成功。朱子由此也延伸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大问题,并提出“佛与吾道不合者,盖道乃无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乐律,则有数器,所以合也”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具有“中学为体”和“洋为中用”等思想。正是这一宏阔气象,自朱子学术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才真正获得了新的生机。
那么“苏袛婆”到底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如何呢?《隋书?音乐志中》对此有较为完整的记载:
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恆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簇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余篇,以明其指。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从译议。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众皆从之。夔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己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曰:“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玄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今译唯取黄钟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而又非其七调之义,曰:“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时牛弘总知乐事,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高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高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3]345-348
上述仅对朱子乐律学思想进行了简要说明,很多问题尤其是具体文本的细读还有待于深入系统地挖掘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