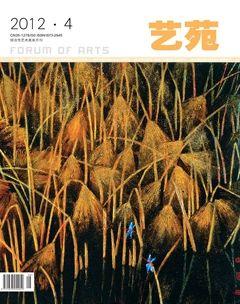《盛明杂剧》中的单折剧研究
莫雅丽
【摘要】《盛明杂剧》中收录的单折剧从内容来看,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强烈反抗情绪及讽刺骂世,揭露现实官场、科场黑暗的剧作;另一类是态度较为平和的抒情剧,主要表现人生理想、避世逃名,将情绪诗化的剧作。《盛明杂剧》中收录这么多的单折杂剧,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各种原因和一定用意的。
【关键词】 《盛明杂剧》;沈泰;单折剧《盛明杂剧》是明末沈泰选编的一部明杂剧集,分初集、二集,约先后出版于崇祯二年(1629年)和崇祯十四年(1641年),每集收剧作三十种,均为本朝盛行的杂剧。从《盛明杂剧》序文中可知,沈泰,字林宗,钱塘人,号西湖福次居主人,与明末杂剧家袁于令、徐翙以及程羽文、张元徵互为友朋,仅此而已。具体生卒年已无法确定,只能大致推断他活动于明末,其交往也未见诸文学家年谱。《盛明杂剧》收录的明代杂剧,多为明嘉靖后的作品。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杂剧现存266种,则《盛明杂剧》收录数量不可谓不多,正如曾永义先生所说:《盛明杂剧》“为明代杂剧作品最丰富而重要之总集。”[1]53庄一拂《汇考》还显示,明代一折剧106种,数量几乎占到所有明杂剧的一半,而现存的58种,有23种收录于《盛明杂剧》中,确实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盛明杂剧》中收录的23种单折剧分别是:汪道昆的《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徐渭《四声猿》之一的《渔阳弄》;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和《文姬入塞》;沈自徵的《霸亭秋》、《鞭歌姬》、《簪花髻》;叶宪祖的《北邙说法》;王衡的《真傀儡》;许潮的《武陵春》、《兰亭会》、《写风情》、《午日吟》、《南楼月》、《赤壁游》、《龙山宴》、《同甲会》;徐阳辉的《有情痴》;徐翙的《络冰丝》;王应麟的《逍遥游》。从内容来看,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强烈反抗情绪及讽刺骂世,揭露现实官场、科场黑暗的剧作;另一类是态度较为平和的抒情剧,主要表现人生理想、避世逃名,将情绪诗化的剧作。
一
先说第一类,即以讽刺揭露、反抗发泄为主要目的的剧作。这类作品首推徐渭的《渔阳弄》(又名《狂鼓史》)。徐渭把凝结于血液中的惨痛人生经历和狂傲不羁的性格,形成为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和对传统的反抗。他将这种精神注入他的杂剧中,长歌当哭,《四声猿》便是他心血的凝结。作为《四声猿》的第一声,《渔阳弄》敷衍《三国演义》中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整部短剧曲词慷慨激越,奔放犀利,毫不掩饰作者的孤高狂傲,刚烈倔强。祁彪佳《远山堂剧品》称其“此千古快谈,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2]141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曹操忿恨祢衡孤高气傲,有意借大会宾客时召他为鼓史,令其击鼓而辱之。祢衡于是击出悲壮之音,又解衣裸体而立,显示了在权势面前不可见辱的凛然气概,但无“骂曹”情节。《三国演义》虽有“骂曹”情节,但稍简略,着重揭示的是曹操的奸险。但《渔阳弄》则以剧情重演的形式让祢衡裸衣击鼓,而以通篇彻骂,历数曹操奸险。这其实是徐渭借祢衡之口,将其一生的不得志及遭遇,连同他身处的这个整治黑暗、权奸当道的社会合盘骂出,酣畅淋漓。
像徐渭这样借单折剧来表达强烈反抗情绪的剧作家,在《盛明杂剧》中并不鲜见。如年代稍晚于徐渭的沈自徵、王衡、叶宪祖等人,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以《渔阳三弄》见称于世的沈自徵(1591-1641),字君庸,人或称之为渔阳先生。明国子监生,屡困场屋。负才任侠,曾游幕东北边塞。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君庸亦善填词,所撰《鞭歌伎》、《霸亭秋》诸杂剧,慨当以慷。世有续《录鬼簿》者,当目之为第一流。”《鞭歌妓》、《霸亭秋》就是与《簪花髻》合称的《渔阳三弄》,收录于《盛明杂剧》初集。单从三部剧作的合称《渔阳三弄》来看,就可知其深得青藤先生之遗风,而深层含义还应该是剧作的主旨。
《霸亭秋》全名《杜秀才痛哭霸亭秋》,借屡试不中的杜秀才之口,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抑郁不平。作者以杜秀才自喻,对明代尤其是明末不合理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抨击。《鞭歌妓》写落魄书生张建封路遇进京述职的裴宽,裴延请张至舟中,交谈甚欢,遂将合船宝物及歌妓相赠。张亦不推辞,反客为主,鞭打蔑视他的歌妓。作者借张建封手中的鞭子,把满腔孤愤狠狠甩下,将世态炎凉和功名富贵统统打碎。这也是作者对明末社会的理解和感受。《簪花髻》敷衍明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学家杨慎的故事,写杨慎因诤谏触怒朝廷,被谪云南,终日以诗酒为伴,醉酒后面敷粉墨,身穿红衣,头戴花髻,徜徉市里。结合作者穷其一生而未被重用的经历,不难理解作者在嬉笑怒骂中所宣泄的悲愤。这三种单折剧深得《渔阳弄》之壸奥,以看似戏谑的方式在黑暗无道的官场、科场以及炎凉世态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不用华丽的排场、精致的妆容、优美的曲词,恰是这等质直自然、挥洒自如的语言,在短短数千字、仅仅一折中,将作者满腔愤怒发泄的淋漓尽致,这恐怕是洋洋数万言、动輒几折甚至十几折的长剧所表现不出来的吧!
另一位与徐沈类似,借剧作表现心中不平的作家,是《真傀儡》的作者王衡。王衡(1561-1609),字辰玉,号缑山,别署蘅芜室主人。少年时便和归去来辞劝其父王锡爵归隐。科考曾中榜眼,却以养亲辞官。《真傀儡》敷衍宋代丞相杜衍,致仕后混迹市井,以此避世逃名。一日入市看傀儡戏,忽而圣旨传到,杜衍公未带朝服,慌忙中借傀儡戏服,跪拜领旨。剧本假托杜衍公,其实是写自己的父亲王锡爵的宦海沉浮。《明史·王锡爵传》记载,王锡爵曾于万历十二年和二十一年两度入阁,后因得罪首辅张居正,其子王衡得顺天试第一而遭人非议等事数起数伏。万历二十三年致仕居家,隐于市井。三十五年,朝廷复召锡爵,辞不赴命。剧中曲白“我想那做宰相的坐在是非窝里,多少做的说不得的事,不知经历几番磨练过来。”一语道破官场难捱、官员难做的苦闷,也是对两度入阁、曾登相位的父亲官宦生涯的辛酸表露。这与《渔阳弄》看似以闹剧收场的结局如出一辙,读者不难看出,个中滋味何等辛酸、何等愤懑!
与以上带有强烈反抗情绪和讽刺发泄意味的剧作不同,第二类作品是借短剧形式来抒发感情,态度较为平和,主要表达人生理想尤其是及时行乐观念的抒情剧。《盛明杂剧》中这类作家主要有汪道昆、许潮、徐翙、徐阳辉、王应麟等。他们的生平经历都比较顺利,不似徐渭、王衡等命途多舛,因此这些作品中愤世嫉俗的意味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淡定,一份宁静。
首先看汪道昆的剧作。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一字玉卿,号南溟、南明、太函、天都外臣,晚号涵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副都御使,兵部右侍郎,后因与张居正意见不合致仕。位列“后五子”,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所作剧本《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合称《大雅堂乐府》,收录于《盛明杂剧》初集。《高唐梦》据宋玉《高唐赋》入戏,写宋玉与楚襄王游云梦,遇巫山神女之事。《五湖游》敷衍范蠡助勾践灭吴后,携西施泛舟五湖,避世逃名,远离尘世喧嚣之事。《远山戏》借汉代张敞为妻画眉之事,表面写士大夫与妻子恩爱情事,实际写官场不值得逗留,远离是非,为妻画眉强似为政劳碌。《洛水悲》写陈思王曹植与甄氏魂魄相会于洛水,表达“繁华是浮沤,趁他未白少年头,樽前宜粉泽,座上即丹丘”这种及时行乐的愿望。这四部戏内容多为风流韵事,文字典雅清丽,但是不适宜舞台演出,可看作文人纯案头剧作。剧作中所透露出对人生、仕途、官场浮华如梦的淡定及浅浅的哀愁,与其争名逐利,不如远離庙堂纷争,心处江湖之远,及时行乐,这其实是士大夫对恬淡、自然的人性生活的一种向往。
作品收入《盛明杂剧》最多的单折剧作家莫过于许潮了。他有杂剧总集《泰和记》,按二十四节气分演二十四折古人故事。收录于《盛明杂剧》初集的就有八种:《武陵春》、《兰亭会》、《写风情》、《午日吟》、《南楼月》、《赤壁游》、《龙山宴》、《同甲会》。这些剧作也是作者假托古人故事,表达对远离官场、政务之外的世俗生活的由衷赞美和向往。
另外,还有叶宪祖的《北邙说法》、王应麟的《逍遥游》、徐翙的《络冰丝》等,或劝化世人行善戒恶,或度脱众生解脱生死,超离名利,或单纯表达一种似梦非梦、飘渺美奂的意境。这些剧作在短短一折中,不求有动人心魄的演出场面、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只是“我手写我心”,强调意境的优美、曲词的清丽,较之第一类作品,韵味显然平淡了很多。
二
我们认为《盛明杂剧》中收录这么多的单折杂剧,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各种原因和一定用意。
首先,《盛明杂剧》中收录这些单折剧反映了当时的创作风尚,而单折剧在明中叶出现并被剧作家用于创作,又有其深刻根源。
明中叶开始,朝政逐步开始向下坡路发展。明武宗正德之后,皇帝或荒淫放荡,或无心理政,朝中宦官专权,奸臣当道,政治上一片黑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被损坏殆尽。庙堂之上,忠臣良将一腔抱负,却因为权奸当道报国无门;科考路上,文人学士满腹经纶,却由于科场不公久困场屋。这使文人士夫们必须找到一个渠道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戏曲无疑是很好的途径,剧作家便是整部戏的最高统治者。在舞台上,权奸大恶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清官忠臣可以明白断案、为民伸冤,黎民百姓可以沉冤得雪。
与朝政松弛伴随的是,明中叶以来官绅士大夫竞相以蓄养家班为时尚,一时间家班盛行,小剧场演出频繁。恰逢此时明杂剧已打破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程式,没有固定的框架,折(出)数不定,音乐体制也相对自由,并出现南曲、北曲、南北合套、南北联套等形式,单折剧便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生成并成长起来。而在小剧场中,长于抒情又短小便演的短剧得以红极一时,成为了家班演出舞台上的新宠,一折短剧更是突破传统戏剧创作形式,争相出现在各个舞台。
从《盛明杂剧》的这些单折剧可以看到,很多剧作家都是带着历经官场、科场的不得意,深感社会流弊,整个社会已病入膏肓的愤懑、担忧,激扬文字,希望对社会、对世人起到警醒作用。
徐子方先生在研究明中后期杂剧发展状况时指出,“真正形成明中后期的杂剧独特面貌,就不仅要在创作态度上形成强烈批判情绪的社会群体趋向,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创作出有别于元代及明初北杂剧,并为时代大多数作家所认同的模式。”[3]222杂剧在经历了元代勾栏瓦舍中面敷粉墨的梨园歌伎,到明初期走向宫廷,成为藩王贵族韬光养晦、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华丽仕女,再随着明代社会机制的溃烂、及至逐渐病入膏肓,杂剧走进深宅大院,成为文人士大夫关上重重门户,在厅堂之中、红氍毹上独自赏玩或用于社会交际的名媛佳丽,杂剧的内容及形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康海、王九思为代表的作家们,开始将个人情绪融入到杂剧创作中,指斥时事,批判现实,将杂剧作为宣泄个人或群体主观意识的工具,形成了明中后期大量出现的文人剧。这些从内容上看属于文人剧的作品,又从艺术形制方面开启了南杂剧的样式,这类作品在内容上注重表现主观意识,体制上突破了元杂剧的传统模式,形式结构较为自由。徐子方先生指出“南杂剧对传统的突破更集中的体现在单折戏上面,研究明杂剧不能不注意到中期以后涌现的一批单折戏形式。”[2]225单折剧在这时出现并繁荣,实是时代的必然。而“南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文人剧作为一个独立戏剧类型的成熟”[3]222。单折剧恰恰是这些南杂剧式文人剧中最有成就的代表。
其次,《盛明杂剧》收录这些单折剧是注意到了它们在承袭杂剧固有特点之外,所反映出的自身新的时代特点。
1.内容丰富多样,选题严肃。就《盛明杂剧》所收录的23种单折剧来看,内容题材涉及到文人剧如:《渔阳弄》、《大雅堂杂剧》、《渔阳三弄》、《武陵春》、《南楼月》等;历史剧如《昭君出塞》、《文姬入塞》;神仙道化剧如:《北邙说法》、《有情痴》、《逍遥游》等。总的来看,传统的婚恋题材较少,主要表现的是对世事的思考,对科场、官场真实状况的反映揭露,对人生、对未来的向往,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和自我意愿的向往。
2.体制短小,结构紧凑,线索分明。它大致相当于元杂剧的一折,演出时间短,“一本杂剧只演一杯酒的间,理应不会很长。”[4]单折剧一般只有几千字,不同于元杂剧的四折一楔子和明代传奇多出甚至十几出的体制,因此这就要求整个剧本结构要紧凑,不能拖沓冗繁。如《渔阳弄》开场即直接进入主题,重演祢衡击鼓骂曹情节,自始至终就这阴司这一个场景,骂曹这一个事件,主要人物不外阴司判官、祢衡、曹操三人,自始至终围绕“骂曹”这一个主题一通到底,不受驳杂的人物关系或其他枝节的干扰(当然不排除个别文人化气息较浓的作品,只在意语言的诗化和意境的优美)。让观众在短时间内跟随祢衡的痛骂和疯狂的鼓点,将自己胸中不平之气喷泄而出,酣畅淋漓。
语言丰富,雅俗俱备。这从《盛明杂剧》中的23个单折剧就可以看出,既不乏文人雅士的典雅清丽,也可见乡村野老的粗鄙诙谐。即使是表现骂世的《霸亭秋》,在从头到尾都应是痛哭场景中,末(杜默)与(书童)也不忘调笑打诨;在《渔阳弄》中,作者也在“骂曹”之前加入两个女乐唱曲儿的成分,无疑是增加了“戏”的成分,使整个剧作虽然短促但并不失“戏剧”的本来面目。
音乐体制比较自由。《盛明杂剧》这23种剧作中,便出现了南曲、北曲、南北合套、南北联套、南北复套这五种形式,彻底打破了元杂剧北曲一统全剧的规范,在宫调使用方面也不恪守成规。如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杂剧,就有【北调新水令】-【南步步娇】-【北折桂令】-【南江儿水】-【北雁儿落带得胜令】-【南侥侥令】-【北望江南】-【南园林好】-【北沽美酒带太平令】-【南尾】这样南北曲牌联套的形式。而且剧中旦、生、贴旦、外末、众都可以上场演唱。这种南北相杂、众人皆可任唱的形式,使舞台演出更为活泼、形式更为自由。明末杂剧这种体制上的特点,使本就简短的一折剧本更添魅力。
最后,《盛明杂剧》收录如此之多的单折杂剧,与编选者的戏剧观念有关。
沈泰在该书《凡例》中明确指出:“此集只词人一脔,然非快事、韵事、奇绝、趣绝者不载。”[5]对这段话沈泰并未做解释,但在接下来的序文中,他的朋友们向我们揭示了《盛明杂剧》选辑的标准。徐翙序文云:“今之所谓南者,皆风流自赏者之所为也;今之所谓北者,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5]程羽文序:“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啼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5]这两位曲家都指出才人韵士创作的原动力是“借长啸以舒不平”,即司马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故述往事,思来着”,他们的方式就是通过戏剧创作,将嬉笑怒骂、满腔怨恨赋予剧中人物形象,并不“直写”而是“曲摹”,不是“庄语”而用“戏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