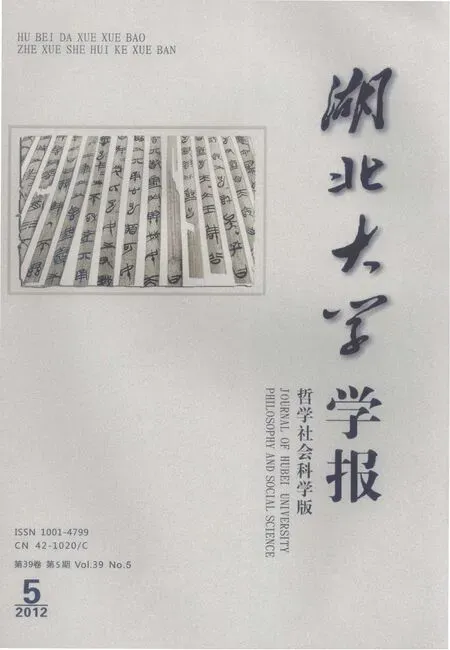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
吴长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乔恩·埃尔斯特在他的著作《理解马克思》的序言中写道:“G·A·柯亨(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的出版是一个意外(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须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仁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1]2历史往往由埃尔斯特所述及的诸多的“意外”与“偶然”构成,但这些“意外”与“偶然”恰恰孕育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柯亨及其他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继阿尔都塞之后扛起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大旗。
一、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
马克思主义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为诞生标志的16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阵营内部都不断地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以一种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哲学的武器而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开始初现端倪;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则进一步走向深化;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重焕青春”和国际工人运动遭受挫折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也乐观欢呼“历史终结”理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或“重释”或“重建”或“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支队伍中最为重要的生力军之一。
1.人本主义溯源
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词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人性”、“人情”和“万物之灵”[2]62。德文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的希腊文词源antropos和logos,意为人和学说,通常指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就曾倡导“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将人类探索外部世界的目光引向对人的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发源于14世纪下半期的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它主张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汉语中人本主义又译为人本学、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根据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词的解释:“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是一种具有复兴色彩的文化推动力,是个人主义和批评精神,倡导从对宗教的关注转移到对现世的关注。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诗人彼得拉克。”[3]788(In Renaissance Europe,cultural impulse characterized by a revival of classical letters,an individualistic and critical spirit,and a shift of emphasis from religious to secular concerns.It dates to the 14th century and the poet Petrarch.)美国《哲学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人本主义是指任何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4]758德国大百科全书《拉鲁斯辞典》的解释是:“把人和同人有关的事物看作核心、尺度和最高目的的人生哲学,都是真正的人文主义。”[4]785按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人本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但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同来源的解释和表达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人本主义者把人当做万物的尺度,强调人道价值、自由和尊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Sanction)的哲学”[6]11。
2.科学主义溯源
科学主义和科学一样,都是外来词。英文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与科学的英文science是同源词,science最早在国内译为“格致”,后因日本明治维新后译法的影响改译为“科学”。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了著名的《科学》刊物,从此,“科学”成为了science的定译[7]52。科学主义的英文scientism在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应该有所区别,人文学强调“主观”,科学强调“客观”,彼此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强”的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弱”的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The belief that the assumptions,methods of research,etc.,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re equally appropriate and essential to all other disciplines,including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8]1279。在哲学领域,科学主义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科学主义是与科学方法的信念紧密联系的,认为利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科学是关于实在的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另一种理解认为科学主义是欧洲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趋向,赞同科学可以用来改造哲学,使哲学像科学那样具有实证性的知识体系,成为科学的哲学。
3.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历来存在比较大的争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各执一词的不同解读方式,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人本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等人,在他们那里人本主义的解读基本占据主流;另一种解读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到伽利略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如法国的阿尔都塞、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科莱蒂等人,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科学主义,反对人本主义,这一派的观点稍占下风。就这一问题的定论本文姑且不予论述,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持续争论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和科学主义解释的论争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论争初现端倪;第二阶段是二战后的20世纪40-60年代,其论争进一步深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呈现多元化。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的过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必然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有效缓和,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繁荣时期,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论断在这一时期似乎也失去原有的“革命色彩”。工人阶级内部开始滋生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改良主义的情结,集中体现在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伯恩斯坦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修正主义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一种庸俗的经济史观和宿命论的决定史观。恩格斯在晚年就“经济决定论”进行过有力地批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反击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时,把历史解释为一种没有人的主体能动性活动参与的结构运动的历史,这可能也被称之为马克思科学主义的雏形,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是马克思科学主义解释的早期代表[9]6~8。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失败并走向沉寂,促使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和反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理论,以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为标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斯等人通过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历程,通过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强调,拉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解释的帷幕。
二战后的20世纪40至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两大特征:一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走向繁荣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空前的缓和;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处于空前的低迷期,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逐渐占据西方社会的主流。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斯所描述的通过“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从而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场景并未出现,革命的到来也仿佛遥遥无期。在这种背景下,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思考,以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了新的人本主义的解读。法兰克福学派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发挥人的各种潜能。……马克思关心的是人,而且他的目标就是让人从物质利益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人从他的安排和行为所造成的束缚自身的囚牢中解放出来。”[10]11~1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则倡导一种深层的文化和心理革命,通过人的“心理获得解放”,改变“人病态的社会性格结构”,使人从总体异化的社会状态中解放出来,然后再谈及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11]46。处在同一时期的马克思科学主义者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解读进行猛烈的反击,其中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方面理论贡献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时期,随着法兰克福等马克思人本主义学派影响的日益扩大,尤其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批评之后,马克思人本主义的解释更加占据主流。在马克思人本主义解读被“泛化”的背景下,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公开呼吁“保卫马克思”,恢复马克思科学主义解释的本来面目。阿尔都塞这样陈述:“要是没有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我的靶子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描述。”[11]4~5
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特征一方面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西方各国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经济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是以1968年席卷全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的失败及苏东的剧变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遭受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哲学意识形态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思想家着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反思,明确提出“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德里达、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着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解构,继承并认同马克思的理论武器“批判精神”;在受多元文化充斥和或“重建”、或“重构”、或“重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奠基性的科学清理工作”。正如乔恩·埃尔斯特在他的著作《理解马克思》的序言中写道:“G·A·柯亨(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的出版是一个意外(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须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
通过回顾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论争历史,我们大体可以厘清马克思人本主义解释和科学主义解释的主要特征。马克思人本主义解释强调主体研究的首要性,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强调人的心理结构、阶级意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主体以外的客体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人本主义大多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本身存在缺陷,主张用各种人本主义思想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科学主义的解释则以科学认识的理论、科学逻辑、科学方法为精确和可靠获取知识并达到认知的有效路径,科学主义往往忽视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由结构决定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走上历史舞台,客观上成为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不同解释路径就不会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重建”,没有这种“重构”与“重建”的前提,也就不会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走向历史舞台的必然逻辑。概而言之,20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虽然进入到一个多元的时代,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解读仍然是主要对峙的两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思想家是人本主义解释的主要生力军,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则是科学主义解释路径的“旗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构成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
二、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及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
1.“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可以追根溯源至20世纪20年代的卢卡奇、柯尔斯和马尔库塞等人。柯尔斯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这样陈述:“从上个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危机的阶段”。马尔库塞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十九世纪‘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来的。今天,资本主义进入到‘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已经被时代所超越,正在‘被误解和走向错误’”。科莱蒂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作的许多预言今天并未实现,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萨特与列斐伏尔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官方化了,变成了行政条文,经院化了”,“教条化”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和“拜物教化”[12]1。阿尔都塞也公开宣称:“我们毫无理由害怕这一词。马克思主义不是经历过其他的危机阶段吗?但是马克思主义摆脱了危机。我们不怕说出这个词,确实,从很多迹象来看,马克思主义今天处在危机中。这个危机是公开的,所谓公开就是有目共睹的。”[12]1克拉辛作为原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曾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都正处在极为深刻的危机之中,尽管这种危机并不代表俄国社会中价值危机的全部,但却是这种危机之中的最主要的方面之一。”[12]1苏东剧变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掀起了一股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反马克思主义的狂潮,一些西方学者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已经被埋葬”,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这样描述这些人的欢呼:“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13]75~76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至少导致了两个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出现采用新方法、新视角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罗默在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就这样陈述:“……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出盛衰无常,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令人将信将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上个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一种方式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另一种方式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上是错误的东西加以抛弃。第四种方式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这样,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14]2由此可见,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采用了第四种方式,成为了运用了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博弈论等现代科学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辩护”和“重构”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另一直接影响是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强加的政治性“压迫”与“排斥”相对较弱,尤其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处在一个政治相对宽松的环境。正如安德鲁·莱文所说:“英语国家从未发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随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在欧洲的爆发,主张把马克思清除出大学校园的压力会大大减轻,但这种减轻只会促进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化、非政治化倾向。”[15]26“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一方面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得以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客观上营造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欧美国家的“学院领域”迅速成长的外部环境。
2.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
冷战结束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经济的严重“滞涨”困境而无能为力时,欧美一些左翼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传统理论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而使得西欧、北美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并且得以在学术上发展。据统计,20世纪的70、80年代,仅美国的各大学哲学系就共开设了数百种之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美国政治学协会”等等[16]21。英国则兴起了一批像《新左派评论》这样的左翼刊物,一些出版社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托洛茨基的作品等。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趋势表现在“一是出现了多种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置放在后现代话语的视域中,进行自由地阅读。这一时期既凸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强烈关注,又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已结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17]53。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趋势同样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滋生和成长的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柯亨为代表的一场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的理论潮流开始在英美国家流行起来,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鼎盛,成为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多元图景中最具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多元”之一。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1941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犹太工人的家庭,其父母都在犹太人开设的共产主义工厂工作,都信奉共产主义。柯亨幼年在犹太人共产主义组织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Morris Wincheswsky Yiddish School)[18]12。据说,柯亨学习的学校及当地的共产主义组织曾遭受加拿大魁北克省警察局“红队”的袭击,使得学校无法为继,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给幼年的柯亨留下了深刻的恐怖印象,但他幼年时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及当时社会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为柯亨成年后用毕生精力转向马克思研究埋下了伏笔。柯亨在麦吉利大学后转到牛津大学学习期间,这一时期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时期,此时的柯亨正埋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阿尔都塞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他仔细研读过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但他一度为阿尔都塞的“含混表达”感到困惑,从而转向分析哲学方法的研究,师从牛津大学著名教授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直到1978年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公开发表,标志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舞台,这一登场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趋势又一重要体现。
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组织保障:“九月小组”
从可以收集到的资料看,本文作者基本赞同陈伟博士在《阴山学刊》上的撰文《“九月小组”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在博士论文中有关“九月小组”的“一个考证”。1978年,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者柯亨、威廉姆·肖和埃尔斯特同年出版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三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逻辑与社会》,他们发现彼此志趣相投。而且,他们还发现,采用“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没有运用或者没有能力应用的研究方法”[18]16——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使“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不但清楚还能够经受得起严格的检验”[18]16。在这一背景下,经埃尔斯特的提议,1979年9月的某个周末,在柯亨工作的伦敦大学哲学院召开了一个由十多位“志同道合”来自英、法、比利时等国的左翼学者参加的学术沙龙活动,这便是“九月小组”的雏形。之后,小组决定每年举办一次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直到1981年9月,“九月小组”以相对稳定的学术团体或学派团体在伦敦正式诞生。
1981年以后,“九月小组”的成员基本固定,他们包括罗伯特·勃伦纳、G·A柯亨、菲利普·范帕里斯、约翰·罗默、希勒尔·斯泰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埃里克·赖特、普拉纳布·巴德翰、塞缪尔·鲍勒斯和乔舒亚·柯亨等[18]16。但在1993年,可能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及苏东的巨变导致了约·埃尔斯特和亚当·普泽沃斯基的离开,“九月小组”随后走向分崩离析。“九月小组”的核心人物柯亨不幸于2009年8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柯亨的永久离开使得“九月小组”乃至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处在瓦解的边缘。
正是因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20多年来坚持每年一次“九月小组”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得这一学派得以存在并充满活力。作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组织保障的“九月小组”目前虽然濒临瓦解,但事实证明,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他们在各自新的领域正积极地进行着各种探索,罗默提出“一般剥削理论”而在哲学界名声大噪,埃尔斯特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即理性选择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赖特在阶级理论及中间阶级的界定等方面成绩卓著,威廉姆·肖在重构马克思历史理论方面采用了新的方法和新的分析视角等。柯亨虽然离开了他所热衷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但柯亨及其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重构却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
四、结论
由以上论述,我们对“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的命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与纷争铸就了这一学派产生的内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及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背景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得以滋生和成长创造了外部环境;“九月小组”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并很快成为西方国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之一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
[1]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胡敏中.论人本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 沈恒炎,燕宏远.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一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5] 杨寿堪,李健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J].学术月刊,2001,(11).
[6] 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M].贾高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7] 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3).
[8]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New Revised Edition,Portland House,1986.
[9] 刘方现.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百年轨迹寻踪[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
[10] 弗洛姆.人的呼唤[M].北京:三联书店,1991.
[11]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2] 楼培敏,黄德兴,曹维铭.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J].复旦学报,1982,(3).
[13]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4] John E.Roemer,Analytical Marx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5] 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M]//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6] 曹玉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张广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J].长白学刊,2001,(5).
[18] 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以柯亨的历史理论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