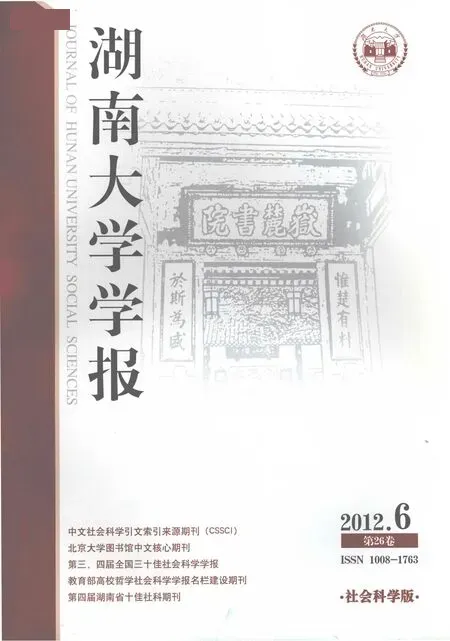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李承贵,王金凤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宋代儒家学者虽然致力于儒佛的分辨与评判,但朱熹并不感到乐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朱熹推崇的程颢、程颐、张载虽然在辨别儒佛差异上相当努力,但显然不能令朱熹满意①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第二章、第三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二,程氏弟子如谢良佐、游酢、杨时三位竟然说出“佛儒体同末异”的话,这让朱熹很不舒服;如此,儒佛关系的分辨与厘清仍然是一项急迫之事。那么,朱熹在辨别儒佛差异上做了哪些独到的工作呢?
一 道体的特性:“体用为一”与“体用两分”
在《近思录》“道体”部分,朱熹罗列的范畴有“太极、仁、性、心、理、诚”等,也就是说,在朱熹的心目中,这些范畴可以被确定为儒学中的“道”或“道体”。而对于“道”或“道体”的特性,《中庸》的某些描述或许能给后代儒者以启发。比如,“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13章)这是说“道”与人及其生活是须臾不离的,“道”的生命与价值就在生活中。比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这是说,“道”既是平常的又是高远的,是贯通上下的。比如,“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25章)这是说,“道”既有内在性,又有外在性,是内外一体的。显然,这些经典性论述,对启发宋儒关于“道”或“道体”性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朱熹对儒佛差异的辨析与判断,就很有代表性。
1.从表述道体范畴的关系看,儒学的“道”是一,佛教的“道”是二。如上所言,在朱熹的《近思录》(合作者吕祖谦)中,“太极、仁、性、心、理、诚”等范畴都被确定为“道体”,那么,这些“道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彼此孤立毫无瓜葛的?还是彼此关切直接同一的?朱熹认为,对儒家而言是合一的,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述而已,但对佛教而言是两分的。他说:“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①《答郑子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6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那么,佛教何以执“心、理为二”呢?朱熹分析道:“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物咸备也。”②《答郑子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691页。就是说,佛教之所以把心、理分为两个东西,乃是因为佛教所见“心”空而无理,而儒家所见“心”虽空但备有万物。事实上,心、理、良知、仁为“一”,是宋明儒的共识。比如,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③《伊川先生语四》,《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一册,第204页,中华书局1981年。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④《书·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陆九渊集》,第4页,中华书局1980年。王阳明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⑤《与王纯甫》,《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4页。由此看出,“道体”在儒学中虽有不同的表述形式,甚至每个不同表述形式的“道体”所负载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但在根本意义上,它们是“一”。也因此,儒学的“道体”是创造生命的源泉,以造化万物,这叫“理一分殊”。但在佛教那里不是如此,因为佛教所言“心”、“性”,都是空无一物的,因而不能与“仁”、“理”、“良知”等实有范畴同日而语。
2.由本体末用关系看,儒学的“道”是一,佛教的“道”是二。从“道”的体用上看,儒学的“道”或“道体”有体有用,但体用是一,无有分别。比如二程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观其所见何如耳。”⑦《与吕大临论中书》,《二程文集》卷九,《二程集》第二册,第609页。朱熹的看法与二程完全一致,他说:“释氏虽自谓唯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虽云心生万法,而实心外有法,故无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备。然为其说者,犹知左右迷藏,曲为隐讳,终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则天人性命岂有二理哉?”⑧《与张钦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朱子全书》(贰拾壹),第1327页。在儒学中,“心”就是“天序天秩天命天讨”,就是“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因而尽心即知性,知性则知天,存心养性即是事天,因而心外别无什么大本,它们是一体通透的。但佛教不是这样,佛教心外有法,所以佛教的“心”中立不起天下大本,从而导致道之内外不备。因此说,佛教根本不理解心体,不明白天人性命本是一“理”。在朱熹看来,不仅“心”是体用合一的,“性”也是如此。他说:“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⑨《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43页。虽说佛教识心见性,但所识性不能付诸于用,因而是体用两分,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作用处弃君背父。而儒家是明其性且率由之,所以功用充塞天地。可见,从心、性之为道体看,在儒家,其体其用是合一的;在佛教,其体其用则是两分的。
3.由内圣外王关系看,儒学的“道”是一,佛教的“道”是二。所谓道体的内外,就是指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养性,是做人;外王是经世致用,是做事。对儒学言,内圣外王是一体的。比如,从觉悟看,朱熹认为,儒学的觉悟是内含事业的,而佛教的觉悟是空洞无物的。他说:“释氏一觉之外更无分别,不复事事,而吾儒事事无非天理,此语是也。然吾儒亦非觉外有此分别,只此觉处,便自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毫发不可移易,所谓天叙天秩天命天讨,正在是耳。”⑩《答詹兼善》,《朱子大全》卷四十六,《朱子全书》(贰拾贰),第2123页。佛教以“觉”为满足,无需再谋他事,而儒家之“觉”即是天叙、天秩、天命、天讨,所以儒家之“觉”乃为谋事。因此,佛教之“觉”虽可同于儒家“敬以直内”,但无“义以方外”工夫:“问:佛教如何有‘敬以直内’?曰:他有个觉察,可以‘敬以直内’,然与吾儒亦不同。他本是个不耐烦底人,故尽欲归去。吾儒便有是有,无是无,于应事接物只要处得是。”①《程子之书》,《朱子语类》卷九十六,《朱子全书》(拾柒),第2224页。也就是说,佛教言“觉”处,虽有“敬以直内”工夫,但不能应事接物。因此,佛教之“觉”虽可与“敬以直内”并论,但由于没有“义以方外”,其“直内”也无“是处”。而且,由于缺了“义以方外”工夫,佛、儒之别就不仅是在同异层面,更在是非层面。再如,由克己复礼看。朱熹认为佛教只有“克己”,没有“复礼”。他说:“克己是大做工夫,复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也。释氏之学,只有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便至以君臣为父子,父子为君臣,一齐乱了。”②《论语二十三》,《朱子语类》卷四十一,《朱子全书》(拾伍),第934页。在儒家学说中,“克己”意味着言行举止处处皆合规矩准绳,所以克己复礼是一件事。为什么这样说?克己是“内”,复礼是“外”,但不是“克己”之外还一个“复礼”,“复礼”是落到实处。但佛教不是这样,由于佛教无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关系的存在,无视仁、义、礼、忠、孝、弟伦理的存在,所以即便它有“克己”工夫,那也仅仅是自我修养而已,仅仅是独善其身而已,当然可以说是没有“复礼”工夫了,当然可以说是内外两分的了。朱熹看得清楚明白:“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佛老虽不可谓之有私欲。只是他元无这礼,克己私了,却空荡荡地。他是见得这理元不是当,克己了,无归著处。”③《论语二十三》,《朱子语类》卷四十一,《朱子全书》(拾伍),第936页。因此,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的“道”是一,佛教的“道”是二。
4.由下学上达关系言,儒学的“道”是一,佛教的“道”是二。所谓道体的上下,在儒家学说中,“上达”指形上之道,道德性命之学,“下学”指形下之器,道德学问之实践。儒家主张上下一贯,“下学”即“上达”,“上达”亦“下学”,但佛教只有“上达”无“下学”,而没有“下学”,实际上“上达”也不足。朱熹说:“须是下学,方能上达。然人亦有下学而不能上达者,只缘下学得不是当。若下学得是当,未有不能上达。释氏只说上达,更不理会下学。然不理会下学,如何上达。”④《论语二十六》,《朱子语类》卷四十四,《朱子全书》(拾伍),第1018页。朱熹认为,就一般情况言,“下学”、“上达”本应是一以贯之者,“下学”是“上达”的前提。但如果“下学”不当,“下学”作为前提也就毫无意义。佛教正是不理会“下学”,其所谓“上达”自成泡影。佛教“下学”、“上达”不一还表现在“敬”上。儒家重“敬”而轻“静”,认为“敬”则存物,但“敬”能存物的前提是将“敬”诉诸于具体实事上,否则仍是上下不一贯。所谓“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如释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没下面一截事。”⑤《学六》,《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全书》(拾肆),第187页。佛教虽然能“敬”,但只知上面一截事,没有下面一截。因而朱熹将那不知穷理而妄言心性之行为等同于佛教只知进涅槃世界而不知俗界之事的弊端。朱熹说:“愚谓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为知之端也。无焉则非人矣。故诠品是非乃穷理之事,亦学者之急务也。张氏绝之,吾见其任私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岂释氏所称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遗意也。呜呼!斯言也,其儒释所以分之始与!”⑥《张无垢中庸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贰拾肆),第3476页。诠解分析是非即是穷理之事,如无此工夫,则只算是不管是非而直取无上菩提之禅法。这也正如二程所指出的:“佛氏之道,一务上达而无下学,本末间断,非道也。”⑦《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第四册,第1179页,中华书局1981年。
概言之,在道体特性、本体末用、内圣外王、上达下学等方面,佛教与儒学存在明显的差异。于儒学言,体用、内外、上下都是“一”,而在佛教,体用、内外、上下都是“二”。正如二程所说:“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⑧《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二程集》第一册,第3页。所以,朱熹强调不能将佛教的“道”混同于儒学的“道”:“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审。明道先生所谓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见得亲切,如何敢如此判断耶?”⑨《答吴斗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836页。
二 伦理的关怀:“有缘之慈”与“无缘之慈”
佛教与儒学在伦理道德上的差异,向来是儒家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接近一致的观点是,佛教是弃人伦、害伦理的,与儒家全心于建构俗世伦理以提升民众道德修养的理念大异相趣。那么,朱熹眼中的佛教与儒学在伦理道德上有哪些差异呢?
首先,道德规范之有无。朱熹认为,儒家立有条理和准则,而且要求按照条理做事,遵照准则行动:“或(问)曰:吾儒所以与佛氏异者,吾儒则有条理,有准则,佛氏则无此尔。曰:吾儒见得个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如此。佛氏则说:‘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⑩《孟子二》,《朱子语类》卷五十二,《朱子全书》(拾伍),第1134页。由于佛教言行举止不讲条理、不守准则,因而坐无正姿、喜怒无常、胡作非为。朱熹说:“释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胫坐也得,叠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将见喜所不当喜,怒所不当怒,为所不当为。他只是直冲去,更不理会理。吾儒必要理会坐之理当如尸,立之理当如斋,如头容便要直。所以释氏无理。”⑪也就说,佛教的言行举止过于随便而至粗野。那么,佛教本也有戒律,何以说其毫无章法呢?何以说其无视伦理呢?朱熹分析说:“若是如释氏道,只是那坐底视底是。则夫子之教人,也只说视听言动底是便了,何故却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居处、执事、与人交’,止说‘居处、执事、与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着个‘恭、敬、忠’?如‘出门、使民’,也只说个‘出门、使民’便了,何故却说‘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①《释氏》,《朱子语类》第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5页。朱熹指出,孔子教人,并不只是让你知道视、听、言、动,而且要告诉你应该怎样视、听、言、动,不只是让你知道居处、执事、与人交,而且要告诉你应该怎样居处、执事、与人交,不只是让你知道出门、使民,而且要告诉你应该怎样出门、使民,概言之,孔子教人不只是教形式,还要教内容,不只是教你知其然,还要教你知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就是“礼”,而佛教没有这种观念,当然异于儒学。
其次,道德关怀之深浅。毫无疑问,佛教有其独特的道德关怀,正因为它的独特性,才显示出与儒学道德关怀的差异。那么,佛教与儒学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呢?第一,从亲亲之爱说,朱熹认为佛教与儒学不同。他说:“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然却认为己有,而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既见,便不认作众人公共底,须要见得为己有,死后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寓。譬以旧屋破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黄蘖一僧有偈与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绝灭天理可知!当时有司见渠此说,便当明正典刑。若圣人之道则不然,于天理大本处见得是众人公共底,但只随他天理去,更无分毫私见。如此,便伦理自明,不是自家作为出来,皆是自然如此。往来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②《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18页。佛教虽也识得一点天理大本,但认为“生命”仅是一种寄赋而已,只把父母之身视为一个寄托处,并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因而是无情义、灭天理,疏于对父母的爱。第二,从爱物角度看,朱熹认为佛教也不能与儒学相提并论。他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然谓之爱物,则爱之惟均。今观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兽之类是也;有无知之物,草木之类是也。如数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圣人于有知之物,其爱之如此,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于市,圣人于无知之物亦爱之如此。如佛之说谓众生皆有佛性,故专持不杀之戒,似若爱矣,然高宫大室,斩刈林木则怙不加,恤爱安在哉?窃谓理一而分殊,故圣人各自其分推之曰亲曰民曰物,其分各异,故亲亲仁民爱物,亦异佛氏自谓理一而不知分殊。但指血气言之,故混人民物为一,而其它不及察者,反贼害之,此但据其异言之。若吾儒于物,窃恐于有知无知亦不无小异。盖物虽与人异,气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气所生,与无知之物异。”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691页。就有知之物言,儒家主张不杀幼小生命,对无知之物,儒家主张伐之以时,这充分体现了儒学道德关怀的细微、体现了儒家的生态意识。而佛教虽言众生皆有佛性,提倡不杀之戒,但对砍伐树木根本没有犹豫;而且佛教混同人与物,对那些无力顾及的人物,就戕害它。因此,儒家的爱虽有差等厚薄,但比起佛教来,要进步得多。朱熹认为,佛教与儒学道德关怀的第三个差别,在于佛教重“无缘”胜于“有缘”。所谓“禅家以父子兄弟相亲爱处为有缘之慈。如虎狼与我非类,我却有爱及他,(如以身饲虎)。便是无缘之慈,以此为真慈。甘吉父问‘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时举因问:释氏说慈,即是爱也。然施之不自亲始,故爱无差等。先生曰:释氏说‘无缘慈’,记得甚处说:‘融性起无缘之大慈。’盖佛氏之所谓慈,并无缘由,只是无所不爱。若如爱亲之爱,渠便以为有缘;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④《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53页。在佛教看来,“慈”分两种,一是有缘之“慈”,一为无缘之“慈”,而以无缘之“慈”为真慈,而且佛教之爱不是由亲及人,所以没有差等。但朱熹认为,佛教之“慈”也还是有“缘”的,只是无所不爱,因而佛教是以无缘之慈为“真慈”,所以有父母却弃而不养,这当然是与人间义理背离的。可见,在施爱范围、对象、方式等方面,佛教与儒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孔子曾经因为自己不能尽臣、尽子、尽兄、尽友之道而感伤,这在佛教纯属是自作多情。
最后,道德实践之存弃。儒家伦理道德来源于世俗生活,又关注世俗生活,是谓入世伦理。佛教伦理以出世为特征,有其特殊性,但朱熹认为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反伦理的。所谓“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佛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⑤《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41页。在佛教看来,只要皈依佛门,即使有老母在家,出家为僧,不予奉养,也是善行。而这对儒家而言,有老母在家,即便犯罪,也要以奉养老母为重。足见佛、儒对伦理道德见识之异。在社会伦理方面,佛教也表现出极端的鄙视,根本不理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为幻妄。”⑥《周子之书》,《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拾柒),第2126页。佛教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故也以君臣父子之“理”为幻妄。所以,佛教之学是乱大伦之学——“佛氏以绝灭为事,亦可谓之‘夭寿不贰’,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会,所以做底事皆无头脑,无君无父,乱人之大伦。”⑦《孟子十》,《朱子语类》卷六十,《朱子全书》(拾陆),第1276页。人伦乃忠君孝父,佛教却绝灭了,所以是乱人之大伦。因而与老庄相比,在灭绝伦理上,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或问佛与庄老不同处。曰:庄老绝灭义理,未尽至。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方子录云:‘正卿问庄子与佛所以不同。曰:庄子绝灭不尽,佛绝灭尽。佛是人伦灭尽,到禅家义理都减尽。’佛初入中国,止说修行,未有许多禅底说话。”①《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19页。不过,人伦之理毕竟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佛教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伦理秩序之外。朱熹说:“天下只是这道理,终是走不得。如佛老虽是灭人伦,然自是逃不得。如无父子,却拜其师,以其弟子为子;长者为师兄,少者为师弟。但是只护得个假底,圣贤便是存得个真底。”②《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19页。佛教虽要灭人伦,但也拜师,以弟子为子,以长者为师兄,以少者为师弟,虽然此师、子、兄、弟之礼与俗世有异,但至少说明佛教终归灭绝不了伦理。
不难看出,佛教与儒学在伦理规范之有无、道德关怀之深浅、道德实践之存缺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佛教与儒学在伦理道德上存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朱熹有这样的解释: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则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纤毫之间,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纤毫造作轻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若夫释氏,则自其因地之初而与此理已背驰矣,乃欲其所见之不差所行之不缪,则岂可得哉?盖其所以为学之本心,正为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己不得一席无理之地以自安。厌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无理之时以自肆也,是以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坚苦用力之精专,亦有以大过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实有见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则其所见虽自以为至玄极妙,有不可以思虑言语到者,而于吾之所谓穷天地亘古今,本然不易之实理,则反瞢然其一无所睹也。虽自以为直指人心,而实不识心,虽自以为见性成佛,而实不识性,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③《读大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朱子全书》(贰拾叁),第3376页。
在朱熹看来,大宇宙中只有一个正理,这个“理”是万物所以为万物的终极根据。天得此“理”为天,地得此“理”为地,生于天地之间的万物各分得此“理”为性、为它自己,此“理”之成纪即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此“理”之成法即为仁、义、礼、智、信五常,都是这个“理”流行的结果,所以这个“理”无所不在,无时不流。识得此“理”,儒者从中得心之本然,所以此心内外精粗不容有纤毫之间,修己治人,也不容有纤毫造作之私,以修己治人,以参天地之化育。佛教开初便与此“理”相悖,因而所见也差,所行亦谬。佛教所谓为学之本心,正是因为厌恶此“理”之充塞、之流行,因而离世出家。所以由其言其行看,虽然自以为玄妙,与儒家穷天地亘古今之实“理”相比,则是一无所睹,一无所取。因为佛教所谓直指人心,实际上不认得心,所谓“见性成佛”,实际上不识得性,所以殄灭人伦法度而与禽兽为伍。因此,儒佛在伦理道德上的差异,实在于佛教不识宇宙正理所致。
三 工夫的路径:“动静顺时”与“栖心淡泊”
佛教所有教义、教规的建立,只有一个目标,帮助众生成佛,以脱离俗世之苦。而不同的佛教宗派对成佛路径理解不完全相同,从而提出了各种“识道”、“教学”、“修行”的工夫。而在朱熹看来,佛教的工夫与儒家工夫大异其趣。这里由“识道”、“教学”、“修养”三方面看朱熹言佛教工夫与儒家之不同。
首先,由识道工夫看。所谓识道工夫,即指识得事物之理、人生之理、宇宙之理的工夫。佛教与儒家在这方面有哪些不同呢?朱熹说:“鸢飞鱼跃,只是言其发见耳。释氏亦言发见,但渠言发见,却一切混乱。至吾儒须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④《中庸二》,《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朱子全书》(拾陆),第1373页。鸢飞指老鹰飞上青天,鱼跃指鱼儿在深渊跳跃,比喻持中庸之道的人能对上下进行详细考察,以发见事物之理。佛教亦言见道,但一片混乱。儒者则能上下考察事物之理,所以能识得事物之定分。由于佛教见道方式杂乱,因而求道愈求愈远。朱熹说:“所谈儒佛同异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论所以求乎儒者之学,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参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虚白清镜,火珠静月,每现辄变之说,则有大不可晓者。不知儒者之学,自六经孔孟以来,何尝有是说,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杂,无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⑤《答汪叔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815页。就是说,为儒家之学,求圣人之道,却杂乎“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虚白清镜,火珠静月,每现辄变”等神秘怪说,既不能求得事物之理,更不可能求得圣人之道。于人生道理方面,朱熹说:“来书云夫子专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则兼人鬼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谏书中亦有此意,已于答伯谏书中论之矣。他日取观可见鄙意,抑又有说焉,不知生死人鬼为一乎?为二乎?若以为一,则专言人事生理者,其于死与鬼神固已为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后兼也。若须别作一头项穷究晓会,则是始终幽明却有间隔,似此见处,窃恐未安。”⑥《答吴公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朱子全书》(贰拾贰),第1960页。儒家认生死为一,因而言人事生理即可;佛教认生死为二,所以兼言生死,即便如此,其实仍是分生死为二。在认知生死之理上,可看出佛教见道工夫之非、之邪、之浅,因而佛教那里无公理可存。所谓“圣人不说死。已死了,更说甚事?圣人只说既生之后,未死之前,须是与他精细理会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说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见,佛不言显而言幽。’释氏更不分善恶,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狱。若是个杀人贼,一尊了他,便可生天。”①《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9页。也就是说,佛教为了除去物累,不分善恶,凡物扫尽。儒家却只要求消除邪见,邪见消除,理即呈现,而于生于死也无牵累。圣人不说死,因为死了没有什么可说,圣人只关注生、只讨论生。可见,儒家识道,清楚明白,平平常常;佛教虽识得某些道理,甚至高于一般识见,但只是随意略过,终究不能真正识道。所谓“儒者见道,品节灿然。佛氏亦见天机,有不器于物者,然只是绰过去”②《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1页。。
其次,由教学工夫看。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僧徒的代代相传。而僧徒的代代相传,是以传道、学习来实现的。换言之,教育僧徒的工夫,是佛教得以传承、光大的重要步骤。儒家也是以教育子弟为传播、传承思想的主要途径,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其中既有传经者,也有传道者。朱熹认为,在教育子弟方法方面,佛教与儒家也有差别。儒家教人,注重从实际行为出发,佛教教人,却以“静”为重。他说:“圣人教人,多是于动处说,如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颜子‘克己复礼为仁’,正是于视听言动处理会。公意思只是要静,将心顿于黑卒卒地,说道只于此处做工夫。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教之说。佛教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的如此。”③《论语十二》,《朱子语类》卷三十,《朱子全书》(拾伍),第1097页。儒学教人注重行为,重“动”;佛教注重意念,重“静”。但佛教之“静”是“空无一物”,因而“静”应改为“敬”,所谓“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而以敬为主,而欲存心则不免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外面未有一事时,里面已是三头两绪,不胜其扰扰矣,就使实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释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④《答张敬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朱子全书》(贰拾壹),第1345页。“敬”即严肃认真、诚实持守之意,且“必有事焉”,即非虚静。正如程伊川说“敬以直内,有主于内则虚,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是,则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须把敬来做件事着”⑤《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二程集》(一),第149页,中华书局1981年。。在朱熹看来,以“敬”为主与不以“敬”为主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佛教是不能理解以“敬”为主深意的。而不以“敬”为主,不管是以“静”教人之法,还是以“动”教人之法,都不一定有积极效果。所谓“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⑥《答张元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朱子全书》(贰拾叁),第2989页。不要刻意静坐,“敬”字通贯动静,这才是真正的求道工夫,因此,“敬”不是“虚静”——“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⑦《周子之书》,《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拾柒),第2143页。佛教教人方法正与此有异:
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常欲学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侥幸一旦恍然独见,然后为得,盖亦有自谓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辞气之间,修己治人之际,乃与圣贤之学有大不相似者,左右于此,无乃亦惑其说而未能忘耶,夫读书不求文义,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若曰儒释之妙,本自一同,则凡彼此之所以贼恩害义伤风坏教,圣贤之所以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后,乃益信其为幻妄,而处之愈安,则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于此矣。⑧《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1页。
佛教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儒家以读书穷理为大功;佛教教人倾心于不可知之世界;儒家教人致力于俗世之理;佛教教法神秘玄妙而伤风败教,儒家教法浅易明白而兴教正心;这样,佛教与儒教学工夫之异一目了然。因而朱熹说:“吾儒之学,则居敬为本,而穷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处在此。”⑨《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935页。儒家的教学工夫是以“敬”为本,又以“穷理”扩充,内圣与外王并显,佛教无此工夫也。
最后,由修养工夫看。佛教追求的是成佛,成佛需要修养,儒学要求人们成圣,成圣也离不开修养。佛教、儒学各有其修养工夫。但朱熹认为,佛教的修养工夫与儒家也有异。在修养方式上,儒家更多地注重读书、格物,进而才有修身、诚意、正心、养性,而且因为儒家之道是日常之道,因而不太强调修养工夫的刻意性,而主张修养的自然而然性。
且论其大者,如:
栖心淡泊,与世少求,玩圣贤之言可以资吾神、养吾真者,一一勘过,只此二十余字,无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如何须要栖之淡泊然后为得?且此心是个什么,又如何其可栖也耶,圣贤之言无精粗巨细,无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无二致,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岂独为资吾神、养吾真者而设哉?若将圣贤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无交涉,圣门之学所以与异端不同者,灼然在此。⑩《答许顺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贰拾贰),第1746页。
朱熹认为,求仁格物工夫,无需刻意去栖心淡泊与世少求玩,因为依儒家之学,人心当动则动,当静则静,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即光明,此亦乃本心全体大用,故求仁格物工夫只是时止则止,时动则动,时显则显,时隐则隐。顿悟工夫却属于刻意追求的工夫。朱熹说:“知,只有个真与不真分别。如说有一项不可言底知,便是释氏之误。若曰须待见得个道理然后做去,则‘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工夫皆为无用矣!顿悟之说,非学者所宜尽心也,圣人所不道。”①《学三》,《朱子语类》卷九,《朱子全书》(拾肆),第144页。这就是说,在佛教思想世界,有不可言的知,有不可思议的世界,但人的感觉与理性又无法认识这个不可思议之世界,只有顿悟才能洞察、把握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这在朱熹看来是一种谬见,因为知识只有真与不真两种形式,没有什么不可言的知。因此,如果说做事要等到识得事理再去做,即是有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如此一来工夫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识得道理后,工夫即为多余。顿悟即此类工夫。所以,由于儒家一方面否认有不可思议的世界,另一方面强调修养工夫的自然性,顿悟工夫自然为儒家所否定,因而儒士们不应醉心于此。我们注意到,由于朱熹对“知”的理解与佛教有不同,佛教言不可言的知,是指知的对象或状态,朱熹所谓真知、假知,是指知的性质。因此,有不可言的知,才有顿悟工夫,有真知、假知,才有读书穷理格物工夫;有不可思议的世界,才有刻意的顿悟;视世界皆日用庸常,则无需刻意修炼,是谓体用一然也。
由于佛教所见之道为空幻不实,因而识道工夫是混乱无序,教学工夫是邪遁诐淫,修养工夫是刻意做作。因而佛教工夫与儒学工夫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别。所谓“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其它有恶趣者,皆是众生饿鬼。只随顺有所修为者,犹是菩萨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见得个道理便实了,故首尾与之不合。”②《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1页。但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关于佛教识道方式的理解,关于佛教教学工夫的评论,关于修养工夫的批评,是否完全符合佛教实际呢?佛教识道工夫似乎不仅是一种理性直观,即便是理性直观,能否以一般的知识论原则否定它?而佛教教学工夫,更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既有读经,也有对问对答,更有后来的棒喝、机锋等,这些教学工夫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在修养工夫方面,佛教更是拥有丰富且宝贵的资源,佛教注重修养而且创造修养方式,成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修养的结晶,并不像朱熹所批评如此简单和毫无价值。正如朱熹自己所说:“言释氏之徒为学精专,曰:便是某常说,吾儒这边难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无一念走作别处。学者一时一日之间是多少闲杂念虑,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学非所学,枉了工夫!若吾儒边人下得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学者有二病:好高,欲速。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则是所以学者失其旨,二则是所学者多端,所以纷纷扰扰,终于无所归止。”③《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2723页。佛教信徒所学虽非正道,但在成佛的道路上所下的工夫之深、之苦、之繁,却是值得儒士们仰望与学习的。
如上由“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较详细地考察了朱熹对佛、儒差异的看法。没有疑问,朱熹对佛、儒之异的揭示,内容丰富、见识深刻,贡献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识见,显示了朱熹对佛儒关系理解、把握的深厚功底。但由于朱熹更多地关注的是儒佛之异和对立面,甚至认为儒佛是不可调和的,所谓“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龟山云:‘儒释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观之,真似冰炭!”④《释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拾捌),第3934页。视佛、儒关系如冰炭不可两立的立场,不仅与朱熹自己的理学体系之实际相悖,也妨碍了他更多、更合理地理解、利用佛教资源。这应是儒佛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