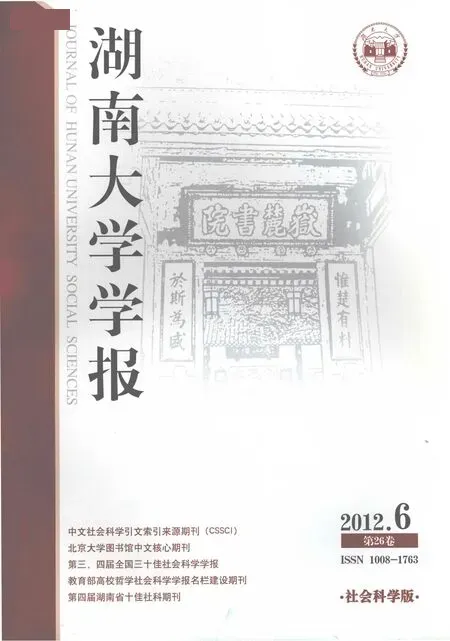和谐社会语境中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以对民事司法个案的反思为视角
陈秀萍
(河海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作为法律人的法官一方面受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不涉”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在面对“法律与道德困境”中,他们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迁就道德作出违背法理的判决而成为法学界的笑话;从“法律人”的视角作出违背社会生活伦理的判决而受到公众的强烈批判。
(一)司法个案简介
[案例1]“二奶继承案”:黄某和蒋某1963年结婚后,没有生育,抱养一子。1994年,黄某认识张某并于次年同居。1996年底,黄某和张某租房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2001年2月,黄某到晚期肝癌遂立公证遗嘱将自己的个人财产留给“朋友”张某。黄某去世后,张某据遗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蒋某执行遗嘱。法院判决认为:尽管遗赠是真实的,但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因此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彭宇案的一审判决:2006年11月的一天上午,原告徐老太准备乘坐同时进站的后面一辆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摔倒,第一个从前一辆公交车下车的被告彭宇将徐老太搀扶了起来。原告声称自己是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而受伤的,而被告辩称和原告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将其搀扶。法院在证据不足时,根据常理和社会情理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判决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案例3]合法妻子状告二奶返还财产案
2002年女大学生刘云(化名)因偶然因素与有妇之夫吴海洋(化名)产生婚外恋情,至刘云怀孕打胎到2004年底二人分手前,吴海洋共赠与刘云巨款21万。获知消息的吴妻于2005年初将刘云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丈夫的单方赠与行为无效,并要刘云悉数返还受赠财产。2005年底,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为,吴海洋私自将部分共同财产给了“二奶”刘云,侵害金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所有权。因此,侵害金晶权益的是吴海洋,与刘云的接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金晶要求刘云归还21万余元的诉讼请求。
(二)问题的提出
本文在此选择的司法个案都是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并在审理过程中或审理后引起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案例,也是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的,引起很多争议的案例。
在“二奶继承案”中,虽然法官的判决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掌声,然而学者们对这一判决却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很荒谬,说:“如果我们的法官能够以某个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德为由,就可以否定法律规则的效力,那么,整个法律制度都将崩溃”[1],“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2]当然也有学者赞同这一判决,认为面对合法婚姻家庭已经变得如此脆弱、道德舆论的支持已经不足以抵御金钱和利益的力量这一现实,如果法官此时再拒不对合法配偶援之以手,其社会良知安在?[3]人们不禁要问:道德能否成为法官的裁判依据?
对彭宇一案,人们的分歧更大。就法官与实务界的律师而言,理解这一判决的意见不少;普通民众和学者大都反对这一判决,但基于不同的理由:前者基于法律对公民的要求(基于义务的行为和自我保护意识)与道德对公民的要求如乐于助人之间的冲突;后者则对法官进行事实认定所依据的常理提出了质疑。[4]那么,法官认定事实时,是否应该考量道德的因素?又该如何考量道德的因素?
对合法妻子状告二奶返还财产案的判决,学者们之间也颇有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巫昌桢教授认为“二奶”必须返还21万元赠款,其法律依据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没有特殊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具有平等处理权。[5]而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二奶”财产权应获法律保护。他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二奶”应受谴责,但“二奶”首先是人,是具有独立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人们在谴责‘二奶’行为的同时,不能谴责她的人格、剥夺她的权利。[6]那么,法官司法裁判时,如何才能保持中立的立场,既不将对当事人行为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相混淆,也不刻意地将不道德者的无效行为认定为有效?
二 法律的伦理性:法官民事裁判的理论前提
在民事裁判中,法官应该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困境,又如何把握“忠于规则”的职业要求与“实现伦理”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从法律的伦理性说起。
(一)法律的伦理性与法官的伦理解释
所谓法律的伦理性就是指任何时代的法律所具有的与特定社会的伦理精神相一致的特性。从法律产生的历史来看,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习惯与道德,即如学者所言:“习惯法的形式是‘法律’的,内容是‘习惯’的,而精神则是‘伦理’的。”[7]虽然现代社会法律的形式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律的技术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但是,有智识的人们透过种种纷繁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法律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它总是体现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和精神价值。
由于法律具有天然的伦理属性,立法者制定法律就是将特定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伦理要求具体化为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然而,就在伦理具体化为法律的过程中,由于对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充分考虑就可能使法律在某一具体的案例中偏离自己表达和实现特定伦理的目标。所以,法律的伦理性还意味着作为司法者的法官应该尽可能将法律规范体系理解为在伦理方面是一致的。
(二)规则之内的伦理维度:法官民事裁判之一般情形
忠于法律、坚持法律与道德不涉被中国学者认为是法律人的共同理想与信条,所以,法律人应该对道德问题保持沉默,摆脱传统社会中政治、行政、道德或宗教的束缚,使法律职业成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8]实证主义法学家基于正义、道德的相对性,认为“法律所应当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永远不可能从那些不断变化且必定是主观和形而上的道德标准中获致的”[9],执法、司法的法律属性意味着执法与司法中不能用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10]坚持法律与道德不涉是建立法律确定性与权威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它也应该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事实上,法官裁判的“忠于法律”与“伦理维度”是一致的。首先,法律是以实现特定社会伦理为根本目标的,其在价值理想的“实质”方面具有抽象的正义、人道等特性。其次,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由于法律的形式性要求使得忠实于法律的判决可能与实质正义不完全一致,不能实现绝对的公正时,严格遵守规则也是为了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义务性道德,这是实质正义的必要妥协,因为法律一旦从其母体——伦理中独立出来以后,就有自己的形式与逻辑。虽然法律的这一形式化、理性化要求可能导致法律在某一具体的案例中偏离自己的伦理目标,但在具体的司法中只有遵守法律自身的逻辑与形式要求,才能建立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从而真正实现特定社会的伦理。最后,在民事领域,法官通常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当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时,坚持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是阻止法官的恣意与任性,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11]
(三)规则之外的伦理维度:法官民事裁判之例外情形
一般情形之下,法官裁判应该忠于法律、严格遵守规则的明确规定,但这种严格规则是有例外的。这个例外就是:人类必须敬重普遍生命及由此产生的行善原则。敬重人类生命的原则就意味着:“第一,任何人不得任意杀戮;第二,任何人的生命不得遭受不必 要 的 危 险 和 威 胁。”[12](155-156)这 一 人 性 规则是基于基本社会生活原理而产生的。“行善原则要求,在善与恶之间,必须总是选择善;在善与更善、恶与小恶之间必须选择更善与小恶。和实践理性原则一起,它构成了所有理性行为(道德、智谋的和作为手段的)的基础。”[12](155)规则之外的伦理维度就意味着:当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与两个基本伦理原则相冲突时,必须作出符合基本伦理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符合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道德行为的鼓励——的判决。比如说,这样一个案例:一对年近六旬的老年夫妇,拣到一个被遗弃女婴,含辛茹苦将她抚养到14岁,可是一场无情的车祸夺去了女孩的生命,肇事司机赔偿7万元。女孩的亲生父母为争夺这笔赔偿金将这对老年夫妇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赔偿金归女孩的亲生父母所有,理由是老年夫妇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样的判决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 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的现实分析
根据法律的伦理性,作为民事裁判者的法官,自然应该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与理论逻辑。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从本文选取的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法官应该更加谨慎处理的几个司法个案来看,法官的判决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官判决中的道德实用主义倾向
我国许多法律都是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移植过来的,尤其是在民法领域。但在司法适用中还是优先考虑事实情形和解决实际问题。它立足于一种从事实到原则再回到事实的认识方法,和现代西方大陆法的形式主义认识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3]一般说来,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都有体现道德的原则条款,但这些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都是极其谨慎的。在司法中首先应该适用法律规则,只有在适用法律规则会产生类似于“帕尔默遗产继承案”中的荒唐结果或者违背最基本的人道原则的时候,才以体现道德的原则作为补充依据。但就中国司法情况来看,对原则的适用远不如西方谨慎。比如说,在“二奶继承案”中,法官当然知道,根据继承法方面的法律规则,经过公证遗嘱应当是有效的,但如果认定遗嘱有效,那就意味着“二奶”胜诉。就此结果而言,有道德正义感的法官也会觉得破坏别人家庭的“二奶”得到这份遗产对其合法妻子而言是不公平的,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与社会舆论一起造就了“二奶”败诉的结果。作为法官,他同样知道合法妻子的权利本来可以通过追究重婚和侵犯配偶权等途径获得救济,但她似乎放弃了这一权利。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为了较为公平地解决这一问题,法官找到了“二奶”败诉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言,“在指导法庭判决的具体法律条款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接受了西方形式主义的权利原则,同时又改变了这些原则的普适性主张和目标,而代之以适合中国现实的实用性规定。它背后的法律思维方式其实是和清律一样,是一种实用的道德主义”[13]。
(二)过于迁就现实道德而忽视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
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理念。虽然法律与道德都以特定社会的伦理——即以实现最低层次的道德和鼓励愿望性道德为目的,但法律本身的确定性、程序性和逻辑性等形式性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于追求实质正义的道德,这些可能使得在具体的案例中法律与道德不完全一致。即使如此,法院也应该首先尊重法律的这一形式要求,这是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的要求,也是人们信任法律的前提。在“二奶”继承案中,判决的掌声是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为代价的。虽然我们可以认为“二奶”和被继承人的行为不道德,但这主要是他们的同居行为,而不仅仅是留“遗嘱”的行为。如果他留“遗嘱”是为了他的孩子和“二奶”的生计,那就不违背“公序良俗”。①在德国和日本都有相关的判例。具体可参见何兵:《冥河对岸怨恨的目光》,载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 boardid=92523&id=18788,2009年3月25日访问;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载http://linlaifan.fyfz.cn/blog/linlaifan/index.aspx blogid=60380,2009年3月25日访问。对法院而言,如果要作出判决,就应该尊重既存法律条文。由此,笔者认为,只考虑实质正义和道德,而对当事人的复杂行为作出简单化的判决,虽然判决结果照顾了受害者的利益,但是如果以不尊重继承法的具体规则和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为代价,那显然是不合适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法律制度的基础是确定性与客观性……,如果以维护法律权威为职责的法院,公然宣布依据道德处理案件,那么,谁又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呢?……谁又有权力确定社会公德的内容和标准?”[1]而在“合法妻子诉二奶返还财产”案中,显然也是在实质正义即“不能让‘包二奶’者人财两得”和“二奶也是受害者”这一道德原则影响下作出判决的,也一样牺牲了具体的法律规则。从表面上来看,“包二奶”者人财两得,好像不公平,“让‘包二奶’者人财两得”的判决可能不利于对“包二奶”行为的抑制,但如果直接判决不让“包二奶”者人财两得,既是对法律规则的违反,也是承认了“二奶”的身体与金钱的直接交换,这显然不利于女性独立人格的培养,甚至有助长“包二奶”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可能,因为女性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是从根本上阻止或减少“包二奶”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况且,如果“二奶”确实受到欺骗,其权利受到侵害,她当然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过于强调“法律人”思维而忽视社会生活之伦理
法律不同于道德,而中国法律道德化的传统常常被法学家们认为是阻碍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于是有些法官的做法可能与“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与权威性为代价来实现道德或实质正义的要求”的做法相反,认为司法应该独立,判决不应该受社会舆论和大众道德的影响,似乎故意要与道德划清界限。殊不知,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法律的伦理性、实现最低层次的道德和鼓励愿望性道德②美国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分为义务性道德和愿望性道德,前者是低层次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也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而后者则是高层次的,永远没有边界的。具体可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第一部分,强世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是法律的永恒追求。法律不同于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所提倡的就是法律所反对的,法律的判决就一定要跟道德观念相背离;法官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并不意味着法官在自由裁量与自由心证时也不受法律的“实现最低层次的道德和鼓励愿望性道德”的约束。在彭宇案中,法官在自由心证时,是以法律人的逻辑与思维来推定“相撞”事实的存在,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是法律人。法律规定人们必须遵守某些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只会尽自己的义务,而不去做得更好,事实上人们都是乐于行善的。相反,依据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常理,已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相撞”事实的存在。而且法官在推理时,也不能无视其判决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在“合法妻子诉求二奶返还财产”案中,法官也似乎故意要与道德划清界限,即不能因为“二奶”是不道德的就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如果这一判决是遵循了法律规则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那么这当然是很好的判决,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这一案例,本来法律的规定与道德是一致的,如果未经共同所有人的同意而将共同财产赠与非“二奶”的第三人也应当是无效的,第三人也应当返还所赠财产。显然,法官自然不应当以受赠人是“二奶”而认定其不用返还了。
四 法官裁判的伦理维度之实现
显然,在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中,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是必要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的实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心证时的社会利益考量
自由心证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可以根据自己良知和理性、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而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自由地取舍证据,认定证据证明力大小。无疑,自由心证制度有助于法官在当事人证据不够充分的具体个案中作出妥当的事实认定,但同时它也容易导致法官的专横。所以多数国家实施自由心证的同时,也有诸多法定证据规则和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就当代中国法治现状来看,虽然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官可以自由心证,但深受移植法律影响的、越来越职业化的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时,应该尤为谨慎:首先,他应尽可能用一种普遍承认的相对客观标准而不是法官自己的癖好和信仰作出事实认定,应该坚持“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法官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法官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14]其次,法官还有必要权衡比较当客观事实与其根据自由心证所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反时,其裁判结果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或者对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彭宇案中,对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相撞问题,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法官自由心证时必须依据当代中国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常理和情理来认定事实;其次,法官还有必要就其自由心证结果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出更加慎重的权衡,并对此加以更加充分的论证和说理。如果根据自由心证认定原告与被告相撞,事实没有相撞时,这样会对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反,如果认定他们没有相撞,事实上相撞,又会对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显然,前者对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行为的引导就可能是“做好事要谨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是后者,对当事人及其他人行为的引导可能是以后自己应该尽量注意不被别人撞着,一旦被撞要尽最大可能保存好证据。法官应该反复斟酌“冤枉好人”和“放纵侵权”相比,哪个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更大,法律首先应该实现的是不“冤枉好人”,还是不“放纵侵权”。
(二)自由裁量的伦理限制
由于立法者无法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情况立法,他必须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权力的行使还是要受法律的实现伦理生活之目的的制约,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能够体现对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道德行为的鼓励和保护。比如,我国司法法官对 “婚姻关系中的违约金条款问题”的处理。原告和被告在结婚前签订了合同,或者在婚后签订“忠诚协议”,约定: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出现婚外情就支付给对方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有关违约金的规定是合同法的主要内容,而婚姻关系是身份关系,不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同时,我国婚姻法也没有关于“婚姻合同”或者“忠诚协议”的违约金条款的规定。这种“协议”或“合同”是否有效?这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但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并不是完全不受制约的,而是应该考虑作出有利于道德方或不利于不道德的过错方的判决。当然这种判决必须是经过仔细权衡、反复论证以后作出的。在这样的案例中,出现婚外情的被告显然是不道德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似的“合同”或“协议”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让过错方支付另一方违约金既符合法律的逻辑,也有利于弘扬公序良俗。因此,法官认定协议有效,判决支持原告。这样的判决只要经过充分的说理,就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并接受法官的自由裁量,从而便于判决的有效执行。
(三)法律解释之伦理取向
虽然西方对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已经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转向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但针对中国的法治状况,在民事裁判中,法律解释的伦理取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特殊情形下对法律作出整体性解释的伦理取向;一般情形下解释法律概念边缘“空缺结构”的伦理取向。这里的特殊情形是指前文所说“规则之外的例外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可以对法律作出整体性解释,具体可通过对“善意违法行为的赦免”、“恶意行为的合法利益的取消”、“明显道德行为者利益的保护”等途径来实现。[15]
在一般情形下,适用法律规则的结果并不违背最基本的正义和人道,此时更应该强调法律的确定性。从理论上来说,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和逻辑统一性为法律的确定性准备了前提,法律的确定性成为法治建设的理想目标,然而,源于文字的歧义性、文化的特殊性和生活复杂性的法律的不确定性却是我国法律实践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肯定法律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但并不能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哈特认为,法律规则有一个其意义毫无争议的核心,同时所有的规则也都有一个不确定的边缘,前者称之为“意思中心”,后者则是 “空缺结构”。[16]在“意思中心”,由于语言的外延涵盖明确,人们对规则的理解不易发生争议,如交通工具当然涵盖汽车、摩托车;而在语言的“空缺结构”中,语言的外延涵盖不明确,人们容易对规则产生争议或者困惑,如交通工具能否包含带轮滑板或旱冰鞋。[15]无疑,在法律概念的“意思中心”,即使适用这种确定性法律解释的结果有失公正,只要道德一方的利益能够有其他救济途径时,就不用以牺牲法律的权威与程序为代价。[17]而法律语言的“空缺结构”却给法官在具体案例中相对自由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可能。他们也还应该根据法律的根本目的(符合伦理的生活)进行法律解释,即其解释的结果,应该是与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幸福相一致。
[1] 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学研究,2002,(6):3-14.
[2] 杨立新.2001年热点民事案件点评[N].检察日报,2002-01-04.
[3]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 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 =10395,2002-10-23/2011-05-27.
[4] 周永坤.常理与判决——兼评彭宇案的判决理由 [EB/OL].http://www.jcrb.com/fxy/blog/200806/t20080613_22446.html,2007-10-25/2011-12-02.
[5] 许英.“女大学生错发短信结孽缘”引出法律难题[EB/OL].http://jsj.ts.gov.cn/jsj_newcenter.asp?newsid=12957,2005-06-27/2012-04-02.
[6] 智 敏.不 让 “包 二 奶”者 人 财 两 得 [EB/OL].http://www.gmw.cn/01wzb/2006-06/25/content_439304.htm,2006-06-25/2012-04-02.
[7] 胡旭晟.论法律源于道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4):1-10.
[8] 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J].中外法学,2001,(3):328-339.
[9] 邓正来.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EB/OL].http://www.studa.net/2003/4-23/2003423133732-11.html,2003-04-23/2010-05-25.
[10]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的难解之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1):1-9.
[11]何四海.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商 基于法院和当事人协商的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59-62.
[12][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3]黄宗智.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EB/OL].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65,2007-10-31/2012-04-04.
[14][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5]陈秀萍.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J].南京社会科学.2008,(7):91-99.
[1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郑成良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7]张翔.论公民合法财产权的刑法保护[J].湖南社会科学,2011,(3):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