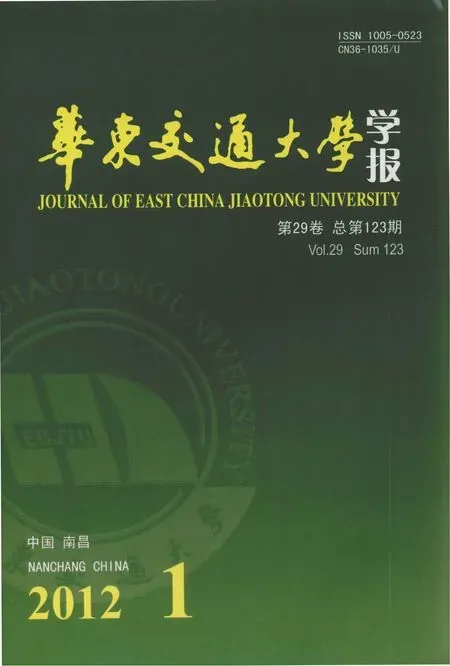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及其渊源
单伟红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富有创新成就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劳伦斯在世时间不长,但创作成果十分丰硕。在他创作的各类作品中,他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主题近年来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欧洲各国的人们始终保持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即人与自然平等和人与自然对立。坚持人与自然是对立关系的人们认为,人类应该成为自然的主宰,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坚持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的人们则认为,人与自然不存在贵贱优劣之分,都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应该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两种自然观也经历了一个相互转变的过程。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面临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威胁,历尽千辛万苦去战胜自然中的一切灾难就成了人们的首要任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渐渐远离了自然界,过着丰衣足食的现代化生活。此时,面对环境的污染和城市的喧嚣,人们又开始怀念大自然的纯净和美好,油然而生一种向往自然、眷恋自然的心态[1]。英国文学巨匠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崇尚自然的典范,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诗歌、游记、散文以及绘画都反映出了他的生态哲学思想。
1 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及生态意识
劳伦斯出生于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工厂”时代,面对一切都被机械化的社会,劳伦斯在其作品中深刻地批判了工业化、机械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带来的破坏,用自己的创作对自然之美高唱赞歌,竭力寻求自然和谐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批判讨伐,希望以此唤起世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回归自然和谐的社会。
1.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劳伦斯的作品里,几乎一切野生动植物都是神圣而有魅力的,《鸟、兽、花》中的自然被劳伦斯描述成了一个“新地球”,他以一个非人类的视角来探索自然世界,自己仿佛是其中一员来表达动物的欢快和自由。[2]在他的收山之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篇,劳伦斯却直言不讳的指出人类已经到了一个悲剧性的时代,人类已身处废墟之中。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位精神萎靡的庄园主夫人康妮,半身瘫痪且追求不同的丈夫令她几近绝望,身体也日渐消瘦,面对丈夫附庸风雅的追求也是厌恶至极,此时的康妮只有逃离令她窒息的庄园,通过在自然中的释放,对生活重又有了新的希望。而为了逃避妻子纠缠的梅勒斯在自然中找到了宁静,过着简单却又平静的生活,他们在自然中的相遇给彼此带来了重生。备受读者和评论家喜爱的《虹》这部作品中,汤姆那强健的生命活力和气息也来自于他常年随着自然节奏的劳作,因为有着模糊的理性意识,汤姆能够很好地顺应自然的规律,从而收获了和莉迪亚的幸福生活。在劳伦斯的作品里,处处流露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让人油然而生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学者蒋家国就曾评述:“劳伦斯对自然的崇尚,绝不仅仅是对大自然和自然美的崇尚,更主要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与推崇。”[3]
1.2 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大多是以英国工业社会的大环境为创作背景,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和批判。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原来拥有的恬淡安宁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快节奏、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模式。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梅勒斯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从此过上风光的生活,但他的不愿循规蹈矩本性使然,怀着对活力和自由的渴望,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的森林作了查泰莱的猎场守护人。他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上流社会的语言,但他却宁愿使用那有血有肉的下层阶级的土话来表达他真正的思想。在梅勒斯看来,军营里的上层阶级同样形同缺乏生命力的机器,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梅勒斯对战争的无情和残酷认识深刻,对于金钱对人精神的毒害和所谓文明对人类精神的摧残更是深恶痛绝,他希望极力保持着自己纯洁和独立的生活。在康妮出现之前,梅勒斯本想守住自己的孤独,没想到康妮的出现便将这一切彻底打破,使他又一次建立起了人间的关系。梅勒斯甘愿做一个守林人,其目的是为了能远离机械和金钱。劳伦斯理想地希望顺从人的生命本能,让本能的欲望得以满足,从而建立理想中的“新文明”,这是一种富有人文情怀和人道精神的设想,因而具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尽管劳伦斯的习惯是用感情去衡量一切,但他又确确实实从未放弃过理性,对周围理性世界的一切,他的心理是既接受又拒绝的,充满了不满的矛盾心理。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关注和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他在呼唤一种人的新型关系和新的人性,在企盼一个伟大的人类、自由的民族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诞生[4]。
1.3 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为了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竞争也渐渐异化,从而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双双遭受破坏的情形下,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在劳伦斯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菊馨》中,他深刻地刻画了工业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和隔阂。矿工妻子伊丽莎白的生活充满了恐惧,酗酒的丈夫常常过家门而不入,她只好在猜测、悔恨与烦躁中等待。最终她却等来了在矿井事故中丧命的丈夫。这一刻,面对丈夫沃尔特仍然温热的身体,她才在猛然间意识到丈夫和她彼此之间是多么陌生,作为夫妻,除了孩子是唯一的纽带,他们之间甚至从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对方。伊丽莎白与丈夫之间由于缺乏了解与信任,她从内心排斥丈夫,甚至不尊重丈夫,直到丈夫死亡她才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多么失败。在这部作品里,劳伦斯给我们刻画了煤矿工人的不安、忧虑和艰辛,反映了工业文明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甚至是夫妻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在《儿子与情人》中,无论儿子保罗与母亲之间,还是莫瑞尔夫妇之间、以及保罗和克拉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其实质都是文明价值观与自然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劳伦斯所希望体现的,正是他一以贯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 生态思想渊源
2.1 历史背景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大门,也打开了中世纪束缚着西方人智力的枷锁,从而带来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腾飞。在手工劳动逐步被蒸汽机的利用取代之后,各种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以及钢铁的冶炼都让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因而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而地处大不列颠岛的英国,有幸第一个享受到这场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核心的国家,有着相当比重的农业人口此前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从1770年至1870年为期仅10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己经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手工生产被机器生产取而代之,手工作坊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机械工厂所代替。工业革命的后果是:尽管英国的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然而变成了工业国之后的英国,绝没有变成人间的乐园与天堂。“在工业革命前夕,就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来说,英国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出多少,英国工业的某些技术还落后于一些国家。然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得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5]原来英国人享受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渐渐远离,曾经茂密的森林也由于工业生产的需要几乎被砍伐殆尽,而随着工业机械的开进,田野里的花草也同样遭遇了被铲除的命运,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乡村因此而变得满目苍夷与荒凉。乡村不再宁静,取而代之却是隆隆的火车和机器的马达声。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过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环境污染,其后果是人类不得不再一次受到自然的控制。同时,高科技的战争武器也在两次大战中给人类带来了深重可怕的灾难。“英国变成了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工业化的步伐扰乱了托马斯·哈代的‘牧歌式田园’,哈代《绿荫下》再也没有了乡村的自然风光。”[6]
一代文学巨匠劳伦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于1885年9月10日在英国出生了。
2.2 文化背景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固有的资本主义矛盾也由于这些进步的科技和发达的物质文明被激化出来,从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西方国家在战后都对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在短期内收获了相对明显的成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困扰西方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起被概括为人和社会的异化问题。19世纪,西方世界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生产力走向了电力时代;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标志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学革命”,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对于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运动之间的统一性问题;第三次技术革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次的技术革命以原子能利用、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开发利用为标志。在这几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从危机走向发展。但伴随而来的也有很多严重后果。一方面,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演变成难以控制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导致个人的无能为力和严重的依赖感,从而引发一系列诸如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导致生态平衡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些伴随现代高科技发展而来的问题和后果,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学艺术关注的焦点,对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劳伦斯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富有创新成就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一代作家的创作都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无论是把艺术家的生命意义从理性转向意志本能和直觉,从客观世界转向人的内心深处的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是从现实生活走向人的个性潜意识道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们都把人的生命的展开作为核心思想,高度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致力于通过解放传统理性束缚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劳伦斯等现代作家对社会、人生以及艺术的崭新观念无不受到这种生命一时的深刻影响。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文学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开始呈现,出现了多种流派和多样的创作手法。尽管如此,在表现认得的异、重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究这一文学思想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作家对违背自然人性的现代社会深为不满,他们的创作多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因侧重从人性的角度和人类灵魂深处进行审视。而这种创作的整体环境无疑也深深影响了劳伦斯的写作。
2.3 生活经历
劳伦斯自幼体弱多病,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肺病的困扰。而父母由于个性和文化差异导致失和的家庭氛围让幼小的劳伦斯获得了非同一般的母爱,母亲把她几乎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儿子身上,而体弱多病的幼子劳伦斯更是得到了母亲的特别钟爱,这种超出了正常母子亲情的关爱致使劳伦斯的心理和情感发展都失去了平衡,这些经历给他的创作和人生轨迹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劳伦斯的初恋以失败告终。1912年,他到语言导师家拜访时与教授夫人弗里达·威克利的一见钟情改变了他的一生。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两人最终结为夫妻,而弗里达也成为了劳伦斯的终生伴侣。从此之后,劳伦斯的生活都是在弗里达的陪伴下度过的。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的缘故,劳伦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一种自然舒适的生态环境,来缓解城市的污染空气给他带来的不适。他们先后到过意大利和巴伐利亚。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弗里达的德国藉身份,他们到处受到驱赶,为此夫妻二人只能远离城市游走于乡村之间,不过,乡村环境的优美幽静以及廉价的房租更适合需要呼吸清新自然空气的劳伦斯[7]。虽然在此期间劳伦斯也到过伦敦做短暂停留,但污染严重的空气终究不适合肺病缠身的劳伦斯,于是,他们只得再一次踏上寻找心中自然生态的旅程,这一次,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西部等地的自然原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直到1926年,劳伦斯的身体已经有比较严重的不适,他因故回到家乡诺丁汉短暂停留之后,不得不为寻求一个能让他的肺呼吸道新鲜空气的地方而再次踏上追寻生态荒野的征途,辗转于法国和意大利。1925年他被确诊为肺结核,1929年,劳伦斯的朋友为他寻找到法国的旺斯作为疗养之地,他于1930年3月2日死于此地。
纵观劳伦斯的一生,由于出生时就体弱多病,身体的虚弱和肺病的折磨给他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局限,他不得不一次次离开环境恶化的工业城市,游走在没有受到污染和破坏的自然荒野中。劳伦斯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生时家庭经状况的拮据,父母背景和文化差异不同所带来的争吵和冷漠,这一切都没能让幼小的劳伦斯感受到童年该有的快乐和幸福。青春年少时,正赶上英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富饶的田地被侵吞,美丽的自然被践踏,宁静的生活不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着残酷剥削,工人即使辛苦劳作也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双重影响之下,劳伦斯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性格也变得沉默内向。他的作品“扎根于英国土壤,又站在时代这个制高点上审视社会所有的骚动和危机”[8],他对和谐美好自然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在他的创作中也是无处不在。
3 结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以及生活经历的影响之下,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在他的创作中随处可见。从他的第一部作品《白孔雀》开始,就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揭示了导致作品中主人公婚姻悲剧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田园生活的淳朴与工业文明带来的铜臭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已初露端倪。在他的谢幕之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他把自己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阐释得淋漓尽致,无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是精神生态方面都表现了自己一贯的探索和追求,给人们展示了自然之美以及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扼杀与摧残。尽管劳伦斯的习惯是用感情去衡量一切,但他又确确实实从未放弃过理性,对周围理性世界的一切,他的心理是既接受又拒绝的,充满了不满的矛盾心理。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关注和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他在呼唤一种人的新型关系和新的人性,在企盼一个伟大的人类、自由的民族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诞生。
[1]苗福光.生态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4.
[2]潘灵剑.劳伦斯《鸟·兽·花》:人的复归与宇宙和谐秩序的祈唤[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1):20-24.
[3]蒋家国.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1.
[4]张璇.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看劳伦斯的生命意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7-100.
[5]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19.
[6]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530.
[7]布伦达·马多克斯.劳伦斯:有妇之夫[M].邹海仑,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48.
[8]王雅琴.爱的拥有,爱的超越——浅论劳伦斯的性爱小说[J].江南大学学报,1991(1):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