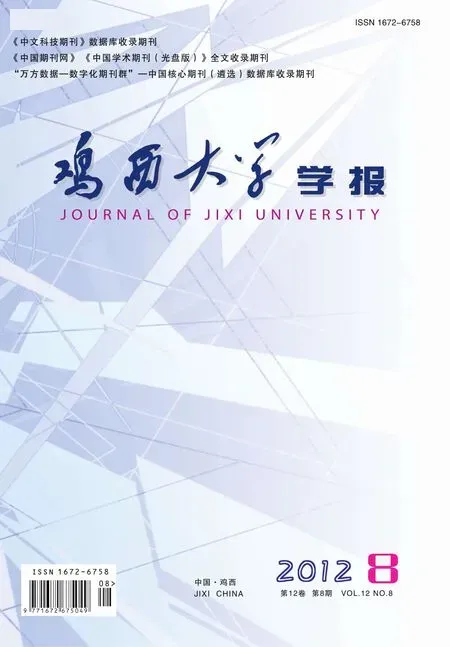云南甲马的艺术价值探析
何 奎
(保山学院艺术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甲马在民间有多种称谓,北方地区称为神马,江浙一带称为纸马,而云南也因不同地域称谓也有所不同,如甲马、纸火、甲马子等多种称谓。甲马是流行于民间,专供民间宗教祭祀活动中用于焚烧或者张贴的民俗文化用品,是劳动人民祈福纳祥、禳灾辟邪的特殊精神寄托媒介,是一种民间木刻版画。甲马艺术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名气的普通民间艺人利用闲暇时间创作的,带有清新、质朴的随意性,不过分雕琢和修饰,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虽然这些民间艺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但他们随时随地都和普通劳动大众生活在一起,深谙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需求,创作出了一张张形象生动、鲜活的艺术作品。也正是这些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民间版画艺术的民族形式,反映劳动大众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趣味。这些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作品,建构了民间文化艺术精神的主要力量,坚守着最为朴实的民众审美意识。甲马艺术的表现题材广泛,集民俗、宗教、艺术于一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内涵,是珍贵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 “甲马”考释
甲马又名“纸马”,是民间版画的一种艺术奇葩,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作是民间迷信之物、不健康的封建残余而难登大雅之堂,不被广大艺术研究人员所重视。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一处于边缘位置的民间版画艺术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在地处边疆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甲马艺术滥觞于唐代时期,经五代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出现了高峰。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确切年代稽考的中国第一幅木刻版画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施刊的一卷《金刚般若经》卷首的扉画。[1]这幅木刻画为我们研究甲马起源提供了最直观、真实的图像左证。从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有关甲马记载的文献是来自唐代郑远古(号谷神子)的《博异志·王昌龄》一节中记载:“见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纸马献於大王。”可见,甲马艺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比较流行。
“甲马”在元明清的小说中也频频出现,以四大名著为例,其中有关甲马的记载就有三大名著。元末明初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记载: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有关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腿拴甲马神行走路的故事如: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我的这法,诸人都带得。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无妨碍。”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吴承恩的《西游记》第四八回也有关于甲马的记录:(陈澄等)祝罢,烧了纸马,各回本宅不题。另外,纸马在小说《红楼梦》中也出现过多次。如第五十三回贾府除夕祭祀: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等。甲马在小说当中频频出现,丰富了甲马艺术的民俗文化意义。
那么甲马究竟为何物?清代虞兆隆《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中给出了答案:“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同样赵翼《陔余丛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世刻版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前者,名日纸马。或谓昔时画神像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马”。因此,甲马是画或印神像于纸上供焚香祭祀拜神时所用的“凭依”,是通天、通神、通鬼的焚化之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甲马文化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大繁荣,“甲马店”“纸马铺”的出现是最好的见证。北宋著名风俗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了很多家店铺,打着各种招牌。画面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便画着一家专门经营祭祀用品的店铺,门前竖着“王家纸马”的牌子。《清明上河图》上绘制的“王家纸马”店是解释甲马艺术在宋代兴盛发展最可靠的实物图像左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清明节,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东京梦华录》中关于纸马铺的记载,从文献上再次证明了甲马艺术发展到宋代出现了高峰。
二 表现题材丰富——宗教大融合(泛“神”化)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万物有灵论”的阐释是:“万物有灵论是宗教哲学的基础,从野蛮人到文明人来说都如此。虽然最初看来它提供的仅是一个最低限度赤裸裸的、贫乏的宗教定义,但随即我们就能发现它那种非凡的充实性。因为后来发展起来的枝叶无不根植于它。”[2]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人类社会产生了宗教,随之也就有了关于神灵的崇拜和仪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图腾和宗教信仰,既有多神崇拜也有一神崇拜。甲马文化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民族信仰和宗教祭祀的基础上产生的,甲马艺术的表现题材众多,从周围环境中的山水、草木、牛羊、龙蛇等自然题材到民间传说中的诸多神鬼,无一不表现在一张张不足20厘米的纸上。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大省,由于历史原因和交通闭塞等因素,云南至今还保留着甲马这一古老的民间版画艺术形式,并且发展广泛、自成体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各民族有各自的民族图腾和崇拜神灵,“万物有灵”、诸神并列的地域特性为云南甲马艺术的表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甲马所刻的神鬼异物几乎无所不包,从帝王将相、天公地母、鸟兽鬼怪,到神佛仙道、瘟司蛊煞、喜神哭神、灶君财神,几乎集儒、道、佛、巫及本土诸神鬼(当地人称本主)于一方巴掌大小的糙纸之中。劳动人民在四时八节、婚丧嫁娶、猎耕鱼樵时总会请来诸神化身的甲马印符,为他们消灾避难、驱瘟冲喜、祈福纳祥。如送灶君(司命灶君)。《淮南子.万毕术》中记载: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传说灶君是玉皇大帝派来人间保佑全家的“家神”,但同时又要把每年家人的过错向玉帝禀告,所以百姓都很敬畏他。郑玄注《礼记·记法》也说:(灶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因此为了贿赂灶君在玉帝面前不说家人的坏话,民间便形成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晚祭拜灶君的习俗。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祭灶词》中写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饰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兮。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民间祭祀灶君的目的:让灶君“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另外,袁牧在《讨亡术》中记录: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孙欲问无由,必须以四金请陈作术……命家人烧甲马于门外。甲马作为劳动人民祈求上天庇佑的精神媒介,其用途和分工十分明确,有专用于供奉的、求吉利的、传信的、招魂的或者巫术的,甚至有直接命名为“精神甲马”的专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特殊“乘骑”。
三 造型稚拙——儿童般的思维方式
“大巧若拙”(《老子》第四十五章)天然而成,无须过分雕饰,稚拙随意,如出水芙蓉,妙不可言。鲁迅先生讲:“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甲马艺人似乎深谙这一名训,保持着孩童般的思维,创造了甲马这一“大巧若拙”,更符合艺术的最高境界的艺术形式。
儿童般的创作思维。毕加索在一次观赏儿童艺术展后感叹:“我像他们那么大时,已经可以画出如拉斐尔一样的画来,但是我穷尽一生的时间,去画出像他们那样的画。”[3]马蒂斯也曾表示要用儿童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保持儿童般思维的纯真是两位艺术大师共同的艺术追求。事实上我们无须舍近求远去学习毕加索、马蒂斯,因为在我们的民间艺术中处处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民间美术造型变化万千,风格纷呈,并非像一般人理解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夸张和异想天开的想象。它来源于中国古老文化千百年的积淀,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4]如果我们以学院艺术的标准去衡量民间甲马艺术,那么我们用的最多的词汇可能是:结构不准、没有体积、不合逻辑、幼稚不成熟等等。事实上,正是这样的不成熟甚至拒绝成熟的民间艺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传承着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滋养着所谓的“上层艺术”。鲜活、没有模式、流淌着生命的力量是甲马艺术真正的魅力所在。
甲马主要以人物(众神鬼)、动物为多,一般都以黑白、线条表现为主,少有着色。人物造型严守正面律,动物为侧面。风格稚拙、古朴、粗犷、生动,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强调表现对象的整体性,表面看来,结构不合比例,人物造型笨拙,印制粗糙,但正是这种创作随意简单,似不合逻辑但合目的的文化艺术,反而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稳健,散发着朴素的泥土味。刀味十足,纵横捭阖间充分表达了民众的意愿,稚拙的外表下更显民间韵味、更具当代感。形象夸张变形、构图饱满、平面化、装饰性的艺术语言,时时让人将之与西方现代艺术联系起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不就是民间的毕加索、马蒂斯吗?”。不同的是,西方现代派艺术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的背离和颠覆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物象的分离和重新组合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与其传统文化是相悖的。甲马艺术的创作却是同本身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是在尊重民族传统审美追求和文化诉求的基础上创作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甲马这一民间版画艺术在本质上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根本的区别。
四 当代影响
“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切美术的基础,不论历史上的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还是现代社会新的美术创作,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民间美术既是美术之源,又是美术之流;它的过去是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它的现在是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的艺术体现,是民族艺术的活的传统。”[5]甲马作为一种民间版画艺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甚至是其他艺术创作,同时也给现代版画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之源。云南普洱版画家群的现代绝版木刻创作具有很强的民间、民族韵味,无疑受到了民间版画艺术的浸润。如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获版画金奖的郑旭的《拉祜风情》,1989年获全国第七届美术作品展金奖的魏启聪《村寨》就明显地表现了艺术家对民间美术的关注和兴趣。
五 结语
随着学术界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甲马艺术也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民间艺术而引起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甲马作为一种竟乎被遗忘的民间艺术,它是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民族心理的集中表现,它的传承与发展融入了整个民间文化观念、社会背景、民俗活动等,是长时间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交融、渗透而形成的,是劳动人民集体意识的文化见证。研究甲马艺术将丰富民族民间非物质物化遗产的保护,为研究中国版画、民俗文化等提供资料和参照。
[1]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0.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一卷[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26.
[3][美]布拉德利·柯林斯.凡高与高更——电流般的争执与乌托邦梦想[M].陈慧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3.
[4]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8.
[5]孙建君 .中国民间美术鉴赏[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