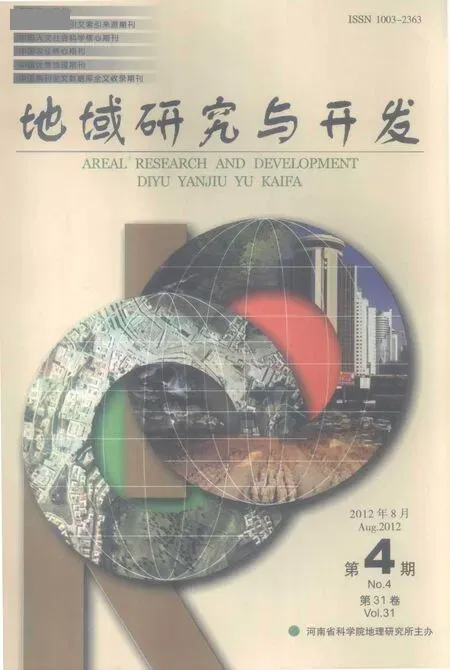地方生产网络尺度、结构与组织研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马海涛,王 琳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510275;3.北京华文学院,北京100037)
1 地方生产网络内涵
地方生产网络(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简称LPNs),国内外研究者给予的定义并不多,通常表达某地围绕生产某类产品形成的相互联系密切的一组企业[1]。事实上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产业区概念指出同一产业的大量企业的地理集聚可以产生地方化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地方产业系统与当地社会有很强的不可分性[2],这些都是地方生产网络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后期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内容渐趋多样化,从商品生产为主的关系研究(诸如产业链、商品链)转向围绕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资金流动、信息传递、知识创造等多个方面,并产生了多个与地方生产网络相近的概念,例如,后福特式的弹性专精地区、新产业区、创新环境、创新氛围等。后来,Hart和Simmie在探讨创新的空间性时提出了“地方生产网络范式(LPN paradigm)”概念[3],是对表达创新性企业趋于集聚的相关理念的总结,已经从对经济地理现象的描述上升为理论。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介绍和应用非常多,但对地方生产网络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仍显不足。随着世界各国对提升地方竞争力的广泛关注,国内城市对如何提升创新能力的讨论也不断升级。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生产网络将会成为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对解释地方经济现象、寻找发展中的问题,甚至对制定地方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这些方面都有哪些研究进展,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我国经济地理学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应该朝哪些方向努力,还需要认真梳理和思考。
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空间尺度、结构形态和组织方式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的3个重要方面。(1)空间尺度是指地方生产网络在不同空间尺度的联系特征,包括地方—地方、地方—国家、地方—全球等方面的不同尺度联系。空间尺度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网络的重要特征,也表明地方生产网络与外部网络和环境是分不开的。空间尺度可以看作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的横坐标。(2)结构形态是指地方生产网络的节点及连结的表现与分布特征。如果说空间尺度主要是考察地方网络同外部空间的联系情况,那么,结构形态主要讨论地方生产网络自身特征。结构形态可以看作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的纵坐标。(3)组织方式主要探讨地方生产网络不同空间尺度联系和结构形态是如何组织形成的、如何组织运行的,又是以谁为核心的。组织方式是一个阶段的行为,也是推动网络向下一阶段演化的动力。它可以看作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的竖坐标。下面从这3个方面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2 空间尺度方面的研究
地理尺度性(geographically scalable)是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4],地方生产网络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地方尺度。地方生产网络的空间尺度研究并非局限于地方之内,而是将与地方行动者发生联系的外部行动者考虑在内。Ter Wal认为地方生产网络中的发明家和应用者不仅仅包括与本地行动者联系的本地其他行动者,也包括外地行动者,因此,他将网络关系区分出3个尺度:地方—地方、地方—国家、地方—全球。他比较了法国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市(Sophia-Antipolis)2个产业的发明家在不同地理尺度的连接指向情况,发现各尺度的连接都随时间有增加,但2种产业有区别。信息技术行业的发明家地域联系随时间增加较快,且地方内部的交互学习的数量增加与地方同外部联系的数量增加同步;而生命科学行业的发明家地域联系随时间增加较慢,且在后期地方同外部联系的增加是以地方内部交互学习数量的减少为代价的[5]。该案例说明了地方相同但行业不同,其发明家网络联系的地理指向具有不同的变化。Ter Wal还使用专利数据,通过合作网络在不同空间尺度的演化考察城市创新能力的外部动力向内生动力的转化机制,发现电子信息产业的地方合作创新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地方与外部的合作创新数量并没有因此减少;而医药产业的地方合作创新数量仍然稀少,但地方同外部的合作创新数量却在增加[6]。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空间尺度的合作都对行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作用,但各地因地方特性有所差异,而且行业属性的不同对空间尺度的合作创新需求影响更大。
地方生产网络重点讨论地方内部经济现象,但不可忽视其与外部空间的联系。网络本身就是开放的概念,地方的发展也是始终与外部存在人员、物资和信息流通的。例如,Dimitriadis和Koh详细地分析了地方生产网络同外部紧密的物质和信息交换[7]。Saxenian分析了来自硅谷的跨国企业家对台湾和印度的IT产业兴起的重要作用[8]。Miao,Wei和 Ma对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开发区的研究发现,跨区域的联系是开发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联系[9]。Dimitriadis和Koh对希腊卡斯托利亚地区皮衣产业的分析,揭示了多种类型的参与组织是运行于产业区外部的,包括狩猎者、中介、辅助产品的供应、最终产品的销售等,也包括希腊和国外银行、希腊和国外政府、欧盟、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政治的、金融的和教育的组织等,它们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中[7]。这些研究证明了地方生产网络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需要不断地输入和输出物质和能量。
地方生产网络嵌入到地方环境的同时,也是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的。Yeung将企业集群描述为多个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脚印在一个地方的重叠[10];实际上,这种说法更适合于“地方生产网络”概念。从地方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上考虑,有些地方生产网络由全球生产网络“降落”[11]在地方,被“黏住”后逐渐发展而成的。这种地方网络可能会因全球网络的重新选址而随即衰退,而受本地长期发展历史和文化影响的地方生产网络[7]虽依然受全球网络的牵制,但其自生能力相对更强。
3 形态结构方面的研究
对于地方生产网络的要素构成及其重要性,研究观点在发生变化。起初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界定,一般认为是由中小规模企业构成的地方化生产组织,很多研究者把中小企业网络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代名词。例如,Kalantaridis按企业人口规模划分了地方生产网络中3种构成企业[12],分别是5人以下的家族企业、5~50人的小规模企业和51~100人的中等规模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中小规模的。然而,后来的研究认为大企业在产业区中的地位会变得更为重要[13]。Markusen依据企业的构造、对外和对内指向以及企业的治理结构等要素将产业区划分为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和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4种类型[14];其中,卫星平台式产业区主要由跨国公司或多厂企业的分支工厂或机构组成,就强调了地方生产网络中跨国大公司的作用。目前,对地方生产网络的构成认识逐渐统一,大中小企业都可以作为其构成,但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重要性程度仍然各执己见,这与现实中不同类型企业发挥作用有较大差异相关。
从整体上分析地方生产网络的结构更有助于对地方经济的剖析。一些学者从行动者的动机上将地方生产网络结构划分成随机网络和结构网络2种,其中,随机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随机连接而成,它的度分布(节点拥有的连结数量)遵循正态分布且没有聚类的特征;而结构网络是行动者之间根据某种原则有选择地连接形成,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15]。Giuliani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3个葡萄酒企业集群的知识网络结构,分别是非连续派系结构、双子群结构和核心外围结构[16],其中,非连续派系结构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网络结构,表明了由于企业知识本垒的差距较大,造成了集群内企业知识交流的障碍,使最大节点与本地其他节点没有知识联系;双子群结构是一种多个子网组成的结构,但各子网的密度不同,子网之间也有稀疏的联系;核心外围结构是一种网络中心密度高外围密度低的结构,有利于知识的扩散传播。
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的概念对于解释地方生产网络结构具有借鉴意义。例如,He Shaowei从网络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疏密程度上划分了密网(closure)和结构洞(structure hole)2种关系类型[17]。密网反映了地方网络内部行动者之间紧密的联系,结构洞则表明了地方网络之间弱联系的存在,这2个概念都是来自社会学对网络的研究。在密网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系非常频繁,途径非常多,但行动者获取的知识却大多是冗余的,一个行动者获得的信息其他行动者同样也可获得。在具有结构洞的网络中,行动者获取另一个小团体的信息往往需要借助数量相对很少的媒介,经过媒介获取的信息知识是新异的并有重要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媒介功能的企业一方面能够掌握多个小团体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在其他企业通过它获得新异知识时作为媒介可以得到额外的回扣(brokerage benefits)。因此,需要对地方生产网络中的密网和结构洞进行分析,这有助于在关键环节进行地方创新氛围的建设。
网络形态的描述也有助于对地方生产网络结构的理解。地方生产网络具有不同的结构形态。Liu和Brookfield研究台湾机床产业时,提出单中心和多中心的网络组织形态[18]。单中心包括星形、环形和层级3种,以星形最为常见。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生产网络是由多个单中心组成的多中心复杂形态,常被比喻为群星灿烂的星座;当然,星座并不仅仅由多个星状网络组成,还包括了关系较为疏远的个体[7]。结构形态是对网络结构的一种形象化表达,但很多结构是综合性的,难以用语言描述,而借助软件制作形象化图形是目前较为推崇的做法。
4 组织运行方面的研究
网络是一种既非市场又非等级制度的独特形式,它以关系作为其沟通方式,是开放和互惠的,介于市场和层级制之间[19]。因此,网络的组织方式也是介于市场的自由化组织方式和等级的垂直命令链组织方式之间,既通过水平的也通过垂直的相互调节来达到协调,其中,非价格关系的重要性允许不同程度地发展[20]。
对地方生产网络组织的内部动力有不同看法,一种强调合同以及激励决断(determination of incentives)的中心角色,它们是构成网络的关键因素[21];另一种强调这种结构发展中的相互信任角色[22-23]。其实2种情况应该同时在历史事实(路径依赖)、主流实践和地方环境的发展程度等框架下共同讨论。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必须保障合同中职责和规范的完成,因此,供应者和合作者之间无形的交换以及网络动力被限制。地方工厂与原料及辅助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大都是口头协议的合作交易关系,协议中的详细内容没有被写下来,不构成合同,它是在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非正式途径实现的。总之,网络中的连接不会构成一个绝对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过可靠性(solidity)形式也可以通过易变性(lability)形式;这与2种可能性有密切的关系,一是长期双边流动的产生,二是协议条款及关系管制机制的变化[20]。
各构成企业在地方生产网络的组织运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Dimitriadis和Koh通过案例分析了其中的组织规律,他们将地方生产网络企业划分为4种:领导厂商、主要生产体、次要生产体和自由生产体[7]。其中,领导厂商通常是区内最大的企业,组织并协调它的直接生产者网络,但却不会控制整个网络。主要生产体直接从领导厂商获得订单,往往完成不了任务,会进一步外包给其他的企业;它被领导厂商协调的同时,也会协调其他企业并建立自己的网络。次要生产体是最小的一种,从主要生产体中获得订单、原材料和样式,仅仅按要求进行生产,不会外包。自由生产体主要是为本地的生产需要进行加工,很少外包,也很少为其他企业生产,但它们的行为受本地生产内部世界的限制[1,7]。Kalantaridis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组织方式的解释有所不同,他将地方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划分成代理商、初级转包商、次级转包商、原料供应商和辅助服务商,其中,代理商主要接受外部订单并转包给主要转包商,自身不从事生产,却对地方生产的组织起到控制作用[12]。从上面案例分析中发现各类型企业在网络组织和运行的重要性程度上不同。领导厂商或代理最为重要,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要辅助者和协调者,管理、领导和控制成员的行为并保证网络目标的实现,直接推动主要生产体运行,间接促进整个网络发展。领导厂商在英国也被称为“管理者(caretaker)”[24],在意大利被称为“经济人(impannatori)”[25]。主要生产体或主要转包商尽管也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网络,但要遵循领导厂商或代理商的生产指示和交货期限,不能称为网络的管理者[7]。其他生产个体只接受生产任务,是被调控的企业,虽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但处于从属地位。
5 结论与启示
地方生产网络在空间尺度、形态结构与组织运行方面的研究,可以打开新产业区、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等研究的黑箱,以企业间关系网络为切入点,讨论各种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网络结构、生产组织方式和特征,并注重地方企业与其他不同空间尺度的企业间联系。这些研究可以透彻地理解产业集聚区在某个时段的生产组织特征。综合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对地方生产网络空间尺度的讨论,主要是对网络行动者在地方—国内—国际—区域—全球不同尺度扩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对行动者在地方尺度微观变化及其过程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2)对地方生产网络形态结构的研究,以对理想化类型的总结较多,而具体案例分析较少,这也与企业关系数据的获取难有直接关系;此外,在少量的案例研究中又少考虑企业的地理微观区位特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没有考虑企业的微观空间属性。(3)对地方生产网络组织运行的讨论,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往往局限在某个时段内,少有对不同时段组织运行方式变化的研究。
地方生产网络是分析地方经济的重要工具,而城市作为地方经济最重要的实体,今后可以在二者的结合上开展研究,以服务于我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能力增强的现实需求。在空间尺度方面:(1)城市产业发展应放在全球产业体系和全球生产网络中去考虑,分析城市企业与全球企业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2)城市各主导行业的创新能力与不同空间尺度企业的合作需求有何差异,如何根据企业需求制定行业发展战略和促进政策。(3)如何通过增加城市的对外道路交通和通信通讯联系,提高城市同外部的知识信息交流。在形态结构方面:(1)城市生产网络不同行业的构成有何差异,不同构成对城市经济的作用程度如何,有何问题。(2)城市生产网络的结构有何特征,是否存在结构洞,如何改善网络联系的薄弱环节。(3)如何用城市生产网络的结构来解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开发区建设中的关键企业培育、处理好多个开发区之间关系以及开发区同主城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建议。在组织运行方面:(1)不同城市网络的组织动力有何差异,如何根据城市地方特性制定促进政策。(2)如何充分发挥不同网络行动者的作用促进城市生产网络的高效运转。(3)可以通过对城市生产网络多个时段网络特征的追踪,探讨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内在动力,进而从网络环境改善和原动力提升方面为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探寻路径。总之,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可以为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城市发展实践又可以丰富地方生产网络的理论内容,地方生产网络研究与城市尺度的结合可以建立城市生产网络概念和分析框架服务于城市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地理理论与城市规划实践的互动发展。
[1]马海涛,周春山.西方“地方生产网络”相关研究综述[J].世界地理研究,2009,18(2):46-55.
[2]Marshall A.Elements of Economics of Industry[M].London:Macmillan,1910:19-48.
[3]Hart D,Simmie J.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J].Local Economy,1997,12(3):235-246.
[4]Sturgeon T J.How do We Define Value Chain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J].IDS Bulletin,2001,32(3):9-18.
[5]Ter Wal A L J.Cluster Emergence and Network Evolution: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nventor Network in Sophia-Antipolis[R].Utrecht:Paper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2008:1-24.
[6]Ter Wal A L J.From Exogenous to Endogenous Growth in Sophia-Antipolis: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Its Knowledge Network[R].Jena:Interdependencies of Interactions in Local and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2007:1-20.
[7]Dimitriadis N I,Koh S C L.Information Flow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the Role of Peopl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J].Production Planning & Control,2005,16(6):545-554.
[8]Saxenian A.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Industry& Innovation,2002,9(3):183-202.
[9]Miao Changhong,Wei D Y H,Ma Haitao.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7,48(6):713-732.
[10]Yeung H W C.Industrial Cluster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pproach[C]//Kuroiwa I,Toh M H.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Integrating Economie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83-120.
[11]Weller S.Beyond‘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Australian Fashion Week’s Ttrans-sectoral Synergies[J].Growth and Change,2008,39:104-122.
[12]Kalantaridis C.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of Macedonia,Gree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and Research,1996,2(3):12-28.
[13]Corò G,Grandinetti R.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J].Human Systems Management,1999(18):117-129.
[14]Markusen A.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J].Economic Geography,1996,72(3):293-313.
[15]Boschma R A,Frenken K.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A Proximity Perspective[R].Utrecht:Paper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2009:1-16.
[16]Giuliani E.The Structure of Cluster Knowledge Networks:Uneven and Selective,not Pervasive and Collective[R].Denmark:DRUID Tenth Anniversary Summer Conference,2005:1-20.
[17]He Shaowei.Clusters,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Knowledge:A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Model of Clusters[R].Denmark:DRUID-DIME Winter PhD Conference,2006:1-35.
[18]Liu R,Brookfield J.Stars,Rings and Tiers:Organisational,Networks and Their Dynamics in 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y[J].Long Range Planning,2000,33:322-348.
[19]Ansell C.The Networked Polity:Region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J].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0,13(3):303-333.
[20]Yoguel G,Novick M,Marin A.Production Network Linkages,Innovation Processes and Social Management Technologies: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pplied to the Volkswagen Case in Argentina[R].Danmark:DRUID Electronic Paper,2000:1-22.
[21]Williamson O E.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36(2):269-296.
[22]Bianchi P,Miller L.Innovation,Collective Ac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An Essay on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al Change[M].Milan:IDSE,1994.
[23]Saxenian A.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Cambridge M 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26.
[24]Boyle E.Managing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n Britain:the Role of the Caretaker[J].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1994,19(4):13-23.
[25]Howard R.Can Small Business Help Countries Compe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68(6):8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