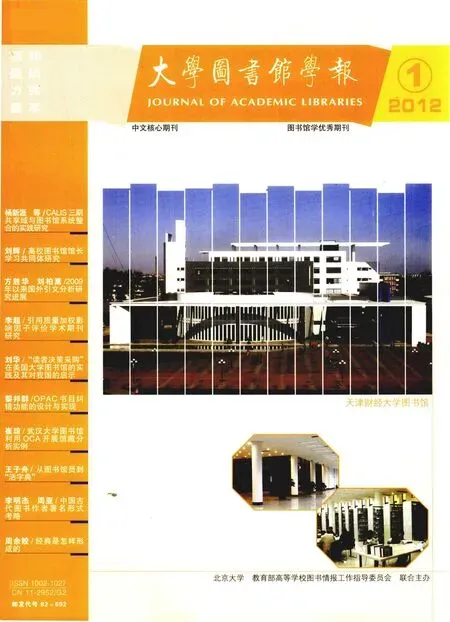从图书馆员到“活字典”——记张政烺先生
□王子舟
1 引子
张政烺先生被文史学界称为“活字典”,下面考古学者米文平向张政烺先生请教一例[1],足以说明这本“活字典”非同小可。
米文平是内蒙古研究鲜卑学的一位考古学者。鲜卑是中国古代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它曾经建立了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二百年,忽然就消失了。《魏书·序纪》称拓跋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魏书·礼志》言其祖先以石室为祖宗之庙,但后人一直不知大鲜卑山、石室所在何处。《魏书·乌洛侯传》还记载石室是拓跋鲜卑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2]
为了解开鲜卑山与鲜卑石室之谜,米文平多年来一直矻矻寻索。1980年7月,米文平与友人在第三次探访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时,发现洞中石壁上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时所刻的祝文。该祝文与《魏书·礼志》中所载祝文大同小异。由此,世人始知所谓大鲜卑山即是大兴安岭,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
米文平很快依据发现的祝文撰写了一篇论文《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并将石室祝文拓本上的文字全部录了下来。但在《文物》杂志已出清样即将刊发该文时,石室祝文中使用祭品的一段话“用骏足、一元大武、□□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中,有两个字因漫漶而难以确定为何字。为了尽快确定这两个字以使祝文不再存疑,米文平专门到张政烺家里求教。两天以后张政烺先生告诉米文平,这两个□□,应该是“柔毛”。《礼记·曲礼下》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孔颖达疏:“羊肥则毛细而柔弱”[3]。
米文平拿着张政烺先生手写答案的纸条,如获至宝。赶紧在文章清样两个□□的地方,填写上了“柔毛”二字。北魏石室210个字的祝文终于卒读。《文物》杂志1981年第2期头篇文章就是米文。该文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月报》转载,并引起海内外历史学、考古学界的轰动。
2 大学期间得名
张政烺先生(1912.4.15-2005.1.29),字苑峰,山东荣成县崖头村人。六岁上小学,毕业后又读私塾三年。少时博览群书兼习篆书。十四岁入青岛礼贤中学(教会学校,即今知名的青岛九中),遵旧制读四年,十八岁插入北京弘达中学(在西四大木仓胡同郑王府西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读高二。1932年,张政烺高中毕业,分别报考了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终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当年7月考清华时,国文中的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对子题为“孙行者”,都是史学家陈寅恪拟出。张政烺对出的对子是“胡适之”[4]。
张政烺入北京大学时,北大校长为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史学系主任是陈受颐。史学系教师中,钱穆教秦汉史,蒙文通教魏晋南北朝及宋史,辽金元史为姚从吾,明清史是孟森[4]。张政烺从小喜爱古文字,入大学后曾从马衡、唐兰两位大家学习古文字学。他的同学不乏才俊,如杨向奎、胡后宣、王树民、孙以悌、高去寻等,他们组织了潜社,切磋学问,出版社刊《史学论从》,张政烺也参加了进去,曾在《史学论丛》1934年第一册上发表专门研究中国最古的碑碣文字——石鼓文的论文《猎碣考释初稿》。这篇文章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郭氏曾将张政烺文章部分文字摘抄于其所撰述的《石鼓文研究》的书眉[5]。之后,张政烺又在《史学论丛》1935年第二册上刊发了专门研究古陶文的《“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他曾专门赠郭沫若一份印样,郭沫若回信称:“……尊说确不可易,快慰之至。”[6]
1936年,张政烺上大四的时候,一次听文学系的李光璧同学说,文学史课上胡适先生讲到《封神演义》至今未能确定作者,希望同学们有己见者可率尔以对,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征引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咸丰《兴化县志》等记载,细考明代万历间兴化人陆西星(字长庚)可能是《封神演义》作者。胡适看后很高兴,回信肯定了张政烺的观点,并在信末言:“我写此信,只是要谢谢你的指示。你若不反对,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独立评论》发表。”[7]后张、胡二人通信果然刊发于《独立评论》1937年第209号。张政烺连续几篇“干货”论文的面世,不仅得到师长好评,也深得同学赞服。
3 史语所图书馆“取书手”
1936年,张政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年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后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为著名辽金元史专家,文革中自杀)一同分到时在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就任图书管理员。当时史语所所长是傅斯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之成绩较优者,他必网罗以去[8]。从此,张政烺在史语所一呆就是十年,历任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
傅斯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近七年,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崇尚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192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倡导史学研究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9]。他认为历史学、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易由个人单兵作战式地进行孤立研究了,要靠图书馆、学会提供材料,要有好的合作环境方能有起色。因此,傅斯年非常重视史语所图书馆的工作。张政烺初到史语所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即负责图书采购。张政烺先生晚年回忆曰:
傅所长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他对图书工作要求很严格,单就购书而言,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资料。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的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在南京的那一年里,掌握了所内藏书的家底,也锻炼了记忆力和辨析力,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自然在实现傅所长采购图书的原则时就不会出现大的差误。购书时我注意选择那些经济实用的好书,让一定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史语所有的中青年学者说,当年我挑选的书,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没用的都没有。这样的议论,反映出那时我们忠实执行傅斯年所长的治所方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0]。
这段文字,说明在一个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称职的馆员应该要了解书、懂得书才能胜任工作,而张政烺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加之他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所以很快就对史语所图书馆的馆藏了如指掌。因此,当读者借阅书籍、查找资料,有什么疑难问题时,张政烺都能大显身手,给予必要的帮助。史语所的研究人员有时称张政烺为助理研究员,他总会一本正经地说:“不对,我不是助理研究员,我是‘取书手’。”[11]图书管理员在研究单位是职位低下的工作,张政烺毫不顾忌地宣称自己是“取书手”,是知他并不以此为窘,反以为荣,深知其工作价值与服务意义。
了解书、懂得书,必须要掌握版本目录学知识。张政烺在史语所图书馆任管理员期间,自学版本目录学。1937年春,受傅斯年所长之派,他与另一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到南浔嘉业堂购买《明实录》,他利用此机会在江南浏览诸多藏书家、刻书局的古籍珍善本,由此增加了许多古籍善本的感性知识。此后,他利用所学还编印馆藏方志目录一册,撰写过版本目录学文章并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
4 与图书颠沛流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史语所开始漫长西迁过程,先迁长沙,再迁重庆,又迁昆明,再到四川李庄。当时史语所图书馆馆藏图书13万册(中文12万册,西文1万册),张政烺参与西迁书籍的押运,一路颠沛流离,十分辛苦。如张政烺回忆长沙到重庆一段历程曰:
我们在长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条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达汉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转换船耽搁时间较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书运到重庆。这批书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坝新盖的三间大房子里,为全所人员从昆明再迁四川南溪李庄开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是我到史语所后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当然是一大快事[10]。
把苦事作为快事,反映了张政烺晚年回想当年事件有着引以为豪的感觉。1938年春,史语所研究人员到了昆明。大家集中后,在云南大学旁与靛花巷仅隔一条马路的竹安巷租下一个宽敞、幽静的四合院,以作研究室与图书馆。留在重庆的书籍于是陆续从邮路寄往昆明。张政烺与潘实君在重庆用牛皮纸把13万册书包成邮包送到邮局投递。由于邮寄时间漫长,后来张政烺到昆明得病虐痊愈后,他又负责从邮局收邮包(潘实君因另有任务留在重庆),成为投邮、收邮的同一人[12]。
1938年10月,邮包未收全,图书馆尚未开馆,遇敌机轰炸昆明,不得已史语所及其图书馆又转搬北郊龙泉镇棕皮营宝台山。图书馆的中文书库及阅览室安排在山上高大宽敞的弥陀殿里,文书兼管理员那廉君在此负责及办公;善本书库安排在弥陀殿南的观音殿里,张政烺住此负责及办公;西文书库及阅览室放在响应寺的观音殿里,傅乐焕在此负责及办公。宝台山相对安全安静,从1938年秋到1940年秋,史语所人员的生活、研究得到了难得的两年稳定时间[12]。
1940年秋,滇缅公路中断,云南告急,史语所不得不再次搬迁到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史语所的石璋如先生回忆当时图书馆搬迁的情景言:
同仁们不但辛苦地忙着装箱,还要分批押运,为着配合运输公司的方便,每次3车,最多5车(很少),每车有一位押运员。由龙泉镇到板栗坳这段路程分为四段,虽然各段的路程长短不同,但每段均有人照顾转运。由龙泉镇到四川泸州,路程最长,为陆运,用汽车。因李庄没有大码头,须先到宜宾再转返李庄。由泸州至宜宾路程次长,为长途水运,用大汽船。由宜宾返运至李庄路程较短,为短途水运,用小木船。由李庄至板栗坳路程最短,为山路,用人抬,要上一百多个石头台阶。陆路方面,在叙永之南,一辆汽车坠入山谷中,箱子滚脱,幸未至谷底的河水中,经派车营救,幸箱子装钉得牢固,没有伤害。水运方面,在宜宾一批书籍,由大船转至小船的时候,小船歪斜,书箱浸水,经检查晾晒,亦无大的损失。在押运方面,车队行至毕节,押运员那廉君先生忽然上吐下泻,连续不止,当地又找不到医生,岌岌可危!在万般无奈之下当着大众讯问病者,“在昆明曾购有前线救急灵药,阿斯匹林,您是否敢用?”病者宣布“敢用”。“得救,谢谢诸位;不得救,决不认为药毒所害。”幸而试之,泻止,大家才喘过气来。以上三例,至今思之余悸犹存[12]。
史语所迁至李庄板栗坳,租用了南溪首富张家的一片住宅。居住条件比龙泉镇宝台山好得多。图书馆的中文书库及阅览室安排在张宅田边的前庭,仍由那廉君负责;西文书库及阅览室设在后庭,由管理员王育伊负责;别存书库(善本书库)及阅览室设在最南的新房子,因院中有两颗高大的茶花树,该处又叫茶花院,由游寿(字介眉,在史语所时期名游戒微)小姐负责。张政烺此时已从事研究工作兼做图书馆采访,他的宿舍与研究室就在茶花院内。到了1942年10月,史语所图书馆的藏书已经发展为15万册(中文13万册,西文2万册)[13]。
从1941年至1946年,史语所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在李庄五年有余,从容苦居,不废研求,直到抗战结束。那时的李庄聚集了诸多文化教育机构,中研院史语所之外,还有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是抗战时期中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当时的史语所图书馆是西南中国最好的一座学术图书馆,常有其他学术、文化单位的人到这里查阅书籍[14]。史语所图书馆也因此声名远播。
5 版本目录学成就
张政烺一生追求学问,遍涉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俗、书法等领域,但是著述不多,至今可见文章仅有百篇左右。何兹全教授在《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座谈会上尝言:“苑峰一肚子学问,早在三、四十年前,我就劝他写出来。以至后来他都怕见我,一见我,我还未说话,他就先说:‘我写,我写。’可是终究没来得及写,就生病住院了。今天《张政烺文史论集》中的文章,也不知只能占他学问的几分之几。”[15]
在从事图书馆工作中,张政烺先生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虽然文章不多,但篇篇为杰作。今仅就其版本目录学论文以及平生所持有关观点撮述一二。
1943年张政烺写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主要考证《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不是南宋岳飞之孙岳珂所撰写、刻印。根据主要有:其一,《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依据廖莹中世綵堂所刻《九经》中《九经总例》翻刻、增补而成,廖莹中刻印《九经》约在南宋咸淳(1265-1274)年中,岳珂则生于淳熙十年(1183),嘉熙四年(1240)已58岁,离卒年不远,不可能见到廖氏世綵堂所刻《九经总例》。其二,明万历内阁书目称《九经三传沿革例》为“宋相台岳珂家塾刊本”以来,后人皆有“相台岳珂”之称,“相台”(相州有铜雀台,故曰相台)仅是岳飞家族的郡望,非岳珂专属,其他岳氏宗族也可用此郡望。其三,《九经三传沿革例》的真实刊刻者为元大德末年宜兴荆溪的岳浚(字仲远)。岳浚非岳飞后裔,曾因助修岳飞墓而与岳飞家族通谱,故也以“相台”为郡望。岳浚刻九经不避宋讳,其刊梓事元人诗文多有提及,如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送岳德裕如大都》诗中,有云岳浚“君家万卷刻书籍”句,郑元祐《侨吴集》言岳浚“延致名德巨儒雠校群经,锓诸梓,……海内号为‘岳氏九经’。”其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九经三传沿革例》为岳珂翻刻廖刚本,这是馆臣故意做假证。馆臣知道廖莹中世綵堂本是岳氏翻刻的底本,但因碍于乾隆上谕里曾称相台书塾为岳珂的颜面,只得再往前追溯至早于廖莹中的先人廖刚之处,以圆其说。张政烺言:“此种官僚习气在《四库总目》中往往见之。”“自来帝王吐词为宪,苟与真理相违,亦鲜有不失败者矣。”[16]张政烺对“官学”的痛贬,可谓淋漓尽致。
张政烺写完此文,当时并没有刊布。过了四十八年,他才将《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发表于《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一集中。但他没有将辛苦读书得到的研究成果密不示人,相反,其观点很早就交流于友人之间。1960年赵万里编《中国版刻图录》时,就采用了张政烺的观点,云“张说甚确。”[17]
张政烺先生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叫《王逸集牙签考证》(1945年)。该文对黄浚《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第四十六页著录的“汉王公逸象牙书签”图录进行了详细考证。该象牙签长3.5厘米,宽2厘米,上有孔,正面文字为:“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反面文字为:“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子延寿有俊才/作灵光殿赋”。张政烺在考证中广征博引,他认为:从其字迹古朴并体式在隶楷之间的特征看,当属魏晋或北朝时书秩上使用的牙签;范晔《后汉书·王逸传》的文字与象牙书签上文字略同,但言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其中《汉诗》当为《汉书》,牙签所载为正确,能纠正范晔之误,可谓一字千金;所谓《汉书》,即《东观汉记》,当时史籍常有同书异称,由此证明王逸参加了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百余篇的编纂;悬挂该牙签的书秩是专门包裹东汉王逸、王延寿父子文集的,换言之,王逸父子文集装于同秩;《后汉书》与牙签上关于王逸父子的文字属同源,都来源于《王逸集》、《王延寿集》之书录中;《史记》、《汉书》、《三国志》皆无“文苑传”,范晔创意为之,所有文苑传文字多载著作及篇数,体式整齐划一,盖皆选录于当时《中经簿》或《文章叙录》等目录中之书录,而非范晔独创[18]。
张政烺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并不拘泥一事一隅,其视野十分开阔。如他谈到版本目录学研究历史时说:“明清以来,除北京外,善本图书大多集中在东南江浙一带,虽然藏家有兴衰,书籍有转移,然大体不出东南一隅,故其地学者均真见有故籍,得详其行款格式、楮墨题识,著书则多为藏家簿录。叶德辉生于湖南,湘中藏书远逊江浙。虽然湘军将帅或有弆藏,然亦为同治军兴时得自江浙者,叶氏治版本,几于无米之炊,故其精力转致于辑录前人著作中论及版本者,著成《书林清话》一书,类似版本学教科书,其影响翻出东南簿录之上。”[19]
抗战结束,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他一概不留用伪北大教员,故急缺师资。1946年2月,张政烺被傅斯年调离史语所到北大任历史系教授。1954年,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离开北大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张政烺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曾兼任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他给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过版本目录学课程。第一堂课讲的内容是《甲骨文不是书》。张政烺认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将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书,这个观点以及后人因讹传讹是错误的。其一,殷商甲骨刻辞、周代金文中已经有表征竹简的“册”字;其二,《尚书·周书·多士》中记载了“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其三,考古出土多有战国、秦汉竹简书籍[20]。后来考古学者李学勤也认为,最早的书籍是简册,不是刻辞甲骨与青铜器,在纸质书籍以前,殷商时期有了简册,继简册而起的还有帛书[21]。张政烺的学生李零也认为最早的书籍为简册[22]。考古学界的这些观点,应该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注意。图书馆学界通常认为最早的书籍是刻辞甲骨,显然图书馆学界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对于古籍的认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张政烺都很有深度。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曾对年轻的研究人员张泽咸说,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今传本有遗漏,其内容可在《史记汇注考证》中找到;又说康熙刻本《太平御览》丢失的宋刻本《太平御览》有关条文,光绪刻本又给补上了[23]。所以,季羡林先生说过:“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对张先生也很佩服,赵万里对书的装帧、用纸等表面的东西很熟悉,但不知内容。而张先生对版本表、里皆知。”[15]
此外,对于古籍的今译,他也持反对意见。张政烺认为,以今注来说,能达到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水平的今注作品十分稀少,说明古籍今注难度极大,不仅要有古文献的功底,还要对现代出土资料十分熟悉,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学者实在不多。再说今译,古今文法不同,能译出字义而难译出意境;古籍中涉及典章制度、名物服器的地方更是难译成白话的,通白如《资治通鉴》尚有读不懂的地方,古籍如何能够今译?缘此,他再三强调:今注可以提倡,今译要慎重从事。尤其是那些有工期的古籍今注今译出版项目,更是要不得[24]。这一见解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知道后,立刻要求行将印行的1995年第4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撤下要发表的自己文章,改登张政烺的文章《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3],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6 文史学界的活字典
1960年,张政烺被迫调离北大。事后北大历史系教授、蒙古史专家邵循正曾对友人讲:“我们北大把张苑峰放走是个失策,那是个‘活字典’。”[25]
文革期间,张政烺也挨批被下放“五七”干校养猪、烧茶炉。到了七十年代,因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的需要回到北京。当时其他各史都由研究有素的专门史学家来分领,唯独张政烺被安排点校《金史》,缘由是原来点校《金史》的傅乐焕辞世后找不到合适人选,而他博闻强记,对古籍十分熟悉。当时一起共事的刘乃和讲,谁有了问题,都找张政烺,他若马上解决不了,过几天也能给你解决[25]。据中华书局的编辑黄克回忆,那时中华书局的黄克参与标点清人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的诗词部分,碰到的最多问题是王琦的注文多不标出出处,使他无从核查文献,如多次出现“郭璞诗……”。黄克找张政烺求教,张政烺告诉他:“郭璞诗”指的是郭璞《游仙诗》,郭璞无别集传世,《游仙诗》都收在《文选》里。黄克一查,果然如是[26]。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要有大相扑在北京表演。政府有关部门想了解中国古代有无相扑记载,于是派人找张政烺请教,张政烺不仅举出史书上最早的记载,而且说明清小说里不乏此例[23]。文革结束公审“四人帮”,起诉书中要使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语,中共高层领导为慎重起见,想知道这句话的来历以及是否有此规定。任务下达给教育部,教育部派北大历史系田珏办理,田珏没有办法只得找张政烺,最后还是张政烺给予了解决,他从《词源》找出“八议”,解释了古代王子犯法是从不与庶民同罪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语出清代李渔《比目鱼传奇》,是皂吏对权势者说的一句话,原为“岂不闻皇亲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是旧时代民间的一种愿望[25]。
张政烺进入晚年,求教者纷至沓来。有一次,他笑着对自己的研究生孙言诚说:“这些年,从头(发式)到脚(缠足),我也不知解答了多少问题。”[11]孙言诚在怀念文章《我的导师张政烺》中写到:
有些人到张先生家里请教,其实是为了找材料。他们知道先生藏书很多,且很熟悉,找起材料比自己大海捞针省力得多。遇到这种情况,张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从书房进进出出,从书架上爬上爬下。有的人不光找材料,还要讨观点,说白了就是利用先生的学识来充实自己的论作。先生心知肚明,但绝不设防,坦然讲出自己的研究心得,悉心相助。有时候,一次“请教”能长达五六个钟头。好心人常劝傅先生(张先生的夫人)挡挡驾,可是张先生来者不拒,热情有加,傅先生怎么挡得住呢?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李学勤先生曾愤愤地对我说:“有些人太不像话,自己不查书,鸡毛蒜皮的问题也问张先生,耽误先生的宝贵时间。”是的,张先生这一生,帮别人做学问的时间,比自己做学问的时间还要长。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固然可贵,而他汲引后学、无私襄助他人的精神,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11]。
来访者太多,影响了张政烺的读书与生活,而对于来访来求教者,张政烺是怎样的感觉呢?其夫人傅学苓(曾在科学出版社工作)回忆言:
一次尹达找我,让我协助历史所在家里阻挡求教者,以免张先生被过多打扰。可是我阻挡不了,我上班后,有人登门,他照样接见。我想了几天后,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反问我说,中国现在做学问的人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说,太少,尤其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太少。他听了哈哈大笑,举前几天来求教的一个年轻人为例。他也是在报纸上看到张先生的文章,慕名登门求教的。张先生说,人家几千里跑来,我要是不见,不帮助,他回去可能永远不搞学问,去卖油饼了。由这以后,我就不阻拦张先生了[15]。
7 结语
张政烺先生被誉为“活字典”,经常接受来访者求教,其友人、同事、学生每言及此,皆归结为先生记忆非凡、学识渊博、学品高尚。这确为中的之论。然而,还应看到,张政烺先生的这种特点,其实是与其年轻时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的经历有关。
图书馆是百科知识的总汇,珠隐玉藏,非沉潜不能有所得,非博览不能索其要。这样的环境必然造就张政烺先生的博学特点。在史语所时期,他自署书斋为“视月书舍”。“视月”一词有典。《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晋人褚裒、孙盛二人对谈,褚言:“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之道林闻之说:“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27]后李延寿编《北史》,也讲到经学研究上“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28]张政烺用“视月”为书斋名,有自谦学问博而不专之意[29]。坐拥书城,文熏典陶,自然会让人养成博瞻的视野,有时,甚至会导致写作文风的变化。读张政烺先生的文章,其写作风格可用钟嵘《诗品》评价任昉诗作的话来描述,那就是“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30]。
图书馆是个学术性的服务机构,经常传播知识与他人,习久会成自然。张政烺先生不拒来者,有求必应,这是操守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留下的后遗症。而且只有虔诚做图书馆工作的人,才能以“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为乐,才能将这种精神移植到内心而持续终身。张政烺先生被外人况喻为有求必应的“土地公公”,他对慕名而来者从不发一句怨声,甚至不同意妻子、同事“挡驾”,这就是图书馆员精神的一种延续。他曾郑重地说过“我一个人再有学问,写出来的文章再多,也不如让更多的人走上治学之路好,会做学问的人多了,中国的学术发展就能正常繁荣起来,这不好吗?”[23]这番话是他对图书馆员“为他人做嫁衣”、常做“为人之学”之崇高境界的最好注释。
张政烺只有短短五六年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经历,但我们说张政烺是“懂得书”的图书馆员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图书馆界,尤其是在研究型图书馆领域,他迄今是无人能比及的一块丰碑。在张政烺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参考资料
1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2 魏收.魏书·卷一百·乌洛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册]2224
3 孙希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曲礼下第二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154
4 陈智超.张政烺先生访问记.见: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
5 谢桂华.张政烺先生传略.见:吴荣曾.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06-410
6 张政烺.“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46-57
7 张政烺.《封神演义》的作者.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61-65
8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8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71年再版]1本(1分):3-10
10 张政烺.我在史语所的十年.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848-850
11 孙言诚.我的导师张政烺.文史哲,2007(6):27-34
12 石璋如.与张政烺先生谈对日抗战期间史语所的图书馆.见: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19
13 国立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研究所概况报告表(1942-1943).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41
14 张弘.岱峻:挖掘李庄精神.博览群书,2010(2):24-31
15 刘源.何兹全、任继愈先生谈张政烺.往复·国史探微,(2004-04-23)[2011-07-13].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3/410.html
16 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848-850
17 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目录:春秋经传集解]57
18 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1971年再版]14本:243-248
19 刘宗汉.从《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看张政烺先生的版本学成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5):15-20
20 张政烺.中国古代的书籍.见: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521-526
21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2003:61-69
22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4
23 张永山.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我认识的张政烺先生.见:张永山.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147-157
24 张政烺.关于古籍今注今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4):83-85
25 张守常.记业师张苑峰先生.见: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7-11
26 黄克.一瞥劫后灿烂:记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几位老先生.文史知识,2009(8):82-88
27 刘义庆;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16
28 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9册]2709
29 刘宗汉,周双林.张政烺先生在解破数字卦中的贡献及给我们的启示.见:张永山.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101-107
30 钟嵘;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