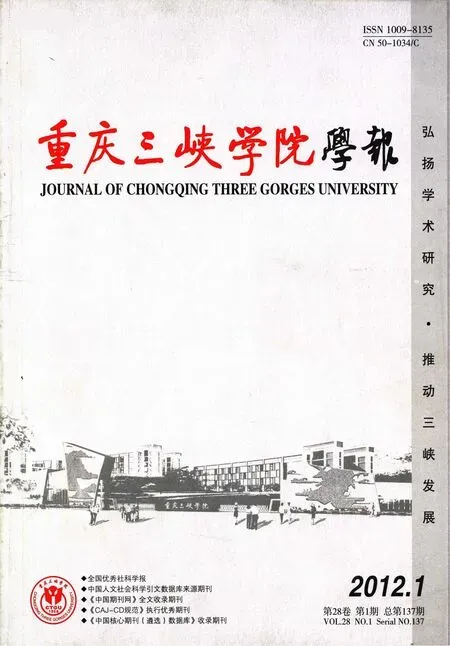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内证寻绎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内证寻绎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白居易《长恨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之一,对其主题的解读历来多有分歧。重读这篇经典及其与之有关的《与元九书》、《霓裳羽衣歌》、《江南逢天宝乐叟》等作品,从其中的“长恨情结”、“世俗情结”、“霓裳情结”和“盛世情结”入手,对于明确把握《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寻绎内证的意义。
长恨;世俗;霓裳;盛世
白居易《长恨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之一,对其主题的解读历来多有分歧。重读这篇经典及其与之有关《与元九书》、《霓裳羽衣歌》、《江南逢天宝乐叟》等作品,从其中的“长恨情结”、“世俗情结”、“霓裳情结”和“盛世情结”入手,对于明确把握《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寻绎内证的意义。故笔者谓之“也说”。
一、长恨情结
以往那种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只限于“讽刺”、“批判”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仅归于“后妃干政”而致祸邦家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白居易的本意不相符合的。
一方面,白居易作《长恨歌》,诗中直接写“恨”,全在末两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诗经·王风·葛藟》:“绵绵葛藟”。朱熹《诗集传》注:“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白居易写的虽是大唐皇帝,但卒章显其“叹”,不无同情与感伤之情,他将此诗编入“感伤”类即可为证。诗人用笔,以道士觅妃篇幅最大,思妃次之,得宠再次,贵妃之死笔墨最少。所以我认为这“恨”主要是指玄宗之“恨”(当然也有贵妃之“恨”)。“恨”之“绵绵”,亦即“思情绵绵”,是充满着“痛苦”和“惋惜”的。
另一方面,“诗言志”,且“缘情”。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风情”者“男女相爱之情怀。”(《辞海》)“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写唐玄宗的钟情;“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是写唐玄宗的倾情;“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是写唐玄宗的别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这是写唐玄宗的思情;“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这是写唐玄宗的痛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这是写唐玄宗的苦情等;“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含情凝睇谢君王”、“唯将旧物表深情”——这些又都是写杨贵妃的多情和恋情等。因此“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所写的就是李杨的风情、韵事和爱情故事,并通过唐玄宗对自己的追悔和惋惜,把民间传说的故事形象化和典型化为艺术的“长恨”。《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806),其时白居易三十四岁,正值青年时期,又加上“深于诗,多于情”(陈鸿《长恨歌传》),诗中表达了对于悲剧人物李杨的同情,其伤感的成分显而易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一个名作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故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作了《长恨歌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所以,我认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痛心和惋惜,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绵绵”“长恨情结”。
二、世俗情结
白居易写于元和十年(816)的《与元九书》是白居易人生哲学和诗学理论的完整表达,他站在“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立场,从肯定儒家“美刺”批评标准出发,强调《诗经》六义对“讽谕诗”创作的指导作用,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原则,与《新乐府序》所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相呼应,不啻吹响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强劲号角。但是,白居易在表达他的诗学理论的时候,明显地陷入了对自己作品评骘与实际社会效果相矛盾的二难中,即主观评判与作品反响发生严重分离。白居易详实地列举了《长恨歌》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说明“今时俗所重在此”,他自己却觉得那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坦言自己追求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诗学之道,宣布“平生所尚者”就是“讽谕诗”和“闲适诗”,郑重表示:如果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诗文,就把那些“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作品略去算了。白居易似乎看到了“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主观评判和作品反响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再次说明“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并对“宜人之不爱”的“讽谕诗”和“闲适诗”作了解释:前者意思激切,言语质直,后者意思简淡,文辞迂缓;质直而且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但是,他又以韦苏州为例,似乎把人们对“讽谕诗”和“闲适诗”“未甚爱重”的改变,寄希望于“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
可见《长恨歌》问世以来产生的为“时俗所重”“人所爱者”的大众回应,白居易创作时也许始料未及。他向元稹表白,自己所作的“感伤”类诗歌,是“有事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长恨歌》自在其中。很显然,白居易说的“时俗所重”、“人所爱者”无疑就是“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长恨歌》了。白居易“释恨”,“时俗”和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倡妓爱“恨”重“情”,“恨”便带着广延的社会性被作者典型化为艺术品,充分说明了作品本身对创作理论的突破。难怪《唐宋诗醇》的作者评曰:“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
此“恨”谓何?瞿佑《归田诗话》似有所悟:“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元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20字中,内涵丰盈,以情致见长,特别是“闲坐说玄宗”一句,容纳了无尽的历史沧桑、时代变迁和人世感伤,其中多有贵妃入宫、安史之乱、马嵬兵变、玄宗幸蜀和孤处“西宫南内”等等不堪回首的悲戚往事。所以,着一“说”字,是不无忆旧、痛惜和伤感、缺憾之“恨”的。皇家宫廷尚且如此,民间的传闻和演绎可想而知。这是《长恨歌》得以广为流传而达到“时俗所重”“人之所爱”以至于“童子解吟长恨曲”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机制。黑格尔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从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美学·序言》)《长恨歌》正当作如斯观。
元、白生活的时代,世俗观念和文学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盛唐”不复再现,雄宏气象已成昔日,盛世豪情一去不返,诗歌中的浪漫激情、狂狷进取、尚侠任武被哀怨冷寂、空漠感伤、男女风情所代替。“时俗所重”“人之所爱”的社会需求和社会认可则是这种变化的根本推动力。罗根泽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学的内在本质要变,但向哪里变,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决定于内在的文学本质,而决定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文学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需要随时不同,文学的供给自然也随时变易。”[1](168)中唐时期,文学的变易,以商业发展、都市繁荣和市民崛起为背景,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通俗尚实的大步子。其领军人物非元、白莫属。赵翼《欧北诗话》卷四有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韩、孟雄奇怪警,元、白通俗尚实,两大诗派,都旨在创新,完成了不同诗风的铸造。
通俗尚实之风,远绍国风、汉魏乐府民歌,近接杜甫自拟新题乐府,是元、白对诗圣“直道当时语”的强烈呼应。因为“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2](88)影响到元和以后诗章便“学浅切于白居易。”(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例如,元稹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就是“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2](95)的,这种史实传闻糅合,想象虚构结体,人物事件“拉郎配”的描写,正是“时俗所重”“人之所爱”连动趋向的力证。而白居易作于元和四年改定于元和七年的《新乐府》五十首多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当朝弊政、鞭挞权贵丑恶为能事,但是“愍怨旷”的《上阳白发人》所描写的白头宫女因被嫉妒“潜配上阳宫”的寂寞生活颇与《长恨歌》玄宗思念贵妃相似。随着传奇小说的长足发展,以故事性、抒情性而泄导人情的长篇叙事诗堂堂皇皇的登上诗坛。对此,白居易在《编集拙诗一十五卷引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诗中总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明确宣布《长恨歌》是描写李杨“风情”故事的作品,市民意识的潜移默化显而易见。沉湎俗世生活、追求享乐、追求情爱、率真地面对现实人生的苦乐悲欢的市民意识,“使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色彩,从而带动了唐代文学精神的发展变化。”[3](17)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长恨歌》所蕴含的世俗情感,怎一个“恨”字了得!
世俗情感是普通人的情感,享乐和情爱最为浓厚。中唐以后,关于李、杨爱情的世俗化话题,在诗人的创作中不绝如缕,人们心目里的李隆基已不是荒淫昏聩的误国之君,而是值得同情和惋惜的情种;杨贵妃也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祸水女人,而是令人感伤的不幸弱者。他们的风情韵事具有“普通人”的意义,不免带有几多缺憾和美中不足而成为飘逝的绝唱。许多题有“马嵬”二字的诗歌之所以深深地打上了忆旧、痛惜和伤感、缺憾的烙印,无不受到《长恨歌》的文学精神濡染。像白居易一样,诗人们并不在意李、杨爱情的具体背景、详细情节和全部经过,而是着力表现他们的无穷无尽的遗恨、悔恨、憾恨和作者自己的追思、同情、伤感之情,即程千帆先生曾经说过的:《长恨歌》“叙事状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写中寓有隽永的情味。”[4](188)就是嗣后出现的“作意好奇”、“各征其异说”、“传要妙之情”、“究在文采与意想”的唐传奇、小说,《长恨歌》的影响恐怕也不可低估。
三、霓裳情结
倘若再行考查,就会发现《长恨歌》和《霓裳羽衣歌》以及其它有关“霓裳”的描写,在白居易的笔下着实积聚成一种“霓裳情结”。
《霓裳羽衣歌》是白居易在宝历元年(825)由太子左庶子改任苏州刺史后写于秋季的作品。这篇作品,诗人通过回忆详实地记录了唐代宫廷大型乐舞《霓裳羽衣》演出的盛况和过程,对其构成的“散序、中序和曲破”三大部分进行了细致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唐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耳闻目睹”者,“白居易为挽救它(《霓裳羽衣》)濒临灭绝的命运所付出的不懈努力。”[5](27)他对《霓裳羽衣》的一往深情非同一般。
诗说白居易到苏州以后,秋来无事,寂寞闲闷,忽然想起霓裳羽衣舞来。但又碍于无处打听,只好写信询问元稹。元稹于长庆三年(823)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使,其部属有许多能歌善舞的乐人,想来会得到一些消息。然而元稹的回答是,他所在的“七县十万户”,竟没有一人知晓霓裳羽衣舞了。所幸元稹随信寄来长诗霓裳羽衣谱,倒让白居易喜出望外。白居易根据谱中“霓裳实录”和“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时亲眼所见的霓裳羽衣舞的印象,依照原来的结构和场记,决定重新排演。“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字里行间充满着白居易对霓裳羽衣舞的特殊感情,表示要用诗歌的形式使它重现光彩。
“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对霓裳羽衣舞的这种特殊感情,在其它诗歌中多有表达,如《江南逢天宝乐叟》、《琵琶行》、《偶题五绝句》、《嵩阳观夜奏霓裳》、《早发赴洞庭舟中》、《醉后题李马二妓》、《重题别东楼》、《湖上招客送春泛舟》、《得梦得诗》。联系中唐社会和士人中普遍弥漫的世俗情感和感伤情调,白居易厚爱霓裳羽衣舞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融歌、乐、舞于一体的《霓裳羽衣》,原是印度的一支舞曲,开元年间始得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引造,遂逐渐传入中原,后由唐玄宗在吸收《婆罗门曲》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工、整理和润色,创制而成一种唐代大型歌舞,或称《霓裳羽衣歌》,或称《霓裳羽衣曲》,或称《霓裳羽衣舞》,或称《霓裳羽衣》,或简称《霓裳》;乐部属法曲,调属黄钟商;全曲十二遍,前六遍无拍,到第七遍时有拍而舞;舞者“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上衣白,下裳红,整个的仙人装饰;始在京城皇宫演出,其后传布四方,各地节镇亦可排演。它和唐玄宗其它创制的40多部乐曲一样,象征着“盛唐气象”的一个方面。但是,“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给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4](178)一方面,它为“唐代的历史划了一条界线”,也为“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6](77)尤其是“安史叛乱带来的社会残破和精神打击,使乱后的许多诗人心上蒙上了一层阴翳。”[4](181)“中晚唐文学大都不再像初盛唐时期一样写自己锐意进取的抱负,而是写自己及周围的世俗生活,写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表现一个普通人所体验和追求的人情味;就文学风貌而言,也不再像初盛唐文学那样追求气凌霄汉,而是表现出艳、狭、俗的世俗化色彩。”[3](19)所以,“闲坐说玄宗”,不仅是当时白头宫女聊天的话题,而且是民间传播的话题,更是诗人关注和回味的话题,这中间恐怕比较多的当然要数李杨的爱情故事和传说了。“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杨贵妃的生死转折点,也意味着李杨爱情的悲惨结束。对此,白居易没有像他的讽谕诗那样按照“纽王教”、“系国风”、“存炯戒”、“通讽谕”、“劝善惩恶”、“补察得失”的儒家重功利的诗教理论处理题材,而是从世俗观念出发,还原了李杨故事本身内涵的普通人情感,在“玄宗思妃”和“道士觅妃”的幻化和仙化描写中加重“感伤”分量。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又写了《霓裳羽衣歌》。这两首长诗都有一条主脉贯穿,那就是“霓裳羽衣”。《长恨歌》中的绵绵之“恨”,全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引起,而唐玄宗在海上仙山首先看到的就是“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唐玄宗对渔阳鼙鼓的情有独钟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是统一的,像“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样,那“仙乐”“缓歌”“谩舞”也着实让他“尽日”“看不足”。杨贵妃“宛转”“马前死”后,唐玄宗的“朝朝暮暮情”无疑便是对“仙乐”“缓歌”“谩舞”和贵妃的因乐舞而思人之情。在这里,“渔阳鼙鼓”的历史转折既毁灭了李杨的爱情,又毁灭了“霓裳羽衣”,双重毁灭的精神打击使得唐玄宗“孤灯挑尽未成眠”。一代天子尚且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破坏可想而知。这种惨重的精神打击从天子到臣民都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是国“恨”和情“恨”永无绝期的绵绵之“恨”。白居易自不例外,他以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回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历史大悲剧,因为“普通”,所以更具有普遍性、社会性和感伤性、典型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于长庆三年(823)的《江南逢天宝乐叟》,白居易把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回味再通过天宝乐叟之口加以宣达。那位天宝乐叟对玄宗旧朝、旧事、旧乐的怀念,尤其对“冬雪飘飖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情景的怀念是很有代表性的。王权的丧失和普通人自身的遭遇一旦结合起来,就凝重为刻骨铭心的历史沧桑和巢倾卵破的社会悲剧。“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阖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天宝乐叟眼中旧宫、旧殿、旧苑的荒凉和寂寞不也正是《长恨歌》中“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的真实写照吗?《霓裳羽衣歌》和《江南逢天宝乐叟》的作时距安史之乱分别为70年和68年,就是作于元和元年的《长恨歌》也只有51年,大乱和破坏在人们心中毕竟记忆犹新,如此写照在白居易的作品中便积聚成一种“霓裳情结”,而当这情结借助于李杨的风情、韵事和爱情故事形象化为艺术的“长恨”的时候,男女风情的寄托和感伤世事的同情以及由寄托和同情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就社会心理化和情感世俗化了。这是《长恨歌》赢得历代广大读者的根本原因。
四、盛世情结
唐代开元天宝时代,以中国古代历史特有的盛世辉煌深深地嵌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中唐社会尤其如此。封建王朝的盛世辉煌都极为短暂,如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唐代玄宗时期的“开天盛世”、宋代仁宗英宗时期的“太平盛世”分别仅现于 40年左右,而所谓时间最长的清代“乾隆盛世”也只不过维持了100多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创立封建帝制到辛亥革命结束,在封建帝制漫长的2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盛世简直是“弹指一挥间”了。正因为如此,对盛世的怀念和追忆自然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家、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心理取向、价值判断、题材选择和生活话语。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是这种盛世情结颇具代表性的艺术表达。
李杨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开元天宝盛世之际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代社会蓬勃向上、儒教松弛、思想自由、个性张扬的典型象征。盛世的政治进步、政策宽松、社会开放、经济繁荣、观念超前、意识解放、个性不拘等等,都在开元天宝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示,其鼓荡的青春和活力为后世惊叹不已,就连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尔斯也大声疾呼那是居于世界“伟大的领先”地位的“中国的极盛时代”,它“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扬”并在“文化上和世界上支配世界”,[7](629)而中外有些专家学者干脆称之为最具有“世界主义”[8](108)和“人文主义”[9]色彩的朝代,或者誉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10]为文学史家所称道的,一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二是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李杜诗歌描述的气象无疑只有他们已经经历的盛世才具有。这种气象在群臣早朝的升平隆重中尤显得不同凡响,从贾至的《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便可见出消息。此诗一出,和者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如王维、岑参、杜甫的同题《和贾舍人早朝》诗,就思想性而言,价值并不高;就艺术性而言,虽然标志着近体七律的成熟和精严,论者却对它们的评价也远远低于诗人们的其它作品;然而,就史料价值而言,其认识意义正在于那胀溢出的一番盛世气象,可与史书记载相参比。作者以和诗的形式,围绕“早朝”,从多个侧面映现了大唐帝国的兴旺、威势、庄严、臃拥和由此而流露的典重、大气、富丽、堂皇,自豪之情充满言表。
盛世气象是社会前进和上升过程中的总体风度和风格,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固然重要,而人的青春再现和少年意气则是最根本的原始动力。诗酒风流、潇洒浪漫、享受人生恰好淋漓尽致地表现着开元天宝人的青春和少年,即使儒家礼教所禁锢的“饮食男女”他们也不那么过分认真:皇帝纳妃可以不顾伦理,朝臣并不妄加议论;文人携妓游乐,社会多不以为非;妇女袒胸露肩,众人从不觉得怪异;男女相悦,直率大胆,毫不掩饰。这一切宽容和大度大概只有开元天宝的盛世才能做到。李杨的结合,既有他们性格和好尚的相投,又有盛世风情使然。“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白居易看来,“安史之乱”毁灭了开元天宝盛世,破坏了李杨爱情,当然也制造了李杨爱情悲剧。它距白氏生活的中唐并不遥远,昔日的辉煌记忆犹新,李唐王朝的江河日下让诗人们把心理落差直接转化为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回首一望。唐德宗时戎昱的《八月十五》诗说:“忆昔千秋节,欢娱万国同。今来六亲远,此日一悲风。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盛世和衰世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两极,盛世一极的光明和灿烂,犹如丽日经天,“风景这边独好”;衰世一极的战乱和动荡,就像危巢倾覆,鸡犬不得安宁。“千秋节”的盛大和热烈,与“梨园几人在”的悲怆和冷落,颇同天堂跌落地狱。盛衰强烈对比的触发点往往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回忆和追念有感而来,戎昱的诗当可作如斯观。《长恨歌》的盛世情结全在于那个《霓裳羽衣曲》的触发。盛世情结一旦还原为霓裳情结,李杨的爱情故事和悲剧结局就艺术地浓缩在《长恨歌》的千古绝唱中。
《长恨歌》由“汉皇重色”起笔,中经御宇求妃—承欢侍宴—渔阳鼙鼓—蛾眉惨死—马嵬泣归,最后收结为道士觅妃,其落脚点不是别的,就是唐玄宗在海上仙山所首先看到的“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全诗在李杨情爱的交叉叙述中贯穿的感情主线就是“霓裳羽衣”。此曲此舞此歌,是盛世的产物,是以高雅的形式展示出来的盛世文化,从宫廷到社会,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它本身。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是糅合了倾国之色和霓裳之艺的,而色的气质和艺的高超又不能不说是开放宽松的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作用的结果。盛世的一去不复回不但使唐玄宗“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而且也使白居易生发出“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霓裳羽衣歌》)的惆怅和空寂。《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霓裳羽衣歌》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20年后的白居易念念不忘“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世崩溃的一幕,足见“长恨”的情结之深。[11]诚如程千帆先生说过的:“安史叛乱带来的社会残破和精神打击,使乱后的许多诗人心上蒙上了一层阴翳”。[4](181)白居易的心理阴翳凝聚为盛世情结就必然地发作“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挽歌了。《长恨歌》的著作权无疑属于白居易,可是,它的创作和流传以及由创作和流传弥漫着的对开元天宝盛世的怀恋和追念成了一种具有广延性的社会认同,士人、诗人和世人、百姓概莫能外。《长恨歌》的盛世情结所产生的永恒内在艺术生命就在这里。
加之,开元天宝盛世,儒释道虽然并行,朝廷共同提倡,但是唐玄宗尤其爱好道教,治国修身多以道家思想为宗,对道教的迷信和对长生的追求无以复加。是的,唐玄宗无为无欲的道家治国修身,收到了“开元之治”可与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媲美的效果。盛世崇道是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唐高宗莫不如此,汉唐两朝的繁荣和发展都伴随着尊奉道家鼻祖老子的热闹场面,而唐玄宗的师从当朝大道士司马承祯和将当朝有名道士罗公远、张果、叶法善、三藏等召进宫中拜师求道,其妹其女出宫入道,则使这种热闹场面登峰造极。《太平广记》根据《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逸史》等书的记载,传说罗公远用神仙法术把唐玄宗带到月宫,唐玄宗于飘飘然中还偷记了《霓裳羽衣曲》,从此改造、加工、整理和润色而成为流布朝野的大型歌舞。旧题柳宗元撰《龙城录》和宋初乐史根据旧闻撰《杨太真外传》均有详载。《太平广记》和《龙城录》、《杨太真外传》的可信度我们姑且不论,《霓裳羽衣曲》确实象征着开元天宝盛世的辉煌则不可否认,尽管它以音乐歌舞的形式出现。联系白居易对“道士觅妃”浓墨重彩的描写,《长恨歌》的盛世情结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唐玄宗迷信道教方术,追求长生不老,最终走上了怠于政事、权倾佞臣的歧途。宋代范祖禹《唐鉴》评论道:“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其实,政治和历史的评论视角向来与文学描写的角度大大不同。《长恨歌》的“绵绵无绝期”之“恨”,恰好淡化了李杨爱情故事的政治和历史的价值评判,它要着力通过悲剧的强烈震撼和情节的起落回荡,把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典型化世俗化平民化为对盛世的追忆、留恋和惋惜。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高明的独到审美之所在。
[1]陈平原.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的开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寅恪.元白诗笺稿·新乐府[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孙学堂.中国文学精神·唐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杜兴梅.试论白居易对《霓裳羽衣》的贡献[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6).
[6]王瑶.李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7]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张鸣.林庚先生谈文学史研究[J].文史知识,2000(2).
[11]刘利.一篇长恨有风情——兼论白居易的爱情观[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3).
On Elegance and Emotion Embodied in the Ballad of Long Hatred:an Explanation of the Main Theme of the Ballad of Long Hatred by Bai Ju-yi
KANG Huai-yua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Chongqing, 404100)
The Ballad of Long Hatredby Bai Ju-y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ancient poetries,and divergences exist in people’s comprehension of its main theme. It is found that our re-reading of the classic work and some other related works may be greatly significant in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main theme embodied in theBallad of Long Hatred.
Long Hatred; secular; great time
I206.2
A
1009-8135(2012)01-0060-06
2011-10-21
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理事,重庆三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