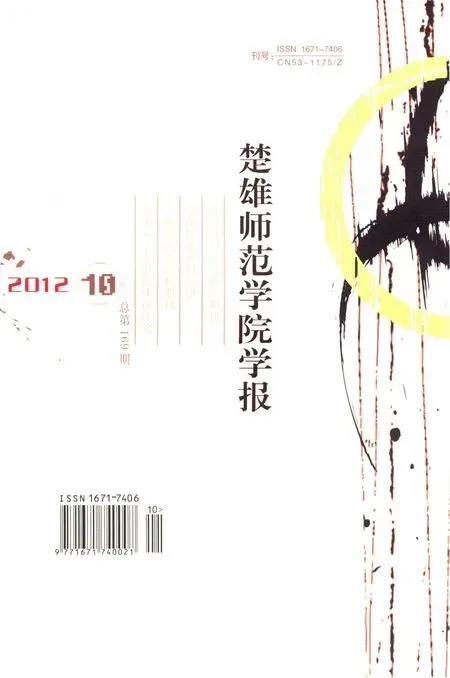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左汉林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南宋后期,首先登上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即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他们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开始转而学习晚唐诗,使唐体重新流行。再有就是姜夔、刘过、戴复古、刘克庄等江湖派诗人,①按在江湖派诗人中,戴复古受到杜甫的影响较大,“颇得杜诗沉郁顿挫的风神”,参见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215页。成分比较复杂。宋亡之际,又出现了文天祥、谢翱、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等一大批诗人,用诗歌歌咏和记录亡国的痛苦与悲哀。在这些诗人中,文天祥、汪元量等写诗有明显的以诗存史的意味,受到杜甫的影响比较明显。考察这个时期的诗歌可以发现,南宋后期诗歌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一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尽管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取得的成绩有限,但他们以晚唐姚合、贾岛为宗,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代表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也是宋代诗人对江西诗派创作方法不断反思的结果。
永嘉四灵指南宋后期的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他们关系密切,交往比较频繁,诗中颇有些同题之作。四灵诗风接近,从形式上看,他们都惯于使用五言律诗。从内容上看,则大多是写景咏物、流连光景之作。四灵的咏物诗,所咏为花草树木、山水禽鸟之类。他们很少用典,即使用典也不佳。如徐照在《石门瀑布》中说:“一派从天落,曾经李白看”,[1](P24)用李白诗歌的典故,就很不自然。从风格上看,他们的诗均浅显细碎,以晚唐姚合、贾岛为宗。他们的诗歌很少涉及社会现实,内容单调狭窄,风格单一。
四灵诗歌的最大缺点是不能使人感动,即使是哀挽之作,即使是悼念最好的朋友,也多落入俗套。《四库全书总目》说:“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2](P1389)“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画之词,盖一时风气所趋,四灵如出一手也。”[3](P1390)纪昀说:“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4](P1410)他们诗风清淡细碎,其诗既很少触及社会现实,又难以抒发自己的性情。此后的江湖诗派,其实也是如此。
永嘉四灵写诗据说是为了改江西诗派之病。北宋中期以来,宋代诗人最终选择杜甫为诗歌的典范。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极大影响了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以黄庭坚和陈师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通过对杜诗艺术技巧的学习,特别是通过对诗歌字句的反复锤炼,创作出平淡瘦劲、平和内敛的诗歌,而且确立了一种依靠才力做诗的方法。江西诗派讲究字句的锤炼,重视用典,其不足之处在于诗情寡淡,诗味贫乏。江西诗派创作的诗歌虽然模仿杜诗的法度,却与杜诗相去甚远,这是这个时期的诗歌学杜的深刻教训。永嘉四灵的成就远不及江西诗派,但他们从晚唐诗歌入手的学诗途径,代表了宋代诗人对江西诗派不良风气的反思,也代表了南宋后期诗歌向唐诗复归的倾向。
二
南宋后期永嘉四灵之后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从文天祥、汪元量等诗人的诗歌可以看出,他们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即自觉地用诗歌记录宋末天崩地解的大变动,记录大变动中的事件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以诗存史的写法同杜诗有相同之处,文天祥和汪元量也是这个阶段学杜的最有成就的诗人,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文天祥与汪元量的诗歌并不相同,文天祥对故国有着强烈深厚的情感,所以他的作品尽管比较直白,但感情真挚而充沛;汪元量先仕宋后仕元,他对宋亡的态度也似怜似讽,所以他记录历史的诗歌“冷静”得可怕。尽管如此,两人以诗存史的观念却是相同的,这是杜甫“诗史”精神所产生的影响。
文天祥是宋末抗元的英雄,他的诗歌以元军攻破临安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比较无聊,内容平庸琐屑,“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作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5](P279)
文天祥后期诗歌,往往直抒胸臆。作者自云:“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6](P313)他的诗歌以诗存史,记录了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以及诗人自己的心路历程,可称诗史。文天祥的诗歌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如文天祥有《纪事》绝句一组,据此诗诗序,诗人使北期间,北人渐不逊,文天祥慷慨云:“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6](P314)从这些诗歌之中,也可以看出诗人救国殉国的决心。《高沙道中》是叙述诗人从敌营逃出的长篇叙事诗,这是一个人的逃亡经过,是这个国家兴衰的一个侧面,是一个时代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大都,一路所见所感,寄之以诗。他经过保州,作《保州道中》,诗叙写路过保州所见风物,追述此地的历史人文,抒发自己被俘的感怀,颇有沉郁之气。
钱钟书说:“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诗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7](P3)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文天祥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平铺直叙的毛病,显得粗糙了一些,但算得上是真正的诗史。
汪元量的创作情况与文天祥不同。汪元量是南宋的宫廷乐师,宋亡后随三宫赴大都,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羁留北方期间,曾在元朝廷任翰林院供奉,也曾奉命代元君主祭祀名山大川。他后来以道士身份回到南方,流连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元延祐四年 (1317)前后卒。汪元量诗歌受到杜甫的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汪元量以诗记宋亡历史,其诗有诗史之称。他把自己的诗歌称为“野史”,他说“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8](P37)他的这类诗多为七言绝句,有所谓“幽忧沉痛”的风格。但细味其诗,过于流利畅达,押韵合辙,总体不脱其乐师本色。汪元量《醉歌》有诗史意味,此组诗歌写元军入城、宋室投降事,多正史所未载,刘辰翁称之为“江南野史”。汪元量有《越州歌》二十首,叙述元军入临安后情况,回忆南宋旧事。他还有《湖州歌》九十八首,写宋帝后从临安到大都的详细经过及期间发生事件的种种细节,都具诗史意味。《湖州歌》九十八首,是宋亡诗史,这些诗通俗晓畅,琴师的格调宛然。在这些诗歌中,诗人的态度似叹似讽,此点尤堪寻味。在《湖州歌》中,他还写到宋宗室在大都受到优待,所谓“三宫满饮天颜喜”,“须臾殿上都酣醉”,恐怕都有不少虚美和夸张的成分。
有人认为汪元量的诗歌具有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9]本文认为,汪元量对宋亡的态度是值得认真寻味的。钱钟书云:“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五周方《跋》:‘余读水云诗,至丙子以后,为之骨立。再嫁妇人望故夫之垄,神销意在,而不敢哭也’。”[10](P1079)他又引章学诚语云:“亡国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国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后则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民也。”[10](P1080)如此,汪元量恐怕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遗民。后人对汪元量不无讥讽。王国维就说:“(汪元量)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具在,不必讳也”,“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倡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者有别。”①王国维《湖山类稿水云集跋》,参见《汪元量集校注》引《诸家评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页。王国维所说不无道理。
其次,刻意模仿杜诗与化用杜诗。汪元量自谓少年即读杜诗,但当时不解杜诗佳处。及流离北方,在毡帐中读杜诗,始知杜诗句句可传,所谓“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11](P121)这说明他对杜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汪元量有《浮丘道人招魂歌》是学杜之作 (按浮丘道人即文天祥)。文天祥于至元十九年 (1282)十二月初九日就义,汪元量此九首诗作于此年年末或稍后,是为悼念文天祥而作。九首诗中不仅使用了许多杜诗成句,而且九篇全效杜甫《同谷七歌》,是汪元量刻意模仿杜诗之作。
另外,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二十三首,多用杜诗典故,如“近法秦州体”、“吟登李杜坛”、“黑入太阴中”[8](P25)等,这组诗也颇有杜诗神韵。
汪元量的诗中化用了许多杜诗。他说:“我宋麒麟阁,公当向上名。”[8](P7)此出自杜诗“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他说:“杜子肯依严武”,[8](P16)“同谷歌臣甫”,[11](P98)“勿诮草堂翁”,[11](P119)此均用老杜事。这样的例证较多,不一一列举。
此外,他还有些句法学习杜甫,如他诗中的当句对:“莫思后事悲前事,且向天涯到海涯”;[12](P41)“山林虽乐元非乐,尘世多魔未是魔”;[12](P44)“车笠自来还自去,笳箫如怨复如愁。”[11](P96)他还偶尔用时空并驭的句法,如“十年不见身为累,万里相逢舌尚存。”[11](P104)此类均是。
汪元量以诗记宋亡历史,其诗有诗史之称。他熟读杜诗,有些诗歌是刻意学杜之作,他的诗中也化用了不少杜诗,这都是他受杜甫影响的地方。但是,他做过元朝的官吏,从其诗歌看,他对元也多有赞颂,对宋朝廷则似怜似讽,这与杜甫的忠厚恳切大不相同。在天崩地解的大变动中,汪元量善于自保,他算不上真正的遗民。他的诗歌也过于流利畅达,带有明显的乐师色彩。
文天祥和汪元量的诗歌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以诗存史的观念,其诗歌创作都受到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和汪元量的诗歌,代表了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三
南宋后期,文天祥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集杜诗,这些集杜诗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这是南宋后期诗人学杜的成就之一。
文天祥不是最早集杜诗的人,但他作的集杜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集句诗的开始比较早,[13]大约在汉魏六朝就已经开始。在宋代,这种方式有较大的发展,王安石集中的集句诗就有六十多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宋代的孔毅父“作了大量的集句诗,并且进一步开了专集杜诗的先例”。[14](P305)文天祥有《集杜诗》二百首,表明杜甫对文天祥有很大的影响,杜甫的精神与文天祥产生了共鸣。文天祥说:“予所集杜诗,自予颠沛以来,事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这说明文天祥有以诗存史的观念,而这二百首集杜诗也的确有诗史的意味。莫砺锋指出,“文天祥的这些集杜诗是历代集句诗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莫砺锋把文天祥的《集句诗》二百首按照题材内容分为七大类,认为这七类之中有六类皆有佳作,尤其以咏宋末史事及有关人物和诗人自己抗元入狱经历的集句诗,成就最为突出。但其中有些诗歌“有支离破碎之病,读来不免有勉强拼凑成篇之感”。[15]《集杜诗》中的一些作品,如《祥兴第三十四》等篇,情思顺畅,浑然天成,使人感到这就是文天祥的创作,“忘其为子美诗也”,说明集杜诗中有些诗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文天祥还曾经集杜诗为《胡笳曲》,开创了集杜诗入乐的先河。他在《胡笳曲》的前言中说:“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急徐,指法良可观也。琴罢,索予作《胡笳》诗,而仓促中未能成就。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16](P369)(按水云即汪元量)从小序可知,《胡笳曲》为文天祥所作,他“与水云共商略之”,当是商略集杜诗入乐的问题。文天祥说集老杜句“成拍”,可知这诗歌是曾经入乐的,故以《胡笳曲》名之。《胡笳曲》共十八拍,均集杜甫七言诗为句。各拍的句数并不相同,这可能是根据入乐的需要而确定的,当是与汪元量“商略”的结果。诗人自云“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但从全诗看,《胡笳曲》虽然有破碎杂凑之病,但也反映了诗人飘零异国的感怀和思家恋阙的心情。集杜诗为诗并且入乐,是文天祥的一个创举。
四
除文天祥、汪元亮以外,宋末的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虽然都受到杜诗的一些影响,并有以诗存史的观念,但是,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虽然也创作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诗歌总体上艺术性并不强。
林景熙被称为“宋元之际最富成就的诗人”,[17](P8)他的诗歌多是以遗民的身份写对故国的怀念。如《南山有孤树》:“南山有孤树,寒乌夜绕之。惊秋啼眇眇,风挠无宁枝。托身未得所,振羽将逝兹。高飞犯霜露,卑飞触茅茨。乾坤岂不容,顾影空自疑。徘徊向残月,欲堕已复支。”[18](P1)此比宋为南山孤树,而以寒乌自比,抒发无枝可依的感怀。他又有《商妇怨》、《故衣》等篇,均是采用象征手法,寄托深远,抒发故国之思,风格凄婉幽渺。他有《古松》、《昆岩》、《妾薄命》、《精卫》等诗,用以表示自己坚贞的节操。他还有《故宫》、《西湖》、《拜岳王墓》等篇,均表示恋恋不忘故国之意。他有《题陆大参秀夫广陵牡丹诗卷后》云:“南海英魂叫不醒,旧题重展墨香凝。当时京洛花无主,犹有春风寄广陵。”[18](P18)也抒发了深沉的亡国之痛。他在《书陆放翁诗卷后》中说:“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19](P265)亦是沉痛之言。
元军破宋,尽发宋帝诸陵,弃骸骨草莽中,林景熙等人收拾宋帝遗骨,葬于越山,种冬青树为标志。这是他平生所做的一件大事,他的《梦中作》及《冬青树》即写此事。其《梦中作》幽婉苍凉,足以动人,人比之为屈子《离骚》,杜陵诗史。林景熙诗歌的总体风格是清空婉渺。他在《寄芗林故人》中说:“狺狺多楚狗,何处续离骚。”[19](P244)此当是激愤之言,但也反映出他诗歌直露的一面。
林景熙在他的诗歌中也化用了一些杜诗,如杜甫云“桓桓陈将军”,他则云“桓桓李将军”;[18](P4)杜甫云 “路经滟滪双蓬鬓”,他则说“客鬓双蓬老拾遗”;[18](P11)杜甫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他则说“惟闻丞相嗔”;[18](P71)杜甫云“杜曲幸有桑麻田”,林景熙云“桑麻杜曲忆春风”,[18](P86)“杜曲桑麻归已晚”。[20](P121)杜甫云“安得赤脚踏层冰”,林景熙说“脚踏层冰思远壑”;[20](P216)杜甫云 “翻手作云覆手雨”,林景熙云“世交翻覆如云雨”。[20](P219)林景熙诗中的“溪冷浣花宗武哭”,[18](P92)“臣甫再拜鹃”,[20](P102)“老矣杜陵客”,[20](P235)“安得千万间”等,[20](P235)也使用杜典。他有时还偶尔使用时空并驭的句法,如“万里梦魂形独在,十年诗力鬓俱苍”;[18](P15)“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18](P63)“九万里程惊落羽,三千年事抚遗编。”[19](P258)
林景熙有一些诗歌与杜诗略似。林景熙《京口月夕书怀》:“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20](P167)他在《答郑即翁》一诗中说:“初阳蒙雾出林迟,贫病虽兼气不衰。老爱归田追靖节,狂思入海访安期。春风门巷杨花后,旧国山河杜宇时。一种闲愁无着处,酒醒重读寄来诗。”[18](P80)陈增杰云,此诗笔意跌宕,感慨悲凉,而又缠绵悱恻,代表了林景熙郁勃沉挚的风格。[18](P81)但是这样的诗歌在林景熙集中较少。
总体上说,林景熙只是使用了一些杜诗的典故而已,他只有极少作品稍有壮气,其诗的总体风格与杜诗并不相似。他只是诗歌史上的一个小诗人,诗歌的成就和影响都是有限的。他曾经感叹说:“人生皆有死,百年同须臾。独遗文字芳,乃与天壤俱。”[20](P152)林景熙自然可以不朽,因为他的诗歌,更因为他收拾宋君遗骸的壮举。
在南宋的遗民诗人中,还有谢枋得和郑思肖。谢枋得是英雄烈士,最后用绝食表示了对宋室的忠诚;郑思肖也是时刻不忘故国,有着高尚节操。他们的诗歌虽各具特点,但成就也都不高。
谢枋得在宝祐四年举进士,因抨击权臣被夺官。宋亡之后,谢枋得作了南宋遗民。他慷慨地说:“宋室孤臣,只欠一死”;[21](P1)“今年六十三矣,学辟谷养气已二十载,所欠惟一死耳,岂复有他志”;[21](P7)“某愿一死全节久矣”。[21](P11)他又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间常道也。”[21](P11)最终阖家尽节,美名千古。他的诗文散佚较多,从他留下的七十多首诗看,其诗并不甚佳。
谢枋得的诗歌古质笨拙,缺少才情。和文天祥的早期诗歌一样,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是写给相士的,他自己大约也有这方面的才能。他有几首绝句写得较好,如《庆全庵桃花》:“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22](P149)《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22](P150)《武夷山中》: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22](P152)这算是他集中较有情韵的作品。
他欣赏杜诗,说杜诗“辞情绝妙,无以加之”,[23](P197)但其诗不似杜诗。他在《谢张四居士惠纸衾》中说:“独怜无褐民,茅檐冻欲偾。大裘正万丈,德心欠广运。天下皆无寒,孔孟有素蕴。愿与物为春,衾铁吾不愠。”[22](P122)此略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情怀。他的“靖节少陵能自解”,[22](P141)使用杜甫典故。他的“三起三眠时运化,一生一死梦天常”,[22](P144)算是他律诗中的当句对。谢枋得英雄烈士,其诗固不可以文字工拙求之。
郑思肖出生于杭州。元军南下时,他是南宋朝廷的太学生。宋亡后隐居吴下,他的名字是宋亡后所改,寓有思念故国之意。郑思肖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宋亡后他“为兰不画土根,无所凭藉”,[24](P334)用以表示故国的沦丧。郑思肖有《一百二十图诗集》收诗一百二十首,又有《锦钱馀笑》收诗二十四首。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本名为《心史》的作品,收诗二百五十首。但《心史》是郑思肖去世三百多年后在苏州承天寺的古井里发现的,自清代开始,就有人认为是伪作,①关于《心史》真伪问题的讨论,可参看陈福康《论〈心史〉绝非伪讬之书》,《郑思肖集·附录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89页。可存而不论。在《一百二十图诗集》中,郑思肖借诗歌销愁舒愤,诗歌都是题画诗,表现的是对故国的怀念和对自己节操的坚守。《锦钱馀笑》则是充满滑稽意味的白话诗。
郑思肖有两首诗写到杜甫。《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图》云:“雨卷风掀地欲沉,浣花溪路似难寻。数间茅屋苦饶舌,说杀少陵忧国心。”[25](P225)《杜子美骑驴图》云:“饭颗山前花正妍,饮愁为醉弄吟颠。突然骑过草堂去,梦拜杜鹃声外天。”[25](P225)二诗大略借杜甫抒发忧国之情和故国之思。他另有《子美孔明庙古柏图行》,主要吟咏诸葛亮事迹。总体上看,郑思肖的诗歌艺术性不强,也不似杜诗。
考察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遗民诗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受到杜诗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并不高。
综上,考察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可以发现,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尽管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取得的成绩有限,但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也是宋代诗人对江西诗派创作方法不断反思的结果。南宋后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从其诗歌可以看出,他们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自觉地用诗歌记录宋末天崩地解的大变动,记录大变动中的事件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以诗存史的写法同杜诗有相同之处,文天祥和汪元量也是这个阶段学杜的最有成就的诗人,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集杜诗,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种创新,这是南宋后期诗人学杜的表现之一。除文天祥、汪元亮以外,宋末的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虽然都受到杜诗的一些影响,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但他们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1]徐照.石门瀑布[A].芳兰轩诗集:卷上·永嘉四灵诗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芳兰轩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西岩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宋)文天祥著.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M].北京:中国书店,1985.
[7]钱钟书.宋诗选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宋)汪元量著,胡才甫校注.汪元量集校注:卷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9]程瑞钊.浅论汪元量诗歌的人民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4).
[10]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宋)汪元量著,胡才甫校注.汪元量集校注: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2](宋)汪元量著,胡才甫校注.汪元量集校注: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3]张明华.集句诗的发展及其特点[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4).
[14]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5]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2,(3).
[16](宋)文天祥著.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指南后录[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7]陈增杰.林景熙集校注·前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18]林景熙集校注:卷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19]林景熙集校注: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20]林景熙集校注: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21](宋)谢枋得著,熊飞等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卷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2](宋)谢枋得著,熊飞等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卷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3](宋)谢枋得著,熊飞等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卷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4](宋)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附录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5](宋)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一百二十图诗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