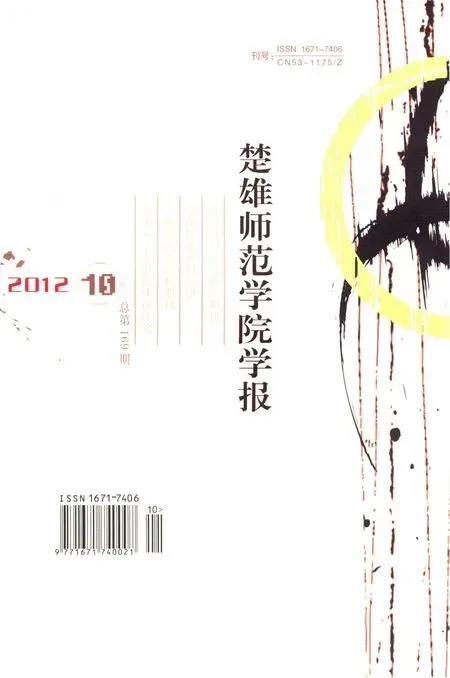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颂莲悲剧形象刻画手法论析*
王奎军 陈 霞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之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这部电影的改编原著《妻妾成群》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当然由于电影是声音、画面及图像的综合性艺术,而小说主要是文字的艺术,不同的艺术门类决定了它们的表现手段各有侧重,同时电影对于小说有很大的改动,因此,使得对于小说的分析和由它改编成的电影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这篇论文主要不是对小说原著《妻妾成群》进行解读,而是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进行一些细致分析,必要时和小说原著加以参考对照,从而论析电影中颂莲这一悲剧形象的刻画手法。影片对于颂莲的刻画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达到的:描绘悲剧的外部客观环境,用环境烘托出颂莲命运的悲剧性;赋予颂莲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加深颂莲命运的悲剧性。
一、悲剧的外部客观环境刻画
人生活在环境之中,必然要受到环境对于他 (她)的影响,我们常说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由此可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之大。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悲剧的环境是造成颂莲悲剧人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悲剧环境的描绘烘托出颂莲人生的悲剧性,这也是导演塑造这一女性悲剧典型的重要手法。电影对颂莲所处的环境——陈家大院,主要刻画了以下几个方面。
1.无处不在的红灯笼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色彩是沉默的语言”,[1](P36)而电影是一种视觉的艺术,色彩在电影中的地位显然比在小说文本中更受重视。张艺谋对于色彩的表现效果是非常重视的,除了《黄土地》中的黄色,经常看张艺谋电影的观众会注意到他特别喜欢红色。无论是《红高粱》中的红高粱,《菊豆》中的红染布,《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这些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红色偏爱的原因,张艺谋曾经说过:“这跟我是山陕西人有关。陕西的土质是上红的,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即陕西和山西在办很多事情时都会使用红颜色。他们那种风俗影响了我,使我对红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演这种红颜色。”[2](P127)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红灯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知道,红灯笼是一个喜庆的装饰品,在传统习俗里,逢年过节都要在院子里挂上红灯笼,尤其是结婚这种大喜事,当然是少不了红灯笼的点缀。但是看完《大红灯笼高高挂》,观众的感觉却是红灯笼烘托的不是喜庆气氛,而是悲剧哀伤的气氛,是在以喜托悲。张艺谋说过,红色有正衬和反衬的作用:“同样的颜色,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现,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按常规,红色是一种火焰般的颜色,象征着热烈和奔放。但我们有意识地将红色用在不同的段落中,情绪上就给人以迥然不同的感受。”[2](P14)和小说比起来,电影的长处在于可以用流动的画面和鲜艳的色彩来增强艺术表现力,张艺谋很好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灯笼起到了正衬和反衬两种作用,但主要是反衬的作用。在影片的开头,颂莲刚刚嫁到陈府的时候,在她的院子里面挂起了红灯笼,这里的红灯笼给人的印象是喜庆、祥和,因为这是颂莲大喜的日子,不管她嫁的是不是她喜欢的男人,这终究是她大喜的日子,在这里,红灯笼起到的是正衬的作用,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气氛。到了影片的中后部分,红灯笼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了女性得宠的象征,但此时观众对于它恐怕就没有影片开始时的喜庆印象了。特别是梅姗死后那一晚,颂莲跑到梅姗的院子里将所有的红灯笼都点亮,同时放起梅姗生前最为得意的戏曲唱片,在这里,红灯笼烘托出的不是祥和与喜庆,而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反衬作用,烘托出的是梅姗命运的悲剧性。和梅姗的悲剧一样,颂莲正是在红灯笼的照耀下由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一个疯子,红灯笼对于颂莲的悲剧命运起到了一种以喜托悲的反讽效果。这种以喜托悲的手法在中国传统小说里也比较常见,例如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作家用薛宝钗出闺的喜庆气氛烘托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悲剧,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2.史前时间和孤独的陈府
除了红灯笼本身之外,在影片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场景的不断重复:姨太太们每天傍晚在自己的院子门口等候着陈老爷的光临;红灯笼无数次的亮起和熄灭;台词“按照陈家的规矩”的反复出现;还有每次饭桌上太太们的必不可少的勾心斗角。我们以为,这是导演在表现一种和现代时间不同的另一种时间:史前时间。“史前时间的特点是循环往复,而与这种史前社会时间的循环相对的是现代时间,现代的时间则是一种不可逆的线性时间,即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是一个进化论的时间观。它的向度是指向未来的。”[3](P262)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时间是一种积极的时间观,海德格尔就认为,“人是他还没有而可能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每个人都被可能性、潜在性决定。这就为我们指引了一个未来的维度,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在都是指向未来的,当每一个未来变为现在之后,又有新的未来马上来临。这就是未来的维度,这个维度给每个失意人以希望。”[3](P170—171)在电影中我们看到,陈府里的时间是一种史前时间,这种史前时间是一种消极的让人绝望的时间,它指向的不是未来,只是不断的重复。这就意味着对于生活在陈府的太太们来说,她们的日子永远是悲剧命运的一天天的重复:饭桌上的勾心斗角、饭后的搬弄是非、傍晚等待老爷的驾临,她们在重复中走向死亡,而不是指向有希望的明天。正如古人所言,一入侯门深似海,陈家大院就是一个大监狱,太太们被监禁在其中,永远只能看到高墙上四角的天空,没有一点自由。除此之外,细心的观众还会注意到,影片除了开头一段取景于陈府之外,从颂莲踏进陈家大院之后,镜头就再也没有出过陈家院子,我们也没有看到颂莲跨出陈家大门。陈家仿佛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和外界隔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牢狱里,时间之河仿佛停止向前流动,只是不断地在原地回旋、重复,颂莲们就在这回旋、重复中走向她们生命的末日。这让我们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主题:孤独走向灭亡。
和史前时间循环相对应的是诡异季节的循环。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出现了夏、秋、冬三个季节,但却唯独缺少春季。没有春季,一年就不完整,而且春季是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季节,代表着希望。没有春季,也就象征着陈家妻妾们的生活是没有活力和生气的,没有希望的。陈家大院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没有春季的魔窟,是她们青春的坟墓,她们跨进陈家大院后,生活里就再也没有了春天的温暖,有的只是夏的酷热、秋的凄凉、冬的严寒。而且随着季节的变更,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也是颂莲命运一步步走向悲惨的过程,最终成了“疯子”。但颂莲并不是真正的疯子,而是因为她发现了陈府杀害三太太梅姗的真相被陈府硬给扣上一顶疯子的帽子,正如陈老爷所说:“胡说八道,你看见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已经疯了。”
3.悲剧场景的轮回
影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片首和片尾的呼应。在影片的开头,颂莲在一片唢呐声中乘着花轿嫁到陈家,她的悲剧就此开始了。而到了影片的结尾,二太太已被缢死,陈家大院的唢呐又响起,精神失常的颂莲见证了一个新的女人被迎接进来,做了陈太爷的五姨太,在这个鬼气阴森的大院里又一个悲剧即将上演。这种悲剧的轮回,使我们想到沈从文的小说《萧萧》的结尾:“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这讲的也是悲剧的轮回。萧萧是童养媳,她嫁到夫家做媳妇时才十二岁,那时候丈夫还不到三岁,因为丈夫太小,后来萧萧被家里一个做长工的小伙勾引使坏,怀了孕,照当地规矩萧萧是要身上绑块石磨沉潭的,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缘故,萧萧不仅生下了个男孩叫牛儿,还和丈夫正式拜堂圆房。在牛儿十二岁的时候,家里也给他找了个媳妇,媳妇年纪长他六岁,小说的结尾写的正是牛儿结婚,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看热闹的场景。这是一个古老风俗的延续,也是悲剧的延续。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作为一个受害者,见证了另外一个女人 (五姨太)即将重复她悲剧的道路,正如萧萧作为一个受害者,见证她的儿媳——另一个童养媳,跨进她的家门。这种结尾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如果说《边城》的结尾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还给人一丝希望的话,那么,《大红灯笼高高挂》给人的印象则完全是绝望。
4.符号化的男权
影片给我们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镜头没有让我们看到陈老爷的正面,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对于他的长相却无从所知。影片中陈老爷的镜头至少也出现了十多次,但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镜头,这显然是导演的有意为之。笔者认为,陈老爷之所以被模糊化是因为他的长相并不重要,他象征了那个社会的男权,就算你看不见他的面容,但你却能听到他的声音,陈老爷的台词并不多且语气温和,但每句话都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一句台词是“按照陈家的规矩”,这个“陈家规矩”的制定者自然是男性,而这个像幽灵一样在整个影片中不断回响的声音——“按照陈家的规矩”,就是男权的传声筒。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不难理解颂莲的悲剧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家的环境就注定了颂莲的悲剧性。颂莲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恰如她自己的独白:“我就是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也正如苏童所说:“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痛苦常常酿成悲剧,就像颂莲的悲剧一样。”[4](P62)颂莲的悲剧形象通过悲剧的环境描绘很好地烘托了出来。
二、颂莲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在影片中,颂莲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害者。在嫁入陈家之前,她是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美丽如花的洋学生,但是到了影片的结尾,颂莲已经沦落为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子。刚刚进陈府的时候,颂莲还对姨太太们的争宠嗤之以鼻,但是到后来,她很快就加入了争风吃醋的行列,这表明她由一个不谙世事的纯洁的小姑娘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姨太太,这是颂莲自己的悲剧。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颂莲是造成三太太梅姗和丫头雁儿悲剧的直接凶手,虽然根本原因不在于她。在电影里,三太太梅姗的死是因为颂莲喝醉酒后无意之间说出了她和医生的私情,而小丫头雪雁的死和她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她本来只是想惩罚一下雁儿,给二太太卓云一点颜色看,哪知道雪雁的脾气那么倔强,竟然跪在雪地里一个晚上,最后被活活冻死。虽然颂莲本意不是要让雪雁死,但最终结果却是雁儿死了。关于颂莲对他人造成的悲剧,我们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来解释。亚里斯多德认为:“它 (悲剧)所模仿的行动必须是能引起哀怜和恐惧的——这是悲剧模仿的特征。因此,有三种情节结构应该避免。一,不应让一个好人由福转到祸。二,也不应让一个坏人由祸转到福。因为第一种结构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只能引起反感;第二种结构既不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又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三,悲剧的情节结构也不应该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从福落到祸,因为这虽然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却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不应遭殃而遭殃,才能引起哀怜;遭殃的人和自己类似,才能引起恐惧;四,剩下就只有这样一种中等人: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们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5](P102—105)颂莲给他人带来的灾难,能够引起我们对于因过失或弱点而犯大错的恐惧。这里我们可以说,一方面颂莲自己的人生是悲剧的,但另一方面她也造成了别人的悲剧;她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施害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颂莲的命运更加曲折、复杂,使得她的形象更富于悲剧性。
总而言之,由于张艺谋很好地运用了电影艺术的特长,刻画出了颂莲生活的悲剧环境。同时,对于小说原著进行了有选择的改编:在小说《妻妾成群》中,三太太梅姗的死和颂莲没有关系,但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让颂莲成为三太太梅姗之死的直接凶手,这也就造成了颂莲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别人苦难的施害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颂莲的悲剧性超出了原作,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女性悲剧形象。
[1]梁明,李力.镜头在说话[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2]张明主编.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3]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A].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 (第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