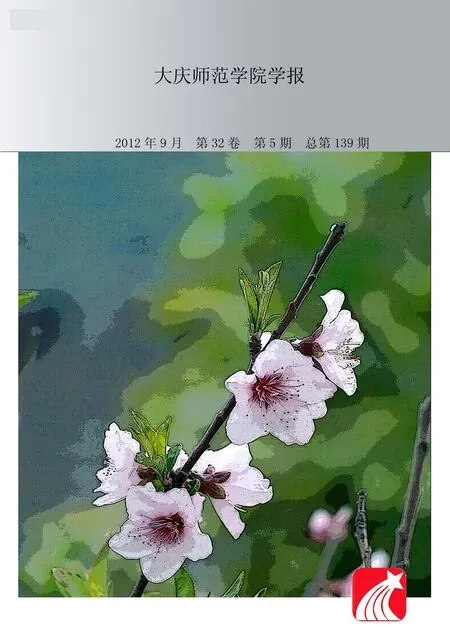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病因之争
毛利霞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1831年秋,霍乱随德国汉堡的船只首次踏上英国国土,迅速传至英国各地,导致2万多人死亡,社会各界普遍患上“霍乱恐慌症”,霍乱严重的城市还出现社会骚乱。与霍乱突然现身一样,肆虐一年多后它又神秘消失。岂料1848年,它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杀伤力再次肆虐英国。在约翰·斯诺于1849年公布霍乱的传播方式之前,对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霍乱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所有一切均处于一头雾水之中”[1]166。围绕霍乱是否传染这一问题,英国人分裂为观点迥异的两大阵营,一方认为霍乱不传染,另一方认为霍乱传染。两大阵营各执一词,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霍乱病因之争。
一、非传染派的观点
非传染派认为霍乱是不传染的,持这一论调的大多是非医务人员。其支持者不是从医学的角度探讨霍乱传染与否,而是从道德、阶级、种族等层面挖掘霍乱出现的社会文化根源,霍乱的出现是英国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落的恶果。医学对霍乱的束手无策和民众对现实的绝望无助使非传染派的各种观点盛行一时。
(一)道德论
19世纪初,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革对英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伦理产生重大冲击,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成为英国上下的一致行动。无名小卒投机钻营试图打入上流社会,而贵族、王室丑闻迭出,逐渐丧失社会的尊敬与爱戴。与对金钱的无比热爱相反,英国人的宗教信仰逐渐冷漠,出现信仰危机。上帝、权威和传统受到严重挑战,有些人甚至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种流于形式的空谈和装饰门面的点缀。为了重塑教会的尊严,教会人士不失时机地把霍乱与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霍乱病因中的“道德论”。
教会人士认为,霍乱是对工业发展阴暗面的无情揭露,是上帝对道德堕落、精神松弛、酗酒、不遵守安息日和其他清规戒律的惩罚,是对英国现存精神面貌的一种批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原罪”在作怪。[2]23-24故而霍乱与英国道德的沦落相关联,道德越堕落的地区,霍乱就越严重。人类如果想摆脱霍乱困扰,就必须洗刷自己的“原罪”,回归到宗教的怀抱中来,祈求上帝的原谅。
1831年,霍乱刚出现在英国时,福音主义者列出全国禁食日,得到国王威廉四世的支持。[3]1681832年,伦敦主教布罗姆菲尔德在全国祷告日上告诫他的忠实信徒,霍乱对公众而言是一个信号,目的是“促进舒适和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盖茨黑德圣斯蒂芬教区的牧师西奥菲勒斯·托伊认为霍乱被派来“阻止男人娶他们亡妻的姐妹”[4]147。牧师麦克尼勒博士于1849年在格拉斯哥布道时认为霍乱是对“支持教皇制度”的国家的审判。[5]230通过一系列的说教和布道,英国教会找到宗教信仰、道德准则与霍乱之关联。
教会除了要求教徒尊重道德和回归宗教,也从道德因素上寻找医治霍乱的药方。公理会提出“对付霍乱的道德防腐剂”,即节欲、清洁、勤奋、坚韧和阅读福音。[2]168这在务实主义者看来,只不过是“隔靴搔痒”。对于“成群的男女、小孩不分性别、年龄蜷缩在一个狭窄的公寓里畅谈道德”这种做法,有人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之情,认为有“纸上谈兵”之嫌,相当于“在猪圈中谈论清洁,或者在下水道的沉积物中讨论清澈纯净”[6]7,根本无助于霍乱问题的解决。报刊《雷诺的政治观察家》认为是现实的原因导致了霍乱,“我们猜测霍乱因忽视热情而加剧……这是一种自然灾难”[5]230,反对从宗教的角度解释霍乱。德高望重的沙夫茨伯里勋爵[注]沙夫茨伯里勋爵:本名安东尼·阿希礼·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811—1851年间被称为阿希礼勋爵,1851年开始成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7th Earl of Shaftesbury),故而此处称他为阿希礼勋爵最为恰当。然而许多英文著作为了名称统一,大多直接称他为沙夫茨伯里勋爵。本文也沿用此称谓。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的社会状况固然依靠城市的道德状况,但是“一个城市的道德状况……取决于城市的物质状况;取决于食物、水、空气和居民的住所”[6]7,主张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去解决霍乱问题,通过物质的改善实现道德的提升。这是一种世俗的、切合实际的观点,得到具有现实主义眼光的牧师的支持。因道德论观点具有较为鲜明的主观说教色彩,无法具体论证宗教与霍乱之关系,到1853年第三次霍乱暴发时,这种观点基本上消失。
道德论提醒英国民众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自身的道德素质和宗教信仰,然而依靠道德的改善和宗教信仰的回归来根治实实在在的霍乱不过是一厢情愿。道德论不是根除霍乱的一剂良方,只是缓解肉体和精神阵痛的一副安慰剂。
(二)阶层论
阶层论认为霍乱具有鲜明的阶层好恶,是穷人的疾病,贫民窟是霍乱滋生的温床。深受霍乱之苦的穷人也认为霍乱是富人屠戮穷人的一个秘密武器。其根据是感染霍乱的大多是穷人,富人很少受到感染,霍乱患者中穷人的死亡率也高于富人。
1831年,霍乱横扫英国,在贫民窟大显威风。在一个儿童救济院,孩子们3人或4人睡在一张床上,结果300个儿童患上霍乱,其中180人死亡。[7]2051848年赫尔深受霍乱之苦,80000人口中2 000人死亡,其中穷人聚居的老城霍乱死亡率是24.1‰,而较富裕的郊区的死亡率仅为15.2‰。[5]231-232富人把霍乱看作穷人的副产品,而社会批评家则把霍乱视为展示社会问题的一个显微镜,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把霍乱与贫穷联系起来。
极端的马尔萨斯论者把穷人看作“侏儒的物种”、“社会渣滓”[2]31,把霍乱看作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一种有效方式。维多利亚的作家发现霍乱具有一种“流浪特征”,“在它的漫步游荡”中,“偏爱泥浆和泥沼、拥挤的房屋、低洼的地区”[2]27。1852年,《庞奇》杂志用一幅名为“霍乱国王的巢穴”的漫画形象地指出,霍乱是英国贫民窟的统治者,英格兰是霍乱的故乡。[2]29亨利·梅休在调查伦敦东区之后,毫不掩饰地把伦敦东区典型的贫民窟雅各布岛称为“霍乱恰当的首都,伦敦的杰骚[注]杰骚:印度地名,以肮脏著称。”[2]31,此地茅舍简陋,污秽遍地,霍乱横行。[2]29有感于此,英国人动用丰富的想象力编织出霍乱如何从穷人的茅舍传入富丽堂皇的富人家中的可怕故事。在一篇名为《廉价衣物和污秽》的文章中,医生查尔斯·金讲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其目的是揭示穷人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威胁富人,扰乱社会。[2]34
面临霍乱的死亡威胁,穷人们要么默默承受——霍乱高峰期,因霍乱死者较多,医护人员忙不过来,以每具尸体5便士(相当于普通工人2—3天的工资)的价格雇人专门运送尸体,贫民窟的幸存者都渴望得到这“恐惧的工资”[6]119;要么积极反抗——1831年穷人掀起一场场骚乱,他们不顾危险,涌上街道,声称“面包是治愈霍乱的良药”,袭击医生,并从医院的救护车上抓住他们患病的同伴。[8]333富人的幸灾乐祸并没有持续太久,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9]1631848年,富人也与穷人一样成为霍乱的受害者,证明霍乱没有阶层差别,“霍乱是穷人的疾病”的阶层论不攻自破。至于为什么霍乱主要袭击穷人,贫民窟受害尤甚,这与穷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有关,而非霍乱具有阶级好恶。
(三)种族论
在富人把霍乱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一些种族论者把霍乱与种族挂钩。道德论者和阶层论者聚焦于国内的普通民众,而族论者则把视线放在外来移民身上。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爱尔兰移民和非洲黑人是霍乱传播的帮凶。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经常被视为欧洲灾难之源,这一次也不例外。1831年,霍乱刚在兰开斯特出现,英国国教牧师古奇就把霍乱“归因于支持非国教者和犹太人,而不是英国教会的议会选民”[4]147。涌入英国的爱尔兰人因信奉天主教一直不受英国人欢迎,一度成为某些英国人解释霍乱灾难的替罪羊。在伦敦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七转盘,警察不允许爱尔兰人靠近他们的霍乱亲属,也不允许他们为亲属送行。詹姆斯·菲利普·凯伊·舒特沃斯是曼彻斯特某个防疫站的一名内科医生,在《曼彻斯特棉纺厂雇佣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一书中,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毫不掩饰地认为爱尔兰工人是传播天主教信仰的源泉,是英国工人中不道德的传播者,是传染病的根源。[10]1681836年,几个证人在伯明翰的爱尔兰穷人调查委员会作证,强调爱尔兰人在传播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委员们得出结论:“伯明翰的爱尔兰人是社会的蛀虫,他们产生传染。他们床铺肮脏,不爱干净,不分性别、年龄紧紧蜷缩在一起,他们是不断产生、传播传染性疾病的工具。”[11]151847年,伦敦的一个官方委员会调查伦敦的卫生情况时,询问一位证人:“爱尔兰人涌入这些地方,他们的肮脏习惯使他们沾染疾病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6]10
英国人把霍乱归咎于爱尔兰人的原因除了其一贯的排斥外来人口、反对天主教阴谋外,还与爱尔兰人大量涌入加剧英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在1841—1851年的最大移民潮时期,大约34000爱尔兰人涌入伦敦。1851年英国进行人口调查时发现,伦敦总人口200万,其中爱尔兰人10万多。其他城市的爱尔兰人比例更高,在利物浦占总人数的1/5,在曼彻斯特占1/7[12]9,爱尔兰人的移民潮刺激了英国人种族灭绝的危机感。此外,爱尔兰人特别喜欢群居,几乎任何一个工业城市都有爱尔兰人聚居区,即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小爱尔兰”。这些流亡英国的爱尔兰人大多是穷人,他们蜷缩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几乎每个“小爱尔兰”都是贫民窟的代名词,霍乱的“首都”雅各布岛是伦敦东区颇具代表性的爱尔兰人集中区。爱尔兰人的酗酒、堕落、脾气暴躁、粗鲁野蛮等恶行劣迹让英国人毫无好感,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嫌恶,此外,他们还与穷困不堪的英国工人阶级争夺饭碗,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恨[6]10,甚至有人把爱尔兰人称为“白人中的黑猩猩”[2]45。爱尔兰人成为英国教会、富人、穷人共同的敌人。
更有甚者,某些种族主义者还把霍乱看作一场无声的战争,种族入侵的先兆。在他们的意念里,霍乱病菌犹如野蛮军队的“东方特别攻击队员”, 携带“火与箭”等秘密武器,向不列颠民族发动攻击,目的是改变不列颠民族的血液和肤色,完成种族变异和军事征服。[2]43霍乱患者在数小时或者几天内身体变黑,使很多人以为工业的发展要以英国人的“种族”变化为代价,是民族衰落的一个象征,有使英国沦为野蛮、落后状态的危险。早在1832年,一位英国评论家在论述欧洲大陆的霍乱时曾提到:“它攻击国王们的宫殿,将之看作鞑靼人或波兰人最肮脏的住所。”[3]781842年,《季刊评论》的文章暗示,城市化提供的生活状况低于“在国外发现的原始人”。不列颠,虽然确立了它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是城市风景正变成“人造文明最奇怪的乱麻和世界上曾经存在的最原始的野蛮主义”[2]30。亨利·梅休甚至把英格兰的某些城市比作埃塞俄比亚的沼泽地,因为殖民地的疾病霍乱成功地在英国兴风作浪。[2]29
综上所述,种族论认为霍乱与本国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有关,不但表现出对种族异化的恐惧,还折射出对工业革命后果的反思。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大多集中在新兴的工业城镇,很少生活在农村和苏格兰地区,为什么这些地区也出现霍乱呢?种族论者对此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
二、传染派的观点
霍乱的快速传播带来的高死亡率使许多英国人认为霍乱具有传染性,传染派的观点逐渐拥有更多的追随者。围绕什么是霍乱病菌的传染源这一核心问题,传染派内部也存在分歧,大致可分为瘴气论和卫生论。[注]英国政府最早采取的隔离措施也是从霍乱会传染这个角度出发的。隔离是英国对付一般传染病最常采用的手段,此处不把隔离看作一种专门的霍乱病因理论。
(一)瘴气论
霍乱的早期症状与斑疹伤寒、发烧等疾病相似,都会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许多瘴气学家把霍乱看作普通发烧的变种,认为霍乱与当地的瘴气(污浊的或不干净的空气)有关。在他们看来,霍乱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腐烂物发生化学反应时混入毒气,分散到空中形成瘴气,逐渐向周围扩散[1]167,比如1832年的霍乱恰好在发烧严重的地区流行。据此有人认为“霍乱在它的前进中注意到普通传染病的法则,被同样的物质条件(指瘴气)所影响,并且攻击同样阶层的人”。他们还用斑疹伤寒的发病原理解释霍乱的病因:最容易受霍乱影响的因素不是贫穷或饥饿,而是“平常呼吸的不干净的空气”[14]48。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这些不干净气体被吸入人的血液,在心脏、大脑和神经中运行,或者直接毒害这些器官,引起更严重的腐烂,出现中毒的症状;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神经,最终破坏人体器官,从而引起呕吐、腹泻和其他症状。这样一来,瘴气很容易把普通的、温和的发热转化成更为严重的传染病杀手——霍乱。[5]232
为什么霍乱出现在一个地区,而未波及附近地区?瘴气论者强调地理、气候和个人的差异:“一个国家的发烧与另一国的发烧并不一样,在同一个国家,一个季节的发烧与另一个季节的发烧也不一样,即使同一个季节的发烧在任何个人身上也不一样。”[1]173地势低洼地区附近,瘴气浓密,霍乱也相对比较严重。城市一般地势较低,受到的影响也比地势高的农村严重,所以城市霍乱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不是源于“较多的悲惨”,而是“恶臭的瘴气”。这种观点得到了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的支持,许多医学人员积极论证瘴气论的正确性。医生威廉·法尔和约翰·韦伯斯特在1849—1855年间计算出海拔和霍乱之间的微妙关系。1849年,海拔20英尺的地区的死亡率是10.2‰,比平均死亡率6.2‰高1/3。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瘴气越少,霍乱病例越少;海拔越低,情况正好相反。法尔进一步提出瘴气的“浓度”还与周围空气、水和土地等自然条件相关。[5]232为什么同一地区穷人和富人遭受霍乱的比例差别巨大?法尔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此后他逐渐由瘴气派转向卫生派。瘴气论也在卫生论兴起后逐渐衰落。
(二)卫生论
卫生论把霍乱产生的原因归咎于肮脏的生活环境和室内卫生,认为是肮脏导致了霍乱的大肆繁衍。
第一次霍乱时卫生派初露端倪,他们反对粗暴的隔离措施,主张当局要特别关注穷人,改善他们的卫生状况来预防霍乱。1831年11月7日,霍乱首次在纽卡斯尔出现时,煤矿村庄深受打击,这是因为此地“大多数房子与猪、家禽的圈舍相混杂”。纽伯恩是一个拥有13间房屋,550名居民的煤村,竟出现 320起霍乱病例,55人死亡。[1]41-42卫生派认为此地的霍乱与周围环境卫生糟糕、臭不可闻有关。
霍乱首次出现时卫生派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到第二次霍乱时,卫生派的观点脱颖而出被普遍接受。这得益于埃德温·查德威克于1842年出版的《大不列颠劳动人民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它“证实了肮脏和过于拥挤与霍乱之间的联系,并且形成了一个公众舆论来支持证据”[12]7。仍以伦敦为例:伦敦东区的克里斯托夫街怀特切佩尔大杂院位于一个死胡同,入口狭窄,院子的后面是一个大垃圾坑,到处是垃圾。一位卫生检查官把此地看作最肮脏的地区,恶臭之气味可恶至极,令人难以容忍,没有一丝清新空气。楼上的空气令人作呕,头晕目眩,笼罩着死人和将死的气味。楼下的气味更为可怕,一打开楼梯口的门,厕所的恶臭扑鼻而来。地窖里霉烂、排泄物、尿液和稻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呕吐不止。60个居民中13人感染霍乱[8]334,成为伦敦霍乱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他感染霍乱的地区差不多也是如此,最肮脏的地方成为霍乱最严重的地方,肮脏与霍乱成为如影随形的朋友。
卫生派主要由医学界人士和某些社会改革家构成,他们认为,霍乱极有可能通过分解的垃圾和腐烂的排泄物进行传播[15]127,过于拥挤、肮脏、发霉的堆放物,潮湿、污染的排水沟,从肮脏的排水道和公墓中排出的污浊的水等都可能成为霍乱传播的途径。[8]335在1851年的国际卫生大会上,医生约翰·桑德兰以简明易懂的语言论述了卫生与疾病的实质——疾病是自然和谐状态失衡的后果,是垃圾和废物不可避免的结果。[15]127只有清理这些垃圾,霍乱才有可能得到预防与遏制。
1848年霍乱第二次暴发时,英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揭露城市的卫生状况,认为霍乱用骇人听闻的方式找到了最肮脏的居住处。这时候霍乱不只是“穷人的疾病”,更被视为一种“社会病”。它犹如一个勇于揭露社会丑闻的正义急先锋,充当了最公正无私的“卫生改革家”。一向以中立、稳健著称的《泰晤士报》公开宣称:“霍乱是所有卫生改革家中最优秀的,它不遗漏任何错误,不原谅任何过失。”[2]58同样在1848年,《伦敦时代》称霍乱为“最好的卫生改革家”[6]117。1848年9月,亨利·梅休受《晨报纪事》之托在伦敦霍乱比较严重的伯蒙兹地区进行调查,在致《晨报纪事》的信中,他描述了亲眼目睹的霍乱情况:霍乱把“伦敦划分为不健康地区和死亡区”,“(伦敦)北部和东部充斥污秽和发热,南部和西部到处是贫穷、肮脏、垃圾和霍乱肆虐”。[2]471849年,《爱丁堡评论》也把霍乱称为“卫生监督员,它用可怕的精确和无可驳斥的准确指出那些不仅偶然有死亡,而且随时是疾病孵卵器的地区”[2]58。1831年以来一直认为霍乱与肮脏有关系的《伦敦医学报》更是以他们的先见之明为荣,“我们一向认为霍乱不是纯粹的传染病,也不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流行病,而是由人类的接触传播”[14]61。
其实,有些城市在第一次霍乱时已经把改善城市卫生作为对付霍乱的一个手段。1832年霍乱暴发期间,爱丁堡成立地方委员会,耗资19000英镑来改善城市面貌。但是地方委员会是临时性的,霍乱消失后,所有的举措也戛然而止。16年后霍乱再次出现时,爱丁堡的卫生问题又再次被提出来,下水道、垃圾处理等方面更为糟糕。[6]24
卫生派不遗余力地揭示霍乱与肮脏之间的关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848年议会批准成立卫生总会,发起公共卫生运动,负责改善城市卫生面貌。卫生派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霍乱,然而其主要观点仍不乏支持者。甚至在1866年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已经人尽皆知之时,里河基金会的工程师N.比尔德莫尔仍坚持认为“过于拥挤、下水道、食物低劣比不纯净或不充足的水更可能招致霍乱”[15]90,足见卫生派的影响之大。
(三) 传染论的其他观点
除了瘴气论和卫生论,传染论中还存在其他解释霍乱病因的理论。“微生物理论”认为,霍乱是由某种微生物造成的疾病;“霉菌理论”把霍乱归因于食物和水中的细微替代物;“陆生理论”宣称,霍乱是地球蒸发产生的毒药,它没有在海上同时暴发足以证明这一点;“污染理论”认为是肮脏的空气和食物感染了霍乱病菌;“地质理论”认为,霍乱的毒气仅仅在水中含钙和镁的盐发挥时才传染;[7]193“电力理论”认为霍乱是由缺少臭氧引起的[8]341……这些霍乱病因理论与霍乱的治疗方案一样五花八门,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难以自圆其说,仅在某些专业人士中盛行,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影响。
三、小结
英国第一次暴发霍乱时,非传染论者拥有不少追随者;霍乱第二次暴发时,由于虔诚的国教徒受到霍乱袭击,富人也成为霍乱的受害者,与爱尔兰人没有任何瓜葛的某些英国人也因霍乱而死亡,非传染论者的观点一一被颠覆。许多非传染论者根据事态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观点,传染派的观点成为主流。
传染派内部的瘴气论者和卫生论者争论不休,最终卫生派在争论中占据上风,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官方的霍乱预防理论。它脱颖而出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瘴气论者无法明确指出瘴气存在于何处,如何预防,在事实上难以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而卫生派认为霍乱是由肮脏引起的,预防和根治霍乱的关键在于清理垃圾和贫民窟或其他产生污浊气味的堆积物,把霍乱的矛头指向肮脏、拥挤,不会导致公众恐慌或遗弃病人,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和阶层矛盾,也不会带来商业贸易的损失。
其次,隔离和封锁不得人心。随着自由主义精神的渗入,英国的许多人都认为封锁和隔离是野蛮的和过时的,是专制国家(如俄国和奥地利)才会采取的措施,与英国这样的自由国家的宗旨不符,卫生派的观点更适合时代的“自由精神”。英国人对中央卫生委员会的态度变化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转变。1831年,为应付霍乱而成立的中央卫生委员会是隔离措施的倡导者,在第一次霍乱期间被委以重任,大力推行隔离政策,并得到议会的鼎力支持;1848年,当它企图重新采取隔离和封锁时,被议会指责为“军阀”。[16]27
综上所述,英国人围绕霍乱是否传染出现的各种观点和争论最终以卫生派的观点占上风而告终。这场争论加深了英国人对霍乱的认识——从主观臆断的偏见到着眼于现实的理性分析,从普通疾病到“社会病”的表现,协调进而明确了英国人的霍乱应对之策,加快了以城市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卫生改革的步伐。故而当欧洲大陆国家固守传统的隔离和封锁措施时,英国人改弦易辙,在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卫生派的积极努力下,展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运动。可见,霍乱的出现以及围绕霍乱的争论成为19世纪中叶英国积极推行社会改造的不容抹煞的背景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恰如阿萨·勃里格斯所预言的,“对19世纪霍乱史的研究远不止是流行病学领域的课题,而且是社会史中重要而又被忽略的篇章”[13]76。此外,19世纪中叶英国人围绕霍乱问题的争论和探索也为我们今天有效预防和治疗霍乱及类似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 Vinten·Johansen, Peter. Cholera, 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A Life of John Snow[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O’Connor, Erin. Raw Material: 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Kiple, Kenneth F.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Lane, Joan. 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Health, 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 1750—1950[M]. London: Routledge, 2001.
[5] Smith, F.B. The People’s Health, 1830—1910[M]. London: Croom Helm, 1979.
[6] Wohl, Anthony S.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Lewis, R.A.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 1832—1854[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8] Finer, S.E.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M]. London: Routledge / Thoemmes Press, 1997.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0] Snodgrass, Mary Ellen World Epidemic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Era of SARS: A Cultural Chrology of Disease[M]. Jefferson: McFarland & Co., 2003.
[11] Flinn, M.W.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T. Britain[C].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12] Burnett, John.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Briggs, Asa. Cholera and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J]. Past and Present. April 1961.
[14] Pelling, Margaret.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 Baldwin, Peter.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Luckin, Bill. Pollution and Contro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ry[M]. Bristol: Adam Hilger,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