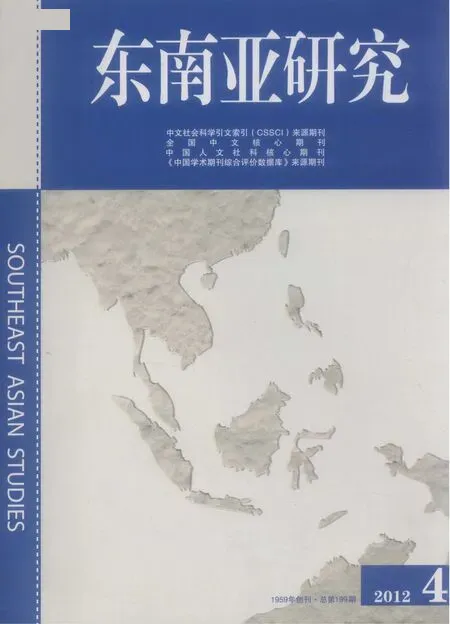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
汤锋旺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厦门361005)
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
汤锋旺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厦门361005)
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社群化;制度化
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会馆成了各帮创办华校的主导力量。要了解华人社会是如何在会馆主导下创办新式教育,必须对会馆学校进行研究。鉴于此,笔者以新加坡较早成立的几所新式华校为研究重点,并结合相关的特刊、账本、会议记录等历史文献,具体讨论了新加坡移民时代“会馆办学”是华人社会举各帮之力并使之制度化的一种创建教育机制的尝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教育进入历史新阶段。从1905年到1920年间新加坡成立了36所华文学校[1],其中,许多华校是由会馆创办并加以管理的。五大帮群先后创办了新式学校:客家人的应和会馆1905年创办了应新学校;1907年,广、惠、肇三属合作兴办养正学校;潮籍人士和闽籍人士分别筹办了端蒙学校和道南学校;海南会馆则于1910年创立了育英学校。可以说,“会馆办学”是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办学的主要模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的主要有两类:其一,关于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研究的论著。此类论著在厘清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初步勾勒了“会馆办学”的具体情况。周聿峨教授在《东南亚华文教育》中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虽未专门就“会馆办学”进行阐述,然其有关新加坡近代学校兴起、发展革新的论述实则勾勒了会馆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郑良树博士则阐述了清廷、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社办学的影响,他肯定了会馆在20世纪前期在“学校的创办及资助方面做出的贡献”[2],并对“会馆办学”的诸多困难做了详细论述。此外,王秀南、陈育崧等诸位学者从新马华文教育发展史所作的研究也有部分涉及“会馆办学”内容。其二,关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史研究的论著。刘宏教授在叙述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中专门就华人社团与教育进行阐述,具体讨论了会馆对学校的影响模式、会馆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他认为战后新加坡华文教育与认同的本土化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3]。颜清湟博士对战前新马闽人教育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因素和福建社群精英对闽人教育事业的影响。李志贤博士对新加坡潮人学校转型的观察侧重讨论教育与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归纳来看,这些著述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会馆办学”的影响。
从上述两点来看,学界现有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探讨“会馆办学”的历史背景、影响因素以及面临困难等方面。这为进一步研究“会馆办学”奠定了基础。但是,要探究此时新加坡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原因除了外部客观历史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探讨此时作为主要办学模式的“会馆办学”具有怎样的运作机制。具体诠释“会馆办学”的真实面貌则须通过对此时会馆学校的具体运作情况进行研究。换言之,对“会馆办学”的诠释,其实就是探究此时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制度性因素。
一 华人“会馆办学”的历史背景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香港下南洋,于1900年抵达新加坡,寻求华社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之后便开始倡办新式学校。孙中山先生广州起义失败后,奔走海外,鼓励华社倡办教育以加强团结。这两股政治势力在华人社会中的活动引起了晚清政府的恐慌。他们认为:“今日之海外侨民可以利用亦可以隐忧者莫如南洋各岛……其人民富于财产缺于教育……是故善用之则外强可折内乱可弥,不善用之则所以厚敌……亟应兴教劝富以系人心而杜隐患。”[4]同时,清政府出于同英殖民当局争夺华人社会认同的考虑,采取了设劝学所、派视学员、刊发钤记、颁奖匾额等措施来加强对海外华侨教育的指导。中国因素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兴办教育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晚清政府、维新派和革命派对新加坡华校创办华校的影响各不相同。晚清政府主要通过派遣官员或视学官、颁奖匾额等形式来推动华校的创办。1905年,“晚清工商部,及粤督岑春煊,先后遣派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张弼士,视学刘士骥,南来劝办商会及学校”[5],客属的嘉应社群在其影响下创办了应新学校。1906年,刘士骥受两广总督张人骏的派遣再次南来视察,同潮帮领袖商议兴学办法后便创办了端蒙学校[6]。学校创办之后,晚清各部官员多次莅临参观。1907年5月,驻英大使汪大燮道经星洲回国,参观应新学校时“赠经费三百元”,并赐“声教南暨”横额一块。同年6月,宣慰华侨钦差大臣杨士奇到访端蒙,捐助教育品一百六十余元[7]。1909年,福建提学使司派视学员陆君睦和海澄视学郑郭棠到道南学校视察,亲自“试验甲乙丙丁各班学生论说等文蒙”[8],并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嘉奖。诸如官员到访华校的参访事例不胜枚举,且在日后逐渐常态化。晚清政府及官员的支持无疑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来说是莫大鼓舞。与晚清政府相比,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华社创办新式学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些华校创办者多数是其两大阵营的支持者或成员。应新学校创办人汤湘霖不仅是嘉应客帮的领袖人物,还是“保皇党在新加坡的重要领袖”[9]。端蒙学校创办人陈云秋、养正学校发起人朱子佩、道南学校倡办人吴寿珍都是维新派在新加坡的重要人物。而且,据康有为弟子伍宪子所说,南洋新式华校的创办十有八九都与维新派有关。如果此言确凿,则维新派对华校创办的影响可谓甚矣。育英学校则是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兴办的,其创办人黄有渊乃革命派人物,革命派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影响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学校的创办人不仅是各自社群的领导人物,还是维新派或革命派在新加坡的代言人。
新式学校的创办还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状况息息相关。首先,英校流行,私塾教育存在弊端。当“其时吾国人之侨居星洲者,不下二十余万,遍查子弟之所学,多崇尚英文,中文学校,寥若晨星,有之只不伦不类之蒙塾耳”[10]。此种情况令华侨子弟为难,华人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华文教育,而私塾教育又不能满足华侨子弟日后发展的需要。以课程为例,“义学课程着重于传统思想伦理之灌输,旁及写信与算术,独缺少英语之教授,这对生长在英殖民地的华人子弟来说,不论是谋事与处世,是很不利的。”[11]华人社会普遍感到必须创办新式学校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萌生了改革私塾教育的意识。其次,“会馆办学”同华人不同社群之间竞争及社群内部权力斗争有一定的关系[12]。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各社群的人口和经济力量都获得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创办新式华校不仅是各帮竞逐的舞台,也是各帮领袖人物施展领导能力的绝佳机遇。第三,新加坡华人社会精英对教育改革的呼吁。林文庆是较早认识到教育重要性的华人社会领袖。在他眼里,“华校是新加坡最差的学校,地点不当,光线不足,六岁小童就被问‘人之初’之类的无聊问题。学校的时间存在着根本的弊端,其间运动和休息必须适当分配。体育锻炼与课本学习应该并重。在这些华文学校只教授华文。由于染上许多恶习,致使学生离校,其品行竟比当初入校时更坏。”[13]这令华人精英分子对自己族群的教育问题感到担忧,因此大声疾呼改革私塾教育。可以说,此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已经积蓄了创办新式教育的力量。
从上述新式学校创办的内外因素来看,中国因素在新式学校的创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政府从其所推行的华侨教育政策及措施方面对华人社会兴办新式教育加以支持;保皇派和革命派则主要通过其成员或支持者来推动新式华校的创办。从内部因素看,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开始认识到发展新式华文教育的必要性,华人社会的精英阶层更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和推动。此外,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不闻不问的放任政策也是促使华人社群积极办学的重要因素[14]。整体而言,新加坡华人社会新式学校的创办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二 “会馆办学”的社群化运作
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整合进入新阶段,华人社会帮的结构基本稳定下来,各帮的内部整合继续深化。华人社会通过“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华商俱乐部等各类社团和组织,以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15]。对于地缘性组织的会馆来说,推广教育是其重要功能,应和会馆、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等都将此列为主要宗旨之一[16]。“会馆办学”不仅是会馆传承中华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华人社会整合的组成部分。新加坡华人五大方言群会馆分别创办自己的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在华人社会帮的建构下创建,并在各帮所属会馆主导下开展校务管理和经费管理。会馆学校的运作实际上是华人社会结构“帮”特点的折射,方言群成为“会馆办学”的力量源泉。尽管,此时新马华人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华人社会的社群边界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开始模糊。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和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都把现代学校视为破除南洋华人社会的帮派障碍的一种手段”[17]。然而,在实际办学中各帮所体现出的社群边界依然畛域分明、不可逾越。
首先,从会馆学校的人员组成来看,无论在董事、教师还是学生,都具有明显的社群属性,这反映了会馆学校的运作是在“帮”的系统内进行的。具体情况如下:第一,各校董事会成员都是由所属社群选举产生的,各校的董事基本都是各自社群领袖。道南学校《历年来董事教员名录》①道南学校编辑委员会:《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1932年,第1-5页。、养正学校《廿二度董事一览表》②新加坡养正学校出版委员会:《新加坡养正学校概况》,1933年,第329页。以及育英学校《本校现任校董名籍录》③新加坡育英学校校刊编辑部:《育英学校校刊》(第一期),1925年,第54-56页。都表明了这一点。第二,各校章程或招生简章中对会馆学校的学生进行权利的限定。章程中会馆学校规定本帮弟子享有某些特殊待遇,如应新学校规定只有嘉应子弟才享有免费和减费的权利。而且,“这种帮派的观念还很清楚地显示在招生的广告上”[18]。因此,会馆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本社群。应新学校学生籍贯大都来自梅县、平远、兴宁、蕉岭、五华的嘉应子弟。端蒙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潮州八邑。据1931年的调查显示,潮州八邑籍贯的学生人数在端蒙学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高达90%[19]。道南学校的学生以福建人居多,1932年道南学校学生总共有257名,而只有13名来自其他社群的学生[20]。第三,会馆学校的校长及教员从属于会馆学校的社群属性,各校校长及教员的籍贯基本上与各会馆学校的社群属性相一致。据统计,二战前的道南学校教职员55.6%的籍贯是福建。而从1933年至1941年的端蒙学校教师全部是潮州八邑人士[21]。由于校长掌一校大权,各属会馆自然倍加重视挑选校长。与教师籍贯比较,校长籍贯属本社群的比例更高。应新学校前十任校长都是清一色的嘉应人士,育英学校的前十任校长亦皆来自琼帮。一般来讲,学生、教师、董事的社群属性一致在会馆学校是普遍现象。会馆办学的主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于其所属社群。
其次,学校经费状况也是会馆集社群之力兴学的反映。从创办经费的筹集来看,各校在经费上是不平衡的。道南学校在创办之初,福建会馆决议“通过逐年校费不敷由天福宫余款支补,并向闽侨募捐四万余元为基金及开办费并逐月月捐数百元为经常费”[22]。育英学校“即在前清宣统二年,共得捐款九千余元,并提拨琼州会馆存款六千余元,都为一万六千余元”[23]。和道南学校相比,育英学校办学经费的规模和金额都显得稍逊一筹。从各校常年经费状况来看,端蒙学校在1905年至1930年间几乎是年年入不敷出[24],道南学校的情况则较好。会馆对学校每月的津贴也是视会馆自身经济状况而论。据账本记载,1928年应和会馆每月津贴应新学校280元[25],这与此时福建会馆对道南学校的津贴数目相比就少了许多。此外,各帮属的庙宇对会馆学校给予了很大支持。应新学校办学经费中很大部分来自海唇福德祠,道南学校亦与天福宫关系紧密。因此说,会馆学校经费来源的社群属性明显,会馆学校的经费状况是华人不同社群经济力量的反映和延伸。
第三,会馆学校以方言为教学用语是会馆办学社群化的体现。据黎宽裕先生在《浮生追忆——一位新加坡人之自述》中谈到,他在1910年转入应新学校就读时,因此校是梅州人士所办,故授课用语为嘉应客话[26]。道南、端蒙、养正等会馆学校亦莫不如此,方言教学使得各会馆学校之间筑起了一道壁垒。在这过程中,会馆通过方言教学所塑造的次族群认同实际上是会馆社群内部整合的重要部分。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当华人民族主义唤醒华人的民族意识后,社群认同在华人社会内部被一定程度的削弱与消解。1916年,道南学校首先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教学[27]。随后,各社群相继开始废除方言教学转而使用国语教学。这样看来,会馆学校教学用语从方言到国语的转变,代表着会馆办学从社群化走向超社群,华文教育从而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华社的整合与发展。
概言之,会馆办学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建构与整合的重要内容。它是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帮的建构之下进行创办、管理与运作,其资源来自于社群内部。董事会在社群内谋划校务的管理,教职工与学生则在会馆学校之下进行教学和学习。会馆学校在人员社群属性的整齐划一,会馆与学校连接成一体,有利于社群内部齐心协力办教育。这也是会馆办学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会馆促使整个社群为学校的创办、管理及运作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以确保办学能够正常、有序地发展。在整合中办学,以办学促整合,会馆学校成为华人社群整合的重要纽带。这是会馆办学的方式,也是会馆办学的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说,方言群是会馆办学的力量源泉。
三 “会馆办学”的制度化管理
与早期华人社会办学的形态不同, “会馆办学”所呈现的是制度化办学模式。这个特点反映在组织结构、经费筹集及校务管理等方面。在20世纪上半期,新加坡华文教育良好的发展势头与“会馆办学”的制度化模式有很大关系。
首先,组织结构的制度化。会馆学校的组织构架是“双轨制”,它由董事会议与校务会议共同组成。董事会为最高机关,校长受董事会聘任,代表董事会主持学校行政[28]。从董事会的组成和职责来看,董事会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董事,选举设有唱票、记票和监票人员,以保证董事及职员选举的公开透明[29]。董事会章程明确规定了总理、副总理和董事的职责,并确保董事会在筹划、管理学校事务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校务会议方面来看,校长领导下的校务会议包括教务部、事务部和训育部,各部又分别设有教务会议、事务会议和训育会议,每个会议下面分别设置职责不同的股。在此基础上,各部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形成了严密、规范的校务管理体系。当然,各校在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差异。在董事会的人数、董事权责以及会议制度等方面,各校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以会议制度为例,养正学校规定以“七人以上”出席为法定人数,若不足则改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但第二次会议则不再受法定人数之限制,只要四人以上到会即可表决上次议案[30]。其他学校的董事章程对会议制度的规定则不尽相同。尽管,各校规章制度的具体规定略有不同,但都采用董事制管理学校事务,并以此加强组织结构的制度化。
其次,办学经费的制度化。能否实现经费来源的常态对学校来说至关重要,“会馆办学”相比之前的华商办学,在办学经费方面改观甚大。这固然与华社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但更是得益于董事会制度化管理经费的结果。从经费来源来看,会馆学校的经费来源具有多元的特点。以端蒙学校为例,其经费来源包括特别捐、常年捐、学生学费、万世顺公款之租息等项[31]。其他各校收入项中亦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为了解决庞大的经费,校董事会还置办起学校产业,以其租金收入作为稳定收入。另外,学费在整个学校收入中所占比重虽小,但是相对稳定。有些学校学费收入在收入总额中也接近一半[32],对学校的正常运作颇为重要。为此,会馆学校在章程上对学费缴纳的时间、数额、方法加以规定。商人和商家每年所认捐的款项也较为固定。当学校面临特殊事项需要经费而自身无力解决时,通常会通过多种方式来筹集,最常见的是举行游艺会演。董事会通过成立演剧筹款会、具体讨论筹办工作、相关人员出售剧券和正式演出等四个部分来筹办游艺会[33]。虽然作为临时性的措施,董事会也是依据一定程序来进行筹款活动。
第三,校务管理的制度化。在校务问题上,会馆学校首先必须处理好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因此,“为划清权限以利校务进行计”,董事会规定:“董事会专任筹捐经费策划进行。其余凡关于管理教授上各事由校长教员负完全责任”[34]。同时,在章程上对校长职责加以确认并在聘请校长之时将权责具体化、法律化。聘请校长的“关约” (合同)中一般包括校长的授课时间、任期、薪资、权责等具体条款[35],从章程和条约上明确了校长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也通过章程、合约形式来规定教职员的权责。教职员职责一般包括协助校长处理一切校务、恪守教务职守和遵守关约 (合同)等方面。学校为此专门制定章程管理教职员。但是,董事会一般是通过授权校长来间接管理教职员。而校长则通过同教师签订合约将教职员的权责具体化,承担包括所教科目及课表、课外服务时间、请假等职责[36]。董事会通过章程和合约形式赋予校长管理教职员的权利。另外,会馆学校还在课程、学科时间、教科书及学生事务等方面明确规定。学校课程一般包括国语、英文、公民、历史、地理、卫生等。教科书则主要来自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37]。而且,会馆学校在依据中国颁布的教育规章制度的同时根据本地情况做出适当调整。如根据当地情况增加英文课程,调整上课时间等等。可见,会馆学校对其事务的管理是以各类章则为准绳,以确保办学秩序的井然。
综上所述,会馆学校的制度化建设表现在:其一,会馆学校的组织结构特点在于通过组织结构制度化建设构建起双轨制的学校管理模式,董事会议与校务会议各司其职,行政与教学分离,以确保教学秩序的规范;其二,会馆学校的经费管理是基于其组织结构制度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有了制度保障才使得办学经费具有多元、稳定的收入渠道;其三,董事会通过各项章程、条例的制定使得学校事务有章可循,校长则依照规章制度对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管理。会馆学校的制度化是建立在华人社群的基础上,制度化是“会馆办学”的重要特征,它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行。
四 “会馆办学”机制的分析
“会馆办学”是20世纪前期东南亚华人包括新加坡华人办学的主要模式。就新加坡华人社会而言,虽处于英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然而华人会馆承担起了兴办教育的功能和使命。会馆以华人社会结构为基础,在社群内部积聚办学力量,促使华文教育发展到新的阶段。尽管,“会馆办学”这一概念早已为人所知,然囿于各种因素却未能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通过对会馆办学机制的研究,以了解“会馆办学”的力量源泉以及制度建设,从中挖掘“会馆办学”的内涵。而且,如何认识和评价“会馆办学”关系到对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 “会馆办学”与“华商办学”存在差异。“海外华人社会同传统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有天壤之别,海外华人社会由‘商’和‘工’两个阶层组成”[38]。在商业氛围浓厚的新马地区,商人阶层的佼佼者成为华人社会的领导层,并成为华社办学的主要推动者。从“华商办学”到“会馆办学”,新加坡华人办学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办学主体大大增加。以往“华商办学”是个人的行为, “会馆办学”则是全民办学,办学主体从商人阶层中的个别人物向社群大众扩展,办学力量大大增强,激发了社群内部各阶层的兴学热情。第二,管理制度的创新。早期华商个人兴办教育随意性比较大,朝令夕改时有发生。然“会馆办学”则建立了以董事会议和教务会议为核心的双轨制,克服了以往华校管理混乱的弊病。第三,办学效果更为凸显。“会馆办学”的成效不仅表现在华校的增多,更显著的是办学理念的转变,积极推进本属子弟在殖民地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从上述来看,以会馆为主导的办学形态相比华商个人的办学形态发展得更充分。
但是,“会馆办学”与“华商办学”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会馆办学过程中,作为领导层的华商参与了华校创办的整个过程,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商人及商号的捐款是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应新、端蒙、养正、道南和育英在创办时,作为创办人的商人都曾捐出不少的款项。以道南学校为例,在其创办时的四次收捐活动中,李清渊、吴寿珍、刘金榜等福建帮商人捐款数额较大,福建社群的商号认捐也非常积极[39]。其他会馆学校莫不如此。第二,华商既是会馆的领导者也是会馆学校董事会的成员, “两团体之董事亦类皆相同,其不同者不过几人而已”[40],华商承担了会馆学校管理者的角色。这些担任会馆学校董事的商人,不仅要经营自己的生意,还要参与会馆学校事务的管理。从这个层面讲,会馆办学中包含了华商办学的成分。但是,华商在会馆办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会馆办学等于华商办学。一方面,虽然华商承担了大笔办学经费,但因创办学校经费数额巨大单靠商人或商人阶层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华商是在会馆学校董事会制度下管理华校的。因此,商人对会馆学校的经费支持和管理是会馆制度办学的重要环节,但非全部。
其次,会馆学校运作机制的合力与张力。“会馆办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办学力量的社群化和管理的制度化两个层面,这也是保障会馆办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但是,会馆办学的内部机制本身存在张力与合力。
从会馆办学社群化来看,会馆学校的经费、学生、师资等都以社群为基础,社群成为“会馆办学”的力量之源,离开了社群会馆学校就无从生存,更谈不上发展。而且,会馆学校以社群为单位的分布格局也激发了华人社群之间兴办教育的竞争,许多方言会馆为了“争一口气”[41],努力为自己方言群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的办学环境。这是会馆办学社群化所带来的办学合力。但这种合力具有局限性和狭隘性。由于会馆学校的社群边界清晰可见,使得会馆学校具有浓烈的帮派主义。譬如董事会在招聘校长、教师之时,往往不是以才论人,而是局限在社群内部以私人关系来挑选人才,这难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会馆学校之间各自为政,教学行政不统一,也不利于教学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会馆办学制度化来看,会馆对学校的管理具有公开、民主的特点。无论在董事及校长人选的选拔方面,还是在具体校务的决定方面,都行民主与协商的精神。这是其管理制度上的优势。但是,会馆学校在管理上也存在董事权责侵害校长权责的问题[42]。加之,会馆学校浓郁的帮派色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办学制度化。这是会馆办学社群化的张力所在。随着新加坡华人社会从社群向族群跨越的整合,原来的社群认同在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之下正在淡化,会馆办学的社群化对制度化抵消开始萎缩,超越社群兴办教育成为趋势。
概言之,会馆对二战前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很多人对会馆办学的涵义却不甚明了。本文的论述表明“会馆办学”其实有其丰富内涵。它在办学力量上以社群为基础,在机制上以董事会和教务会为核心的“双轨制”,实现对华校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会馆办学”成为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华人办学的主要形态。当然,“会馆办学”的模式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其“地方观念”的根深蒂固[43]。而伴随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觉醒,民族主义塑造下的“会馆办学”从单一社群走向超越社群,促使新加坡华文教育继续向前迈进。但是,当民族国家建立后,会馆所承担的教育功能被弱化,会馆也淡出了华人办学的历史舞台。
【注 释】
[1]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2]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年,第194页。
[3]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34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61页。
[5]杨映波: 《应新学校史略》, 《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新小学,1938年,第5页。
[6]林国璋:《本校大事记》,《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端蒙学校,1931年,第1页。
[7]吴华:《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年,第103页。
[8]道南学堂告白,《叻报》1910年1月24日。
[9]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49年,第24-25页。
[10]杨映波: 《应新学校史略》, 《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新小学,1938年,第5页。
[11]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155页。
[12]李志贤:《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与政治环境的互动——潮人学校转型的观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3]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第62、63页。
[14]唐青:《新加坡华文教育》,台北:华侨教育出版社,1964年,第8页。
[15]曾玲:《福祠绿野亭发展史 (1824—2004)》,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2004年,第54页。
[16]吴华: 《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22-23页。
[17]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第154-162页。
[18]颜清湟:《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289页。
[19]《总校学生籍贯人数比较表》,《端蒙学校廿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端蒙学校,1931年,第22页。
[20]《学生籍贯比较表》, 《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新加坡:新加坡道南学校,1932年。
[21]刘宏:《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2]《校史》,《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新加坡:新加坡道南学校,1932年。
[23]《本校过去之史略》, 《育英学校校刊》 (第一期),新加坡:新加坡育英学校,1925年,第43页。
[24]《端蒙学校廿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端蒙学校,1931年,第16页。
[25]《应新学校常年收支账本:1928-1》,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
[26]黎宽裕:《浮生追忆——一位新加坡人之自述》,新加坡:中华书局,1929年,第1页。
[27]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年》,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年,第227页。
[28]李志贤、林季华、李欣芸:《新加坡客家与华文教育》,黄贤强:《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29]《应新学校会议记录:1931-9-1[B]》,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
[30]《本校员办事章程》, 《新加坡养正学校概况》,新加坡:新加坡养正学校,1933年,第269页。
[31]林国璋:《本校大事记》,《端蒙学校廿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端蒙学校,1931年,第3页。
[32]《本校现任董事名籍录》,《育英学校校刊》(第一期),新加坡:新加坡育英学校,1925年,第54-56页。
[33]《育英学校第三次演剧筹款之经过情形》,《育英学校校刊》 (第一期),新加坡:新加坡育英学校,1925年,第49-51页。
[34]《新加坡养正学校概况》,新加坡:新加坡养正学校,1933年,第259页。
[35]《校长聘书》,《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新加坡:新加坡道南学校,1932年,第9页。
[36]《教员聘书》,《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新加坡:新加坡道南学校,1932年,第10页。
[37]傅无闷:《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册》,新加坡:星洲日报有限公司,1930年,第10页。
[38]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论文集》,新加坡:海涅曼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
[39]福建倡设道南学堂广告, 《叻报》1907年4月16日。
[40]《应新学校会议记录:1930-10-1[B]》,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
[41]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年,第216页。
[42]黄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教育杂志》1917年第11期。
[43]李守善:《南洋华侨教育效率低微的原因》,刘士木:《华侨教育论文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第142页。
Study on the School Running by Chinese Guild Hall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World WarⅡ
Tang Feng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the School Running by Chinese Guild Hall;Social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0thcentury,there was an upsurge of running Chinese school in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in which Chinese guild hall was the leading force.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guild hall led Chinese society to found the new school,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chool running by it.For that reason,the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Chinese schools founded earlier in Singapore,and uses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special issues,account books,meeting minutes,to argue that the school running by Chinese guild hall was a try for the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to create education mechanism with their all strength.
D637.333.9
A
1008-6099(2012)04-0090-07
2011-11-03
汤锋旺,厦门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11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石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