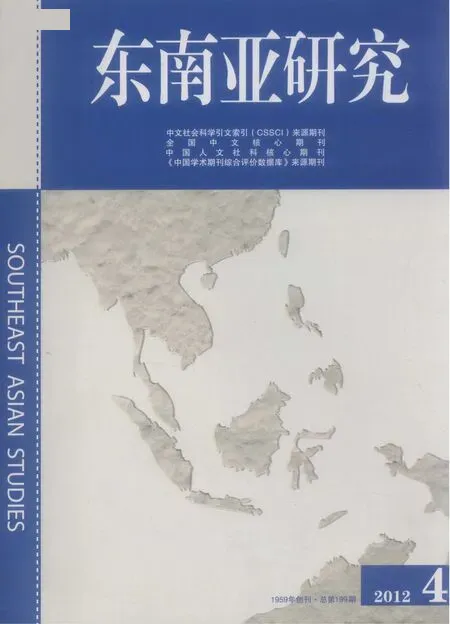安南属明时期政区地名变动初探
郭声波 魏 超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510630)
安南属明时期政区地名变动初探
郭声波 魏 超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510630)
安南属明时期;地名;变动
安南属明时期建立的交趾布政使司在沿用陈、胡朝府、州、县旧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区名称的更改,然学术界对此鲜有关注。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这一时期政区及地名的更改,以及通过对政区通名的研究,进而探寻这一时期政区改名的背景及意义。
1407—1427年是安南属明时期,明朝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等统治机构,对胡朝原有行政区划做了调整,合并裁省了部分府、州、县,更改了很多政区地名。尽管学术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如华林甫对于越南地名的研究即涉及这一时期的地名变动[1],但语焉不详。我们结合相关汉越史籍,参考有关学者著述,拟从各个方面论述这一时期越南地名变更的情况,如命名原则、命名背景、政区通名等,以探究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这对于研究越南历史、中越文化交流、中越关系史等问题当不无裨益。
一 明朝永乐五年所设交趾布政司府、州、县数目考
《明太宗实录》 (以下简称《实录》,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载:永乐五年 (1407年)六月, “定交趾所隶州县:交州、(址)[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义安、顺化,总十五府。”又言:“(永乐六年六月)己丑,吏部尚书蹇义等同六部尚书奏:‘新城侯张辅等平定交趾,建设军士衙门总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这正与《殊域周咨录》所载“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户三百一十二万”[2]之府、州、县总数目相符。
然据《实录》永乐五年六月记载的分州县数目及名单总计,交趾布政司总共设县210个,与上述记载总数目并不吻合。经与完全照抄《实录》永乐五年六月条文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交趾”篇比对,发现原来是红格抄本《实录》府州县名单在交州府利仁州中漏列了古者县(原书六县,实列五县),在新安府东潮州中漏列了东潮县 (原书四县,实列三县),我们认为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总县数的来源,显然,应当以“二百一十县”为是。《天下郡国利病书》 “安南国”篇也载有永乐五年的州县名单,但又在义安府下漏载了驩州及其所领4县。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安南的内容,部分当是抄录《殊域周咨录》之记载,甚至连错误也一并沿袭,如《殊域周咨录》在记载所设15府时言: “北江府领州三县七”、 “三江府领州三县七”[3],《天下郡国利病书》此处记载与其完全相同,只是在附县名录的记载中,北江府却领州3、县13,三江府领州3、县9,多了8个县。同样,《殊域周咨录》记载义安府时少了“驩州”及所属4县,顾炎武如法炮制,延续错误。
《殊域周咨录》所载15府分别是: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府。对比《实录》所载,这个政区名录是永乐十三年 (1415)裁并后的15府之建置。《殊域周咨录》所列15府的属州数是36个,属县数是176个,又演州、宣化州、嘉兴州、归化州、广威州5个直隶州所属县数是22个,总县数是198个。如前述,《殊域周咨录》在记载北江府和三江府时,实际少算了8个县,再加上遗漏的“驩州”所属4县,正好也是210个县。如此,《实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交趾”篇、《殊域周咨录》三者记载的府州县数目皆可相应吻合,证明永乐五年六月交趾布政使司属下确为210县。
黎正甫之《郡县时代之安南》一书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弄清楚这些县数目不同的原因。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对安南古史有精深的研究,他也发现了永乐六年六月蹇义奏议县数与五年六月府州县名单不一致的情况,他怀疑永乐六年六月以前可能发生过州县省并[4]。但我们认为这种怀疑不能成立,因为永乐六年六月以前,交趾地区尚未完全平定,明朝不可能过早进行州县省并,而且山本也没有指出省并的是哪两个县。
新近出版的郭红等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认为,永乐五年所辖县数是211个,《实录》等缺载顺州之“石兰” (亦即“不兰”)县[5],原因是《实录》所载永乐十七年省并之县还有顺化府之顺州“不兰”[6]。按明陈循所撰《寰宇通志》顺化府载有“石兰”,佚名撰《安南志原》顺化府载有“不兰”,《读史方舆纪要》顺化府记为“石兰”。对比《实录》所载逐年裁省政区情况,可知上述三书所载政区名录断限都是永乐十三年八月,因此“不兰”县虽然可以肯定在永乐十三年八月以前已存在,但是《实录》等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州县名单 (包括永乐六年六月蹇义奏议)并无该县位置,所以我们认为郭红的判断是错误的,石兰县只能设置于永乐六年七月至十三年四月之间 (四月以后,交趾州县有减无增)。
还有一些记载的县数与此不同,如丘濬《平定交南录》之“一百六十六县”,《明史·张辅传》之“县一百八十”,《明史·安南传》之“一百八十一县”,很明显这是指永乐四年至五年间从胡朝取得的府州县数。张辅《平定安南露布》云:“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处、县一百八十六处。”[7]可知上述不同的县数,都是“一百八十六”之脱误。此数较之“二百一十”尚少二十余县,可能是当时还有一些州县尚未投降明朝的缘故。
另外,黎正甫误书永乐五年的丘温县为“邱温县”,多翼县为“多翌县”,河瑰县为“河块县”,仙吕县为“仙昌县”,古弘县为“古宏县”、具熙县为“真熙县”,礼悌县为“恺悌县”,持平县为“持羊县”[8];山本达郎误书河瑰县为“阿瑰县”,支俄县为“支峨县”,茶偈县为“黄偈县”,溪锦县为“溪绵县”;郭红误书善才县为“养才县”,洮江州为“姚江州”,河瑰县为“阿瑰县”,四岐县为“西岐县”,仙吕县为“吕县”,杯兰县为“怀兰县”,利蓬县为“利逢县”,思蓉县为“思容县”,蒲苔县为“蒲台县”,因与下文有些关系,也是必须指出的。
二 交趾布政司政区地名改名研究
明朝统治安南的20年时间里,进行了系统的行政地名更改,考察这些政区改名,不难发现,明朝政府有意施加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
永乐五年,“胡氏就擒,明诏求陈氏之子孙立之,官吏耆老皆言‘陈氏无可继者,安南本交州,愿复古郡县。’”[9]于是在当年六月宣布设立都、布、按三司及府州县,制同中原[10],并在胡朝原有政区地名基础上更改部分府、州、县名,如表1:

表1 永乐五年 (1407)所改政区地名
表1反映了各级政区的改名情况,我们还可以根据改名原因分成几类加以讨论:
(一)避讳
中国历代因避讳而更改地名的情况不在少数,明朝设置交趾布政司,同样如此。
1.避国号“明”字。国号是封建王朝的名号,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威,历代皆有避讳。乾隆时期《镇海县志》载:“鄞人单仲友能诗,洪武中征至南京,献诗称旨,因奏本府名同国号,请改之。上喜曰:‘彼处有定海,海定则波宁’,改明州曰宁波。’”明朝设立交趾布政司,制亦效法,如明灵州改为南灵州,山明县改为山定县。
2.避帝王象征、称谓。“龙”、“凤”在封建王朝是皇帝与皇后的象征,明朝设置交趾布政司,把带“龙”和“凤”字的地名基本改换,如龙拔改陇拔,丹凤改丹山等[11],不能说没有特殊意义。这些地名原先应该是越南李、陈、胡朝时期为彰显其皇尊而用的名称,明朝占领安南后,为显示其统治权威,自然要更改。如龙兴府改为镇蛮府,龙眼县改为清远县,龙潭县改为清潭县,丹凤县改为丹山县,龙拔县改为陇拔县,茶龙县改为茶偈县等。“上”在中国古代是对皇帝的敬称,“天”在中国古代代表着至高无上,皇帝称“天子”,即天之子,明朝因此有所避讳。如《明史》载: “陈良谟,字士亮,鄞人。崇祯四年 (1631年)进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庄烈帝虔事上帝,诏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谟。”[12]交趾新定,即改带“上”字地名,如上福州改福安州,上福县改保福县,上路县改路平县,新平府上福县改福康县等。这些地名的更改,一方面体现避讳之意,另一方面也避免名称的重复。改“天”字地名者,如天长府改为奉化府,应天县改为应平县,天施县改为施化县,天本县改为安本县,御天县改为新化县等。
3.避帝室名讳。中国封建王朝,不仅帝王之名是权威象征,不允许他人使用,或省阙,或缺笔,或更改,以避尊讳,甚至连带还要避其未曾做过皇帝的父、祖之名讳。如唐初避李渊父李虎之讳,改虎牢关为武牢关;后梁朱温避其父朱诚嫌名,改武成县为武义县;宋初避赵匡胤父赵弘殷讳,改殷城县为商城县等。明朝占据安南后,把安世县改为清安县,世荣县改为士荣县。嗣德本《大南一统志》卷38载:“(北宁省)安世县,……陈以前县名,属明改清安,……黎光顺复原名。”两处均改避“世”字,我们推测,应该是避朱元璋父“朱世珍”之名,否则无法解释其原因。
(二)美愿
地名通常会表达一些人们的美好愿望,或彰德教,或祈和平,或彰国威。明朝平定交趾后所改地名也体现了这些特色。
1.彰德教。中国历代王朝皆视周边民族和国家为荒野之地、蛮夷之群,中原王朝在占领这些地区后,自然要体现其文化繁昌,广布教化的思想。交趾布政司设立之初,即改一些地名,如宣光州改为宣化州,就含有弘宣教化之意;佛誓县改为善誓县,就意喻向善。
2.祈和平。祈祷和平安定、国泰民安,是中国封建时代表达美好祝愿的主要内容。这类地名的改更在明初的交趾占了大多数。如建兴府改为建平府,布政州改为政平州,古战县改为古平县,上路县改为路平县,左布县改为左平县,独立县改为平立县,安兴县改为安和县,布政县改为政和县等。
封建统治者对于一些新定之地,往往也要更改名称,以表达安边靖远之意,如新兴府改为新安府,安邦州改为靖安州,日南州改为南靖州,统兵县改为统宁县,独立县改为平立县,安邦县改为同安县。
3.彰国威。边疆偏远之地是封建统治的薄弱地带,统治者往往喜欢通过彰显国威来保持安定,这在地名上可略见一二。如龙兴府改为镇蛮府,一方面为了避讳省去“龙”字,一方面所改之名显示了明朝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一种歧视,“镇蛮”即镇抚蛮夷之意;另如把国威州改为威蛮州,“国威”是安南王朝为了彰显其威严的地名,明朝以胜利者自榜,自然要消除其权威,并且以“蛮”相待,改为“威蛮”即是此意。这些地名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不受当地民族欢迎,当明军退出交趾之后,很快就被后黎朝改掉了。
(三)除旧或复古
1.除旧。胡季犛篡夺陈朝王位之后,改大罗城路为东都府,发祥地清化府为天昌府,演州府为灵源府[13]。明朝改东都府为交州府,天昌府为清化府,灵源府为演州府,显然是为了消除胡朝立国的痕迹。
2.复古。一些地名含有复古含义,如费家县改为古费县,杜家县改为古杜县[14],邓家县改为古邓县。诸如“费”“杜”“邓”这些县名可能在陈朝甚至之前就已经有了。近代越南学者邓春榜认为:“明之州县名皆陈时名也,陈史失详耳。”[15]但是明朝在占领安南后更改地名,必定有其特殊意义,如“费”、“杜”、“邓”等地名在陈朝时就已经存在,明朝所加的“古”字,应是对以往的追述,以表达“安南本中国地,复古郡县”的统治思想。交趾初平,统治者没有过多时间去考虑按照越南语含义去更改地名,因为这样很麻烦,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符合,这里用“古”字,仅是单纯汉语意思而已。如九真州的古平县可能就是取唐崇平县 (安史乱前叫崇安县)为名,因为古平、崇平两县均在今越南清化省靖嘉县。此种情况在中国则更多,如宋改添州为“古天 (通‘添’)县”,改故渭州为古渭寨,清改邳州为古邳州,改下邳县为古邳镇,改故蔺州为古蔺州,改故宋水县为古宋县等。现代越南学者陶维英在研究“古螺城”名称来源时认为,越南古代地名中的“古 (Cô?)”字是由“Ke?(个)”变化而来,而“Ke?(个)”字在越南语中常置于另一个字之前以称呼一个村庄的名字,这第二个字常常是指这一村庄的地理或经济的某种特点[16]。然而“螺城”一名,首见于《岭南摭怪》:“筑城半月而就,其城延广千丈余,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唐人呼曰昆仑城,取其最高也。”[17]《岭南摭怪》一书多取民间传说,且成书时间不定,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该书自越南李朝开始,历经陈朝、后黎朝,不断有人补充修改,后黎朝武琼又为此书作序,所以书中的“螺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并不确定。另外较早记载的是《安南志原》一书:“越王城在东岸县,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形如螺也。”[18]由此可知,因为其形如螺,故名“螺城”。以上两种史籍记载皆不言“古螺城”。明永乐间,有孙子良者为人所言谮, “遂坐谪交趾古螺城八年。螺城人素不乐学,公悯其可教,夙夜导之使学,不以已之荣辱婴心,学者化之,多有成者”[19]。这里既提到“古螺城”,又提到“螺城”,显然“古”不是固定称呼,是人们加上去的习惯称谓,可能就是表示“古代螺城”之意。我们赞成陶维英关于“古 (Cô?)”字名称在越南语中最初渊源的解释,但这与明朝更改地名情况不同,不可同一而论。明朝将一些地名同改“古”字,只是为了表示“复古郡县”之意。
三 交趾布政司政区通名研究
越南汉唐以前属中国,自吴权割据、李氏建国,开始逐渐脱离中原王朝。然越南与中国一衣带水,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各种制度均模仿中原王朝, “因而在地名学方面,越南历史上的政区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地名通名,莫不学自中国。”[20]
明朝初平交趾之时,除去所置府、州、县三级政区外,似尚有“镇”之建置。如《实录》载:“永乐六年正月戊辰,设交趾太原、嘉兴、广威、天关、望江、临安、新宁七镇金场局。”[21]“永乐六年六月戊子,…… (新城侯张辅)言:‘交趾旧太原等五镇已改为州,余天关等十三镇未改。’”[22]又载: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壬子,……追至爱母江,得阮帅所遗伪入内检校太傅并义安、新平、顺化三镇骠骑大将军印。”[23]
这些“镇”应该就是陈、胡朝遗留下来的,明朝占领安南后,没有将“镇”全部改掉,而是用其就地安置投降的胡朝官员和将领,一方面以表抚慰,一方面是“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如“莫迪、莫遂、莫远及阮勋冒姓莫者,皆不得志,迎降于明,明并授以官。”[24]“建兴人阮日坚聚众杀镇抚使潘和甫,降于张辅”、“明人以山林隐逸、怀才抱德……搜寻各人正身,陆续送金陵授官,回任府州县,稍有名称者皆应之。”[25]
陈、胡朝“镇”的设置多在重要地区,明朝打败胡朝后进行改制,在当时的形势下,某些镇就地变成卫所,继续执行防御功能,如王颋研究陈朝光泰十年 (1397年)时有宣光、京北、谅山、新安、西平等镇[26],而这些镇的所在正是此后明朝所设卫所的地域范围,如明朝曾设置谅山、新安、新平、演州等卫。我们推测,陈、胡朝一些“镇”与交趾布政司“卫”之建置之间存在着某种转化关系。可能有些“镇”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卫”,而有些则降为更加低级的单位,如清都巡检司等,以致史书中对此鲜有记载。
明朝在安南统治时间不长,加上期间各种反抗势力此消彼长,从未间断,所以明朝在安南的实际控制区仅限于几个据点,即交州、义安、清化、顺化等地,从明朝在交趾地区所设卫所来看,也主要是在交州、清化、谅山、新平、顺化、新安等地,其中交州府设卫最多[27],而大部分地区控制力并不强,基本上是控制在土官手里,而这些土官多是陈、胡朝旧臣,以致会出现黎利揭竿抗明,各地皆蜂拥而反的局面。史载,“帝 (黎利)至东都三日之初,京路及各府州县人民,边镇酋长皆辐辏军门,愿效死力以攻各处贼城。”[28]“时关以东,群盗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盖新设州、县、军、卫太多,交人久外声教,乐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29]如果不是控制力不强,这些地方不会动辄反叛,一反就可以很快围攻到交州府治,所经之地如入无人之境,黎利“命黎篆、黎可、黎秘等领兵二千余人出天关、国威、嘉兴、临洮、三带、宣光等路,掠取其地。……又命黎仁澍、黎备等领兵二千余人出天关、天长、建兴、建昌等府。”[30]对此,明军毫无良策,不是派兵镇压,就是据守城池以待援兵。
由于史书记载不详,对于这些“镇”的建置情况很不清晰,其建置与府、州、县是否有重叠、建制隶属等情况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小结
明朝占领安南后,设置交趾布政司,其所颁布的一切制度规定,无不渗透着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和其自身的特点。
1.安南自李朝独立,凡几百年,尽管已形成独立意识和文化特色,但在某些方面仍然留有中国文化的遗痕,因此明朝恢复对安南的统治后,并未像在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广设羁縻卫所,而是设立交趾布政司,按照内地标准设置政区,而且大改地名,把带“龙”、“凤”、“上”、“天”等字眼的地名基本改换,这一点就与当时明朝其他地区不同,如广西的龙州、陕西的凤翔府、南京的凤阳府等,沿用未改。这可能与交趾地区历史沿革比较特殊有关。
2.交趾布政使司的行政建置和地名更改一方面加强了政区及地名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是一种高压同化政策的实施。张辅在任时,尚能平衡各种势力,“辅凡四至交趾,前后建置郡邑及增设驿传递运,规划甚备。交人所畏惟辅。辅还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将讨之,无功”[31]。但是继任者皆不胜任,且贪污苛刻[32],加之诸多原因,当地人民不断反抗,使得交趾布政司存在时间很短。因此,这一时期政区地名的变动,并没有像其他文教政策一样,深刻影响其文化的发展。后黎朝建立后,所有明朝更改地名全部作废。
3.交趾布政司作为当时管理交趾地区的高级行政单位,与中原地方建置相比,在府、州、县层级之外,还保留有“镇”这一建置单位,这与交趾初平,各种秩序仍然很混乱,很多投降的胡朝官吏就地安置有关,此外就是反抗不断,需要加强防守和管理所致。后来随着形势好转,才陆续转置为府州、卫所、巡检司。
【注 释】
[1]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陆利军:《越南行政地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
[2][3][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5《安南》,中华书局,2000年,第181、182页。
[4]〈日〉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の安南征略Ⅰ》,东京:山川出版社,1950年,第572页。
[5][27]郭红等: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245页、第707页。
[6]《明太宗实录》卷21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1962年,第2156页。
[7][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13,崇祯平露堂刻本。
[8]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251-259页。
[9]〈越〉潘清简等: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12,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第20页。
[10]《明太宗实录》卷6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1962年,第947-952页。
[11]丹凤县,《明太宗实录》误作“丹阳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云贵交趾”篇引《明太宗实录》作“丹凤县”是。 〈越〉阮文超《大越地舆全编》卷5《山西省》载:“丹凤,原丹凤,明改丹山,属慈廉州,黎复原名。”可证。
[12]《明史》卷266《陈良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865页。
[13]〈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60-161页。此三府改名未见于《实录》,疑是永乐五年六月之前已被明军更改。
[14]古杜县,或误作古社县。〈越〉阮文超《大越地舆全编》卷3《乂安省》曰:“香山,李曰杜家乡,属明土黄县地,黎初曰杜家县。”嗣德本《大南一统志》之《义安省·香山县》:“唐为福禄州,李为杜乡,属明为古杜、土黄二县。”可证。
[15]〈越〉邓春榜: 《越史纲目节要》卷3《陈纪》,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220页。
[16]〈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8-40页。
[17]戴可来等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卷2《金龟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18][明]《安南志原》卷2《古迹·城郭故址》,河内:1932年,第135页。
[19][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巻24《参政孙公神道碑》,《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415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5页。
[20]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21]《明太宗实录》卷7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1962年,第1032页。
[22]《明太宗实录》卷8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1962年,第1070页。
[23]《明太宗实录》卷14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红格抄本,1962年,第1720页。
[24][25]〈越〉吴士连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8《陈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刊行委员会,1984年,第489页,第493、496页。
[26]王颋:《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历史地理》第9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6页。
[28][30]〈越〉胡氏扬等:《蓝山实录》,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4页、第48页。
[29][明]丘濬:《平定交南录》,《纪录汇编》第13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8年,第11页。
[31]《明史》卷154《张辅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223页。
[32]陈文: 《试论明朝在交趾郡的文教政策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oponym Changes of An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Guo Shengbo&Wei Chao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
An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Toponym;Chang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Annan followed the ol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ystem of the Chen and Hu Dynasty in Jiao-zhi area.At the same time,Annan carried out a wide range of reforms,which was mainly charactered by the toponym changes.However,this ha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hackles the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oponym first,then does a research on the generic nam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and further,prob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oponym changes at that time.
K333
A
1008-6099(2012)04-0106-06
2012-03-27
郭声波,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魏超,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地理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暨南大学211工程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子课题“越南北属时期政治地理研究”。
【责任编辑:陈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