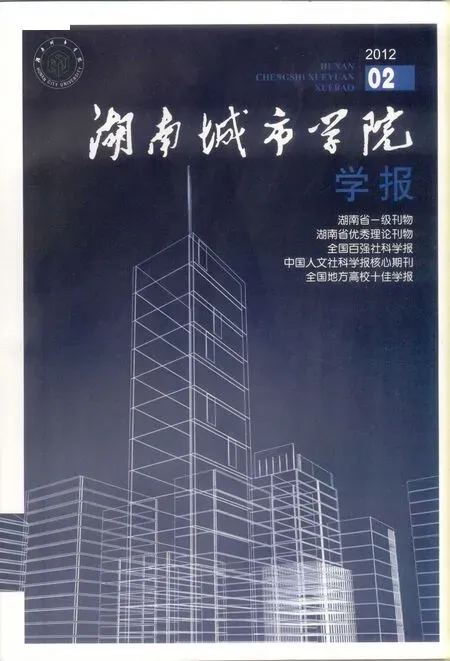《伏藏》的叙事策略及其智慧表达
曾 娟
(湖南城市学院 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伏藏》的叙事策略及其智慧表达
曾 娟
(湖南城市学院 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伏藏》讲述了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作者以悬疑、推理的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藏文化和藏教精神,并选用虚实结合的神奇故事、神秘的传奇人物来展现一段富有冒险的拯救信仰之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藏地叙事方式。作品充分表现了杨志军的叙事策略以及他独特又奇妙的艺术想象力,满足了读者大众的阅读期待。
《伏藏》;神秘叙事;藏文化;西藏精神;信仰
“西藏文化本身有它的神秘色彩,描写西藏文化的作品也很多,很多作家因为西藏的神秘才产生写作冲动,作家在作品中再次营造神秘,最终却越写越神秘。《伏藏》并不是去刻画所谓的神秘,而是让更多人去体会西藏文化的精神高度。”[1]在《伏藏》中,作者传递着一种信息——西藏是一块净土,是信仰的净土,是精神的净土。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我们能找到的不仅仅是西藏文化,也不仅仅是流传下来的藏传佛教,还有人类需要的精神信仰。所以,《伏藏》所叙写的不仅仅是掘藏之旅,也是寻找信仰之旅。为此,杨志军用虚实结合、跌宕起伏的神奇故事和神秘的传奇人物彰显出一种全新的藏地叙事,它“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往往打破叙事逻辑,甚至采取原逻辑思维。”[2]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充分体出了作者独特而奇妙的艺术想象力,满足了读者大众的阅读期待。
一、虚实结合、跌宕起伏的神奇故事
《伏藏》讲述了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作者以悬疑、推理的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藏文化和藏教精神,以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以探险、解密作为叙事动力一步一步揭开历史与宗教的神秘面纱。小说一开始就把一宗凶杀案呈现于读者面前,即以中央民族大学边巴教授的被杀拉开了故事序幕。边巴教授知道如何解开仓央嘉措预言,也就说他掌握了“伏藏”的秘密,所以才被阻止“掘藏”的人暗杀。于是,由这一桩案子引出了众多不同身份的人物:破案的警察、边巴的学生、阻止“掘藏”的宗教势力等。其中香波王子、梅萨、智美的“掘藏”是叙事的主线,他们要继续边巴的“掘藏”事业,解开心中的宗教之迷。而这个过程又是凶险无比、暗藏杀机,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故事在“掘藏”与阻止“掘藏”的冲突中展开,充满了叙述张力。
(一)虚实结合的故事题材
小说故事的整体构架建立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是一个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事。这种题材本身是敏感、现实而又重要的话题,由此,《伏藏》的故事便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生活、贴近了现实。不过,《伏藏》的独特在于作者以人性的眼光审视仓央嘉措,提出了有关仓央嘉措的爱情、家庭及后代的具有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意义的大胆猜想。
首先,就真实性而言,作者善于对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进行描绘,使人们在熟知其普通性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并赋于其超凡脱俗性。如此,读者便可深入地理解仓央嘉措的人性特征及引发有关他的种种猜想。如藏传佛教寺庙拉卜楞寺、塔尔寺、哲蚌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仓央嘉措留下的情歌等等,既真实存在又散发着神秘气息,不仅激发了读者的兴趣,还增强了审美感受。同时,《伏藏》里所提及的历史、人物、寺庙甚至佛像的故事,作者都对其进行了有据可查的详细描述,增强读者大众对西藏历史、藏文化及藏传佛教的真实感受。
其次,就小说的虚构性来说,《伏藏》的主体情节是由许多传说以及历史和现实中的悬疑事件构成。“伏藏”本身就是藏传佛教最大的悬疑,小说中被埋葬与被发掘的“伏藏”,是被视为叛逆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遗嘱;“掘藏”的密码,则是深受藏族人民喜爱且举世闻名的仓央嘉措情歌。杨志军在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进行了神化。此外,小说中还有很多仓央嘉措的故事是无法考证的相关传说,比如玛吉阿米、七人使团、土登朗杰活佛、隐身人血咒殿堂等。小说从这些传说和想象中,给故事附上了一层新奇奥妙的面纱。正因为如此,《伏藏》的叙事便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而这些多样性,除了能激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还能引领人们多角度多侧面地了解伏藏的神秘以及西藏文化的神奇。
(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杨志军从一个真实的宗教行为——伏藏,虚构了掘藏之旅,故事在仓央嘉措的往事和香波王子的掘藏之旅中跳跃,富有历史感、时空感。故事中香波王子、梅萨、智美的掘藏之旅,“隐身人血咒殿堂”骷髅杀手的追杀之路,王岩、卓玛、碧秀的堵截之程,阿若拉嘛的掘藏等,各条线索都以香波王子为主线,条条线索又环环相扣。《伏藏》全部叙事的实现,是在各条线索的千回百转、跌宕起伏之中完成的。
小说一开篇就用一桩杀人案营造了一种神秘气氛,然后在各派势力的纠缠中开始了故事的叙述。新信仰联盟相信“七度母之门”一定是仓央嘉措的遗言,而且遗言饱含了仓央嘉措对自己受难和情人受害的愤怒,是倒出来的苦水,是对陷入权力之争和血腥对抗的政教的失望和诅咒。他们相信本来无懈可击的佛教因为仓央嘉措的存在而有了软肋,他所伏藏的“七度母之门”是佛教留给世界的唯一破绽,一旦昭示于天下,佛教将面对爆炸性的羞辱而无地自容,不攻自灭的结局就在眼前。而在佛教内部,对待“七度母之门”,有多少人赞美就有多少人仇视。赞美派对乌金喇嘛开启“七度母之门”的扬言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佛教的追求始终是圆满,“七度母之门”是最后的伏藏和最高的法门,也是最后的圆满和圣教的根本,所以要发掘,要修炼,要弘扬。他们甚至认为“七度母之门”是唯一可用来抗衡新信仰联盟以及乌金喇嘛的殊胜法门,小说中香波王子、阿若拉嘛就属于这一类。仇视派则相信仓央嘉措遗言是外道之乘、险邪之道,会摧毁圣教形象,决不能让新信仰联盟以及乌金喇嘛的阴谋得逞,封藏、禁绝、毁灭“七度母之门”是保护圣教、延续信仰的必要手段,故事中的隐身人血咒殿堂就属于这一类。这样一来,故事就在这些矛盾中展开,在千回百转之中显现着小说叙事的神秘性。
香波王子在探寻“七度母之门”的过程中,从雍和宫(北京)——拉卜楞寺(甘肃)——塔尔寺(青海)——哲蚌寺、大昭寺、布达拉宫(拉萨),几乎到过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寺院,并且有意识的介绍了寺院的创建背景和佛教圣物。这些空间背景的介绍,不仅向读者展示了大量藏传佛教文化,更丰富了小说的神秘叙事。它不仅是小说的载体,也是线索,更是小说所传达的信仰的寄托。因为庙宇是人们的信仰中心,是人们祈福纳祥、消灾解厄的神圣之地。正如小说中卓玛所说:“从北京雍和宫开始,到了甘肃拉卜楞寺,又到了青海塔尔寺。这是一条什么路线?宗教传播总是有流向的,有人称它为信仰传播带。就好比一条河,它有源头,有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只要不离开这条河,就能从下游走到中游,再走到上游,最后到达源头。”[3]所以《伏藏》中对庙宇的众多描述,使读者在受到感官刺激的同时,也经受了信仰的洗礼,阅读的过程几乎就是朝圣的过程。
二、神秘的传奇人物
《伏藏》的传奇性不仅源于作品中虚实结合、跌宕起伏的故事,还源于小说中塑造的神秘人物,比如香波王子、仓央嘉措。此外还有一些其它传奇人物:为掘藏牺牲的女人,如姬姬布赤、仁增旺姆;新信仰联盟的成员,如卓玛、智美;执意于掘藏的大师,边巴、阿若拉嘛;隐藏于背后的人,如骷髅杀手、珀恩措;追踪着掘藏之路的警察,如王岩、碧秀。这些人物身上的神秘性与悬念丛生、险象环生的情节相结合,彰显出作者的叙事智慧。
(一)人性与佛性相融合的仓央嘉措
仓央嘉措曾是西藏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但在杨志军看来,他给藏传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填补了佛性对人性的忽略,使佛教成为真正的众生信仰的精神。杨志军认为,宗教的终极精神和世俗的最高理想应该不谋而合,它们的彼岸都是“爱”。[1]所以,严厉的宗教和浪漫的仓央嘉措情歌才能在青藏高原上并行,在西藏人民心中共存。
《伏藏》中,仓央嘉措是人性与佛性融合的传奇人物。仓央嘉措首先是一个歌手,其次是一个诗人,再次是六世达赖喇嘛,是神王,是教主。小说以情歌为密码,在整个破译的过程中再现了仓央嘉措悲壮的一生。他是一个悲壮的胜利者,用爱情和情歌把灵魂推向了辉煌与永恒,为此付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权力,甚至生命。就因为他的这些举动,在世俗的观念里仓央加措是一个宗教的叛逆者,但是在小说里,他是把人性和佛性融合在一起的宗教改革家。
仓央嘉措身为宗教领袖人物,敢于真实写出自己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与理想,敢于突破宗教对人性的束缚,敢于大胆向传统势力挑战。在佛教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对传授自己佛法经典的喇嘛,更要毕恭毕敬。情圣仓央嘉措却在诗中真实表达出对佛法和喇嘛的淡漠,而忠诚于对人世生活的热烈追求。如:我修习的喇嘛的脸面,不能在心中显现,我没修的情人的容颜,却在心中明朗映见。那一首首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和谐的优美情诗表达了他对真实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让读者深深折服。他的诗集也被后代藏传佛教及大德们视作参悟修心过程的必修经典。“情歌”成了历代高僧对佛教和藏传佛教精髓的诠释,让人在欣赏情歌、秘传时获得心灵的洗礼。“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实现了佛性与爱情的水乳交融。”[3]仓央嘉措脍炙人口的诗,加上离奇的身世和悲惨命运让作为情圣、诗人的他充满了无尽浪漫与神秘的色彩。
(二)生性风流与信仰高尚的香波王子
香波王子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也是仓央嘉措的化身。他为了开启“七度母之门”,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作为线索,在“光透文字”和“指南”的指引上,踏上了充满险恶的寻找“伏藏”之途。在北京、青海、甘肃与西藏的空间变换与仓央嘉措前世今生的时光流转的交织中,香波王子的掘藏之旅,为我们展现出一幅藏传佛教教义中有与无、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天堂与地狱的矛盾纷争的恢弘画卷。
香波王子生性风流。他高大、英俊、潇洒、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在学校里,没有一次周末舞会不是他在表演,没有一次节日晚会不是他在主唱。他肆无忌惮地张扬着他的天赋,挥洒着他的才情。他是研究仓央嘉措情歌的专家,也是演唱仓央嘉措情歌的歌手。他用完美的表现诠释了一个西藏人的艺术气质。对于爱情他是执着的、疯狂的,他对梅萨的爱情在《伏藏》的情感描写中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香波王子寻找七度母之门,也是寻找他自己的信仰。在小说中,作者对香波王子的刻画充满了神秘感。其一,香波王子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在骷髅杀手、警察的围追堵截当中,香波王子总能奇迹般地逃脱。其二,香波王子的掘藏之路,似乎得到伏藏人的暗中相助,在冥冥之中,香波王子就是那个开启“七度母之门”的人。其三,香波王子学识异常渊博,从他口中叙述出来的仓央嘉措的往事,如同他亲身经历的一般。其四,在众多的巧合之中让读者感受到香波王子与仓央嘉措是如此的相像,香波王子对仓央嘉措的情歌钟爱有加,情歌不仅是他吸引情人的武器,也是他掘藏的杀手锏。此外,香波王子和梅萨就如同当年的仓央嘉措和玛吉阿米,两段爱情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越,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三)其他神奇人物
藏传佛教里有好几个系列的宗教女神,这些信仰女神在世界上其它宗教里面都是不存在的,比如卓玛系列,也称之为度母系列,包括白度母、绿度母、花度母、紫度母、21度母等等,这些度母系列是西藏的女神。所以,小说里面的女性是圣洁、崇高的,具有神秘性。如梅萨,她是“玛吉阿米”在现代的化身,是圣洁的爱情的守护者。随着“掘藏”的展开,每一次解密都会有一位“玛吉阿米”的化身出现,姬姬布赤、仁增旺姆、伊卓拉姆、吉彩露丁、索朗班宗、措曼吉姆,她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千年的等候只为献身于“仓央嘉措情歌”。这是一条让人感到悲伤的线索,却显示出爱的真义。正如张柠所说“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形式,‘掘藏’便是一种信仰追寻的过程。”[4]这些神奇的女性无疑丰富了小说的神秘叙事。
小说还着力塑造了典型的反面人物,如乌金喇嘛。原来的禅定大师,演变成新信仰联盟的恐怖杀人犯。小说巧妙地在开篇埋下伏笔,用一个轮船杀人案,把乌金喇嘛和国际刑警卓玛联系在一起,两者即一人,一个欲颠覆圣教,摧毁全世界信仰的人。边巴老师是发起掘藏的先驱人物,其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他运用迁识夺舍之法化身为山魈,在暗中一直协助香波王子开启七度母之门。除此之外,阿若拉嘛、智美、珀恩措、王岩等人物,他们各自的传奇性增强了小说叙事功能,丰富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
当人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无所适从时,精神是空虚的,道德是低下的,信仰是缺乏的。所以,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信仰缺失成为杨志军写作《伏藏》的重要理由。他认为信仰“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而不是相反。”[1]这是书中贯穿始终的概念,信仰的核心就是“爱”的真义。
《伏藏》洋洋75万字,叙事线索叠加交织,整体结构复杂庞大,然而最终揭示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天上地下,爱情为尊。”[3]在香波王子唱到“那一瞬,我飞天成佛/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喜乐平安”[5]时,我们听到的是仓央嘉措对佛性和人间大爱的深情表达,“伏藏”的谜底此时已不言自明。仓央嘉措将人性和佛性结合起来,将他的信仰追求和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将他的精神高度和我们的日常举动结合起来,这种统一和结合,将他变为世俗和精神不分,在精神高地上他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可以不皈依宗教,但我们不可以不皈依信仰,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6]所以,《伏藏》不仅重现了仓央嘉措一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引领现代人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正因如此,杨志军的写作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表现领域。
[1] 吴晓东.《伏藏》:人不能没有信仰[N]. 中国青年报, 2010-07-27(3).
[2] 曾娟, 王泉.论《藏地密码》的神秘叙事[J]. 天府新论, 2010(1): 142-146.
[3] 杨志军. 伏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70.
[4] 张柠. 当代作家的“边疆”想象——兼论《伏藏》的叙事[N].文艺报, 2010-11-03(2).
[5] 吴碧云.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M]. 于道泉, 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65.
[6] 宋晓嵇. 对仓央嘉措的点滴见解[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4): 34-42.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Fu Cang
ZENG Ju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novel tells a rescue to save the Potala Palace, soul of the story of a hero of faith. In this thesis we are going to decode Tibetan history,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 spirit in a suspect way. Besides, it uses actual situation with the magical story of the mysterious legend to show a more adventurous journey of faith of salvation, to show us a new way of Tibetan narrative. Yang Zhijun’ s works fully reflect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his unique and wonderful art of imagination,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ing public to read.
The Fu Cang; mysterious narration; Tibetan culture; Tibet’s spiritual; faith
I 206.7
A
1672–1942(2012)02–0083–04
(责任编校:彭 萍)
2011-10-25
湖南省社科联立项课题(1011062B);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10C0523)
曾娟(1982-),女,湖南新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