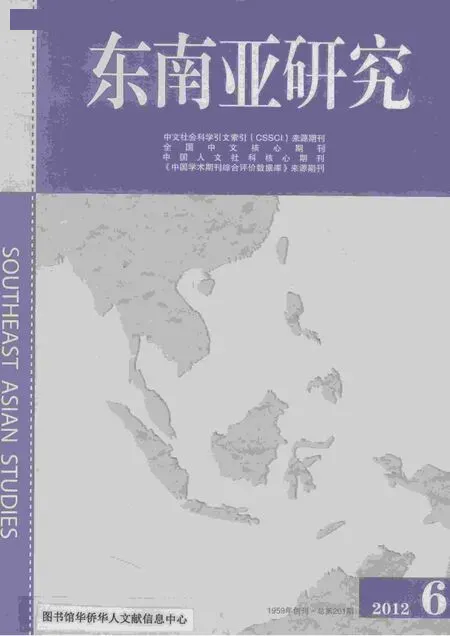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
(美国)周 敏 黎相宜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州510275)
国际移民本身是跨国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当代学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1.54亿上升到2010年的2.14亿,并预计在2050年将高达至4.05亿。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国际移民的新时代”[1],因此,由双向或多向的跨国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移民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2]。
一 单向模式: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与移民汇款研究
国际移民理论与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单向到双向的发展历程。古典国际移民理论和移民汇款研究以往更多地遵循从祖籍地到移居地或移居地到祖籍地的单向流动,对于移民及其迁移、汇款行为进行研究。
(一)从祖籍地到移居地:古典国际移民理论
传统国际移民理论发展分为移民动因、移民过程与移民结果三大研究领域。第一是如何解释跨国人口流动的动因问题。移民动因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论与世界体系论。新古典经济学大多用于解释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问题,包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3]。新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移民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由人际关系产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决策[4]。世界体系论则从国家的层面分析移民动因,强调资本雄厚的、在全球经济中处核心地位的国家对资本贫乏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对跨国人口流动的影响[5]。
第二是关于移民过程的研究。移民系统论指出,移民潮会导致一些较为稳定的移民系统,以推动或制约移民的流向和进程。移民网络理论则认为在持续不断的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网络,进而推动后来的人口流动[6]。组织结构理论指出,国际移民的进程一经开始,便会产生一系列服务于移民的各类私人企业组织、自愿团体和其它非营利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服务于移民的组织进而发展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助于移民取得进入外国劳动力市场机会的组织机构,甚至生成一种移民产业 (migration industry)。因果积累论则指出,每一次的移民行动都为后来的移民决策提供根据,进一步扩大移民的社会范围、改善移民方式、提高移民效率[7]。
第三是有关移民结果的研究,也即移民的社会适应理论,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包括古典同化论(assimilation)、多元文化论 (multiculturalism)、分层同化论 (segmented assimilation)等。古典同化论认为,随着移民在移居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语言和文化的适应、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移民最终将会融入到移居国的主流社会[8]。多元文化论则强调,不同的族裔身份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是难以完全被同化的,移民群体会按照各自独特的文化方式逐渐适应移居国的大社会的文化[9]。分层同化论则指出,当代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的结果是多向而不是单向的,其中包括:摒弃本族裔文化而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的中、上层;摒弃本族裔文化而融入移居地边缘社会的底层;有选择性的同化并利用本族裔资源和文化优势向移居的主流社会融入等三种不同的模式,此理论考虑到不同少数族裔的移民在移居地所处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和在移居国社会分层制度中所处的地位的差异,并强调在特定的条件下,移民的少数族裔文化有助于移民融入主流社会[10]。
(二)从移居地到祖籍地:移民汇款研究
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主要是解释跨国人口流动的因果关系,认为国际移民的迁移是从祖籍地到移居地的单向度、直线性的流动,而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移居地上。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国际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引起了学界对祖籍地的兴趣。有关国际移民汇款研究从这个角度补充了传统移民理论的不足。国际移民汇款研究包括对汇款动机与效果的研究。
针对汇款动机,学术界主要从利他、利己、隐性家庭合约、社会地位等角度进行分析。利他主义理论认为,移民的跨国汇款是为了顾及汇款者的家庭成员在家乡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需求[11]。与利他主义动机相反的是,利己主义理论认为,移民的跨国汇款主要是受个人的经济以及金融利己主义原因的驱使[12]。而隐性家庭合约理论则突破了利他与利己理论的个体视角,将家庭作为主要分析单位。这一理论的立论根据是,移民家庭由移民成员和留守成员组成,移出的家庭成员 (即移民者)和选择留在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建立一种隐性合约,以维护家庭的两地生存的基本需求和共同利益[13]。此外,一些社会学学者则从社会地位的角度分析移民汇款的动机,认为移民汇款是移民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14]。
而针对汇款效果,学术界就汇款是导致依赖还是社会发展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部分学者以研究移民依赖性为重点的微观分析法讨论国际汇款对地方社会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指出汇款促使人口更为频繁的流动从而破坏了传统的地方社会和文化习俗[15]。另一些学者则着重于国际汇款对于原来社区的发展以及克服市场弊病对社区发展 (特别是对原来农村社区的发展)的研究,移民决策和汇款使用方式是家庭生存战略决策的组成部分[16]。关于移民及汇款究竟给祖籍国和家乡的地方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著名国际移民社会学家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颇有见地地指出,这取决于国际移民的流动类型,国际移民短期的循环流动对移出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这是因为回流的移民带回自己的积蓄、资源和专有技术投入到家乡和祖国的建设。但是,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对迁出地社会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永久性的国际移民导致城镇以及整个地区的人口萎缩,减少了侨民往家乡汇款的机会与投资的动机[17]。
二 双向流动:跨国主义与社会发展
无论是国际移民理论还是移民国际汇款理论都过于侧重在移民的祖籍地或者移居地来讨论国际移民的问题。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单向模式的研究框架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人口流动。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方能较为准确地认识其社会影响,较为正确地评价其未来走向[18]。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在移居地建立起新家庭、新社区的同时,与祖籍地保持着频繁而有序的金融、产业、贸易、文化、政治等联系。这种在祖籍地与移居地之间往返的生活方式被学者们称之为“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不仅满足了移民家庭在两地的经济需求,也降低了移民个体无法完全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所产生的不适应感、困惑以及结构方面的歧视[19]。其实跨国主义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但是当代跨国主义在规模、范围、深度、频率以及所带来的多方面后果上都与以往有所区别[20]。
一般来说,跨国主义不仅受到移民个体因素、祖籍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移民在海外族裔聚居区的状况的影响,而且国际移民的跨国主义还会对移民社会地位流动、祖籍地与移居地社会发展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移民个体特征与跨国主义
一般说来,移民个人的人力资本 (例如教育、双语能力、职业技能、公民身份等)以及主要人口特征 (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实践的形式和规模。
现有文献还强调移民群体的社会劣势地位(如在移居国社会遭受种族歧视和结构排斥)或者少数族裔的中间人地位 (middleman minority)对移民跨国主义实践的不同影响[21]。有研究发现低教育程度与低技能的移民会参与到跨国活动中来,他们的跨国实践往往指向祖籍国。他们一般会将汇款定期寄回家乡,用于支持家庭与亲属、购买土地或房子以供他们的跨国生活,或者在家乡开办一些小型的企业。这些方式可以弥补他们在移居国的低廉工资并获得祖籍国的社会地位认可,实现“社会地位补偿”(social status compensation)[22]。
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和有较为稳定高薪工作的移民也会辞去他们的工作而参与到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技能、双语优势以及社会网络来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因此跨国主义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回报最大化并增强了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23]。
(二)祖籍地发展与跨国主义
同时,祖籍国和家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导致了移民群体跨国实践活动模式的不同。比如,当祖籍国还处于工业化与发展程度初期阶段时,移民的跨国活动主要是非正式的贸易。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移民经常往来于祖籍国与移居国,绕过两国的现行法律与国家规定,参与到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中,从两国获得价格以及需求上的优势[24]。
相反,在一些比较发达的祖籍国或祖籍地,跨国活动通常是正式和大型的,包括进出口贸易、跨国信贷以及知识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等,如中国台湾与韩国的移民[25]。这些跨国经济活动对于祖籍国的政策有着积极促进的作用。许多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移民汇款以及经济投资,并将其作为外汇储备、国际贷款以及资本流动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跨国主义也给家庭以及家乡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移民汇款。移民国际汇款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传统的观点。官方报告显示,全球的海外移民汇款流量预计将超过4400亿美元。2010年海外移民汇款最大的移居地为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法国(World Bank,2010)。移民的国际汇款不仅包括用于支持侨眷生活的侨汇和物质,还包括宗教馈赠(religious remittances)、政治馈赠 (political remittances,涉及对于祖籍国平等主义以及政治制度改革)以及社会馈赠 (social remittances,流动于移居地与祖籍地的观念、行为、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资本)等等[26]。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陆续提出了“文化馈赠”的概念[27]。
(三)海外族裔社区与跨国主义
虽然许多国际移民已经在移居国定居下来,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持续地参与祖籍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生活,他们的跨国主义活动给个体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或非经济上的收益,如为自身创造良好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得以经济独立,并在祖籍国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可,等等。
但个体获得的收益并不必然地对其在移居国的族裔社区 (ethnic community)产生相应的收益,跨国活动对族裔社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以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的移民为例,虽然他们有着非常强有力的跨国联系和频繁的跨国活动,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以及社会上的劣势地位[28]。当他们的跨国企业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为个体成员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及对家乡的贡献更大时,对其族裔社区的影响却相对减弱。在纽约,多米尼加移民是最大的新移民群体之一,他们的族裔经济以及移民跨国主义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他们的族裔社区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反而更趋弱化,继续存在着诸多的社会弊病。
相反,华人移民的跨国活动却给纽约的老唐人街带来生机并推动了新唐人街的不断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有大量的国外资本注入以及高技术移民的涌入,许多华人移民是通过跨国主义的参与而获得资本并把资本投入到移居国的社区发展上[29]。
(四)跨国主义与社会发展
国际移民对于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社会发展究竟产生多大或怎样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祖籍国的制度、海外族裔社区的规模以及拥有资源的多少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影响。移民活动对于发展的影响可能只是对地方上的影响,也可能是对整个国家的技术地位以及生产链的改变[30]。
就海外华人移民与中国的情况来说,自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放宽华人移民政策以来,广东、福建两省在“地区倾斜”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从海外华侨华人那里得到了启动经济增长的资本,从而获得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先行一步的优势,也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辟了一条捷径。基于此,从事海外华侨华人、国内侨眷家庭以及跨国主义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从积极的方面来研究移民对于侨乡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探讨华侨华人对侨乡的侨汇、投资和捐赠,对侨乡乡镇 (民营)企业、文化教育、公用设施、医疗卫生、福利事业发展的促进等。在侨乡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形势下,也有学者谨慎地看待华侨华人对于侨乡所带来的影响[31]。这些学者认为,侨乡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具有移民资源为前提而出现的发展模式,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既不能无视华侨华人曾经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发展所作的“特殊”贡献和侨乡的“特殊”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华侨华人和侨乡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推而广之,我们同样需要谨慎对待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是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海外华人移民作为当代国际移民浪潮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走出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的民族主义和乡土情感的旧模式,在国际移民的框架下来探讨海外华人移民与离散华裔所具有的普遍与特殊意义,及其给社会变迁与侨乡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三 未来展望
跨国主义理论在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以及移民汇款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双向流动的研究模式,但这远远不是终点。
从宏观的层面看,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移民跨国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3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如何完善并利用海外移民资源和新型的跨国移民网络。例如,就外派留学生和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方面,中国政府显然已经走在国际前列。过去对留学人员提倡“回”国服务,而现在则强调“为”国服务。现在,中国逐步建立了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和回国创业“三位一体”的海归政策体系,并打造了便于海外华人移民回国或为国服务的各种平台。中国政府还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鼓励海外的高尖端人才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中来①例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计划。自1998年8月实施以来,有效地凝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特别是吸引了一批学术上卓有建树的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从2008年开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施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 (来华)创新创业。。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危机的时有发生、移居国的移民政策转变,这些宏观因素都对未来国际移民的流向以及模式、全球化时代跨国空间形成、跨国网络拓展、跨国化生存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从中观层面来看,国际移民广泛的跨国参与也进一步影响了祖籍地与移居地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国际移民给祖籍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多方争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国际移民的跨国活动为祖籍地的家乡和区域发展与移居地的族裔社区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以及有形与无形的资源,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国际移民的跨国活动有可能造成祖籍地的经济依赖、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分化、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均等等问题的加剧,并且使得移居地的族裔社区的同化问题愈加凸显。以华人移民为例,国内外有关侨乡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提及移民在异国他乡立足甚至有所建树后,总会在返乡时以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向家乡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在非法移民群体众多的地区尤为显著,如福州地区。移民的返乡消费导致了侨乡消费文化与模式的极大变革。而且由于主要劳动力的缺失而形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也在侨乡中逐渐蔓延。这也导致了这些祖籍地的土地价值飙升、房价急剧上涨、生活成本日益增大。侨乡如何能够超越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利用现有的侨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移民的跨国参与在维护传统文化价值、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如何看待以及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仍需深入的思考。
另一方面,国际移民给移居地社会带来的变迁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引起各国关注。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春节期间,仅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累计就高达72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126亿美元 (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②http://news.gog.com.cn/system/2012/02/21/011348893.shtml。如果说中国人的海外消费已足以引人侧目,少数中国富豪在国外的某些行为则更容易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遭致反感。2012年5月12日“中国富豪新加坡驾豪车事件”一出,新加坡民众的排外情绪因这场车祸进一步点燃,社会舆论和互联网上“将中国人赶出新加坡”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称中国侨民为“富豪蝗虫”③http://news.sina.com.cn/w/p/2012-05-16/020824421926.shtml;http://world.kankanews.com/zongheng/2012-05-16/1161048.shtml。这起事件客观上令“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以上种种例子无不引发华人聚居的移居国国民 (包括亚裔)对于“黄祸”的担忧。如果说历史上西方的“黄祸论”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以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那么如今的“中国威胁论”已经超出了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框架,新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遏制中国的公众舆论。因此,在目前中国提倡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以及文化输出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学界对于国际移民以及跨国主义给微观的移民个体、家庭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目前跨国移民研究仍然倾向于认为积极的影响多于消极的后果。最新的研究还乐观地认为,通过跨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移民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困以及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境况,但这一结论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简单地只看单独的结果。例如,双重国籍、海外选举、吸引移民长期投资以及远距离成员资格等方面的政策都给移民与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家庭层面的变化和移民决策的影响则表现在国际汇款是用于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来探讨形成积极或消极后果的决定因素并且考察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国际移民与族群或群体关系是移民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国际移民的涌入无疑会对移民接收国社会的族群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土著印第安人外,绝大多数人口都是近200多年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几乎包括世界所有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或许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是移民国家和多种族国家,先后有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多向分层同化论、新同化论等多种理论及其相关政策探讨不同族群的社会适应模式、族群关系等问题。而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向他国大量输出移民,是一个典型的移民输出国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不仅国内省际和跨地区的流动以及跨国外移的人口数量逐年激增,国际移民向中国移入的人口也在快速增加。例如,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和望京新城等地有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虹桥和浦东出现了欧美高级白领聚居的所谓“国际社区”,广州小北路、广园西路一带正形成非洲人的“巧克力城”,浙江义乌有大量中亚移民聚居的“中东人一条街”。此外,中国北方的青岛城阳区、沈阳西塔街和长春桂林路等地都形成了所谓“韩国城”[33]。这些不同肤色、持不同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来自不同族裔的移民作为他者大量涌入,给当地政府及社会带来了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影响,由此引发的族群文化差异和冲突也给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如何处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却对于涌入中国的国际移民缺乏相关的经验与政策。对跨国移民的排斥和抵触固然是地方社会在走向开放之前的本能反应,但如何妥善地处理国际移民及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族群问题,如何制定一个相对固定与完备的移民政策,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完善以及全方位的移民管理体系,这些既是目前中国政府及社会所面临的普遍社会问题,也是移民研究学者所亟需关注的学术问题。
以上只是我们就国际移民理论和研究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目前研究的状况所提出的一些拙见,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不断提高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研究以及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将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希望与责任!
【注 释】
[1]李明欢:《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2]周敏、黎相宜:《结语》,周敏、张国雄主编,黎相宜、刘进副主编:《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2-410页。
[3]Michael P.A Todaro,“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9,No.1,January 1969.Larry A Sjaastad,“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0,No.5,October 1962.
[4]J.Edward Taylor,“Differential Migration,Networks,Information and Risk”,In Greenwich Oded Stark,ed.,Re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Vol.4:Migration,Human Capital,and Development,Conn:JAI Press,1986.
[5]Alejandro Portes and John Walton,Labor,Class,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
[6]Graeme J.Hugo,“Village - community Ties,Village Norms,and Ethnic and Social Networks: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the Third World”,In Gordon F DeJong and Robert W Gardner eds.,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Microlevel Studi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
[7]Douglas S Massey,“Social Structure,Household Strategies,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Population Index,Vol.56,No.1,Spring 1990.
[8]R E Park and E W 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9]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The Negroes,Puerto Ricans,Jews,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Cambridge:MIT Press,1970.
[10]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Gaining the Upper Hand:Economic Mobility among Immigrant and Domestic Minoritie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5,No.4,April 1992.
[11]S.Bracking,“Sending Money Home:Are Remittances always Beneficial to Those Who Stay behin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15,No.5,July 2003.G E Johnson and Whitelaw W E,“Urban-rural income transfers in Kenya:An Estimated-remittances Fun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22,No.3,April 1974.
[12]Jorge Durand,Emilio A.Parrado,and Douglas S.Massey,“Migradollars and Development: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exican Case”,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0,No.2,Summer 1996.
[13]Michael J.Piore,Birds of Passage: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4]Alison Mountz and Richard Wright,“Daily Life in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Community of San Agustin,Oaxaca and Poughkeepsie,New York”,Diaspora,Volume 5,Number 3,Winter 1996.Leah K.VanWey,Catherine M.Tucker,Eileen Diaz McConnell,“Community Organization, Migration,and Remittances in Oaxaca”,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40,No.1,2005.
[15]Wayne A.,Cornelius and Jorge A Bustamante,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Origins,Consequences,and Policy Options,San Diego:Center for US -Mex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1989.Douglas S Massey,Joaquin Arango,Graeme Hugo,Ali Kouaouci,Adela Pelllegrino and Edward Taylor J.,Worlds in Mo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6]Gordon F.De Jong,Aphichat Chamratrithirong,and Quynh - Giang Tran,“For Better,for Worse:Life Satisfaction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6,No.3,September 2002.Patricia R Pessar and Sarah J Mahler,“Transnational Migration:Bringing Gender I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7,No.3,September 2003.Kenneth D Robertsand Michael D S Morris,“Fortune,Risk,and Remittances:An Application of Option Theory to Participation in Migration Network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7,No.4,December 2003.
[17]Alejandro Portes,“Migr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Politics Society,Vol.8,No.1,1978.
[18]李明欢:《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9]Linda Basch,Nina Glick - Schiller,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Nations Unbound:Transnational Projects,Post 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itorialized Nation States,Langhorne,PA:Gordon and Breach,1994.Steven Vertovec,“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8,No.3,September 2003.
[20]Schiller Nina Glick,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 Szanton,“Transnationalism: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in Nina Glick Schiller,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eds.,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Class,Ethnicity,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New York: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2.
[21]Alejandro Portes,Luis E Guarnizoand William J Haller,“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7,No.2,April,2002.Steven Gold,“Gender,Class,and Network:Social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ransnational Israelis”,Global Networks,Vol.1,No.1,January 2002.Jose Itzigsohn,“Migrant Remittances,Labor markets,and Household Strateg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w-income Household Strategies in the Caribbean Basin”,Social Forces,Vol.74,No.2,December 1995.
[22]黎相宜、周敏: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黎相宜、陈杰:《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3]Ivan Light,Min Zhou and Rebecca Kim,“Trans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Exports in an English-speaking World”,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6,No.3,September 2002.Luis Eduardo Guarnizo,Arturo Ignacio Sanchez and Elizabeth M.Roach,“Mistrust,Fragmented Solidarity,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Colombian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2,No.2,February 1999.
[24]P Alejandro ortes and Luis E Guarnizo,“Tropical Capitalists:US-bound Immigration and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in Diaz-Briquets S and Weintraub S.Migration,eds.,Remittances,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1.
[25]Pyong G.Min,“Filipino and Korean Immigrants in Small Business:A Comparative Analysis”,Amerasia Journal,Vol.13,No.1,1986-1987.Wei Li,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from Chinatown to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Ph 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7.
[26]Peggy Levitt,“Social Remittances: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2,No.4,Winter,1998.Peggy Levitt and Deepak Lamba- Nieves,“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Journal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37, No.1,January 2011.
[27]Juan Flores,“The Diaspora Strikes Back: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mittances”,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Vol.39,No.3,2005.
[28]Luis E.Guarnizo,The Mexican Ethnic Economy in Los Angeles:Capitalist Accumulation,Class Restructuring,and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Migration,La Jolla:Center for US Mexico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1997.
[29]Min Zhou and Susan Kim,“Community Forces,Social Capital,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76,No.1,September 2006.
[30]Alejandro Portes,“Discussion:Transnationalism,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Vol.33,No.4,2011.
[31]程希:《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世界民族》2006年第5期。
[32]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Trans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Mexic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38,No.2,June 2012.
[33]李志刚:《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