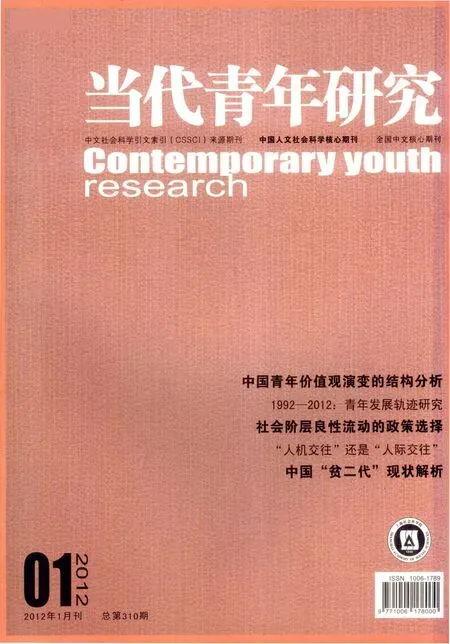青年农民工春节返乡“闪婚”的行为逻辑分析——基于豫西南D村的个案研究
党春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青年农民工春节返乡“闪婚”的行为逻辑分析
——基于豫西南D村的个案研究
党春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基于田野调查,考察了D村青年农民工春节返乡“闪婚”现象,通过对该婚恋模式程序性仪式的展示,力图全面透视当地青年农民工“闪婚”这一婚恋模式的实践背景和行为逻辑,以及在这种行为逻辑背后所彰显的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青年农民工;“闪婚”;代际关系
农村青年大量融入城市务工,在带来城乡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其中“闪婚”是近些年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悄然兴起并日益盛行一种新婚恋模式。王会的研究表明,农村“闪婚”最初是在农村混混群体中开始流行,并受到村民的排斥,随着打工经济在农村的纵深发展,逐渐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盛行并得到村民的认同[1];裴斐、陈建从结构的视角将农民工“闪婚”视为是在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一种挣扎[2];施磊磊亦是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皖北个案农村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结构性动因,认为这种婚恋模式是外出青年务工人员在无奈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苦涩的“理性”选择[3]。笔者试图通过与调查对象的深度访谈,在其生活的现实场景和情景中对豫西南D村青年农民工“闪婚”实践进行社会学考察来分析以下问题:作为正在盛行的青年农民工“闪婚”的婚恋模式何以在传统与现代婚恋模式之间有较大的生存空间?自身经历着再造和重构的青年农民工“闪婚”有着怎样的实践场景与行为逻辑?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透析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这一深刻的农村社会变迁。
D村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以前主要以务农为生,1998年前后,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该村大部分辍学青年进城务工,打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该村在目前中国农村现实中具有代表性。
一、“闪婚”: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行为框架
“闪婚”指青年农民工利用春节返乡的短暂时期(通常为几天到十几天不等),在父母及亲戚朋友的安排下与多位异性“见面”,在高频度的“见面”中快速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选定后男方即向女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礼金以约定婚恋关系,并在短期内完婚的婚恋模式。笔者所调查村落的青年大多选择该婚恋模式,男女双方接触时间短,在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从“见面”到娶亲周期一般为7到15天,很难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婚恋多基于感觉,用调查对象的话说就是见面时“看对眼了就行了”。平时,绝大部分农村青年都在城市务工,没有假期,只有赶到春节才稍有几天的假期,达到本地适婚年龄(17—22岁)的青年男女都会从务工所在地赶回家乡,因而这几天成了青年农民工寻找婚恋对象的最好时期,春节前后会出现大量青年农民工扎堆闪婚。该婚恋模式有着一套仪式化的程序。
第一环节,见面。在“闪婚”婚恋模式中,亲戚朋友承担起值得信任的媒人角色,见面前,媒人一般会把双方的年龄、身高、相貌、家庭等情况告知彼此,亲戚朋友介绍的比较知根知底,会相应减少因时间仓促而无法全面了解带来的“闪婚”风险。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求亲男女居住于对方村中的亲戚朋友往往是促成或拆散一对青年男女的关键人物”[4]。第一次见面,一般由媒人进行简单的介绍,随后男女双方自由交流,时间可长可短,要根据男女双方的感觉而定,若双方感觉好则可能长达几小时,若一方或双方感觉都不好则会寻找借口迅速结束见面。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女方可带自己的家人相男方,男方的家人却不能光明正大地相女方,只能在见面时偷偷躲在一边看女方,否则会引起女方方面的反感。很多青年男女都会有多次见面机会,并从中选择自己满意的异性。第一次见面后,男女双方的家人会询问其子女的想法,同时也会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子女自己手中,然后会把见面结果告知给媒人,若双方都没有意见,则进入第二个环节。
第二环节:换手绢。即见面后有婚恋意向的男女通过互换红色手绢的方式来确定婚恋关系,女方手绢中包些烟、糖果之类的小东西,男方手绢中则要包2000—4000元不等的礼金,视经济条件而定,一般不低于2000元,也即是通常意义上的订婚,换过手绢后的男女原则上不能再通过见面选择其他异性。
第三环节:挑婚节。按当地的说法,也即是换手绢后男方若想“要”女方,则必须到女方家送彩礼以商量结婚事宜。彩礼在当地有一个参照体系,礼物包括烟、酒等10样,每样各10到12件;礼金一般在2至5万之间,有还价的余地。正如古德指出的:“只要存在嫁妆或聘礼制度,自爱婚姻安排过程中就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5],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媒人在男女双方及其家人之间进行周旋,关乎婚恋成败。在礼金之外,女方一般还会提附加条件,如男方要有婚房,若没有,则礼金会提高以作为以后盖新房的资金。调查中曾有一个案例,村里的刘某共有两个儿子,但只有一套房子。按当地村俗,一般由小儿子继承家里的房子,因此大儿子结婚时女方家要求再盖一套新房,但刘某经济上暂时困难无法承担,随后女方要求男方提高礼金数额至7万元,刘某也拿不出,在媒人的调节下送完3万的礼金后又向女方父母打了一张4万元的欠条,才使得大儿子顺利结婚。刘某告诉笔者:“这也没办法呀,若今年婚结不成,吹了,那就只能等明年春节才会有说媒见面的,又要等一年,孩子也大了,早晚都得结,再说明年还不是得要钱嘛。”
第四环节:送条子。根据男女双方生辰八字、属相等相关信息而测定的结婚日子写在一张红纸上,由男方家族里2—3位有头面的长辈送至女方家中。一般来说,不能送“空条”,即要随着条子包上2000元左右的红包,再带一些礼物一起送至女方家中,接下来就可以按风俗到期娶亲了。
对于农村传统婚姻,费老指出:传统婚姻的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抚育,男女个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一桩公众事件……传统婚姻关系的确立却要缔约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履行一番手续,确立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其目的在于使婚姻关系从个人的感情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6]可见,在传统婚姻模式中,婚姻的仪式尤为关键,需要媒人撮合、配生辰八字及完整的迎娶仪式等。另外,媒人在传统婚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人凭其所掌握的婚姻市场的信息资源,在男女之间牵线搭桥,是男女双方婚姻缔结的关键人物,若男女双方父母亦赞同此婚事,则该青年男女的结合就有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因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传统婚姻的代名词。相对于传统婚姻而言,“闪婚”继承了传统婚恋模式中的仪式化程序,抛弃了传统婚恋模式中完全受制于父母之命的弊端,父母只能提供参考性意见,而不能强制个体的选择,婚恋对象完全由个人自主决定,但媒妁之言依然必要,可以说是一种媒妁之言下的自主婚恋模式。
基于自由恋爱的现代婚恋模式并不太注重程序化的仪式,是基于彼此了解、互有感情的基础而建立的婚姻,从时序来说,是先恋爱后结婚。与此相比,“闪婚”下的青年农民工则缺乏一定时间的交往和了解,是基于感觉而草率做出的决定,多是先结婚后恋爱。但“闪婚”亦体现出一种现代快餐文化的特性——追求速度和效率。因此可以说,“闪婚”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行为框架,兼具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元素,这种婚姻形式是其特有城市边缘人身份的一种标识,他们集丢不掉的乡土性和已经接受了的并对自身进行型构的快节奏的城市性于一身。[7]
二、“闪婚”的实践场景与行为逻辑
青年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务工,其生活与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其婚姻却要返回家乡以一种传统仪式来完成,笔者试图通过展示“闪婚”的实践场景,以揭示这一婚恋模式的行为逻辑。
(一)高价的间接婚姻成本:“闪婚”的助推器
依照当地的风俗,只要是“换过手绢”的青年男女,就算正式订婚了,在随后至结婚前这段时间里,每逢中秋、麦罢(农村麦子收割完毕)等节日,男方都要备“四则礼”前往女方家探望,即使青年男女双方都外出务工不在家,男方家长也要前去探望女方家长。每个节日花费至少在500元以上才有面子,不然会被认为不会办事、抠门。落得这样的名声自然会给以后“挑婚节”、“送条子”埋下隐患,甚至在迎娶当日也要受到女方娘家的百般刁难,索要新娘的“上车钱”。为了尽量缩减这种间接的婚姻成本,男方会尽量缩短从换手绢到迎娶的这个时间域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青年农民工“闪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也可算是一种主动的理性选择。
(二)现代婚恋观念及行为下的担忧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大量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并很快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城务工的经历使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现代性有所增强,他们对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未婚先孕等变得宽容,[8]有研究表明男女青年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持“接受”态度的分别占4/5和3/4,再加上青年农民工流动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已经确定婚恋关系的男女青年农民工,在随后各自的外地务工生活中也可能出现变故而转恋他人,要求与原来对象结束婚恋关系,这对男女双方家庭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依据当地风俗,提出结束关系的若是男方,则礼金礼物均不退还,若有女方提出,则退钱不退物),舆论上的压力更是沉重的包袱。毕竟,青年农民工的通婚圈就那么方圆几公里,媒人又是双方家庭都熟悉的人,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很是尴尬。正如彭某所言:“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得很,在外面净乱搞,不结婚是不会老实的,早点把事情办了(指结婚)早省心,万一搞出点事情来,会结仇的,对大家都不好。”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使得本来较为传统的农村接受了“闪婚”这一现代婚恋模式。
(三)适婚不婚的语境及现实压力
农村的父母尽管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但仍会把操办孩子的婚事作为自己对孩子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会通过亲戚朋友等关系网络给适婚年龄的孩子张罗对象。若过了当地适婚年龄还迟迟没有对象,就会引起村里人的议论,被冠以“人品有问题,或条件太挑”的污名,一旦被冠以这样的污名,以后来说媒的人就会很少了,即使有说媒的,其子女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也会降低。另一方面,当地能接受的可以婚配的青年男女年龄间隔一般在0—3岁,若个别青年男女在适婚年龄段内迟迟不婚,就很难再找到年龄适当的婚恋对象。村民李某说:“人家都结婚了,你该结的时候不结,过了这个段,和你差不多年龄的都结完了,你找谁结去呀,年龄相差太多了家里人都不接受,再说,等你想结了,好的早被人家抢走了,你就只能凑合啦,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拿这个凑合。”面对适婚不婚的语境及现实压力,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会想法在适婚时间域内完婚,这无疑加剧了“闪婚”在青年农民工中的盛行。
(四)城市婚姻市场的排斥:无奈的苦涩选择
大量流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青年农民工,依然是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与市民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物质障碍和文化区隔,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也给他们的恋爱与婚姻带来一定的障碍。[9]较为封闭的工作环境和较为狭窄的社交圈子使得他们很难接触到城市异性,被自然地排斥在城市婚姻市场之外。另外,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普遍存在,即使是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城市异性,加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污名也使他们难以受到城市异性的青睐。就农民工个人结婚意愿而言,卢国显的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婚姻选择的逻辑是:地缘关系、外省农民工,最后才是市民[10],这使得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以地缘下的农民工结合为主。
因此,笔者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只是青年农民工“闪婚”的外在因素,婚恋观念的变化及所在村庄的高价婚姻成本与舆论压力才是滋生“闪婚”的土壤,构成了青年农民工“闪婚”的实践场景与行为逻辑。
三、“闪婚”背后是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
“闪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婚姻视为一种个人行为,这就意味着在择偶过程中,个人的认知与情感是决定性因素,而传统意义上的家人参与择偶过程在“闪婚”中被淡化和边缘化了,父母及家庭成员的意见只是作为参考性意见而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
谢某,男,22岁,高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挣的钱一小部分交给父母开支,大部分自己存留。春节回家父母给其张罗婚事,见了几次面,最终相中了邻村一位女孩,但其父母嫌女孩个子不高,性格太弱不爱说话,反对谢与其结婚,但谢主意已定,坚决要找她,父母威胁说若谢找该女孩,彩礼钱他们不出,但谢某还是坚持选择了该女孩,并声称要用自己的钱办婚事,以抗争父母。最终,父母妥协,并出钱帮谢某办了婚事。谢父告诉笔者:“我们那时候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找谁只要父母看着差不多就行了,两个人很难见面,即使见了也不好意思说话,害羞。现在,孩子主意大着呢,刚见个面觉得好就分不开了,天天电话短信不停的,再说了,我孩子还算好的,村东头老范家姑娘,为了嫁人寻死觅活的,搞绝食,做父母的能咋办,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啊,还不是同意了。想开了,谁的福谁享,谁的罪谁受,省得到时候孩子过得不好了还埋怨我们老的。”
林某,女,21岁,父亲较早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出去打工,春节回家,家人介绍对象,邻村的L和远村的H,林某钟情于H,认为H对自己好,什么事都顺着自己,但其母看好L,认为离家近,以后好有个照应,且认为H个子不高,人看起来不怎么样,家庭条件也不如L,担心林嫁过去会受苦,但林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H,并向持反对意见的母亲承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就算将来自己受苦了也自己承受,不埋怨任何人,其母无奈,最终,林嫁给了H。林告诉笔者:“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毕竟我母亲一个人挺孤单的,想我嫁得近一些,可我实在不喜欢L,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我要和他过一辈子的,虽然我也不肯定跟H一起就一定幸福,但至少现在我想和他在一起,只能委屈老人了,好在我母亲还算开明,也不是特别勉强我,伤心了几天就好了,呵呵,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笔者调查中发现不少这样婚姻自己做主的个案,父母开始接受子辈在婚姻等自己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上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这一事实。这种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家庭功能的变迁。在传统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家庭主要是一个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滋生了父权家庭制度,家长掌握着一切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自然在家庭中就拥有绝对的权威,子辈对父辈只能是完全的服从。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权威关系:父母拥有权威,而子女不拥有权威[11]。而在现代社会,大量青年外出务工,农村“非农化”趋势明显,家庭主要不再是一个生产性单位,而变成了一种生活单位,家庭的很多功能都发生了外移,每个个体在家庭之外都开拓出大量的横向关系,有了更多的社会空间,家庭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感情交流的一个载体,父辈绝对权威的经济基础已经失去,其绝对权力的衰落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子辈经济上独立。李东山认为,当个人要依靠家庭获得经济支持时,个人就不得不接受家庭指定的婚姻模式[12],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农村青年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父辈,相反,还可以把自己务工所得的收入拿出一部分资助家里。由于子辈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远高于父辈在家的务农收入,所以,子辈甚至会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提供者,自然在家庭事物的决策上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四、结论与讨论
在D村,绝大部分青年男女都会选择“闪婚”这一婚恋模式来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高价的间接婚姻成本、现代婚恋观念及行为下的担忧、适婚不婚的语境及现实压力以及城乡二元分割下的城市婚姻市场的排斥是当地青年农民工选择“闪婚”这一婚恋模式的实践场景与行为逻辑,这种兼具传统的婚恋形式和现代婚恋内核的“闪婚”模式背后折射出的是农村现代家庭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即“闪婚”这一婚恋模式对婚前与婚后婚恋关系的约束力大为不同。在“换手绢”到举行婚礼这个时间域里,悔婚的事常有发生,笔者曾遇到这样的个案:刘某,女,19岁,打工春节回家在其姑姑的介绍下与王某确定恋爱关系,并迅速准备结婚。但在结婚前一天,与王某及其王某的家人到县城购买衣服时,刘某觉得王某及其家人显得过于小气,下午回家后遂告知王某要结束关系,王某家人以婚宴均已通知亲戚并已准备完毕为由不同意,但刘某坚持悔婚,最终婚事告吹。像这样因小事而悔婚的个案并不在少数,甚至在举行婚礼的当天因新娘“上车钱”谈不妥而悔婚的也时有发生,但村里人却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但是,一旦举行过婚礼,婚姻却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鲜有离婚的,并不像媒体及其他学者研究报道的“闪婚”导致闪离。在该村落,同样是基于很短时间接触而建立的关系何以在婚前极不稳定而在婚后却极为稳定呢?在接受现代婚恋观念的青年农民工身上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来解释婚姻的稳定似乎是说不过去的,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村落规范在支撑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王会.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J].南方人口,2011(3):10.
[2]裴斐,陈建.农民工“闪婚”——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挣扎[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4):74.
[3]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动因分析——以皖北村为个案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8(12):14.
[4]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4.
[5]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85.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2.
[7]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动因分析——以皖北村为个案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8(12):13.
[8]靳小仪.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8(9):24.
[9]凤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1):59.
[10]卢国显.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的实证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3):38.
[11]张杰.“闪婚”与“啃老”——80后理性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J].青年研究,2008(3):36.
[12]李东山.工业化与家庭制度变迁[J].社会学研究,2000(6):34.
责任编辑 裘晓兰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Logic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Flash Marriage when Returning Hometown during Spring Festival——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D Village in Henan
Dang Chuny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in D village,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lash marriage phenomena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flash marriage when they return hometow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Through demonstration of the ceremony of flash marriage,the paper scans comprehensively the practice background and behavior logic of the flash marriage model and inquires into the transition of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in rural family with the rising of right awareness of Filial Generation and the declining of parental generation behind the behavior logic.
Young Migrant Workers;Flash Marriage;Generation Relationship
G112
A
1006-1789(2012)01-0028-05
2011-10-28
党春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