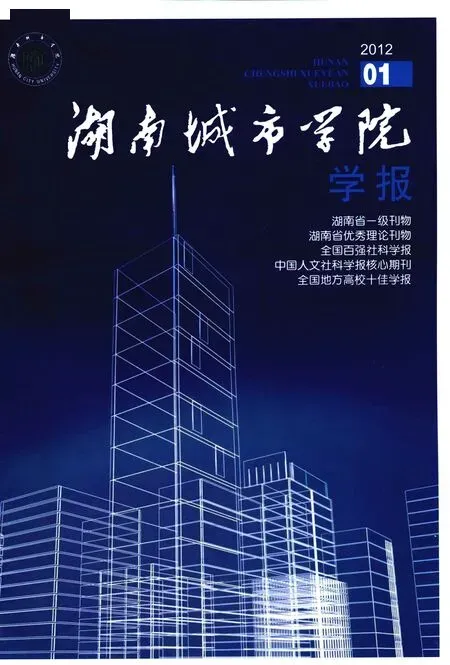中国古典园林中“隔”的艺术
刘堂春,张 婷
中国古典园林是一部感性地打开的美学史册,含茹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和美学思考,通过一系列物质性构件,创造出无数可以畅神悦意的精神家园。隔的手法,就是实现园林旨趣的重要手段。
一、隔以求静
园林审美,需要有相生相应的心境,从而使园林意境向审美主体生成。这种接受心境,金学智把它概括为闲、静、清、和。[1]其实,闲、清、和均可归属于静,或者说生发于静。静与噪相对,人往往由于外界的喧嚣或利害关系的干扰而内心浮躁。老子的“涤除”、庄子的“心斋”“坐忘”、宗炳的“澄怀”、刘勰的“澡雪精神”、郭熙的“林泉之心”大都着眼于摆脱功利观念的束缚,使内心澄净空明,以实现对道或审美客体的观照。只有内心虚静,才能与对象形成亲昵、融和的审美关系。摆脱功利观念的扰心自然是最主要的,隔绝人工物理声光,也利于主体心趋宁静。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说:“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这“尘嚣缰锁”,主要指隐性的利害关系,也含显性的具体噪音。陶潜欣然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是主体“养素”高境界的产物,对芸芸众生而言,人世的车马喧哗是很难充耳不闻的。
(一)墙垣隔阻
中国园林除了要创造使人们“窥谷忘反”的城市山水以外,还突出了园林“望峰息心”的“澄怀”功能,隔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中国园林往往筑于闹市,成为士大夫文人怡情养性的精神净土。要闹中取静,隔园外的尘喧,最有效的方法莫如四周围以墙垣。黑格尔在论建筑艺术时曾说,房屋“要求有一种完整的围绕遮蔽,墙壁对此是最有用最稳妥的”,“墙壁的独特功用并不在支撑,而主要地在围绕遮蔽和界限”。[2]可见,墙垣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隔。沈德潜在《勺湖记》这篇园记中写道:“屋宇鳞密,市声喧杂,而勺湖之地,翛然清旷……”园外是万户鳞密,市声喧嚣;园内则是翛然清旷,泉石幽静。这种判然有别的景象归功于园墙的遮隔作用。
(二)入门奥如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凡入门处必小委曲,忌太直。”这基本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建造的模式。宗白华先生曾比较中西方园林的不同特征,他指出:中国的园林就很有自己的特点。颐和园、苏州园林以及《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都和西方园林不同。象法国凡尔赛等地的园林,一进去,就是笔直的通道……中国园林,进门是个大影壁,绕过去,里面遮遮掩掩,曲曲折折,变化多端,走几步就是一番风景,韵味无穷。[3]
宗先生是从审美角度来谈的,其实,中国园林入门处设置影壁,路径曲折,即创造奥如空间,还有另一重功能,就是阻隔城市的尘嚣。为了不让外面的尘嚣流进园内,所以入门处一般不设虚敝的旷如空间。拙政园一进园门(指中部原来的腰门),迎面一座黄石假山挡住视线和去路,要入园,就得绕道假山西侧的小径。这种奥如空间处理,有类于《红楼梦》第十七回关于大观园的描写:“开门进去,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奥如空间有利于推阻外来的声光,酿造幽静的氛围,创造类似建筑学中的“灰空间”。那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们,在人口处就收敛心神,洗涤尘襟,抚平创伤,进行心理的净化,居尘而发出尘之思。
二、隔以达深
如果把隔以求静称为“移我情”,那么隔以达深就是“移世界”。宗白华先生指出:“‘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4]
中国古典园林常以隔的手法来“移世界”,通过花木、山石、屋宇等具有遮隔功能的实物,使园林的意境空间景深化。这种隔不是完全封闭,而是隔中有透,古代园记中谓之“亏蔽”或“蔽亏”。如“左右皆林木相亏蔽”(宋·苏舜钦《沧浪亭记》),“逾杠而东,篁竹阴翳,榆槐蔽亏”(明·文征明《拙政园记》)“蔽”相当于隔,即挡住视线,使之无法通过;“亏”则相反,是指视线未被遮隔尚可透漏。隔而不隔,透而不透,似隐还显,似浅还深,恍惚变幻。
钱钟书先生说:景物当前,薄障间之,若即而离,似近而远,每增佳趣。……近世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谓艺术之善写后景者,得光影若明若昧之秘,犹花园围以高篱,外人睹扶疏蓊蔚,目穷而神往。[5]
所谓“若明若昧之秘”,就是“善写后景”,就是“花园围以高篱”。由于隔体是高篱而不是全蔽的围墙,蔽中有亏,隔中有透,亦隔亦透,花园—— 后景便呈现出“望而难即,见而仍蔽”惝恍迷离的神秘感、幽渺感、深邃感。高篱的“薄障”效应,创造了花园的景深空间,丰富艺术意境的层次,使之隐然可爱,姿媚横生。
这种手法在中国艺术中更为普遍。宗白华说:中国画堂的帘幕是造成深静词境的重要因素,所以词中常爱提到。韩持国的词句:“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况周颐评之曰:“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静而见深。”董其昌曾说:“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他们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6]
“帘幕”是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从实物的功能看,帘幕就是一种薄障。因为是障,所以具有一定隔音作用,有利于形成比较静谧的环境。又由于其薄,对光线既蔽又亏,既隐又显,使景境幽深玄邈,有似于“窈兮冥兮”(《老子》第二十一章)的“道”的境界,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的极高追求。无论是词或园林,都重视以具有蔽亏功能的隔体深化艺术境界,只是隔体不同而已,词以帘幕为隔,园林以花木、山石等为隔。
济南趵突泉周围,一带拂地的绿柳,柔条千缕,婆娑随风,其疏密之间不断露出无数大亏小空,使被遮掩的厅堂、亭廊、桥泉若隐若现,若明若暗,这颇能给人以依稀朦胧,如烟似雾之感,创造出“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蝶恋花》)的园林佳境。
以上主要是一种静态的隔,中国园林还创造了一种动态的隔。这是通过园林路线设计来实现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最贴切地体现了中国园林路径的美学理念。据金学智考证,该诗句中“曲径”一词,唐人所撰诗集中均作“竹径”,宋代以后换为“曲径”的愈来愈多了。[7]语词的流转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曲径”孕育的美学意蕴认识的深化。
园林中的曲径,其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创造了曲线之美、变化之美,更在于把人指向“幽”“深”的境界。正如中南海“大圆镜中殿”对联所描述的:“芝径缭以曲,云林秀以重。”秀然而深的园林意境,离不开萦回曲折的路径设计。
三、隔以致远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说:“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他总结出自然山水美的两种类型:一是廖廓旷达之境,一种是深婉幽静之境。它为以后园林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依据,即追求奥旷交替的空间组合。在某种程度上说,隔以达深是为创造奥如空间,中国园林还常常通过“隔”以形成旷如空间。
旷如境界与“远”密切相关。中国人关于“远”的观念,可追溯到老庄对“道”的阐发。老庄认为道是宇宙本体,是一种具有“高”“大”“渊”“深”“远”“无穷”“无极”特征的无限境界。它大大激发了中国的文人、艺术家挣脱有限和对无限境界的追求。后来,北宋画家郭熙进一步从美学角度提出“三远”说(“高远”“平远”“深远”),“三远”把道的无限境界落实到具体的登山临水以及艺术创作之中,道的可体验性、可表现性大为提高,于是使“远”的观念更深入人心。深远构成奥如境界,高远、平远造就旷如境界。下面着重讨论以隔的手段创造园林平远的旷如境界。
要在有限的园林里表现出平远,莫过于选择遮蔽物较少的水面。中国园林除了北方皇家园林能提供一望无际的水面外,私家园林囿于规模很难与之比肩。但是江南园林通过隔的手段,同样创造出水面视觉莫穷的旷境。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云:“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郭熙的话启迪了造园家。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园冶·立基》中说:“疏水若为无尽,断处通桥。”“桥”是水面空间的隔体,其目的是为产生“无尽”的视觉效果。文震亨在《长物志·水石》中提出园林水面的创作理想:“石令人古,水令人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具体做法就是在《长物志·广池》所描述的:“凿池自亩及顷(百亩),愈广愈胜。最广者,中可置台榭之属,或长堤横隔,汀蒲、岸苇杂植其中,一望无际,乃为巨浸。”通过“台榭”“ 长堤”“ 汀蒲、岸苇”等隔体(亏大于蔽),创造出“一望无际”的旷如空间。
隔的方法很多,或筑堤横断水面,或跨水浮廊可度,或涉水点一步石,或凌空架桥,或杂植苇草,都是“疏水若为无尽”的隔的手法。拙政园的池水设计就是典型。劝耕亭小岛与东岸、小岛与香雪云蔚亭大岛之间架有石板小桥,荷花四面亭小洲南、西两面与池岸间置以石板曲桥,在空间上虽有隔断之感,却隔而不断,愈隔愈远。
通过长期的园林创作实践,中国的造园家们懂得了隔与不隔的辩证关系,懂得了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以隔的物质手段(实)实现精神的自由遨游(虚)——静、深、远。而静又是达到深、远的前提,所以入门即奥。而“‘远’就是‘玄’,‘远’就通向‘道’”,[8]288叶朗先生所说的“远”就包括高远、深远、平远,深远、平远即本文的深、远,都是玄,也通向道。如果把“静”换成“涤除”,把“深、远”换成“玄”,园林就是形象的“涤除玄览”(《老子》第十章),可以说中国园林是老子“涤除玄览”的形象演绎。由此看来,叶朗先生把中国美学的源头归之于老子是独具慧眼的。[8]20中国古典园林隔的艺术传承了道家精神衣钵,在狭小的城市空间里,开辟出让人“神飞扬”“思浩荡”(王微《叙画》)的精神乐土,以满足人们对无限的宇宙本体(道)的追求。
[1]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0:577.
[2] 黑格尔.美学:第 3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65-67.
[3] 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文艺研究, 1982(2):63-65.
[4]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6.
[5] 周振甫, 冀勤.钱钟书《谈艺录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127.
[6]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26.
[7]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0:451.
[8]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