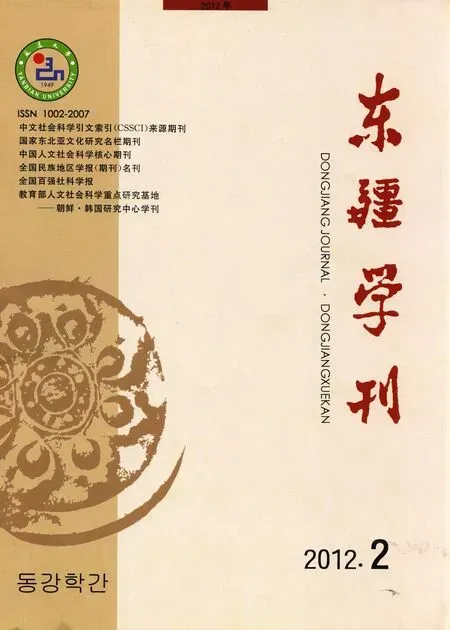在历史跨度和爱情长度之间——评《云水谣》情爱叙事类型创新的得与失
李红云
在历史跨度和爱情长度之间
——评《云水谣》情爱叙事类型创新的得与失
李红云
《云水谣》的情爱叙事类型为中国当代电影增添了创新性的要素:一是采用了大跨度的历史背景来强化情爱叙事的长度和深度;二是将单一的情爱叙事场景复数化,从而创造出“世纪爱情”的奇观化。但是,《云水谣》也没有逃脱“特色即缺憾”的当代电影探索的悖论,油水分离的爱情和历史导致了情感与时空的脱离和割裂,复数化的电影类型停滞于老套镜头的拼贴。《云水谣》在情爱叙事类型创新方面的得与失,将成为中国爱情片探索过程中的珍贵标本。
《云水谣》;情爱叙事;类型
2006年《云水谣》的上映,打破了由古装武打大片《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营造的内地电影市场的“主流”,进入了所谓“以大片终结大片”的时代。但时至今日,《云水谣》情爱叙事类型的创新重新被淹没于层出不穷的类型影片之中,对于它的得与失,似乎再也无人关注。本文拟就《云水谣》在情爱叙事类型创新的特点与问题方面进行探究,以期为中国电影的情爱叙事类型研究增添一个经典案例。
一、“世纪爱情”类型的创造
对爱情震撼力的图像呈现,是情爱片一直追求的目标。激烈的情爱冲突、复杂的情爱心理与矛盾、有情人终究未成眷属的落寞和痛悔等,都曾是以往中外电影所演绎过的经典题材。当代电影,除了在这些叙事要素上大量汲取文学经典作品中的情爱刻画之外,在自己擅长的范围内,还开拓了图像与情爱呈现关系的视野,让“伟大的爱情”变成可以跨越千载、一览无余的图像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坦尼克号”式的情爱类型,把一段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安置在一次震惊世界的沉船事件中,从而借助这一“包孕性的时刻”[1](112),在极其狭小的时空中展开对情爱自由最大限度的荡气回肠的“再现”。另一种可以称为“世纪爱情”类型,即在相当大的历史跨度中,展现一种坚贞不渝的情爱关系,时代的巨变考验并锤炼着一对男女对爱的坚守、期待的情爱品格,使整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经由一条或者几条不断延宕的情爱线索的贯穿,体现出一种对爱情品质的检验和证明,然而它往往会在奔到一个情爱伦理的终端时戛然而止。这两种形式,成为当代电影情爱片类型化生产的主要形式。很明显,《云水谣》的电影叙事策略属于后者。从影片叙事的历史长度来看,它横跨了60多年的历史阶段,以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叙事,通过无数次闪回,呈现出了陈秋水和王碧云两人跨世纪的漫长爱情悲剧。正是这巨大的历史跨度,使这部影片一方面不断延宕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另一方面也加浓了电影情爱叙事的力度。
当代中国电影不乏爱情情景剧,在绵延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展现刻骨铭心的爱情主题也屡见不鲜。从《庐山恋》到《天云山传奇》,从《芙蓉镇》到《山楂树之恋》,爱情均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氛围而受到强化,让我们为“过去”的爱情唏嘘不已。但是,与之不同的是,《云水谣》把这一爱情的“背景”大大拉长了,以至于历史的长度成为了《云水谣》爱情制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60年历史时空的拟造,为王碧云坚贞不渝的爱情守候提供了天衣无缝的心理背景。当与前来辅导弟弟英语的台湾医科大学学生陈秋水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王碧云已经忐忑地开启了少女的爱情之门,同时也开始了宿命般的无望的爱情期待。在这个生活优越的牙医家庭里,陈秋生的闯入及其两人迅速发展起来的爱情成了王碧云生命的全部,从此,她再也没有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她的一生全部汇聚成一个等待的意象。实际上,影片设置的叙事者就是晚年的王碧云,甚至晚年王碧云还以一种现在时态把这一爱情故事继续到了最后,从而再度完成了王碧云作为一个等待意象的全部历程。“初恋”在20世纪40年代末,“等待”在陈秋水避免政治迫害之后杳无音信的岁月,“寻找”在海峡两岸互不相通的艰难时日。半个多世纪,王碧云始终怀着对陈秋水的渴念,照王父的话来说,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漫长的等待与寻找中,王碧云柔弱的病体、几乎神经质的抽签占卜、四处打探消息、拒绝别人对她的无限等待,与她对陈秋水的一往情深、期待到死的决心和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等待的长度、不断变换的空间,伴随沧桑的历史,一步步强化了女性主人公坚贞不渝的情爱品质。从台北到浊水湖畔,从家乡到异乡,从内地到台湾,从美国到大陆,前后几十年,王碧云的爱情追念一次次让观众流下感动的泪水。漫长的历史跨度,大陆一个个风云激荡的历史阶段,都在衬托着一片永不改变的情感。其中,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场景的展现,也都反衬着王碧云对没有“生活”的爱情的矢志不渝。这是影片着力为王碧云烘托出来的漫长的历史镜头,这些图像片断之间的断裂或延续,无一不形成王碧云的爱情底片,而王碧云奔跑在心灵的恒定历史图景中。跳动的历史,在王碧云这里,成了论证她坚贞爱情的证据。在这里,历史的长度就是爱情长度,爱情的长度就是历史的长度,甚至比历史更长。
二、复数化的电影类型
除了采用大跨度的历史来呈现一场“伟大的爱情”,《云水谣》还创造了一种将多种电影类型进行叠加和杂糅的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视觉效果。本片的总制片人韩三平说:“拍摄《云水谣》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类型片进行多样化的探讨。”这种意图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按照电影类型的划分,《云水谣》的所有镜头融合了纯情片、苦情篇、战争片、异域片、革命历史片、怀旧片等电影类型的要素,企图创造出一种观众“要啥有啥”的类型片的新样式。如此繁复的影片类型要素的交迭、转换,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吁求。
在20世纪40年代末台北与浊溪的城乡对照中,影片演绎出一段穷小子与富小姐的恋爱故事。这组镜头可以说是对情爱片中纯情类型的有意模拟,其中两人相爱的障碍性因素来自王碧云的父亲。为了呵护这一类型,连他们爱情的阻碍者——王父——也没有被处理成粗暴的形象。相爱之后即分离。陈秋水和王碧云最后的分离是因为陈是左翼分子,受到缉捕必须逃离台湾,这正好满足了王父的想法。影片侧重刻画两人分离时王碧云的无限牵挂和坚贞的爱情誓言,这些将在情节的进展中受到考验。这一分离情节也是情爱片中司空见惯的,并没有多少想象力可言。但这一情节的设计又包含了一个“革命+恋爱”的经典套路,同时为王碧云漫长的等待提供了恰当的“理由”。风雨之夜,在政治阴霾的气候中,革命者的逃离与爱情的生死分离合二为一,这时候,观众的情感再次被激荡起来。分离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王碧云一往情深甚至变本加厉地思念、寻找爱人并因此终身不嫁,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场景和叙事抒情的要素。真正对观众形成震撼的是由王碧云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品质:坚信自己终于能够等到心爱的人,同时拒绝追求者漫长的等待,满世界打听爱人的消息,以至于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此后,在历史变迁的每一个关口,王碧云无尽的等待都成为电影里最揪心、最痛苦、最绝望的情感氛围。这些镜头和情节完整地构成了一部苦情戏。这场苦情戏跨越了时代,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现场。陈秋水化名为徐秋云,作为军医参战的情节,既交待出两人分离后陈的去向和活动,同时也开始了王金娣和陈的爱情,增添了陈秋水和王碧云两人爱情的考验性要素。当然,战争题材也以增加男主人公形象内涵的方式为影片增添了吸引观众的一个砝码。顺着陈秋水在大陆生活的历史线索,并增强陈秋水作为“老左翼”的立场,遵从上级命令“援藏”是陈必然的选择,同时这一段西藏生活又为影片提供出了异域题材的电影类型。更重要的是,陈秋水和王金娣的爱情在此结合,也在此殒灭。影片不无用心地设计了两人结婚的奇特桥段:王金娣更名为王碧云,在新婚之夜,王金娣洒酒祭奠,表示替王碧云一生守候陈秋水。两人的哭吻,在影片里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内涵:一方面肯定了两人爱情的道德性;另一方面为陈秋水放弃王碧云做出了辩护。这种真实而令人动容的爱情与王碧云的等待意象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刺激了观众对陈的道德审判,也为观众同情、接纳两人的爱情做出了合适的场域铺垫。最后,就像《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采取年迈的主人公追忆往昔岁月的方式一样,《云水谣》同样采取了这样的叙事策略,通过移居美国的晚年王碧云(部分通过其养女晓芮)的追忆来完成故事叙述,同时使得这部影片也带上了怀旧片的浓厚色彩。而怀旧片的类型,对于一场苦情戏而言是必须的,或者说是恰到好处的。
《云水谣》在营造色彩美学方面颇下功夫。对每一个主题类型,影片都确立了与故事相匹配的鲜明的主色调,从而使影片获得了恰如其分的色彩效果。比如,在浪漫初恋的场景中,在浊水湖畔的湖光山色与艰辛的农村劳作中,蓝天白云下,庞大的水车旁,身着白蓝海军学生服的王碧云由恋人依偎在身旁,注视着面前的画架。这是穷小子和富小姐烂漫爱情的典型场景。美轮美奂的初恋场景,暗含着因为出身、地位等因素而受到阻挠的爱情发展线索,同时为可能出现的悲剧起到了鲜明的反衬作用。再比如,战场场景的主色调是土黄色,解放军的军服、战场上的黄土等构成了战争场面的苍黄、惨烈和混乱,紧张忙碌的动作、惨不忍睹的伤体以及徐秋云过度的劳累等,和王碧云寂寞而漫长等待的台湾的沉闷暗色形成了对照,强化了两人极其不同的生活状态。同时,王金娣作为两人爱情的考验因素,带着青春活力闯入了徐秋云的生活。至于以后的西藏异域风光,当然也采取了典型的雪域高原的白色、蓝色主调,并与台湾的暗色形成了对照。不断转换的时代图景和地域图景,依靠一种可以称为“时代主色调”的色彩美学设计贯穿起来,各种主色调的相互碰撞,对观众形成了一种富于历史感的视觉冲击,而在这不断转换的色调中,作为情感基调的陈、王两人的心理状态也被展示出来。
《云水谣》叠加、杂糅了这么多的类型化的情节,融汇了多重可对比或反衬的艺术化了的时空,从而以琳琅满目的多类型的综合创造出一场具有史诗般的伟大爱情。
三、纯粹的爱情与历史的割裂
影片的特色往往会成为其最大的缺陷,这是当代中国电影突出的悖论特征,遗憾的是,《云水谣》也没有逃脱这种悖论。以历史的跨度来强化爱情的长度和强度,以多重变化的时空来构建多重类型化从而增强影片的视觉效果,是《云水谣》成功的类型创新。尤其是前者,能够将漫长的当代史背景化,作为一场伟大爱情的社会历史底片,而不是相反,这是以前的中国爱情片中所没有的。但是,恰在这两个方面,《云水谣》又体现出了纯粹的爱情与历史之间的断裂。
首先,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陈秋水和王碧云的爱情故事,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迁,这一叙事模式的确强化了王碧云执著的爱情里程,强化了她对爱人的追寻以及追寻中的苦辛和坚贞,并一次次撼动了观众的心灵。直到作为叙述者之一的王碧云的晚年,她才由侄女晓芮那里知道,陈秋水的儿子就在西藏,并从即时通讯上看到了他。从王碧云一直在为陈秋水做画像的情节可以看出,她对陈的爱还在继续。对王碧云而言,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历史跨度,如果没有这一种“考验”,王碧云的形象内涵就会大打折扣。影片正是利用了相当大的历史跨度,才能够把这些类型有机地杂糅在一起,从而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同时增加了作为一个故事系统的诸多看点。但是,两人的爱情太纯粹了,纯粹的和那漫长的历史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这样,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就无法进入他们的爱情,或者说他们的爱情中没有熏染社会历史的丝毫内容。伟大的爱情、人性从来都离不开坚实的沧桑历史的支撑。可《云水谣》中油水分离的爱情和历史,导致这场伟大的爱情徒有虚表。
其次,电影类型的杂糅和组合,当然能够构成一种系统的力量或多点透视的视觉效果,但是这种力量和效果还得来自单元自身焕发的魅力。如果每一组镜头缺乏创新性的思索、想象和设计,那么,被整合起来的情节系统就会在一阵伤怀地感叹后重新暴露出其斧凿之痕,甚至矫揉造作。《云水谣》类型探索的缺陷正在于此。所有类型片都是针对一部分特定观众的,其风格、题材和价值观念具有统一协调的程式。正是因为《云水谣》企图通过类型整合来满足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特定观众的心理需求,才导致了影片在处理每一种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关系时出现了生硬而且没有更好创意的弊病。如果把其中每组镜头所勾勒的“类型”拆开来,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类型都是“老调重弹”,无论是初春般的初恋故事,还是生离死别的场景;无论是被动语态中的女性坚贞,还是男主人公的另寻新欢(影片对此做了最大限度的辩护);无论是大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各个历史阶段的图像模拟,还是朝鲜、南京、西藏、台湾等地历史状貌的再现,除了以爱情为线索,遵循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贯穿起来之外,很少有真正的类型创造。影片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类型的营构上,却在每个类型单元上都显得有些苍白。这样,实际上,“各取所需”的“特定”的观众只是从各自的视线里看到了一张张模糊而面熟的“类型”复制,并不能产生“要啥有啥”的意图。[4](29)
正如路易斯·贾内梯所言:“决定在艺术上是否优美的不是类型,而是艺术家如何很好地利用这种形式的程式。”[2](223)由于在每一个类型上并没有很好地在“先例”的基础上做出开拓性的构思,《云水谣》在视觉美学上的探索也只能在静态模拟的程度上停滞不前了。为了加强历史的真实感,惯用的电影技巧是在剪辑中加入黑白片的“资料”类镜头,体现电影“记录和揭示具体的现实”[3](39)(历史),以符合电影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云水谣》的历史跨度极大的叙事时空中,如何处理每个历史时期的图像及其色彩,成为这一类型影片的一个关键问题。《云水谣》色彩处理的简陋之处在于,除了个别黑白片的运用之外,在设计每个时代的典型背景上虽然下了功夫,但是这种“复原历史”的镜头基本上是对以往同类镜头的简单复制,这毕竟是肤浅的,同时这些“历史”镜头并没有和情节的发展形成“互动”的镜头效应。
以历史跨度展示爱情长度的情爱片,实际上是在风云变化的时代更迭中,通过塑造主人公的人生风貌,来强化主人公的情爱主题。时代的代际关系越分裂,主人公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漩进时代漩涡,其程度越大,主人公的情爱品质就越发被阐发得婉转、曲折、悠长,也越发会被演绎得或深邃或坚强或残酷或凄美,从而使漫长的情爱呈现为历经考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并同时产生一种娓娓道来的论证品格,进一步强化受众被故事攫取心理同化的观看效应。《云水谣》在这方面走出了可贵的一步,它的缺陷和不足或许对这一类型的爱情片的继续探索不无益处。
[1][德]莱辛:《拉奥孔》,《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
[3][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
[4]王成:《从“今文学”囹圄中走出来的诗学奇葩——晚清诗学演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
F062.2
A
1002-2007(2012)01-0051-04
2011-11-26
李红云,女,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评论与声乐教学研究。(淄博 255079)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