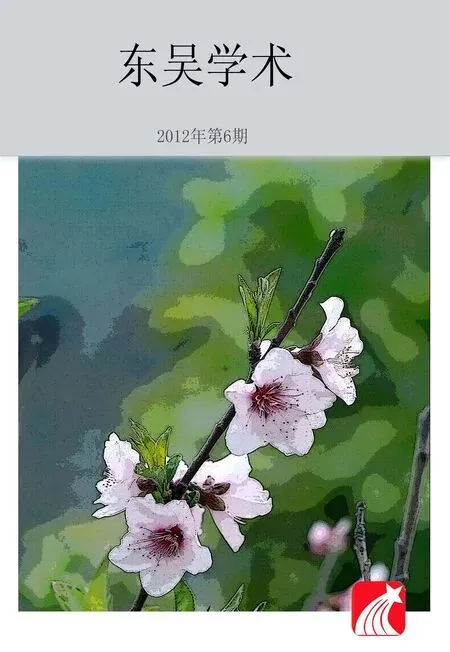雅俗的对峙: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三次历史斗争
余夏云
魏绍昌说,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或“鸳蝴派”)和新文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它们在长达四十年的历程中,“和平共处,互不侵犯”。①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第47页,香港:中华书局,1990。其实,历史远比这个判断复杂。我们知道,五四之后,它们之间就有过多次论争,而且往往是新文学主动出击,批判旧文学,指摘它的是非。鸳蝴派倒是抱着不予理睬的态度,依然故我地写它的美丽文章。虽然偶有回应,那也不过是寥寥数语,聊备一格。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来看,所谓的雅俗之辩,不过是美学上的不同选择,但在新文学人士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们以为这中间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前者为新,后者为旧。而他们要做这样的评判,恰恰就是为斗争策略的需要。旧文学是坏的、死的、僵硬的文学,所以五四起事,就要统统革命。为此,不同美学取向的文学斗争也就由此拉开序幕。这里我依据范伯群在八十年代所划定的三个历史阶段,①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第11-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补充、酌选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论争材料来做历史的回顾,意图还原现代文学场域内的真实占位格局,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人所谓的“雅俗高卑定位”是如何逐步生成,并固结的。
一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革命时期,这主要是指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它包括了文学革命的酝酿、发生以及持续高潮。在这段时期内,许多五四的前驱先行参与了论争,而那时(一九一九年之前)鸳蝴派的名称并未真正出现,但它已经独步文坛,所以批判也总是含糊地采用“当今文坛”如何如何的措辞,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九年钱玄同发明鸳鸯蝴蝶派这个概念为止。
一九一四年程公达在《学生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撰文《论艳情小说》,对当时风行的鸳蝴言情小说予以指责。他说:“近来中国之文士,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以放荡为风流,以佻达为名士。”“纤巧之语、淫秽之词,虽锦章耀目,华文悦耳,有蔑礼仪伤廉耻而已。”在程看来,鸳蝴小说“败坏风俗”,无功于世道人心,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是一种毒害。②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480、51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随后一年,梁启超也在《中华小说界》上发文《告小说家》一篇,表达了他对以鸳蝴为主潮的小说界的不满和失望,以为整个文坛令人惨不忍睹,作品遗祸青年:
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黯者濡染于险诐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窬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公。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③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480、51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追随梁启超,一九一六年李大钊(守常)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近代西方文艺界以新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促进社会进步,而“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他以青年德意志的文明光彩来比照中国文坛的现实黑暗,认为鸳蝴小说与新民的国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驰。④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710-71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接着是胡适对鸳蝴派义正词严的攻击。他说 “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像“《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价值,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⑤阿英:《晚清小说史·晚清小说之末流》,第19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除了斥责鸳蝴作品品质低劣之外,胡适又极言其质量粗糙:“全是不懂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⑥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3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新文学的先锋们尽管骂,可鸳蝴的名士们还是如痴如醉地写、踟蹰满志地编。在一九〇九-一九二〇的这十年间迎来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发展的第二波。鲁迅说,这是“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大概也就是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这两年前后。就目前不完全的期刊统计数目来看,仅一九一四年就有创刊杂志二十四种,一九一五年十三种。⑦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1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这些琳琅满目的杂志在创刊时就明确标举娱乐、消闲的趣味主义文学观。王钝根和陈蝶仙在《游戏杂志》第一期(一九一三)的序言中说:“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霸称王,一游戏之局也。”①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许啸天夫人高剑华女士所编辑的《眉语》一刊,在创刊词(一九一四)中亦是开门见山地表示该杂志是闲暇之伴、寂寞之友:“璇闺姊妹以职业之暇,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纳凉赏月话雪,寂寂相对,是亦不可以无伴。”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
鸳蝴的经典杂志《礼拜六》,其出版赘言(一九一四)中更是开诚布公地将卖点导向消遣,宣称: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③范 伯群 、芮 和 师等 编: 《鸳 鸯蝴 蝶 派文学 资料 》, 第 4、8、7、6、5、12、4、8 页 。 标 点系 笔者 所加。
其他的像什么“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④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野老闲谈之料,茶余酒后,备个人消闲之资”、⑤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⑥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等等,无不标举趣味、休闲之说。尽管这些方面可以看作是鸳蝴的主要特征,但它仍有一面有待我们记忆,即其追随梁启超的 “新小说”理论而展开的舆论转圜。这部分论述往往紧密地联结在“趣味”、“休闲”之中,大有古时候“寓教于乐”的意思。比如《游戏杂志》的序末有这样的婉转语:
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名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读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标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名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且今日之所谓游戏文字,他日进为规人之必要,亦未可知也。⑦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
而《眉语》宣言中亦不失这样的意思:“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以未始无感化之功也。”⑧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4、8、7、6、5、12、4、8 页。 标点系笔者所加。
另外,像徐枕亚、李涵秋这些偏写感伤情调的鸳蝴作家,又哪一个不曾信誓旦旦表示过“小说是为改良社会之一助”、“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支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⑨转引自郭延礼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第326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之类的豪言壮语。这些表面上看仅仅是追逐“新小说”理论的时髦之语,却也正是鸳蝴作者善用“场感”来减轻自己文学主张阻力的聪明举动。至少在用轻松愉快招徕读者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安抚那些旧式文人,使其以为文学也不总是一无是处的。
当然,这样的措辞确实掩过了那些冬烘道学的耳目,但对于五四的新文学而言,国事蜩螗,岂容笑谑,于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些“寓教于乐”、“寓教于恶”(王德威)的篇目和言论又统统遭受了挫折。其中最主要的抨击就集中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这两年,因为其时的 “黑幕书”⑩此处所说的“黑幕书”与鸳蝴作品中的“黑幕小说”有本质区别,不可混同,讨论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226-229页。已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一九一六年上海 《时事新报》、《报余丛载》一栏刊登“黑幕大悬赏”的征文启事,“务乞以铸鼎象奸之笔,发为探微索引之文。本本源源,尽情揭示……共除人道蟊贼,务使若辈无逃形影,重光天日而后已”。起首,揭黑是以改良社会为宏愿,用意纯良,但谁知此风一开,便从此不可收拾,连续二十五个月,“日无间断”,导致黑幕泛滥,许多龌龊不洁之事也竟相借此风混杂鱼目:“夫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校,则直曰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校耳;卖淫书直曰卖淫书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事易时移,黑幕已经变质,其恶劣习气使得教育部也不得不下文告诫,希望其见好就收,最后事情终以《时事新报》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头条发布“裁撤黑幕栏通告”而告一段落。①这一段历史见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221-224页。文中两处引言分别见第221、226页。
其后的故事就是,刚刚登上文坛不久的新文学欲借批驳此事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同时趁机打压横亘文坛已久的鸳蝴派,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文学地盘,争取必要的读者。这其中首先发难的是钱玄同。其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一九一九)的文章《“黑幕”书》,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名称,更是詈责“‘黑幕’书之贻毒于青年,稍有识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书为一种不正当之书籍,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艳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皆是”。他认为这些文类之所以甚嚣尘上,那是与袁世凯的专政、复辟潮流脱不了干系的:“清未亡时,国人尚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国成立,反而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23-824、717-718、720 页。虽然钱玄同并未主攻鸳蝴,而只是裙带连及,但他一出手就为它扣上了一顶 “政治帽”,这实在不能不说是间接将其推上了道德大不韪的境地。
钱玄同之后,鲁迅发表《有无相通》,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发表《论“黑幕”》和《再论“黑幕”》二文,志希(罗家伦)则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等。这些文章仍主攻黑幕,并顺批鸳蝴。因此,鸳蝴在这次被批过程中始终是处于敬陪末座的位置。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几乎通篇谈论黑幕,而并不涉及鸳蝴;倒是志希的讨论,在黑幕之外,提到了“滥调四六派”和“笔记派”。他说前者“这一派的人只会套来套去,做几句滥调的四六,香艳的诗词”,辞藻匮乏,结构千篇一律,代表就是徐枕亚、李定夷等人的言情作品。他说,批判这类的作品,“把我的笔都弄污秽了”。③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23-824、717-718、720 页。同前两人的批判姿态不同,鲁迅是本着规劝的态度来写《有无相通》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完全有能力凭着自己的才华“译几页有用的新书”。所以,他希望“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④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23-824、717-718、720 页。
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所进行的这场批判中,鸳蝴派并不是新文学重点批判的对象,它总是被顺带提及,而且由于鸳蝴的概念并没有被广泛地采纳,所以总是以对个别作家、作品或含糊其词的“当今文坛”如何如何的用语来进行,因而显得有些火力不够集中,并未引起鸳蝴方面的重视。当然,最重要的是鸳蝴本身发展势头正猛,虽然五四崛起给它带来了一定冲击,但毕竟远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严重地步,而且为了避开五四摧枯拉朽式的尖锐锋芒,鸳蝴抱持着不予理会和不应理睬的态度,照样我行我素地去编撰各类以移情逸乐为尚的报刊杂志,试图用读者来维护自己独步文坛的一尊地位。
二
鸳蝴派与新文学的第二次交锋主要集中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的这十年间。它上起茅盾改组《小说月报》,下至三十年代黎烈文接编《申报》副刊《自由谈》。这十年一改从前新文学独唱专场的形式,而变为双方的你来我往,冲突不断。几乎就是这十年,斗争双方基本确立了其在文学场域中的占位格局,而变得意义非凡。
从一九二〇年茅盾参与《小说月报》的编辑开始,到第二年元月,他正式走马上任,全权接编《小说月报》,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新文学与鸳蝴派的梁子由此结下,并于随后全面爆发。茅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这顽固派就是当时以小型刊物《礼拜六》为代表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①茅盾:《回忆录 (三)》,《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5月。
一九二一年一月,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出版,上面刊载了于同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业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中的“游戏”、“消遣”等字眼,显然是针对鸳蝴而发。因为不久前创刊的 《游戏新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又一次明白无误地使用了“游戏”两字,并在发刊词中极言消遣之乐:
今世何世,乃有吾曹闲人?偶尔弄翰,亦游戏事耳,乃可以却暑。岁月如流,凉飙且至,孰能知我辈消夏之乐?盍谋所以永之,余曰:无已,装一书册,颜以游戏,月有所刊,署曰:新报,不亦可乎?众曰:善……堂皇厥旨,是为游戏,诚亦雅言,不与政事……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14页。标点系笔者所加。
而与茅盾等人的文学研究会及其宣言针锋相对的是,在这年的三月十九停刊将近五年的《礼拜六》一声炮响,又复刊了。而且在其一〇三期的《编辑室》中明确写道:“本刊小说,颇注重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以极诚恳之笔出之。”③转引自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254页。这一措辞显然是要与文学研究会所说的文学 “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叫板、抗衡。
茅盾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鸳蝴派的压力,在这一年八月给周作人的信中,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上海谩骂之报纸太多,《晶报》常与《小说月报》开玩笑,我们要办他事,更成功少而笑骂多;且上海同人太少,力量亦不及。④转引自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第5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关于这段故实,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中予以了证实,他讲:
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实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为已。可惜这一类的文字,现在也收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⑤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这些郑振铎所不能寻找到的文字,就是茅盾文中所说的《晶报》开的玩笑,此类玩笑包括了寒云(袁寒云)的《辟创作》以及寄尘(胡寄尘)的《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前者明明白白地批评新文学是“一班妄徒、拿外国的文法、做中国的小说、还要加上外国的圈点、用外国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闹得乌烟瘴气、一句通顺的句子也没有”,而且其矛头直指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文章说:
海上某大书店出的一种小说杂志、从前很有点价值、今年忽然野心起来了、内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创作、所谓创作呢、文法、学外国的样、圈点、学外国的样、款式、学外国的样、甚至连纪年、也用的是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还要老著脸皮、说是创作、难道学了外国、就算创作吗、这种杂志、既然变了非驴非马、稍微有点小说智识的、使决不去看他、就是去想翻他、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顶多看上三五句、也要头昏脑涨、废然掩卷了……
文章最后还说,“如果都照这样做下去、不但害尽青年、连我国优美高尚的文字、恐怕渐渐都要消灭哩”。①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寒云的这些论调可谓是和新文学来了一个以牙还牙。而更甚者是寄尘的后一篇小说,极尽挖苦之能事,讲一个新文学作家被强盗抓去后,如何丑态百出地宣讲“奋斗”和“改造”,并在被放后又如何在同伴面前邀功自夸,讲自己成功地改造了强盗,使其觉悟。②范 伯 群、芮 和师 等 编: 《 鸳鸯 蝴 蝶派 文 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小说讽刺了新文学那些所谓的崇高政治理想,不过是纸上谈兵、痴人的梦呓,不切实际。
为了对这些冷嘲热讽来一次有力的还击,文学研究会专门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 《文学旬刊》,并在上面撰文回应。郑振铎说:“《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他们而发的。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污蔑的话。”③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这些文章包括了郑振铎(西谛)本人的《思想的反流》、《新旧文学的调和》、《血与泪的文学》、《消闲?! 》、《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叶圣陶(圣陶)的《侮辱人们的人》等二十余篇文章。
而其他一些发在别的杂志或报章上的文章,如鲁迅的《“一是之学说”》、《所谓“国学”》、《名字》、《关于〈小说世界〉》,茅盾的《“写实小说之流弊”》、《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反动?》,以及郭沫若、李芾甘等人的文章都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学保卫战。
在这些人当中,郑振铎身先士卒,他撰文《悲观》、《“文娼”》等,对鸳蝴文学进行定位,并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文娼”和“文丐”。他认为时代“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人们的灵魂被扰,心神苦闷,因而“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④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对于郑的批评,鸳蝴人士不但不予辩解,反以“文丐”自豪,认为“靠着一支笔拿来生活”并不可耻,反倒“比着自己做了某小说杂志主任,在化了名,译了小说,算是北京来的稿子,要支五块钱一千字的,我觉得还正大光明得多啊”。⑤范伯群、芮和师等编: 《鸳鸯蝴蝶派 文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
此外,叶圣陶还曾针对鸳蝴“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一句大加挞伐,认为“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无论什么游戏的事总不至卑鄙到这样,游戏也要高尚和真诚的啊!如今既有写出这两句的人……这不仅是文学前途的渺茫和忧虑,竟是中国民族超升的渺茫和忧虑了”。⑥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170-171、171-173、733、177、729 页。
通过以上的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尽管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鸳蝴多有不满,但批判并未上升到郑振铎所说的“严正的理论”高度上,它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性的评判。在理论方面做的较好的其实是李之常和沈雁冰。前者《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在直陈鸳蝴小说的种种是非后,明确提出了文学的功用 “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绝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⑦转引自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第56、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而为了实现这些功用,就必须以“自然主义”作为当前文学的基本规范:
中国底病的黑暗的现状,亟待谋经济组织底更变,非用科学的精密观察描写中国地多方的病的现象之真况,以培养国人革命底感情不可,非采用自然主义作中国今日底文学主义不可。中国文学采用自然主义是适应环境。⑧转引自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第56、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同李之常的观点相近,且又更进一步的是茅盾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七期上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篇檄文:
……引用了《礼拜六》第一百零八期上所登的名为 《留声机片》的一个短篇小说(未点作者的姓名)作为例子,用严正的态度,从思想内容以至描写方法,做了千把字的分析,然后下了判断:“作者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所以他们虽然也做了人道主义的小说,也做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而其结果,人道主义反变成了浅薄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的穷困反成了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了。”又批评他们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封建思想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
这篇文章,义正词严,不作人身攻击,比之称他们为文丐、文娼,或马路文人者实在客气得多。但也许正因为是词严义正的批判,不作谩骂,必将引起“礼拜六派”小说读者的注意,以及同情于此派小说者的深思,故“礼拜六派”恨之更甚。他们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①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茅盾:《茅盾全集(34):回忆录一集》,第 208页,叶子铭校注、定稿,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这施压的后果正是茅盾的离职和商务又衍出一个《小说世界》来专供鸳蝴使用。对于此事,茅盾曾和王统照等人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拟文予以嘲讽和批判,小题为《“出人意表之外”之事》。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页。
事实上,让茅盾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出乎意料的事情,不光来自鸳蝴,同样也来自新文学内部。尽管彼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因着“文学为什么”的问题而酣战不止,但茅盾等人还是不能理解其对鸳蝴姑息纵容的做法。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道:
当时,同样使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创造社诸公的大多数对于鸳鸯蝴蝶派十分吝惜笔墨,从来不放一枪。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曾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狠狠地开了一炮。③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页。
由此可以看出,鸳蝴派和新文学的第二次交锋虽然深入而持久,但其牵涉的新文学面显然要小过第一次。在上一次,新文学的左、中、右各部都投入了火力,但这一次更多的是左翼力量在发挥作用,他们着力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
新文学来势汹汹,通常的看法是鸳蝴派就此吃了亏,变得一蹶不振,而其实,却是它的不甘示弱,越挫越勇,迎来了通俗期刊小说的第三波高潮。一九二一年创刊的著名报刊不下十种,一九二二年又办十五种,一九二三年十七种,一九二四年十余种……生生不息,滚滚向前。④孔庆东:《1921:谁主浮沉》,第18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他们成立青社和星社,专以“吃喝玩乐”为结社方式,每月小聚,吟诗作赋,颇有一些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一本正经、照章办事的文学组织抗衡、捣蛋的意思。青社的社刊《长青》,虽然时日不久,但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倒是清清楚楚的:《止谤莫如无辩》。⑤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239-241页。这篇文章虽然看不到了,也无从知晓这“谤”字到底何指,但我们却可以借其他的一些文章看出点端倪。这些文章多数都发在张枕绿所编的《最小》报上。比如胡寄尘的《消遣?》、《一封曾被拒绝发表的信》,张舍我的《批评小说》、《创造自由》、《什么叫做 “礼拜六派”》,楼一叶的《一句公平话》,毕倚虹的《婆婆小记》,听潮声的《精神……原质》,等等。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表明,鸳蝴是本着“井水不犯河水”和“公好馒头婆好面”的态度来看待此次批判的,他们同样也希望新文学方面的作家“不必把新旧的界限放在心里。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里”。⑥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页。“大家平心静气。破除成见。细细搜求一些对方高深优美的作品来看看。便自然知道都误解了。他们所不同的。只是一点形式。那原质是一样。也有好也有坏呀。”⑦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页。
胡寄尘还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不是党同伐异,而是要自由竞争,最终的优劣存亡,应当让历史自己去做抉择。他讲:
……前清初行邮政的时候。并不曾将有的信局(即民间寄信机关)一例封闭然后再开设邮政局。只将邮政局办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久之终必要消灭。又如上海初行电车。并不曾禁止人力车马驶行。然后行电车。只将电车的成绩办好了。人力车马车自然要减少了。久之终必也要消灭。改革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呢。⑧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51-854、237、181、183、181 页。
尽管胡寄尘句句在理,可惜这毕竟是一场斗争,这样“委曲求全”的方式不免有些天真了。新文学阵营内的宋云彬也曾主张用此法对待鸳蝴,但旋即遭受责难:
(宋云彬)先生说:“我们不必怕《礼拜六》式的‘瓦釜雷鸣’,我们但教把自己的‘黄钟’敲得响。”我们以为不然,因为若在“文字”两字立脚点上说,《礼拜六》简直不配称为文学作品,他根本的不能成立,何论高低,便无所谓“黄钟”与“瓦釜”之分了。①转引自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第46-47页。其实,鲁迅的观点也是同胡寄尘、宋云彬的相近的,见其《关于〈小说世界〉》一文,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858-859页。
可见新文学方面是绝没有“平等竞争”的意识的,他们想除之而后快,所以胡寄尘的这封信“曾被拒绝发表”。
与胡寄尘等人的低调姿态不同,亦有像袁寒云式的盛气凌人,毕竟他是一代贵胄,说话难免有些傲气。他的《小说迷的一封信》,挖苦新改版的《小说月报》是看也看不懂,卖给旧书店的不要,送给酱鸭店做包装纸,老板还要嫌上面的字太臭。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174-175页。又与这两种斗争方式都不一样,且更为高明的是范烟桥。这位鸳蝴派的十八罗汉之一:
……曾在一九二七写过一册堂而皇之的《中国小说史》,追流溯源,把民初以来便盛行不衰的鸳鸯蝴蝶式通俗小说正式纳入中国本土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大书《玉梨魂》和《广陵潮》的承前启后,同时只字不提五四以来方兴未艾的新文学,也算是给新文学运动健将们针对鸳鸯蝴蝶派发出的种种责难攻击一个不卑不亢的回应。③唐小兵:《蝶魂花影惜纷飞》,《读书》1993年第3期。
一个批,一个应,尽管方式千差万别,但最终是谁也没有胜过谁,倒是那新与旧的界线被清清楚楚地画了个分明。而沿着这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斗争的双方把这场没有完结的战役延伸到了三十年代的舞台。但那里时有战争的炮火,所以情形又更为复杂。
三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武侠小说的热潮引发新一波的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泯于战争的硝烟,大致也是十年的时间。其间,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一瞥》、《伪自由书·后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瞿秋白发表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论大众文艺》、《财神还是反财神?》、《学阀万岁!》、《吉诃德的时代》,郑振铎发表了《论武侠小说》、《文学论争集·导言》,沈雁冰发表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钱杏邨发表了《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等文章参与批判。
从一九二二年起,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后更名《红玫瑰》)连载,边写边刊边出书,经过六个年头,到一九二八年全书一百三十四回才告完成”。④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第153页。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市民阶层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 “武侠狂潮”。这个狂潮据说历廿年而不衰,“一直热到一九四九年”。⑤袁进:《鸳鸯蝴蝶派》,第120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而根据小说第六十五回至八十六回内容改编的电影 《火烧红莲寺》,在放映时,更是场场爆满,电影院里叫声、掌声一片。茅盾目睹盛况而撰文《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文中说:
一九三〇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以下,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同时国产影片方面,也是“武侠片”的全盛时代;《火烧红莲寺》出足了风头以后,一时以“火烧……”号召的影片,恐怕也有十来种。
……
《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如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彩……
从银幕上的《火烧红莲寺》又成为“连环图画的小说”的《火烧红莲寺》实在是简陋得多了,可是那风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灭……在没有影戏院的内地乡镇,此种“连环图画小说”的《火烧红莲寺》就替代了影片。①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 第 841-843、841、838、835-836、795-796、812页。
鸳蝴的这股“武侠狂浪”着实是激起了茅盾等左翼人士的极端不满。他批评道:“一方面,这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另一方面,这又是封建势力对于动摇中的小市民给的一碗迷魂汤。”②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 第 841-843、841、838、835-836、795-796、812页。而郑振铎则认为:“武侠小说的发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在收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③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页。同上述观点近似,瞿秋白的文章《吉诃德的时代》还提出,武侠小说不仅会造成“济贫自有飞仙客,尔且安心做奴才”的愚民思想,更会使得“梦想者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作青天大老爷,当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④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页。认定武侠小说百害而无一益。这些文章主要是站在阶级论的基础之上,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对武侠小说予以了批驳,并没有真正就文学而论文学。
同左翼方面一味的攻讦谩骂不同,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保持了必要的客观态度。他对鸳蝴既作批判,也示肯定。文章高屋建瓴,回顾了二十世纪初鸳蝴兴起和变迁的具体情形及模式,将它当作历史上一个真实的现象来处理,并批评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说: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是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一个战斗者,我认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⑤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页。
可以说,鲁迅的态度是公允的,他并未仅仅将鸳蝴看作是一文不名的新文学敌人,而是自己传统的一部分,是一个可以团结的同路人。面对抗敌御侮的严峻形势,鲁迅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联合战线,号召全国的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在倡导联合的同时,鲁迅也强调“在文艺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⑥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第841 -843、841、838、835 -836、795 -796、812页。一九三五年十月,《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宣言上列名者二十一人,包天笑、周瘦鹃也在其列,王稼句说:“这并不是‘恩赐’,而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自觉,表明抗日救亡的决心,共赴国难。 ”⑦王稼句:《关于鸳鸯蝴蝶派》,《十月》2007年第3期。
从上面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此次争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斗争双方既有纠葛又有团结。但总的说来还是斗多于和的。比如,就在宣言发表的当月,郑振铎便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里批斗了鸳蝴,他说:
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处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地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恰和林琴南辈的道貌岸然是相反。有人谥之曰 “文丐”,实在不是委屈了他们。①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805页。
此外,瞿秋白针对鸳蝴也发表了各式议论,但由于过于散乱,容易为人忽略。范伯群教授将其归纳为五,我这里摘要转录如下:
一、他提出了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思想实质是“维新的封建道德”,是“改良礼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二、瞿秋白还批判了鸳鸯蝴蝶派的“笑骂一切的虚无主义”……指出的就是那种鸳鸯蝴蝶派中“赶潮流”者的“命不可不革,也不可太革”的论调,是起着消极的历史作用,实际上是障眼法,有利于摇摇欲坠的现制度。
三、瞿秋白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接受白话的问题上虽然并没有与新文学营垒进行斗争,但他们之废除文言主要是受市场公律的支配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作品是“草台班上说的腔调”,是“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他们就是“运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话……来勾引下等人”,其作用也是很恶劣的。
四、在讨论“大众文艺”时,瞿秋白指出:我们左翼文艺不大善于运用大众文艺的体裁,而鸳鸯蝴蝶派却巧妙地运用了。结果是,他们反倒可以“到处都在钻来钻去,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见它们的狗脚爪的”……鸳鸯蝴蝶善于利用旧有的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庸俗的思想内容……
五、瞿秋白从理论上批判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主义”,以趣味而达到消遣的目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写作信条。②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第24-26页。
除了鲁迅、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就鸳蝴的整体特征作出评介和批判外,亦有人对具体的鸳蝴作家和作品提出批评,比如钱杏邨的《上海事变和鸳鸯蝴蝶派文艺》、夏征农的《读〈啼笑因缘〉》,就对张恨水、徐卓呆、顾明道以及小说《啼笑因缘》等提出了严正指责,认为他们是“封建余孽的小说作家”,作品虽然披上了“国难”的外衣,“所表演的思想,无疑的是充分带有近代有产者的基调的”。他们的作品“是谈不上技术的,虽然在偶尔一两篇内,作者稍稍加以描写,大部分是连新闻通信都不如”。③三处引言分别见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 877、882、869 页。
面对新文学的咄咄逼人,鸳蝴派或抱排斥态度,或持“新旧兼容”心态,④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第65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并未对此类批评做过多回应,想来是这些“文妖”、“文氓”、“封建小市民”的论调他们早已于上个十年听腻味了,故而也就听之任之。但有一件事是真正触动了鸳蝴的,那便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这样,周瘦鹃长达十二年零七个月的主编生涯就此宣告结束。“于是平地一声雷,来了个大转变,换上了一幅新面目”。⑤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第276、3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但旋即,在“一九三三年春,《申报》经理史量才不忍周瘦鹃赋闲,又在《申报》辟《春秋》副刊给他。任《春秋》副刊编辑后,周瘦鹃暗下决心,有心和《自由谈》较量一番,想尽一切办法与《自由谈》争夺读者”。⑥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第276、3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从表面上看,由《自由谈》而《春秋》,完全是《申报》自身的改革和经营策略,但事实上,这中间却是掺杂了许多微妙的明争暗斗的。关于此事,鲁迅在《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周瘦鹃作了导火索,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①范伯群、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803页。
这里鲁迅讲的好戏,恐怕更多的是指一九三三年以来,以范烟桥主编的《珊瑚》半月刊对新文学的反攻。因为只有这些才“比较算得上论争的”。②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第27页。《珊瑚》的第二十号上发了一篇署名彳亍的短文 《新文学家的陈迹》,历数刘半农、鲁迅、施蛰存、戴望舒、黄中、俞长源、老舍、楼建南、叶绍钧、吻云、苏凤、杜衡、滕固等新作家都曾在鸳蝴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文章单列姓名以及杂志的名称,不作任何评论,但意图却很明显,那是要揭新文学的老底。为了更进一步地表明态度,《珊瑚》上自第十三期起就开辟“说话”栏目,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新文学派里,确有当得起‘新’,够得上‘文学’的作品。 《礼拜六》派里,也有极‘新’,极‘文学’的作品”。 关于“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作品,对于新文学作家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的片面批评,也表示了异议,“才子穿了西装,佳人剪了头发,放到小说里,就不算鸳鸯蝴蝶了,把自杀做结局,就算文艺的至上者了,这种观念,我们也得转变些”。“要是噜离噜苏,记些新式簿记,或是旧式流账,都不配称他为好小说。”③转引自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第 658-660页。
这次的论争,同样是一攻一守,而且其中又牵扯着“京派”、“海派”的争斗,所以看上去不免有些情形复杂。而事实上呢,虽然京派批判的对象包括了鸳蝴,但自有杜衡等海派人士的回应,所以他们又是不应战的。而此后战争肆虐,新文学的作家们纷纷奔走抗日,上海成为“孤岛”,这所谓的新旧之争又不了了之。以后的时间,虽有人旧事重提,④叶素:《礼拜六派的重振》,佐思,《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116-13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但毕竟微乎其微。倒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时候,朱自清写了一篇《论严肃》,态度平正,对鸳蝴作了恰当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