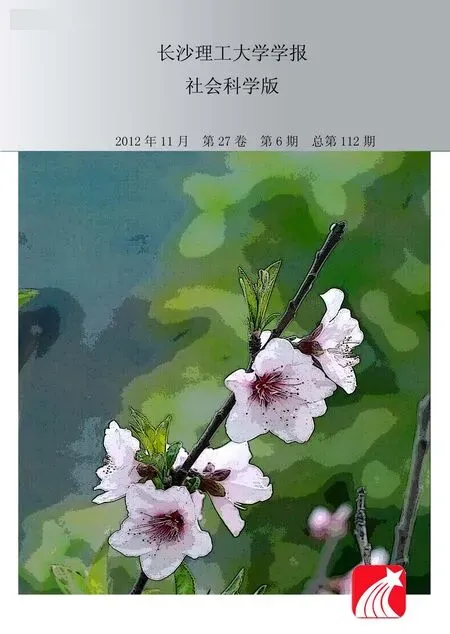超越资本主义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述评
张 辉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缘起:在“历史终结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苏东阵营的解体曾使西方左翼阵营长期陷入失语状态,他们当初借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资源因之丧失了依托,就连一度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在认为苏联圈会永远维持下去的当儿,还保有一定的批判性,可是到了1990年代,却也讽刺地,仅变成了肯定资本主义与国家放肆撒野的‘犬儒主义’(cynicism)”。[1]而对于西方右翼阵营来说,苏东阵营的解体不仅意味着作为实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更意味着作为乌托邦理念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对此,柄谷深感此前自己曾参与其中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解构主义式的批判丧失了冲击力,从而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自我解构和重新整合运动的代言人,这也正应了马克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说法,柄谷感叹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理念想象力的时代”。[1]
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并未因此停止对新的可能性的思考。在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状况,从理论上对其结构进行描述和批判进而探寻斗争可能性的著作,首推哈特、奈格里的《帝国》(Empir)和《民众》(Multitude),而柄谷也早在1990年就发表《关于历史终结》一文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绝对的现实制度存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是通过无限拖延其‘终结’的到来而维持自身存在的一种制度,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所说的‘扬弃现状的现实运动’。因此,两者都是没有‘终结’的运动”。[2]
柄谷坦承苏东解体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同时也给了他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理念的契机,这一契机是通过阅读康德而获得的。他在阅读中发现,康德在不断地以经验论来批判唯理论,同时又以唯理论来批判经验论,这是一种超越“独断论”的“跨越性批判”,他将这种“跨越性批判”用于对马克思的阅读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家马克思”,这使他“很想如马克思所做过的那样,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并找到一条走出资本主义的道路”。[3]沿着这个思路,柄谷积十年之功完成了集其思想之大成的《跨越性批判》一书,他在书中除了继续批判“历史终结论”,还试图扭转自卢卡奇、阿尔都塞以来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转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竭力激活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向度,从而重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实践的可能性。
一、康德与跨越性批判
康德将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建立的认识论称为“哥白尼革命”,后来的阐释者多将其解释为康德完成了从经验论到主观哲学的转向,因而客观世界需要理性的建构才能被认识和改造。柄谷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恰当,如果康德完成的是这样一种转向的话,他便陷入了自己所批判的“独断论”之中, 因此康德的转向另有深意。柄谷认为,“哥白尼革命”本身的意义并非简单地从“地动说”转向“天动说”,而是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关系结构”,从而建立了新的计算体系。以此为喻,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也并非单纯从经验论转向唯理论,更不是在折中经验论和唯理论,康德所做的工作是试图超越将唯理论和经验论视为对立面的独断论,进入到在两者“之间”进行不停转换的思考方式之中,从而在“关系之间”发现超越性的视野。柄谷将这种在不同“关系之间”不断“移动”的批判方式命名为“跨越性批判”(Transcritique)。[4]
柄谷认为,“跨越性批判”是建立在经验论和唯理论对立之上的超越性认识,这正是康德引入“物自体”概念的要义,它并非是一种实体性的理念,而是一种整合性理念,我们并不能认识它,而只能认识它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物自体”又并非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而是可以通过主观之间的“强烈的视差”可以感知的事物。柄谷举例说,就象人的脸的存在(“物自体”)是确实的,但我们却无法呈现它,但是通过肖像画(主观)与照片(“客观”)之间的“强烈的视差”可以感知真实的脸的存在。因此,柄谷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所建立的“跨越性批判”并不是象“换位思考”那样一种司空见惯的视角,它既不同于主观性反思,也不同于“客观性”考察,而是在超越性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强烈的视差”去探寻现象界的变化,从而消除认识论中的二律背反。
柄谷指出,这种批判关键在于对“他者性”的引入,康德通过“物自体”揭示了无法事先获得也无法随意内在化的他者的“他者性”,主观认识的普遍性只有以“他者性”为前提才能得以成立。因而,“跨越性批判”强调的是在不同规则之间的对话,康德由此批判了此前西方反思哲学的传统,这些反思哲学大多都只是一种自我审视,就象法庭上的控辩双方的角色一样:在法庭上,相互对立者之间实际上共享着同一个规则,检查官和律师的角色总是可以互换的。因此,在这样的法庭上,无论怎样相互敌对与辩论,对手都不会是他者,最后都会沦为一种变形的自我对话。
因此,康德的“跨越性批判”通过对“他者”的导入,从根本上体现了它的道德意义:“不能把他者单纯当作手段,还要同时当作目的”,也即自由的相互性原理。在这种情况下,“他者”不只是活着的人,还包括死者以及尚未出生的未来的他者在内。柄谷认为在康德对“他者”的尊重的理念中蕴导着世界共和国的理想——这是一个把他者当手段的同时也视为目的的社会,正是对这样的社会理想的追求,生发出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
柄谷在此着重强调了康德的方法论意义:当我们面对一个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时,不要指望通过从一个独断论转向另一种独断论。相反,我们应该在坚持二律背反不可消解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基本的批判立场,它不是某个与其他立场相抵牾的既定立场,而是关注不同立场之间在建构意义上的裂隙。康德看待事物的姿态实际上是既非从自己的视角,又非从他人的视角,而是直面由“视差”所暴露的现实。柄谷借助康德的超越性理念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要还原一个超验的实体,而是凭借现实经验不可消解的二律背反特征才能辨认出来的社会变迁(历史)。
二、《资本论》其可能性中心
柄谷在思考资本、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用交换方式代替生产方式去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1](P24)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三种交换方式:A、互酬式,B、掠夺——再分配式和C、商品交换式,它不仅指物质交换,还包涵政治、道德和情感等方面的交换。在实际社会构成体中,各种交换方式渗透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方式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是A占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是则B占主导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C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排除掉其他交换方式,而是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混合形态,从而构成了坚固的“伯罗梅欧之环”(lanoeud borroméen)。因此,要想抵抗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就必需同时与这三者对抗,只否定其中一项,结果都会被资本收编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中去。柄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跨越性批判中,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和未来崩溃的结局,而且在其间也蕴含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柄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隐藏的新型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由于货币在商品交换体系中被放置在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等价形态的位置上,从而获得了能与任何商品进行交换的权能,因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获得了核心的地位。经过这样一种错置,货币与商品之间存在的非对称关系被隐瞒了:在商品交换的体系中,持有货币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购买商品处于主导地位;而商品持有者(包括劳动力商品)则处于了被动地位。因此,资本家所要追逐的不过是货币的这种主导“权力”——这正是货币完成自我增殖变身为资本的根本前提;而劳动者除肉体之外一无所有,只能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以换取生活必需品,致使劳动者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能“以被动的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柄谷指出,马克思这样一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的非难,而是说资本家和劳动者在此都不是主体,而是被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规定。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阶级,并非经验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说当代社会中不存在《资本论》那样的阶级关系,这种批判是无的放矢。不仅在当代,就是过去,无论在哪里,也不曾存在过这样单纯的阶级关系”。《资本论》所考察的是这种统治“关系的结构,即被置身于这种场合下的人们在其意识中是怎样呈现这种存在的”。[5]
因此,在资本自我增殖的运动过程中(G-W-G′),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但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也即,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后必需获得这样一种落实:作为总体的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从消费领域中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如果不能获得这样的落实,剩余价值则不能实现。马克思把这一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即作为总体的工人的总工资无法消费掉他们自己生产的总产品。柄谷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流通领域给出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契机,“(在此)劳动者之所以成为劳动者的规定性将消失掉”,从而重新获得作为消费者的主体性。柄谷认为马克思在流通流域的论述中给出了抵抗或者说超越资本主义的第四种交换模式:联合。它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交换方式,而是一种“理念联合运动”,是“在商品交换(C)的位相中,开放给自由的个人来试图恢复互酬式交换(A)运动”,[1](P43)柄谷将其命名为“超越论X式”的交换方式(D),它是交换方式A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而共产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理念联合运动,它“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柄谷所倡导的“新联合主义运动(NAM)”正是建立在这个原理之上。
柄谷凭此原理批判了此前的抵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一方面必须改变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理解为领主和农奴关系的变形的主流观念,因为这种观念遮蔽了资本制榨取“剩余劳动”的秘密,并根据“主奴辩证法”将社会主义革命简化为劳动者打倒资本家的斗争,而把抵抗的场所设定在劳动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在“68年革命”之后出现了各种否定“劳动运动中心论”的市民运动,由于缺乏从资本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和立场,结果均被“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所吸纳,这种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实现财富再分配以解决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想法,最终被社会民主主义所收编。
柄谷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两条抵抗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一是在合作联盟制中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即扬弃“民族=国家=资本”三位一体的制度性原理;二是在资本流通或商品消费的场域中有劳动者成为真正“主体”的可能性,即阻止资本的自我增殖――剩余价值的产生,并最终颠覆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主体存在。柄谷认为,在当今阻止资本不断运动的根本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哈特、奈格里所说的“不劳动”,另一个是甘地强调的“拒买”。前者是跨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横向斗争”,后者则是促使资本制企业变为非资本制企业的“内在斗争”,柄谷所倡导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就是试图同时组织起这两种斗争。而为了使“不劳动”和“拒买”成为可能,必然要在资本运作体系外准备好劳动和购买的场域,通过区域交易制度(LETS) 建立起生产——消费合作联盟,最终实现阻止资本的自我增殖,扬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资本”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
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卢卡奇是通过黑格尔发现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总体性”,那么柄谷则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通过康德发现了马克思哲学中的“跨越性批判”,因此,柄谷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而柄谷所服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则是在继承和推进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的过程中声名渐起的。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是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分离,经济不再具有决定作用,而政治则获得了自主性空间。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分析方法已经失效,阶级政治应该让位于认同政治。二是不承认后现代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作为这种变化的理论反应的后现代主义,对此仍然具有一定的阐释力;另一方面它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最有效的理论武器。因此在苏东剧变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回应右翼“历史终结论”的诘难,还要推进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合法性。
柄谷的努力在《跨越性批判》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中寻求马克思理论的可能性。柄谷以“跨越性批判”重新阐释《资本论》,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在当今的发展逻辑,坚持从资本运作的“内部”去发现抵抗资本主义的原理,拓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的想象力,从而重建“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
二是倡导“非暴力”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进入“黄金发展期”之后,劳资关系似乎并未出现阶级对抗的情形,因此有左翼学者断言,“对于先进的工业国家而言,革命的论调在当前有点过时,阶级之间展开殊死斗争的前景对美国工人比对真正贫穷的不发达国家无产者的诱惑力显然小得多。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西方国家来说,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7]“个人成功”已经成为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阶级意识,资本主义统治也相应采取了间接控制的方式,原有的阶级对抗被其他领域的对抗所转移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和性别等领域的对抗运动,实践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和边缘化的特征,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被消解而碎片化了。
因此,柄谷主张应当改变对抗资本主义的策略,“在必须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不或多或少采用些组织原则的话,那就会被迫走向灭亡”。[5](P146-147)因而在当前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下,实行暴力运动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必须在承认资本主义某些前提的情况下,采取从内部进行抵抗的措施。柄谷倡导的“非暴力”的“新联合主义”经济运动和抽签选举制的政治方案,就是这一新型的对抗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的“去政治化”诉求成为理论思考核心的背景下,从总体上去把握世界的“宏大叙事”遭到了遗弃,西方世界的人们因对政治逐渐产生了冷漠之感而进入了一个默认现状的时代。“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8]这就是导致当今世界普遍缺乏想像力和抵抗资本主义运动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批判理论失去目标的当下,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就显示出一定的意义,它和哈特、奈格里的《帝国》、《民众》一样,重新刺激了人们理论想像力,它提醒我们:象资本主义这样一种隐含极大不公的剥削制度既不会也不可能永世长存,必须对它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才能获得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进而,柄谷极力倡导“新联合主义”运动,推动各区域以自下而上的联合对资本主义进行跨国抵抗,它试图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的运动,阻止贫富差异及掠夺的继续扩大,也成为当今对抗贫穷、战争及环境破坏时凝聚人心的重要根据。
但是,柄谷的改良方案也呈现出浓郁的中产阶级乌托邦色彩,其将马克思康德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品质和实践品质。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对抗,仅凭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个人纵有丰富的理念,也无法遏止被剥夺者的无助感继续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和加深,以及他们的子孙都将在加速累进的贫穷中,成为居世界最大多数的底层牺牲者。因此,柄谷并没有真正建构出一个反抗的“可能性”,其理论的实践性是含混不清的。这种抵抗并不试图去消灭权力,而只是让权力不得通行无阻而已。如此,这种抵抗就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置于一种改良的可能性之中——知识的建构仍然被置身于对权力“小骂大帮忙”的共谋关系之中去了。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正是一种有效的实践决定了知识的社会品格,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就创造不出真正的关于实践的知识。因此,不论知识分子如何在书斋里谈论实践,它仍然是一种有关智力训练的经院哲学。
这并非不可理解。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白领工人的出现和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的比重的下降,大量的中间阶级开始涌现。从这些新的中间阶层诞生了一批新的激进分子,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传统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进行政治认同的同时,却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理论立场,从而保持了巨大的异质性。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左派”。[9]而日本由于20 世纪30年代政治局势法西斯化和白色恐怖,致使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受到抑制,从而转往学院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日本学术界本身就具有将学术“客观化”的传统,即使是意识形态也要诉诸于学理化表述,因此,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被迫以这种“学理化”的方式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使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化的特征愈加显著。综之,由于西方左翼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立场日趋保守化,因此,柄谷把马克思送回到康德的书斋里进行逻辑演绎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布罗代尔曾有过这样的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由‘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社会中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保持警惕的少数统治者的抵抗(他们今天已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决不是几篇夸夸其谈的学说和纲领,决不是几次暂时的选举成功,就能轻易动摇得了的”。[10]马克思曾指出:尽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都清晰地描绘了社会运动的目的”,但是他们不能理解手段,乌托邦主义者“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但是“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11]人类前行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存在没有斗争的胜利。因此,真正有效的政治方案不可能寄望于书斋中的沙盘演练,而只能来自于对现实不同政治力量博奕的形势分析与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斗争策略的制定和践行。乌托邦当然是我们力量的重要源泉,但是乌托邦提醒我们所要改变的,绝不是这样那样的细枝末节,而是制度的结构、政策的基础。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层面上来,回到由其所导致的世界资产阶级专政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中来,看到构成世界历史动力的仍然是世界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矛盾和斗争,从而瞩目于不同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运动,诉诸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那么,不仅想象而且创造另外一个世界才会获得真正的可能性。
[注释:]
①“Transcritique”(跨越性批判)是柄谷行人自创的术语。按他自己的说法,先是有“transcendental”一词,是康德所谓的“超越论式”的意义,这是一种垂直视角;接着还有一个词“transversal”,则有横向的、跨越的意思,是一种水平视角。将这种双重意义的“trans”与表示“批评”、“批判”意义的“critique”进行合成而成为“Transcritique”一词。
②柄谷行人认为,用“生产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变迁,容易产生经济构造与政治构造似乎是有区别的看法。“因此,为了避免混淆不清,想要普遍地来观察资本制以前的社会构成体历史的话,还是得舍弃‘生产方式’的说法为妙”。
[参考文献]
[1][日]柄谷行人.迈向世界共和国(墨科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2007.8.
[2][日]柄谷行人.关于历史的终结[A].关于终结[C]. 东京:福武书店,1990.
[3][日]柄谷行人.以马克思的视角思考全球化[J].世界杂志,1999(4).
[4][日]柄谷行人.再谈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J].文学界,1998(8).
[5][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16.
[6][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
[7][法]雷蒙·阿隆. 阶级社会: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39.
[8][美]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姚建彬译)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3.
[9][英]佩里·安德森.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32.
[10][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顾良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729.
[11][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