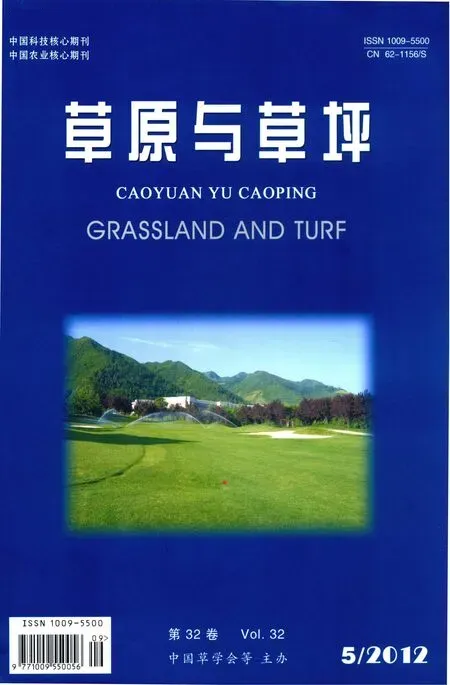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哈萨克族的游牧生产
阿利·阿布塔里普,汪 玺,张德罡,师尚礼
(1.阿克赛自治县林业局,甘肃 阿克赛 736400;2.甘肃农业大学 草业学院/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省草业工程实验室/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1 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态文化
1.1 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1.1.1 牲畜的分类放牧 哈萨克族能根据不同的牲畜选择不同的放牧方式。马、牛放牧在高山牧场。针对冬、夏季牧场的产草量和枯草质量的不同,盛行分类放牧。牧民在不同时间将牲畜放牧到不同的区域,畜群在各时期都能吃到最好的草。3月底,春牧场主要进行接羔、育羔工作。在进入夏牧场之前进行剪毛、羔羊去势的生产活动。6月底,是羔羊断乳和大畜配种的时节。由于畜群中除马能自动避免近亲繁殖外,为保证牲畜的质量,对其他种类的畜群,则靠经常换种畜的办法进行。到9月,给羊群剪秋毛、配种。这一系列生产技能是哈萨克族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生存的有效手段。客观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和他们赖以生息的牲畜和草地。
1.1.2 草地游牧 哈萨克族俗语说:“草地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地的子孙”,“草肥则牲畜壮”。正是由于对草地的重视,哈萨克族对草地使用有一定的规则与习惯,解放前草地划分都是以部落和阿吾勒(牧村)为单位,“由部落和阿吾勒头人、元老和比官会议协调划分,因而他人不能插手更不能随意改变,是固定的”。哈萨克族长期以来习惯于游牧生产,常年在草原上随四季的变化流动放牧。一年转场有2~3次。3月底把牲畜赶往春牧场;6月底,畜群进入高山夏牧场;到9月,牧民将畜群赶到秋牧场;入冬,牧民又迁到冬牧场,利用那里冻干了的牧草过冬,补饲少量储备的干草。游牧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地。同时,对草地的选择也要依地形、气候、水源等而定。不同的草地放牧不同的牲畜,草甸草原适合于饲养牛马等大畜,典型草原则宜于放养绵羊、山羊等小畜,荒漠草原多放养骆驼。
1.1.3 狩猎中的规矩 狩猎业一直是新疆游牧民族的副业之一。狩猎业的存在一方面补充了人们的衣食,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草原生物的多样性。哈萨克族狩猎时,不同的猎物要采取不同的猎取方法,如在猎取黄羊、狐狸、狼、野猪、兔、貂、鹿、虎时,所使用的方法就不同。从事狩猎生产应当遵守规矩,如打猎日期的选择、保护猎物幼仔、迎猎、分配猎物等。至于狩猎工具,大致有动物类的(鹰、犬)、人工制造类的(弓箭、扎枪、铁夹子、签子、猎刀)。为了使狩猎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哈萨克人还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禁忌,对狩猎行为做了规范,避免了盲目的不必要的滥杀。
1.2 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生产特征
游牧民族自身既创造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技能,又使得自然环境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技能是以与自然的适应作为前提条件。但是适应是通过对牲畜及产品的利用来体现的。适应的目的在于利用。二者是辩证关系,对牲畜及产品的利用体现了对自然的有效适应程度。对牲畜及其产品的利用行为实质造就了游牧文化中的物质生产的特征,进而决定了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某些基本特征[1]。
1.2.1 游移性 哈萨克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的特点其实质是凭借天然牧场饲料资源进行畜群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必然建立在对天然牧场适应性利用基础上的生产经营方式,牲畜需根据气候、地形、水源以及草原牧草生长季节性的周期变化而迁徙。哈萨克族有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游牧民族四季游牧的原因:“开春羊赶雪,入冬雪赶羊。”从根本上讲是人随牲畜移动,以畜群的活动为中心,牲畜到了哪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随着到哪里,人的自主性要服从于畜群的生存需要,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降至第2位。
1.2.2 适应性 从人类自身的短期利益,尤其是从生活的安乐舒适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不适宜的。但如果从生态以及从人类生存的长远意义着想,以迁徙来适应的生活方式有其积极和科学的依据。游牧民周期迁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畜群的多样性和足够的食物量,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地表植被的覆盖面。从亚洲干旱草原相对脆弱的生态状况来看,不是游牧民自愿选择了“迁徙-适应”行为,而是环境促使游牧民做出了“迁徙-适应”的举动。游牧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对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维持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适应性是游牧民族在这一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前提与基础。不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生产生活技能,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有意主动地创造出来,其中充满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智慧。正是由于游牧文化杰出的适应性特征及游牧民族非凡的适应能力,才使得这片神奇珍贵的土地得以保留至今天。当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重,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盲目的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所带来的恶果时,古老的哈萨克游牧文化愈益显示出了它的可贵与难得,其适应特征也愈益显示出其科学与合理之处。
1.2.3 实用性 哈萨克游牧文化在生产领域,将与生活有关的物资利用达到了极限的程度,从而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产品的创作上都贯穿着一种实用化的原则。在牧区,以对一只羊(物质产品)的处理过程为例,羊皮当作产品卖掉,换急需的生活用品。剩余部分的加工过程是本着“好吃”和“物尽其用”的原则来进行。哈萨克族这种生存方式,体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特征,保护了生态环境,为自己谋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有效地保持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果说适应性特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实用性特征则是对人自身而言,前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技能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而且我们以后将要看到,正是由于哈萨克族生态文化的这种实用性,才为其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实用性基础。实用性的最大收获就是节约了自然资源,而这恰恰是这片土地最宝贵、最珍稀的东西。
1.2.4 简约性 哈萨克游牧民在一年四季里逐水草而移动,经常处于运动状态中,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大量积累固定资产。若把棚圈、牲畜当作固定资产看待,那也同现代经济学所指的工厂化的固定资产有所不同。因为游牧民的棚圈、畜群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态状况中,而且就游牧经济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划分也是相对困难。例如,牲畜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工具(牛、马都是交通和放牧的工具),与此同时牲畜也是牧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游牧文化中的资产都具备综合功能。这种综合功能在物质生产方面蕴涵了简约特征。一定资产功能的多样化和材料的简约化是辩证的。就一种产品而言,只有具备多种实用功能才能简约生产材料。根据简约材料原则设计的一项产品,只有具备多项功能时才能做到物尽其用。
1.2.5 稳定性 这是就其所具有的影响、意义或历史价值而言。稳定性的存在对自然环境来说意味着被保护和良性循环;对人来说意味着生存权的被保证及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化本身,则意味着发展进程不至于被生硬地打断而得以保持下去;对人类文明,则更是意味着与生态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文明多样性的被尊重与保证。这里讨论的哈萨克族生态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变化”的因素,实际上文化的变迁是时时存在。这里所说的“稳定性”只是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因为环境的变迁是“长时段”性,因而人类为适应这一环境而采取的手段在本质上是一贯的,变化的只是“量”而非“质”。在此讨论的角度是从“能指”出发的,即“应该”是如此,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与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同样脆弱的游牧文化已面临着太多的生硬、不合理甚至粗暴的干扰,生态文化所具有的一贯的稳定性面临严重威胁,而这种稳定性,对人、对环境都不可或缺。
1.3 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用品
1.3.1 适应游牧的衣物 哈萨克族人冬天戴两面有两个耳扇,后面有能够遮风雪、避寒气的长尾扇的尖顶帽子。这种帽子是用羊羔皮或狐狸皮做的。而夏天则戴很薄的平条绒做的颜色各异的尖顶帽。克宰部落和阿勒班部落男子夏天戴的用山羊皮做的轻便的“克宰卡里帕克”,基本上继承了古代先民的特色。哈萨克男子采用柔软、轻便的白布缝制衬衣。哈萨克人的袷袢大皮衣实用且最具“生态”特征。袷袢即长外衣,有单棉之分。袷袢与生活的环境相适应,白天日照强烈,温度较高,夜晚气温降低,寒气袭人,一日之间温差很大。长至膝盖的袷袢穿脱方便,既可以抵御风沙,又可作为夜间的铺盖,极为实用。
1.3.2 适应游牧的食品 传统的哈萨克人的食物分为肉食、奶食、面食和蔬菜类食品,其中,以肉食和奶食、面食为主。肉食的来源主要是牲畜和猎物,其食用方法很简单,多以煮食为主,剩余部分晒成肉干备用。奶食的来源主要是饲养的各种牲畜,有鲜奶、各种奶制品(酸奶子、奶皮子、生奶油、乳饼、酥油、酸奶疙瘩、奶酪液、酸凝、黄奶疙瘩、奶豆腐等)、马奶酒、发酵的驼奶、奶茶等,是牧民日常饮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哈萨克牧民为了适应牧业生产的需要,便于迁徙,十分注意贮藏,常常把奶疙瘩和奶酪晾干晒透,长期保存,作为冬季口粮,也是招待客人的食品。把酥油装进刮净、干透的羊肚子里,然后把口扎死,既不渗油,也不走味,放上数年也不变质。“长期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牧民的乳食种类非常多,他们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乳制品。这些乳制品,都是根据畜乳的性质(马奶不能干储)与需用的目的(即时饮用、久储、携带、调换口味等)而制作的。”至于植物类食物,在传统哈萨克人的饮食中是作为辅助性食物而存在,主要有馕、油炸的“包吾尔萨克”、馓子、油饼、面条等。另外,季节性差异在传统哈萨克人的饮食习惯中也存在,如夏季以奶食为主、冬季以面食、肉食为主。
1.3.3 适应游牧的毡房 传统哈萨克人的居所主要是毡房。哈萨克毡房是先民们对大自然天然选择的结果。哈萨克草原上的芨芨草、柳条、兽皮、畜毛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哈萨克先民对自然原料进行艺术般的加工,精心构思,形成了哈萨克毡房这种居住方式。毡房的构件除了支撑架子用木头制作外,其余部分全部用毛毡、毛绳、毛带等畜产品做成,并且符合游动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哈萨克毡房以其易于搭卸、携带方便、坚固耐用、居住舒适、防寒、防雨、防震的特点而沿用至今。
1.3.4 适应游牧的家畜 哈萨克大规模牧养的牲畜有马、驼、羊、牛,统称“四畜”,马居其中首位。根据考古材料,哈萨克族大规模牧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塞种人居住在伊犁谷地的时候。乌孙时代的“乌孙马”在中原颇负盛名。史载,“乌孙多马,其富人多至四五千匹马”,乌孙王曾以良马千匹为聘,迎娶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足见古代乌孙游牧业及其养马业规模之大。古代康居的养马业也有很大规模,而且培养了优良的马种。汉文史籍多有关于康居产马的记载。哈萨克继承了古老的牧马传统。直到今天,在哈萨克的畜牧业生产当中,马的大规模牧养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传统哈萨克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骆驼以及木轮车。马是用于骑乘的交通工具,人们在迁徙、狩猎、放牧时都要骑着它,马已经成为哈萨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马是男子汉的翅膀”,人们热爱马,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来赞美它,积累了许多经验来确保马匹得到最好的照顾。
哈萨克族生活的地区干旱多戈壁,运输比较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使用骆驼驮运最为适当,而且骆驼载重量也超过其他牲畜,一向被誉为“沙漠之舟”。不仅用于骑乘,还用于拉车、负重。因而一些有骆驼的人家,多用骆驼转场搬迁和驮运货物。驼运一般不用带草料,通常一早起身即行至午前,中午放牧,让骆驼得到休息。日落前起身行至深夜,每走一段可以稍事休整,可以说骆驼在哈萨克族人民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木轮大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交通工具,游牧的先民们都曾使用过,这种车的车轮高大,结实耐用,适用于各种地形,而且载重量大,牧民们用它来拉水及各种物资,尤其是在迁徙时,已经成为哈萨克牧民“移动的家”。
每个哈萨克人家羊群里都有自己喜爱的领头羊,在转场过程中,有时遇到河流、湖泊、大雪封山或遇到险要狭窄山路,羊群迫使停留下来时,主人就会进入羊群里扬鞭大喊,这时领头羊听到主人的声音就挺身而出,勇敢地往前冲,带领其他羊群走出险要地段。如果没有这样几只领头羊,遇到这种紧急关头,就无法将羊群赶到指定地点。
2 哈萨克族牧民放牧活动的特点
2.1 四季草地的利用标准
根据中国哈萨克族游牧生活区域以山区为主、平原、盆地为辅的特点,通过长期的游牧生活,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看看太阳、月亮是否有风圈,特别是细微观察有蹄类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对野生动物的迁移时间、路线以及进入交配期的时机进行长期观察和研究,得出这些活动规律与气候、自然界的微妙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野生动物如果进入交配期的时间比较早,表明来年气候比较暖和;如果进入交配期时间比较晚,则表明来年气候比较寒冷(野生动物的这一活动规律,在上世纪90年代与美国专家一起研究盘羊资源的活动规律时得到了验证)。按照这一规律,哈萨克游牧民族就很好地掌握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什么时候进行转场、什么时候对羊群进行配种等等。另外根据游牧区地形地貌的特征、植被分布规律及气候特征的差异性,按照春旱、多风;夏短,少炎热;秋凉、气爽;冬季严寒漫长、积雪厚等特点,把草场以平均气温为标准具体划分为四季牧场。平均气温稳定在0~20℃划分为春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的海拔比较低、低山丘陵地带,避风遮寒,气候相对暖和,比较适宜羊群保存体力和接羔育幼。植被主要以禾本科牧草为主,还杂有豆科牧草;≥20℃划分为夏季牧场。是指这一区域海拔较高,亚高山、高山草原占据优势,气候相对凉爽,牧草丰富,比较适宜各类牲畜抓膘。植被主要以禾本科牧草为主;0~20℃划分为秋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的荒漠较湿润草原为主,海拔较低,气候相对凉爽,牧草以豆科、半灌木、蒿属类牧草为主,这些牧草营养丰富,有利于牲畜固膘,为安全越冬打基础;≤0℃划分为冬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主要利用雪水,虽然气候寒冷,但避风性很好,牧草主要以半灌木、灌木为主的山地荒漠草场,这些牧草的特点是冬季下大雪不被埋压,对各类牲畜取食有利,便于牲畜安全越冬。哈萨克游牧民族对四季草场的划分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2 畜群结构的控制
随着历史的变迁,哈萨克族牧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经验积累,逐渐确立了对四季牧场的区分和利用,形成了在一定的草原范围之内,按照季节搬迁流动放牧的习俗。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草场资源,严格控制畜群结构,逐渐减少大牲畜的结构比例。优先发展小牲畜,是因为大牲畜主要用来交通、运输等,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且对草场的破坏力也比较大。而小牲畜具有的利用率很高,繁殖能力强,经济效益显著,周转快等特点,很适合畜牧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小牲畜具有发展快、损失小、管理方便、适合各类草场放牧等优点。因此,往往游牧民族严格控制大、小牲畜间的结构比例来发展畜牧业。一般把大牲畜、绵羊、山羊、其他畜种年末存栏比例严格控制为12.8∶63.9∶18.3∶5,从这一结构比例看,大牲畜的比例远远小于小牲畜的比例,这个畜群结构符合减轻对天然草场的践踏压力和提高载畜能力的理论水平。
2.3 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转场[2]
在中国这块“候鸟”迁徙的大地上,哈萨克族深居大陆腹地游牧已有2000多年之久,四周高山环绕,与山脉相间或相邻的有盆地、谷地、平原等。而有限的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到哈萨克族的生存与发展。
2.3.1 季节转场 牧场按季节可分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转场”,就是依牧草生长周期和气候的变化,有序地为牲畜转移草地,是按季节每年进行十几次的循环轮牧的过程。春天把羊群赶放到山坡或山下平原地带;夏天转到高山深处;秋天到山腰,然后留一片草地,打草储存让牲畜冬天吃,冬天在山脚下羊圈周围放牧。每年3月底至4月初,大批牲畜又必须从冬季牧场再次出发,开始新一年的转场生活。
2.3.2 转场距离 哈萨克族地区各季草地相距各异。山区牧民每次转场路程不超过百公里,半牧半农的牧民转场路程更短,在30km的范围内。平原地区的牧民转场路程往往较远,近则几十公里,远则几百公里。有条件的地方,牧民改用汽车运输搬家,牲畜则由牧人赶着另行。由春牧场启程时,要考虑到幼畜出生的时间,看是否长结实,能否随群赶路。这时,日行程为14~15km,哈萨克语中有“羔羊程”的长度单位,指的正是这样一段距离。
转场颇具观赏性。大批牧民成群结队地如潮水般迁徙,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从夏季牧场向秋季牧场转移。在一个海拔2 000m的山口观看,一家接着一家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羊群朝远方一个湖的方向前进,从早到晚的大规模迁徙场面一直会持续半个月。
有一位美国著名探险家这样描述哈萨克人的转场:“我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哈萨克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转场的游牧生活。近则十几公里,远则几百公里,他们的生活处处都在转场中度过,走到哪里,把游牧文化就带到那里,传播到那里。我和他们的长老谈论了关于这次准备‘西迁’的事宜。有人怀疑哈萨克人迁徙近6 000km,能否把整个家庭和牲畜一起转移到印控克什米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天天就在转移,习惯了马背上的游牧生活,就转移草场一样轻而易举到达克什米尔的,但别的民族就无法做到”[2]。
转场取决于畜牧业经济因素。转场可以及时给牲畜提供优质牧草,保证牲畜的成长和数量的增加;可以使畜牧生产专业化;可以使各种牲畜自然淘汰,有利于品种优化。每一次转场,都是哈萨克族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和希望。
2.3.3 转场的路线和转场过程 转场有牧道,邻里之间、牧村之间往来也有马路,草地不能随便践踏。通常在各类草场之间都有固定、大小不等、坦险各异的牧道相通。牧民在山区转场必须按牧道行走。按牧道转场,这样可以畅通无阻,保证安全,又可以防止转场牲畜肆意践踏牧草,破坏草原。不按牧道转场,随意践踏他人草场,甚至有可能引起纠纷。
转场前,阿吾勒(哈萨克语,意为“牧村”)内或阿吾勒之间的亲戚、邻居和朋友会事先商定时间、路线,约定途中宿营地点,仔细盘算每一个细节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如转场过程中将要出生的牲畜数目,老弱牲畜的处理,合理存栏,棚圈设施等。启程要择吉日,穿戴整洁美观,转场队伍尽可能风风光光。路上,你追我赶,人人都不甘落后;甚者还有的分组相互对唱等,场面十分热烈。因为先抵达宿营地者还可以落脚水清草盛的地方,并以主人的身份迎接后来者。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要对后来者迎上前去,端上酸奶、奶茶等供他们喝,以便让长途跋涉的人们歇脚解渴,同时也祝他们一路顺风;如果这一后来者搬到或暂时停留在先来者的附近,那么先来的就会主动前去帮忙卸货及整理家务等,同时还会给他们送过来一顿美味的便饭。如果这一家有小孩的话,还会礼节性地赠送小孩一匹马驹或小羊羔等礼物,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这一传统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转场队伍前,往往牵着健壮的骆驼,驮鞍上围着洁白的围毡,上面铺上华丽鲜艳的斯尔马克,然后坐着一位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驮队的行装要捆绑结实、整齐。凡是女人的乘骑要精悍讲究。队伍后边是气力十足的牛或骆驼,驮着锅碗灶具和天窗架。这种“后勤”驮畜的领队,一般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老年妇女。到了转场营地,男人们就从驮畜上卸下行李物品,给驮畜卸鞍,尽早拉好拴羔环套绳和拴驹索套绳等。只有按时拴住幼畜,才能给牲畜挤奶搭好帐篷。小孩要去附近捡干牛粪和干柴。女主人要尽快燃起篝火,支起茶壶和锅准备食物,布置帐房是女人们干的细活儿。安顿好里外,挤完奶,饭也熟了,全家老少安坐帐内小木桌旁,吃着土豆烩牛肉,喝着奶茶,奔波了一天的阿吾勒这时才进入片刻的宁静和温馨。
2.3.4 转场中的环保习俗 游牧是哈萨克民族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哈萨克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哈萨克人对草原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在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哈萨克族很讲究环保,几千年以来放牧的草地上只留下了羊圈的底子,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人畜留下的痕迹。这是因为哈萨克族在搬迁时要把所有的杂物、垃圾都要烧掉或深埋,还要拿出一些麦子、谷子等谷物抛洒在自己搭建毡房的底子上,这样一方面要讲究卫生、干净,另一方面寓意来年自己的草场水草丰美。同时,每次搬到一个新的草场上,长者都会不厌其烦的向孩子们讲解本民族的优良习俗:不要在外面随意生火,乱拔、乱割刚长出来的青牧草;不要在水源地周围随意大小便或洗衣物,要保持干净;转移草场时对定居点周边的环境进行彻底清理,不留任何痕迹,所有这些措施,是哈萨克民族对天然草原的爱护,是对水源地的保护,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呵护。今天,哈萨克牧民虽然逐渐定居和半定居,但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情有独钟。
在游牧文明濒临灭迹的今天,对于它的内涵的认识和了解还远不能与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程度成正比。游牧文明在旁观者的眼里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而且相当原始。但是,在欧亚大陆上,正是这样的游牧者与农耕人抗衡达30多个世纪,谱写了自己民族的历史[2]。哈萨克族历史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就集中体现在贯穿一年四季的“转场”生活中。哈萨克的游牧文化是在“转场”中诞生的;是在“转场”中传播的;是在“转场”中发扬光大。无论转到哪里,哈萨克人都把游牧文化就传播到那里。
3 哈萨克族游牧生产中的习俗[3]
3.1 哈萨克族信仰的牲畜保护神
古往今来,哈萨克族是世界上最喜欢牲畜和最善于饲养牲畜的民族之一。哈萨克民族世代以养畜为生,他们的乘骑、食物、饮料、衣服、日用品、毡房材料、生产工具等都来自牲畜,所以其文化创造也与四畜(羊、牛、马、驼)密切相关。哈萨克民间信仰观念认为骆驼神是奥依斯尔哈拉,马神是康巴尔阿塔,牛神是赞格巴巴,绵羊神是绍潘阿塔,山羊神是谢克谢克阿塔。在古老神话传说中这些神不仅是各类牲畜的保护神,而且是始祖,牲畜都分别繁衍于它们。因此,哈萨克牧民经常祈求这些牲畜保护神,以期自己的牲畜平安兴旺。
3.2 哈萨克族在畜牧生产中的习俗
哈萨克民族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放牧四畜,所以其民间信仰也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同时两者相成相辅,构成显著的民族特点。哈萨克民族为了使四畜兴旺和便于区分,使用游牧民族的传统方法给牲畜做记号和烙印。在做记号时,他们把割掉的牲畜耳朵尖收集起来,洒上牛奶放在蚂蚁窝边,认为这样做可以使牲畜象蚂蚁一样多。牧民们不把自家灶里燃烧的炭火借给邻居,否则认为把自己牲畜的力量给了别人;也不把半燃烧的炭火借给别人。在母畜怀胎时不把未烧尽的炭火扔到外面,否则认为母畜会早产。当母羊产头胎羔时,牧羊人抱着羊羔向主人的妻子报喜并索取礼品,女主人则向羊羔身上抛撒硬币、糖果、奶疙瘩、油炸果等,说一声“愿你当一千只羊的头领”,然后向羊羔的嘴里吹气。哈萨克民间信仰认为头一个生的羊羔,即拴在绳索第一个扣环的羊羔的毛是圣灵,是具有灵魂的神物,所以剪下来做成护身符戴在自己孩子们的身子上。主人常把头一个生的羊羔作为布施而宰杀,若舍不得就将其口涎抹在其他羊头上宰杀,把它放走。哈萨克俗语说:“驼羔娇贵”。刚生的驼羔十分羸弱,既不能吃也不能走,需要把它安置在暖和的棚圈、地窝子或毡房里,用胎脂擦它的鼻面,身上盖毡被。主人不马上让大家看到驼羔,而是将驼羔用芨芨草立着围起来,甚至有时在驼羔的四周支起帷幔。骆驼的缺憾是母驼不象其他母畜一样把刚生下的仔畜舔干。因此,哈萨克牧民像抚养摇篮里的婴儿一样精心照料驼羔,经常在它的脚掌胳肢,掰开它的嘴吹气,往它的鼻孔灌酥油,用盐水把它的眼睛洗三天,以期早日走路。
哈萨克民族在满山遍野放牧四畜,吃苦耐劳,每年都精心地接羔育羔,以期积累财富,生活富裕,所以把自己的孩子也亲昵地称呼“小驼羔”、“小马驹”、“小羊羔”、“小山羊羔”等,相习成俗。此外,在世代放牧过程中,哈萨克民族对四畜的交配期、怀胎期、哺乳期、生长期、体格形貌、毛色、内脏器官、营养价值、食用草料、习性、疫病、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等了若指掌,并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观念。在四畜中,哈萨克民族认为公马、公牛、公羊是“尊贵的牲畜和福星”,绝不轻易宰杀、出卖或送给别人。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把宰杀的牲畜4条腿都下锅,这表示死者的食物断绝和生命结束,让周围的恶灵拐弯走开。
3.3 哈萨克族在狩猎中的习俗
哈萨克先祖在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中也广泛从事狩猎业。他们把动物分成“清洁”和“不洁”两类,清洁动物是食草动物,不洁动物是食肉猛兽和猛禽。通常哈萨克人只猎取最喜欢的“清洁”动物食用。哈萨克人认为熊是从人类退化的动物,所以不食其肉;不猎取某些具有特殊标志的动物,如独角黄羊,认为它们是具有神性的动物;也不多猎取盘羊、鹿、狍等,在猎取时和它们的幼仔一起猎取,否则认为自己将“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对上述动物的头领,若看到有猛兽追逐不是射猎,而是救助。不用雄盘羊的皮子做睡垫,否则认为男子和妇女要患不育症。哈萨克先祖禁止滥杀滥猎动物,否则认为鬼魅要缠身,尤其绝对不能射猎被视为圣物的飞禽走兽,认为它们是圣人供养的,这一意识很强。所有这一切说明,哈萨克游牧民族自古以来保护自然、爱护自然意识早已形成。哈萨克人认为游牧民族的助手和伙伴狗也具有神灵,把狗不仅当作“七种财富之一”,而且认为“狗有其主,狼有其神”。哈萨克人把罕见的狗、特别值钱的狗称“斯尔坦”,并认为“马之优是白马,狗之优是猎犬”,男子汉应该有3个伙伴,即快马、猎犬和猎鹰。
4 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手工艺生产
哈萨克族的手工艺是构成其游牧文化的重要方面。形式主要有雕刻、刺绣、银器加工、编织等手工艺品。牧民日常用品、服饰、毡房以及生产工具上都刺有和刻有民族风格的花纹与图案。表达了他们爱美的生活情趣和精湛的手工艺技巧。有用桦树皮精雕细镂的碗盆、筷笼、马鞍、马镫,上面都有镶着刻有花纹图案的银饰或铜饰,有的马鞍、马鞭、腰带上还镶嵌着玛瑙、宝石,非常精致美观。刺绣的题材、内容、色彩是与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花草是牲畜的粮食,象征永葆春常在;马是人的翅膀和歌声,鹿标志着吉祥和欢乐。这种民间手工艺艺术,姑娘们从小就要学着做,长大订婚之后,专门在家把自己喜爱的花草、山鹿、骏马等图案绣在枕套、床幄、挂毯、布幔、被褥的罩单、窗帘和花毡等物上,作为结婚的嫁妆。哈萨克族手工艺品图案丰富多彩,着色大胆而又十分讲究,富有象征性,如蓝色表示蓝天,红色象征太阳及光辉,白色象征真理、快乐和幸福,黄色象征智慧或苦闷,黑色象征大地或哀伤,绿色象征春天和青春。哈萨克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工艺制品,主要有刺绣、雕刻等工艺品,其中,不少手工制品做工精细,技艺精湛大方美观。
4.1 哈萨克族的金银珠宝工艺品
用黄金、白银以及宝石在马鞍、马嚼子、马鞍带、马蹬带上面装嵌各种精美的图案,还制作戒指、手镯、耳环、腰带、凤钗和其他新娘头饰等。工艺图案丰富多彩,题材多样。最常见的是日月星辰、动物、花草飞树木及各种几何图案。
哈萨克人喜欢用金银珠宝加工制作各种首饰和日用装饰品,造形美观,精巧玲珑。过年过节或喜庆日子时哈萨克姑娘或媳妇都要用金银珠宝来打扮自己,甚至女孩们自己的马鞍子都要用金银珠宝装饰一番。
4.2 哈萨克刺绣
哈萨克妇女大都自幼学习刺绣,掌握挑花、刺花、补花、嵌花、锻花、贴边花等各种刺绣技术,能用丝线和金线在各种绒料、绸缎上刺绣,图案多以花草纹、羊角纹、人字纹等组成,多用对比色,色彩大方、鲜艳,表现风格不落俗套,具有浓重的草原气息,反映了哈萨克族朴实的审美观。哈萨克族毡房内的挂壁、花毡、幔帐都是刺绣艺术品,使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于艺术殿堂。
4.3 斯尔马克
哈萨克人把做工精美,图案鲜艳的花毡叫斯尔马克,原料主要有毛毡、毛线、布料以及染料等,所有的哈萨克人家少不了斯尔马克,这是哈萨克人的民族的代表物品。斯尔马克是哈萨克最有代表性也是最为普及的家庭工艺品,哈萨克妇女人人会制,家家都有。斯尔马克绣制工艺复杂,图案繁多,耗工多,劳务量大,制品美观大方,结实耐用,一条斯尔马克可用十多年。俗话说:“千针万线绣斯尔马克”,可见绣一条斯尔马克确实不容易。斯尔马克规格有单人斯尔马克、双人斯尔马克和扇形斯尔马克3种。由底毡和面毡两层合成,图案布局多数为方框状,如边框图案、次边框图案和毡心大长方形框内图案,非常讲究上下左右图案的对称。尽管各方框内图案色调对比强烈、鲜明,但底色是统一的,有白色和土黄色2种。斯尔马克图案一般以动物的角来比喻,哈语称角为“米依孜”。双角图案称“好斯米依孜”,单角图案称“加勒哦孜米依孜”,毛角图案称“军米依孜”。还有云彩图案、菱形图案(哈语称“包尔沙克”,因为油炸的包尔沙克多为菱形,所以菱形代号为“包尔沙克”)。以花为图案的有梅花,有四瓣花头图案,或六瓣、八瓣、十瓣等花头图案(绣壁毯时花头图案运用较多)。哈萨克斯尔马克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古老而漫长的过程,从汉朝远嫁到乌孙国的细君公主,在《黄鹉歌》里唱到:“为墙”,可见哈萨克族的斯尔马克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哈萨克族的斯尔马克经过无数代哈萨克人天才般的艺术创造,花样品种越来越多,图案越来越丰富,创作的技艺越来越精湛,成为哈萨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毡房里生活用品和往来礼品及接待客人的主要铺地用品。斯尔马克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结构紧凑,多选用简单的几何对称图形作中心主图案,四周配以对称的羊角变形花纹,大气清爽又显柔美。
4.4 工艺复杂的图斯克依格孜(壁毯)
图斯克依格孜是每顶哈萨克毡房中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挂在床内侧紧挨墙,可起挡风御寒的作用。图斯克依格孜长约1.7m,宽约1.5m,图斯克依格孜是哈萨克刺绣品工程最大、工艺最复杂、用料最讲究、做工最精细的刺绣品。整体设计采用方框线条构图,多在3个以上的方框内才是毯心方框。在各个方框线空间内,采用各种角形、双角形、毛角形及梅花、菱形等哈萨克民间图案。制花方法有扣花、钓花、堆花、拉花等手法,一般快则15天,慢则1个月才能制作完成,是哈萨克姑娘出嫁不可缺少的嫁妆用品。
4.5 编织工艺
哈萨克民间的编织工艺十分发达,主要以各种规格的彩带为主。在哈萨克毡房中用来固定房毡的多条彩带、房内绕房一周的大花彩带,其编制工艺都十分复杂而精致,除两边的装饰线条外,中间都是很规律的大小菱形及其他图案组成。要求图案清晰,造型美观,富有民族特色。
4.6 哈萨克族传统的手工艺品
4.6.1 木雕 哈萨克游牧民族,经常远离城市,而且转场次数也比较多,所以,哈萨克牧民家里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木制厨房用品。木制用品经久耐用,另外可以雕刻装饰,可当赠品。木雕是哈萨克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他们用山杨木或柳木雕成精巧的大小不等各种式样的木碗、木臼、木盆、木盘、木桶、木勺、马鞍子等等,多在底边和沿口周边雕刻上韵味浓郁的哈萨克图案花纹,也有的在用来喝马奶酒的木碗表上,镶嵌银箔、金箔或铜箔的鹿角形图案,非常精巧,金光闪闪,富丽堂皇,显示了哈萨克人民的审美观和艺术风格。
4.6.2 镶嵌工艺品 哈萨克的“假金银”镶嵌工艺历史悠久,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例如,“假金银”马鞍及马鞍配件的金银镶嵌,好像现代的电镀金银一样,表面无任何锻打痕迹,而且在制物上还出一些变色线条。
哈萨克的“假银”马鞍镶嵌图案和上述刺绣图案相同,也是以角形图案为主,其他装饰小图案如梅花钉、月牙钉、菱形钉、五星钉等的制做方法又不同。
哈萨克传统的马鞍式样只有大圆头马鞍一种,前鞍桥呈半圆形,由于半圆面口大,镶嵌成银鞍美观大方,深受哈萨克人民喜爱。有条件的人在银鞍上镶嵌金箔,金光灿灿,十分耀眼,如在鞍面上部镶嵌珍贵的宝石更为富丽壮观。哈密西山和巴里坤的镶鞍制做业十分发达,据外地来的哈萨克干部评价,东疆的哈萨克银鞍制做工艺,在北疆地区是名列前茅的。
哈萨克银鞍之所以深受民间喜爱:一是马鞍更加漂亮美观;二是马鞍更加结实耐用;三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旧时姑娘出嫁,陪嫁的珍品之一就是银鞍,新娘出嫁只有骑上银鞍马才是上乘的。
4.6.3 革皮编织工艺品 革皮编织是哈萨克生活不可缺少的技艺,俗话说:“马是哈萨克人的翅膀”。要骑马必须有马鞭、马龙头、马钗子、马鞍、马肚带等附件。漫长的游牧生活使哈萨克人民创造出了独特的革皮编织工艺。用骆驼、马的熟皮,把革皮按需求用刀子分成宽均约5mm皮条,6~14根编成具有7棱或9棱的精美马鞭;5根或7根的编成马肚带绳;8根的编成马龙头等各类马鞍用具;还有用皮子编成长短各异的经久耐用的牵马的皮绳等。
4.6.4 马褡子 马褡子用自制的毛线手工编织而成,骑马时装东西并背在马背上的兜袋,上面用不同的色线编织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朴素大方,结构严谨,丝条均匀,大都是几何纹样,配以色彩协调的粗犷线条。在色彩处理上,往往使用强烈的对比色,以鲜明地体现哈萨克牧民的艺术爱好和审美情趣。
[1]马青虎.哈萨克族生态文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8(2):92-96.
[2]John Hare.Mysteries of the GOBI[M].New york,2009:213-224.
[3]白贤.甘肃省哈萨克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