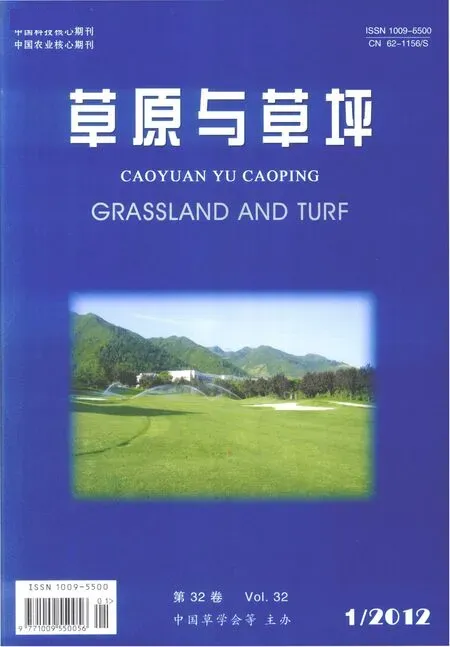裕固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Ⅰ)——裕固族民族的形成、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字
汪 玺,铁穆尔,张德罡,师尚礼
(1.甘肃农业大学 草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甘肃 肃南 734400)
1 裕固族族源与民族的形成
横跨甘肃和青海省的祁连山,其北部是青海草原,而南部是河西走廊农耕区。祁连山从西北部至东部分别居住着哈萨克(阿克赛县)、蒙古(肃北县)、裕固(肃南县)和藏族(天祝县)4个游牧民族。由于不同游牧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从古至今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演义出波澜壮阔的游牧文化。其中,裕固族的游牧文化是受其他游牧民族文化及农耕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游牧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裕固族的游牧文化对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每一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状态、语言与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本民族所特有的心理,构成了与其他民族不同文化。虽然自称“尧熬尔”的裕固族和维吾尔族在族源(尧熬尔与维吾尔是同一个名词)上有共同点,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文化传统。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发展来看,尧熬尔人仍然是亚欧草原的东南一角—祁连山地区最为特殊的一个小小的边缘群体。很久以来他们在阿尔泰语系诸族和汉藏语系诸族的边缘徜徉,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不断对其产生影响。不知不觉中,历史记忆也在发生着变化。数千年没有变的就是那个神圣的名字“尧熬尔”。
1.1 裕固族族名的沿革
裕固族的历史十分悠久,族源较为复杂。现在公认为裕固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是由古代回鹘的一支和古代蒙古的一支共同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现在的裕固族有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裕固族之分。东部地区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的康乐乡、皇城镇和大河乡东部一带;西部地区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明花乡、大河乡和皇城镇西部。无论是讲西部裕固语或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人,都自称“尧熬尔”。
俄国布利亚特蒙古学者道尔吉·班札罗夫认为,在历史上,裕固族有过各种称呼。元代称为“撒里维吾”,明代称为“撒里畏兀尔”、“西拉尧熬尔”,清代称为“西喇古儿黄番”,新中国成立初期称为“撒里维吾尔”。以上“撒里”、“西拉”都是“黄色”的意思。而“黄色”则表示西方。“尧熬尔”一般认为这是句突厥语,其意有几种:一是“粘结、凝固、收拢、搀杂、混合”之意;二是“联合”之意;三是“文化、智慧”之意。还有人认为“尧熬尔”一词源于蒙古语“森林”和“人民”构成,合在一起就是“森林百姓”或“林中的人”之意。
1953年经协商,同意用与“尧熬尔”音译相近的“裕固”作为该民族的名称,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正式定名为裕固族。从此,裕固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中间,并以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绽放出其特有的魅力。
1.2 裕固族族源的民间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在极为遥远的北方,尧熬尔有一片美丽的草原,那里有一条大河,一座高山和一个巨大的湖泊。在大河、高山和湖泊之间,有一片美丽的白桦林。有一天,从天而降的彩虹缠绕着一棵最美丽的白桦。许多日子过去了,这棵美丽的白桦树身渐渐粗壮,像妊娠的女子,九个月后树身开裂,从里面走出九个婴儿,这九个婴儿在白桦林中吮吸着白桦树汁渐渐长大了。于是就住在桦树皮制的茅屋里,在荒原上捕猎野兽为生,饿了吃兽肉,渴了喝白桦汁。故尧熬尔素称白桦树汁为“生命之汁”和“树奶子”。九个兄弟剽悍勇敢、智慧超人,最小的兄弟最为出众。后来,这九个兄弟都做了尧熬尔诺彦(首领),最小的兄弟当上了尧熬尔可汗。人们尊称他为“博格达汗”[1]。
2400多年前,在阿尔泰山往北流去的额尔齐斯河以北,是一片辽阔平缓的大草原,在这理想的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尧熬尔”这个名称,像其他民族一样,严格意义上的尧熬尔(回鹘)人兴起以前就早已有了尧熬尔人民。尧熬尔人的故乡鄂尔浑就是以白桦和西伯利亚杉众多而闻名[1]。
从这些信息中可看出,原始尧熬尔人生活在森林中。这与蒙古语称尧熬尔人“林中的人”是一致的。
1.3 裕固族族源的史料记载
裕固族的历史可直接溯源于公元前的匈奴以及突厥和公元7~8世纪的回纥。“回纥”、“回鹘”、“袁纥”、“畏兀儿”均是“尧熬尔”或“维吾尔”的不同汉语译音,名字不同,但说的都是一个族群的事。尧熬尔或维吾尔这个名字最早在2400年前在匈奴帝国时为人们所熟知[2]。
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前3世纪末,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草原地区,分布着许多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均属于匈奴联盟。所以,也可以说匈奴人是裕固人的远祖。汉、三国时期,回鹘的祖先“丁零”的一部分脱离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中心,游牧于今河西走廊一带(即今酒泉、武威、黑河下游一带),为后来的回鹘人入居河西开了先河。匈奴主体西迁欧洲后,蒙古高原及中亚各游放人由柔然汗国统治,柔然人操古代蒙古语。后来,柔然人西迁欧洲后。这一地区由和回鹘人同一种族的突厥汗国统治。至唐初,部分铁勒人又东迁河西,唐朝将其安置于甘州(张掖)和凉州(武威),后来成为河西回鹘的组成部分[2]。
公元6世纪末,铁勒系的袁纥与卜骨、同罗、拔野古等诸部落逐渐联合形成一个以袁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号称“回纥”,“俟斤”为部落最高首领。回纥部又分为9个氏族,回纥酋长就产生于“九姓”中的药罗葛氏。均属于突厥汗国。唐高宗永隆中年(公元680年),漠北回纥首领—药罗葛氏独解支,脱离在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中心,将其都督亲属及征战有功者徙于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二州,这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后来的药罗葛氏(宋朝译作“夜落纥”)建立的甘州回纥汗国的民众[2]。
到唐武后时期,回纥的一部分迁往河西一带游牧,作为甘州回纥的先驱。公元8世纪末,突厥汗国发生内乱,回纥等部脱离突厥汗国独立,并于唐玄宗天宝3年(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建立回纥汗国,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在黠戛斯和唐朝南北进攻下崩溃,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或译吉尔吉斯)人的远祖。回鹘各部四散,大部分西迁中亚。其中一支投奔河西走廊及祁连山一带,受制于当地势力强大的吐蕃人,史称“河西回鹘”。后来的裕固族的形成可能受河西回鹘的影响。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政府请求尧熬尔兀鲁斯派兵援助,尧熬尔兀鲁斯于公元751年和762年两次派骑兵援助唐朝平定叛乱,收复了被契丹族将军安禄山、史思明占领的长安、洛阳及河北各地。但同时,大批的尧熬尔兀鲁斯壮士,却战死在中原。有一首尧熬尔民歌至今还流传在汉地:
八月十五月才圆/新媳妇儿送人难/解下玛瑙一小串/颗颗玛瑙泪连绵//收复了长安洛阳/奔完了唐家疆场/舍去了回纥丈夫/泪洗我回纥柔肠/保住了天朝社稷/舍去了五万兵将/娶来了可敦娘娘。
歌中说的“回纥”就是尧熬尔。可敦(皇后之意)娘娘,大约指的是唐朝肃宗皇帝把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尧熬尔葛勒可汗一事,时间是公元758年秋天。大约在唐昭宗乾宁年间后,唐哀帝天佑年间以前(公元892年至904年),即9世纪末、10世纪初,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新五代史》有载:“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到此,河西回鹘汗国于唐末五代乱世之时,汇聚散处河西地区的各部回鹘,形成河西回鹘汗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壮大,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其他回鹘集团的文化特征。这对于后来裕固族的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1世纪初叶,甘州回鹘汗国为西夏李元昊所灭,甘州回鹘各部四散奔离。据记载,其中一部分包括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后裔,退出沙州以南,仍过着回鹘传统的游牧生活,这支甘州回鹘余部就是被当时中原史料中称作“黄头回纥”的回鹘人,当时主要游牧于沙州(今敦煌)以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到今罗布泊、若羌一带,同当时于阗国东的城市约昌城(今新疆且末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相毗连。地跨今河西走廊之西南、青海省的西北部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之东南。据《宋史·于阗传》载:宋神宗元丰4年(公元1081年),于阗黑汗王遣部领阿辛上表,神宗曾问其所经沿途情况,使者答曰:“去国四年,道涂居其半,历黄头回纥、清唐、惟惧契丹抄掠耳。”这里的“黄头回纥”就是裕固族的祖先之一[3]。
13世纪初,蒙古西征。据《元史·速不台传》载:“帝命(速不台)度大碛以往。丙戍(公元1226年),攻下撒里畏吾儿特(勤)、赤闵等部。”即攻下沙州回鹘、黄头回纥牧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亦载:“成吉思汗征服了畏吾儿人后,再从那里兴师,他又发大兵进攻撒里畏吾儿人地区”。居住在今甘肃、新疆和青海交界一带地区。此后,元代把操突厥语的撒里畏吾儿纳入统治范围之内,属甘肃行省,当时甘肃行省首府在甘州(今张掖)。
蒙古及其后的元朝中央政府,都曾不断派兵镇守撒里畏吾儿地区,镇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被元朝政府封为武威西宁王、后进封为豳王的出伯及其子孙。出伯是成吉思汗的五世孙,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玄孙,其父是阿鲁浑。出伯本是察合台汗国的宗王,后来在突厥斯坦及河中地区(今中亚五国一带)和窝阔台汗国的海都的战争中失势后,投靠了大都(今北京)的忽必烈政府——他的堂兄弟们,于元朝初年以“诸王”之衔戍守西疆,辖撒里畏吾儿地区,并很快在抵御他的另一部分堂兄弟海都、都哇等人的战争中崭露头角。于公元1304年“以积年防边功,封诸王出伯为武威西宁王”。后“进封为豳王”,出伯死后,其子孙一袭武威西宁王衔,一袭豳王衔。系武威西宁王衔者,成为后来的撒里畏吾儿的组成部分,构成裕固族两大源流支系之一,即古代蒙古支系[7]。
综观上述可以看到,从河西回鹘到沙州回鹘、黄头回纥,历经3个世纪,这支操突厥语的回鹘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特质方面不断吸收新的资源,同天山南北、黄河流域的回鹘人日渐分离,但始终只是回鹘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河西回鹘只是裕固族的先祖之一。13世纪,沙州回鹘、黄头回鹘归属蒙古帝国的统治,蒙古人使这个古老的回鹘群体发生了质变,一个不同于蒙古的新的民族群体正在孕育之中,也就是说,以古代回鹘汗室氏族药罗葛(夜落纥)为首的一支古回鹘人,同蒙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出伯子孙为首的一支古蒙古人相互融合。起源于同一个蒙古高原,并且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回鹘人和蒙古人共同孕育着一个新的民族群体,一个不同于13世纪的撒里畏吾儿人-今日裕固人的前身。
14~16世纪,撒里畏吾儿处于察合台汗国(阿尔泰山以南的整个新疆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卫拉特蒙古人(阿尔泰山南北到巴尔喀什湖及中亚搭拉斯河一带)和明朝3种势力之间,他们都曾先后控制撒里畏兀儿地区。他们每年给察合台汗国、卫拉特蒙古和明王朝送上礼物,送上礼物可说是朝贡或者说是纳贡。后来,明朝在洪武年间,封撒里畏兀儿宗王黄金家族后裔卜烟贴木儿为安定王。还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立半军事性的8个卫所,史称“关西八卫”:安定卫、曲先卫、赤斤蒙古卫、阿端卫、罕东卫、苦峪卫(罕东左卫)、哈密卫、沙州卫。1430年,明廷借口西拉尧熬尔人劫杀察合台使者,派史昭率兵讨伐阿尔金山西端的西拉尧熬尔人,脱克脱不花率部与明军作战,尧熬尔人溃败。明军屠杀1 000余人,俘虏了西拉尧熬尔贵族脱克脱不花和男女340余人,夺马驼牛羊34万多只(头),这一部分西拉尧熬尔人从此衰落、灭亡。1446年,阿尔金山东端的西拉尧熬尔首领喃哥被卫拉特蒙古的也先汗封为平章,他们在战乱和贫困中,准备迁往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这个消息为明朝在肃州的军官任礼得知后,他率轻骑突袭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男女家眷隔离后,分别押送到了甘州塞内,明政府终究不相信他们,很快又把他们押送到了山东的平山、东昌一带,他们就是西拉尧熬尔8个部落之一[4]。
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的撒里畏兀儿,生活在一个瘟疫流行、战火连绵、自然灾害频繁的时代。撒里畏兀儿向东迁徙逃难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4点。
(1)察合台汗国东进至13世纪时,今新疆喀什噶尔以东以北各族大多仍处于佛教和萨满教传播地区。14世纪,这一地区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察合台蒙古贵族的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便开始以武力传播伊斯兰教。他们以叶尔羌、阿克苏、吐鲁番、哈密为据点向东向北进攻非穆斯林民族。
(2)明朝政府软硬兼施的政策。明朝政府一方面用砖茶和封号来试图让西拉尧熬尔地区作为“屏藩”,来阻挡察合台汗国、卫拉特蒙古和其他各种游牧人进攻的可能,实现其羁縻笼络的政策。同时,明朝政府常常以种种军事行动从东和南讨伐掠夺他们认为是“元裔”残元势力的西拉尧熬尔人,每一次征伐都要掳掠动辄几十万头(只)的牲畜,俘虏大量的青壮年人口带到内地分散为奴。
(3)内部混乱和残杀。西拉尧熬尔内部各势力的混战往往牵扯进外部各势力,如察合台、卫拉特人和明朝等等,从而引起更大的混战。而西拉尧熬尔人常常参与其他势力内部的混战和残杀。
(4)草原的退化和气候的恶化。自15世纪起,中亚大陆气候日趋干旱。巨大浩渺达5 350km2的罗布泊在当时已渐渐缩小干枯。阿姆河的茫茫芦苇消失了。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一带的草原不断被沙漠吞没,塔里木的沙漠日益扩大,很多草原被沙化和戈壁化。而在那些绿洲农耕地区,人们开始象蚁群般地多了起来。他们活动的足迹扩展到了阿姆河的芦林荒野和兴都库什山与印度接壤的崇山峻岭中,那里是著名的西域狮生长的地方,西域狮到17世纪已绝迹。中亚地区的大风、干旱、洪水、雨雪、冰雹、尘暴等灾害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是撒里畏兀儿人迁徙逃难的主要原因[4]。
汉文史料记载:正统11年(公元1466年),明朝的甘肃镇总兵官任礼令沙州卫全部入塞,初居甘州。随之,其他诸卫先后东迁入关,明政府的安置原则是“分散安插”。主要安置于“甘州南山”。而“甘州南山”的牧地,就是裕固族民间传说中的“八字墩”(今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草原,也就是以八字墩川为中心的黑河源头,察汗乌苏河—鄂金尼河(今八宝河)和八字墩河(今黑河西支)交汇处的草原[5]。
明朝在撒里畏吾儿地区设的关西8卫中,所谓的“撒里畏兀儿”仅指安定、阿端、曲先3卫部众,罕东、沙州、赤斤卫据史书记载明确为蒙古人。关外诸卫,即这些撒里吾儿人和蒙古人东迁入关后,他们按照当时中亚民族的传统,仍旧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从前的安定王卜烟贴木儿等人的后裔为领袖来维持内外秩序。安定王卜烟贴木儿就是后来裕固族历代大头目的祖先。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任大头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1任县长安·贯布什嘉的祖先。正是这种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条件和共同的政治生活环境,使得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尧熬尔,也就是今天的裕固人逐渐融合形成。
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裕固族的重大灾难,导致人口锐减、牧地缩小、牲畜大批死亡。在裕固人中,不少老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西至哈至”迁过来的。在一首流传甚广的裕固族历史民歌中唱道:
听老辈人说着唱着才知道了/西至哈至是我们的故乡/许多年前那里灾难降临/狂风卷走牲畜,黄沙吞没寺院和帐房/……/走过了千佛洞,穿过了万佛峡/……/来到了八字墩辽阔的牧场/登上了祁连山/……。
据裕固族的民间传说,东迁时,撒里畏兀儿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及狩猎业。东迁后,居住于肃州(今酒泉)以东的撒里畏兀儿人,因与汉族杂居,逐渐向农耕文化过渡。而聚居于甘州南山的诸部落,仍保持传统的游牧文化,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明朝政府在甘州(今张掖)西南70里处设置梨园堡,派兵驻守,作为辖制撒里畏兀儿人的据点,明政府还颁发给大头目管辖八字墩一带草原的执照[1]。
清康熙37年(公元1698年),内迁的西喇古尔黄番仍旧游牧于祁连山腹地及南北两麓,疏勒河源头的安定卫的后裔部分迁至今康乐区一带,部分人仍留在黑河以东的鄂金尼苏美(即黄番寺)附近,这两部分人分别成为后来的大头目部落和鄂金尼(曼台部落)部落。将西喇古尔黄番划分为“七族”,即史称“七族黄番”,并分封部落头目。大头目被封为“七族黄番总管”,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帽。同时又实行“分而治之”策略,将居于甘州南山一带,主要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的诸部落划归梨园营都司管辖;将居于肃州塞内主要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诸部落隶红崖营,属肃州镇总兵所辖。其中,“黄番七族”又有东五族和西二族之分。后来,“七族”实际上已经演变为10个部落[1]。
还有一个特殊的集团。酒泉市黄泥堡尧熬尔属突厥语族尧熬尔人,目前全部使用汉语。据记载,明代1488~1506年就有裕固族人生活在那里。他们从清代中期开始经营农业。部分人是清代1636~1662年迁去,还有部分人是清朝几次西征准噶尔和青海时从梨园河一带的南山逃难到了那里。主要以萨格斯部落和呼朗格部落的人为主。当时在酒泉地区的南乡、北乡、嘉峪区、上黄泥堡和下黄泥堡等地有许多尧熬尔人。1958年酒泉上黄泥堡和下黄泥堡共有112户人家。现分布在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1]。
综上所述,裕固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其直接族源的河西回鹘,到直接祖先“黄头回纥”,汉到元代的“撒里畏吾”直至明代的“撒里畏兀儿”数千年的历史,是一个新的民族群体不断从交融中分离,从迁徙中逐渐形成的历史。
2 裕固族的宗教信仰
2.1 裕固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从裕固族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宗教文化的相互交融多种多样可以看出,裕固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延续中,曾经信仰过多种宗教,其中可以肯定的萨满教、摩尼教、古西域佛教、藏传佛教都是裕固族在历史上先后信仰过的宗教,并对其社会生活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可以说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仰的古老宗教,广义的萨满教包括族萨满出现以前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一些原始宗教。摩尼教文化的遗存在裕固族文化中反映的最少,在裕固族先民-回鹘人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7世纪中叶,也就是尧熬尔在东迁至祁连山100年后。藏传佛教传入,首先大力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因而,藏传佛教自然地成了裕固族人民的主要信仰,直接影响着裕固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充分体现着裕固族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等。
2.2 裕固族宗教习俗
随着历史的发展,裕固族地区的宗教活动虽然减少了,但是仍保留着一些民族习俗。如参加寺院举办的佛事活动,祭鄂博,家中供奉佛龛、丧葬时请喇嘛颂经超度等。
(1)佛事活动 寺院组织的佛事活动每年定于正月、4月、6月、10月举行,每月的第15日还要举行一次小会,活动期间信教群众都会自愿来寺院参加活动,烧香磕头,敬献祈祷,听颂佛经。
(2)祭鄂博 鄂博的祭坛是用柏木制作成的一个方形木框架栽在地上,正中竖一个高高的幡杆,杆顶上饰有日月型图案,杆上挂满大大小小写有经文和图案的嘛呢旗并向四周延伸拉有牛、羊毛绳,绳上拴满了哈达、牛羊毛等,在鄂博旁较平坦处建有煨桑台(池)。鄂博一般建在山顶,山岔(崖豁)或山坡上,其建立的位置、祭祀时间均由大寺院(如裕固族绝大多数去塔尔寺)的喇嘛高僧根据建鄂博的目的、作用,民众住牧地的地形地理情况等,经颂经、占卜等各种仪式后最后确定。鄂博的祭祀形式可分为3种。①个人祭祀,出门人路遇鄂博时,捡路旁白石头垒于其上,然后燃柏香(如身边带有),膜拜祈祷。②家庭祭祀,家长带着全家人及祭祀用品到鄂博上祭祀,祈求驱灾降福。③部落或全村祭祀,是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祭山神的活动。等到祭祀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再举行赛马等文体活动和其他聚会内容。
2.3 裕固族的守护神和神山
(1)白哈尔 守护神白哈尔在神山杰乌拉尔,杰乌拉尔在今肃南县马蹄乡二加皮村的山地草原。传说杰乌拉尔神山上住着以主神白哈尔为主的5大神,藏语名称是:主中部的俄由西土格吉杰鲁神即白哈尔、主东部的河由西斯格吉杰鲁、主南部的拉布西元旦吉杰鲁、主西部的那布希桑给吉杰鲁、主北部的香恩希俄成里杰鲁。叫做尧熬尔5大神。
(2)陕巴美尔 传说陕巴美尔是古代尧熬尔人的一个大将,死后成为守护神,陕巴美尔的陵墓在今马蹄寺一洞窟中(现在洞窟里面部分塌陷)。如今裕固人已做为祖先或守护神来祭祀。
(3)乃曼额尔德尼山 裕固人叫做乃曼额尔德尼的雪山是今青海省祁连县的牛心山或八宝山,裕固人的先辈们东迁到祁连山后,中心牧场就在乃曼额尔德尼一带,他们认为是整个祁连山地区的镇山。乃曼额尔德尼即“八宝”之意。山下有裕固族人古代的鄂博遗址。不远处是古代裕固人的鄂金尼寺院(汉文史料中叫“古佛寺”“黄番寺”)。
2.4 裕固族的习惯法
1958年前在关于狞猎分配、尊老扶幼、互相帮助、婚姻嫁娶、财产继承、宗教祭祀,偷盗、打架、杀人、草原纠纷和家庭诉讼等方面采用习惯法。这些习惯法便是道德规范,习俗礼仪,宗教戒律组成了社会规范,即民族习惯或是叫习惯法。
(1)习惯法的执行者 部落内的一切案件都由部落头目,总圈头,辅帮和“老者”审讯处理。部落头目可以对下属人民任意处罚用刑。例如:大头目到鄂金尼部后,在宴席上因猎户扎西才尔丹对其不够恭敬,而对其施以柳条抽打,罚一匹马给大头目作为了结。
(2)判案方法 ①捞油锅 例如:19世纪30年代,辅帮乔治,万代和在鄂金尼草地抢牧的藏族阿日克部落的富户努日恩拜勒发生争执,乔治、万代抓了努日恩拜勒2只羊。努日恩拜勒给其部落千户却日琼上诉。裁决由千户却日琼主持,在一个铁锅内放一白一黑二石,又倒入了水和泥,烧沸后,由原告赤手捞石,规定捞到白石为赢,黑石为输。原告日努恩拜勒赤手在滚沸的水中摸了2次,没有摸到。千户裁决为乔治、万代赢,努日恩拜勒给曼台部赔了20头牦牛。②神羊裁决 裕固语叫神羊为“赛德尔马勒”,意为各户族庇护神的牲畜。裁决时有部落头目,辅帮等人参加。原被告各牵来一只“神羊”,煨桑叩头各呼其“布尔汗”的名称,然后裁决人将加奶子的水(白水)从羊尾浇到羊头,然后将普通水从羊头浇到羊尾。这时,如果那一只先抖其身上的水,羊的主人便胜诉,输方便赔偿牲畜。③糌粑裁决 这是一种将写有字的纸条分别用糌粑包起来,置于盘中,裁决人端来让原告和被告各拿1个,掰开看定输赢。④投水死刑 即在死刑犯脖子上捆石块将其投于河水中淹死。例如18世纪中叶,曾将造成部落混乱的赛木特尔判为死刑,但终未执行。
3 裕固族的语言文字
3.1 裕固族的文字
裕固族无论操那种语言都曾使用过不止一种文字。按裕固族的语言分两部分。裕固族的远祖突厥回鹘人曾使用过北欧式字母的鄂尔浑文(又叫突厥文),在蒙古高原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等。后来还有自右向左横写的摩尼文,还有自左而右的婆罗米文。当然,通行普遍而使用长久的是来源于古代粟特文字的古回鹘文。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帝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和梵文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元世祖诏令全国通行,不仅拼写蒙古语,还要拼写一切语言,1958年前大部分的寺院有藏族人叫做“霍尔·意格”的八思巴字经书。无论怎么说,裕固族的祖先不仅有文字,而且使用过不只是一种文字。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回鹘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回鹘体蒙古文)。接受藏传佛教后,渐渐在宗教上或很小的官方范围内使用藏文。1949年后,开始接受汉文。
3.2 裕固族的语言
(1)东部裕固语 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于康乐乡、皇城镇东部和大河乡东部。东部裕固语同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蒙古语比较,它居于特殊的地位。粗略地说,在语音方面它和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的共同性多一些,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它又与蒙古语的共同性多一些。
(2)西部裕固语 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主要分布于大河乡、明花乡、皇城镇西部。
致谢: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肃南县畜牧局兰永武同志、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也得到甘肃农业大学胡自治教授的亲切指导。特此致谢!
[1] 铁穆尔.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7-182.
[2] 肃南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尧熬尔文化[DB/OL].[2007-01-06].http://www.yovhur.com.
[3] 胡小鹏.元代西北民族历史与民族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4] 陈高华.明代土鲁番哈密文史资料汇编[G].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5] 莲花持明.莲花生大士全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