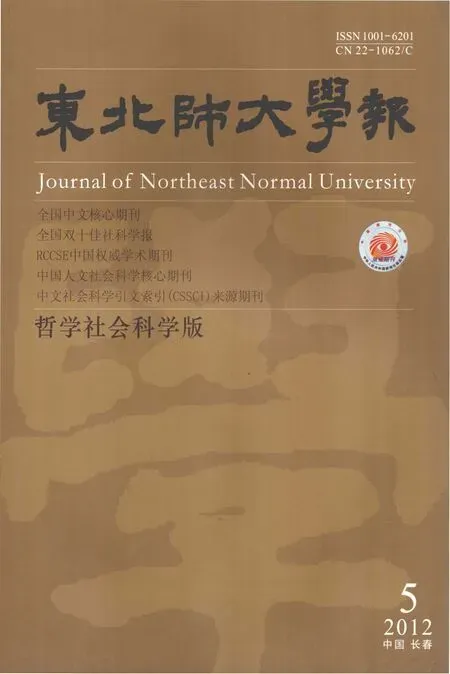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刘洪波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刘洪波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解释著作。洪兴祖创制并选定“补注”体来解释《楚辞》,有其必然性。它是洪兴祖针对《楚辞》文本的抒情特征和以往《楚辞》解释存在的不足,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藉解释体式的传统和经验来选择的结果。
洪兴祖;《楚辞》;解释;“补注”体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从经典的解释来看,古今解释者在解释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解释体式,“补注”体是解释体式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宋代洪兴祖作《楚辞补注》,他创建并选定“补注”体式解释《楚辞》文本,并不是随便或偶然的,因为“解释体式的创建和选定,不仅要针对解释对象的性质和特征,要依据解释主体的视角和目的,而且要凭藉解释学的传统和经验”[1]156。
一、洪兴祖“补注”的创制——针对《楚辞》的性质和特征
每部经典文本都是作者与解释者之间的纽带,文学的特性决定文本本身不能脱离解释者独立存在。洪兴祖选择《楚辞》进行解释,是与《楚辞》的性质和特征密切相关的。
(一)《楚辞》是抒情的载体
《楚辞》与政治、宗教体制强化下的国家经典不同,它是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与解释中逐渐获得权威性的,“这有利于诠释者个体的参与,其作为经典在历史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对诠释者的约束力相对于‘神圣性经典’而言比较小,诠释者所处的时空特性,如学术思想、政治际遇、文化心态、个性气质等,便具备更大的张力,对诠释的影响更大。”[2]6解释者对《楚辞》解释的空间更广阔,解释行为少了些国家意识形态的约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3]116。
不同解释者都是从其自身时代、生活、经验、文化以及性格、审美趣味等方面出发解释《楚辞》、品评屈原的。从汉代到唐五代,文人雅士或对屈原的忠君思想加以褒扬,或对屈原的沉江发出感叹,或对屈原的特立独行给予称颂,他们对屈原及《楚辞》的臧否都与自身的境遇有关。正如郑振铎所言:“屈原成了后代封建社会里一切不得志、被压抑甚至在大变动时代里受到牺牲、遭到苦难的人的崇敬和追慕的目标。”[4]160
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使得忧患意识成为当时士大夫个体必备的修养,并转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而忠君爱国成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基本内核。宋人的爱国忧民往往借追慕屈原的形式表现,文人志士对屈原的怀念和仰慕层出不穷,对《楚辞》也备加亲睐。
在宋朝爱国人士反对与金人和议的主战派的主战声浪中,有“不信亦信,其然岂然,虽虞舜之十二州皆归王化,然商于之六百里当念尔欺”的呼声,“可以想象彼等乃欲效法屈原之爱国精神,以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5]88“两宋士人也正因为屈原式的处境在历史时空中又复‘重演’,向屈原敞开了理解的大门”[6]35。
洪兴祖从少时得《楚辞》十卷到《楚辞补注》最终刊行,对《楚辞》的浸润长达数十年。期间包括他目睹北宋诸般乱象的少年时期,壮志难酬、仕途坎坷的青壮年时期和临近含冤莫白郁郁而死的人生末年。两宋的社会危机、个人的生存境遇使他借助解释《楚辞》表达自己的情怀,是“特定的时代为他理解屈原提供了最好的参照,个人的遭遇使他体味到屈原作品的真谛,相同的感受使他产生深刻的理解。”[7]50
(二)因《楚辞章句》之不足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是存世最早、最完整的《楚辞》解释文本,是《楚辞》解释的奠基之作。这一《楚辞》训诂派的代表性著作,对《楚辞》文本的解释重在释义和校勘。
王注重训诂不重考据,所引古书很少著其所出,有些地方径直缺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逸注不甚详赅”。
此外,王逸字词注释虽多精当,但亦有不少讹误之处。王逸在引用史料时,或未见原著,或转引他书,故有时所言也与史实不符。对此,朱熹《楚辞辨证》就曾指出:“秦诳楚绝齐交,是惠王时事。又诱楚会武关,是昭王时事。王逸误以为一事,洪氏正之,为是。”
王逸说“夫《离骚》之文,依讬《五经》以立义焉”。他用经学家解经的方法相互比附屈骚精神,处处都有依经立论的体现。在具体文句解释上,频频征引《诗经》、《尔雅》、《尚书》、《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来比附,出现了不少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地方。
《楚辞章句》版本流布的方式与历史均较为复杂[8]61。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此书既古,简册迭传,亥豕帝虎,舛午甚多。”宋代苏轼尝亲校《楚辞》十卷,晁补之则通过编辑《楚辞》、《续楚辞》、《变离骚》等书,来表达对屈赋的看法,而据朱熹《楚辞辨证》所言,陈说之曾整理过《楚辞》传本的篇次,总之,“通过考证可以看出:宋代《章句》流传既广,异本甚多,文句讹误现象十分严重。”[9]74
综上所述,洪兴祖之前及当时,《楚辞》流传的最主要注本《楚辞章句》存在着诸方面的问题,亟待整理,所以洪兴祖在苏轼《楚辞》手校本的基础上,以所见诸本参校考异补正。
二、洪兴祖《楚辞》解释的视角和目的——补不足、发己意
选择何种经典文本进行解释,或在经典解释中阐发何种思想,依赖于解释者的主观先见。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正如历史家从事实的汪洋大海中选择出对自己的目的有意义的那些事实一样,他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出那些,而且也只抽出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历史意义的标准是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于他的合理的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能力。”可见,任何解释都带有解释者的主观诉求,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洪兴祖选定《楚辞》解释,是在其解释视角和目的的驱使下展开的。
(一)补《楚辞章句》之不足
洪兴祖力注《楚辞》,以“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是其目的之一。对此,《郡斋读书志》云:“凡王逸《章句》有未尽者补之”,《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说的就是洪兴祖撰作《楚辞补注》,以此来“补王逸《章句》之未备”。
整体而言,洪兴祖对王逸注进行补充、完善和阐发的方面有:(1)荟萃众本,考录异文。广征异本,罗列异文,详加校勘,对考辨版本和文字异同提供丰富资料。(2)凭依书证,援引赅博。广引书证,训释考订,援据赅博,征引宏富。(3)匡正谬误,驳斥旧注。对王注说解词义或引用史料的讹误之处,予以补充驳正。(4)载录遗文,保存佚说。搜集了许多后来散佚的材料补释《楚辞》,这些材料赖洪补得以保存。(5)补释语意,疏通王说。对王注未注者多加以补释,对王注说解不明者加以疏通,对说解简略者加以补充。(6)罗列众说,设问存疑。遇到各家之说互有矛盾而不知取舍时,仅列举诸说以备参证。(7)阐发屈意、品评公允。洪兴祖拓展了《楚辞》意蕴,阐发了屈意,评价了屈原思想。
关于“补注”之所补,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曾说“重点在补义”,“其补义以申王为主,或引书以证其事迹古义,或辨解以明其要。”可见,洪兴祖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王逸《楚辞章句》进行了补正,的确是做到了缺者补之,误者正之,略者详之,浅者深之。
(二)借此发一己之私意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解释是一种当下的介入解释者主体意识的个体创造性行为。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反复申述的:“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洪兴祖进行《楚辞》解释的主观动因,是受到了时代情势的激励,他的撰述行为是两宋时代环境的产物,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洪兴祖个人思想情感与主观诉求的凝合。他的《楚辞补注》体现出了他在进行文本解释时所持的态度和个人的思想倾向。
洪兴祖自小喜好《楚辞》,可谓早已仰慕屈原的高风亮节。后来国事趋乱,奸小横行,忠良遭害,民生凋敝,他有感于时政,自己又壮志难伸、横遭贬斥。所以,概括而言,洪兴祖解释《楚辞》的动因,除“不满旧注、补前贤之不足”之外,还有:感于时政,欲借古以讽今;壮志难伸,寄寓悲愤之情;仰慕屈原,期能企贤入圣。这也是洪兴祖解释《楚辞》的视角和目的,也就是说,洪兴祖以《楚辞》解释为载体,寄寓了自己对宋代时政、对自身遭遇、对屈原品格等方面的态度和思想情感,亦即借解释《楚辞》来抒发己意。
洪兴祖解释《楚辞》的视角和目的正是“由于北宋多位学者之努力,《楚辞》之研究愈见兴盛,所给予后人之宝贵心得亦复不少,然而就全面性及精密性而言,代表作依旧付诸阙如,学者所凭藉者大抵仍以王逸《章句》为主。兴祖鉴于王逸本流传日久,文字多歧,更重要者,王注虽称最古,实有若干疏漏与致误之处,亟待后人加以补充与改正;兴祖既痛朝政之不修,复因己身之遭贬而对屈原寄予崇高敬意与深刻感情,故而不畏权势,不辞劳苦,尽力于‘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卒能完成是书,裨益后学。”[5]93
三、“补注”体式的选定——凭借解释学的传统和经验
解释者在解释典籍时,依据解释对象的特点和不同的解释取向,进而采用某种解释体式,体现出了解释者看重了某种解释体式的特点。洪兴祖创建“补注”体并将其书命名为《楚辞补注》,“补注”一体在形式方面的开创性,是洪兴祖凭借着解释学的传统和经验来选定的结果。
(一)“笺”体启示下的创制
“洪补作为古文献阐释史上特有的一种体例,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就形式而言,洪氏补注一书,前之未有,亦可谓发凡起例。”[10]64而“补注”体例的这种发凡起例,不是凭空而造的,而是在对传统的解释体式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和改制。
依周光庆来看,“补注”体是在“笺”体启示下产生的。他说:“笺体。这是郑玄在《毛传》基础上重新解释《诗经》时创立的解释体式。郑氏《六艺论》自云:‘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已经宣告了他注释《毛诗》,创立笺体的主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而指出:‘康成特因《毛诗》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笺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使学人进一步认识了这种解释体式。而深入考察郑氏的《毛诗笺》即可以发现,《郑笺》对于《毛传》力争做好三种工作:一是《传》文解说隐晦质略者,则加以申述,使之明确;二是《传》文解释片面疏漏者,则予以补充,使之全面;三是《传》文训释可能失误者,则辨而正之,使之完善。”[1]163“从中国古典解释学体式的实际发展来看,‘笺’这种解释体式启示或引发了后世的疏、补注、考辨三种新的解释体式。”[1]163
由此,不仅可以明确“笺”体创制的目的、特点,还可发现“补注”体与“笺”体两者存在渊源关系。洪兴祖好古博学,精于校雠,对解释体式必有深透的认识。从前文所言《楚辞补注》对《楚辞章句》之所补,亦能看出“补注”体在对解释内容的申述、补充、辨误等方面,是对“笺”体的拓展与延伸。
(二)“补注”体命名之含义
每一种解释体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在其命名中往往有所体现。如集注,顾名思义就是集众家之说而为之注。由每种解释体式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来看,解释者在解释经典时命名或选定不同的解释体式,体现出不同的解释取向。
就“补注”的命名而言,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说:“洪书盖补王逸章句之未详者,故谓之补注。”可以说,洪兴祖创建“补注”体并将其对《楚辞》的注释命名为《楚辞补注》,这“补注”体在形式方面的开创性,不仅说明洪兴祖撰作《楚辞补注》之初有明显的“补《章句》之未备”的解释倾向,也说明这种解释体式在实际的解释活动中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解释体式。
对于“补注”,黄建荣认为“这种注释体式,与传统训诂学中的‘义疏’比较相似”[11]32。但其不叫“义疏”而叫“补注”,说明“补注”体并不等同于“义疏体”。具体而言,就是“补注”作为一种新的解释体式,洪兴祖虽以疏解王注为主,但并未完全执行疏解原文及注的功用,亦未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
故此,从“补注”体的命名来看,是因为洪兴祖面对的解释对象——《楚辞》的注本存在诸方面的缺憾,而洪兴祖解释《楚辞》的目的就是补不足、发己意。对洪补的价值,岳书法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不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将王注大大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在形式方面更具有开创性”[10]68,“使 中 国 传 统 传 注 体 系 中 多 补 注一体。”[10]64
(三)“补注”体重补之分析
洪兴祖“补注”体“补”的意图非常明显,这在具体的补注内容的量化分析上亦有体现。
今所传洪兴祖《楚辞补注》,非宋时付梓旧貌,已散入其所作《考异》和被其所引用之《释文》。针对《楚辞》正文,就散附后的今本《楚辞补注》具体训解补释体例来看,李温良曾统计归纳为三类十四种[5]152-164。今以2002年修订本《楚辞补注》为本,重新考释,大体得训解补释的体例,共有三大类二十一小项:(一)正文下有王注者13种:1.王注+考异+洪补;2.王注+考异+五臣注+洪补;3.王注+考异+五臣注;4.王注+考异;5.王注+五臣注+洪补;6.王注+洪补;7.王注+五臣注;8.王注+考异+柳宗元《天对》;9.王注+考异+柳宗元《天对》+洪补;10.王注+柳宗元《天对》;11.王注+柳宗元《天对》+洪补;12.王注+五臣+考异+洪补;13.王注+五臣+考异;(二)正文下无王注但有洪补者5种:1.考异+洪补;2.考异+五臣注+洪补;3.洪补;4.五臣注+洪补;5.五臣注+考异+洪补;(三)正文下无王注亦无补曰云云者3种:1.考异;2——五臣注;3——考异+五臣注;
综观上举,以类而言,第一类之实例最多,第二、三类之实例较少,究其成因,“观兴祖著作之意,乃以补正王注为主,故全书之中王逸无注而兴祖重加诠释者实仅少数。”[5]164其次以项而论,则第一类中之(1)(王注+考异+洪补)、(2)(王注+考异+五臣注+洪补)、(6)(王注+洪补)诸项为最多,第二类之第(5)项(五臣注+考异+洪补)及第三类之第(2)项(五臣注)为最少,这也与洪兴祖补王注为主的解释态度有关。“其遇王逸有注者则往往详加考订,并广引他书以疏通证明之……而洪氏遇王逸无注者,乃专就其中重要而难晓之字句补释之,余者一仍其旧”[5]164。可见,洪兴祖是依据王逸注释之详略程度来决定补注与否,主要取向在于对王注的是正阐发,所以这三类二十一项中,其前有王注的类或项出现得较多,而其前没有王注的项很少出现。从洪兴祖的补注能看出洪兴祖创制“补注”体的一个意图所在。正如李温良所言:“若细绎洪书各卷之形式,乃至各句之训解,益知其创作之旨,诚为补王注之未备而发,期能明屈赋于千载之后矣。”[5]149
[1]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邹福清.“诗人”、辞赋之士:经典诠释传统与屈原形象定位的文化内涵[J].理论月刊,2007(11).
[4]杨金鼎.楚辞研究论文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5]李温良.洪兴祖《楚辞补注》研究[D].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
[6]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J].中国文学研究,2005(1).
[7]马建智.洪兴祖评价屈原思想的卓识[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6).
[8]邓声国.《楚辞章句》流传及版本考[J].兰台世界,2008(8).
[9]李大明.宋本《楚辞章句》考证[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10]岳书法.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4(6).
[11]黄建荣.《楚辞》古代注本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2.
The Research About the Style of Chu Ci Bu Zhu from the Hermeneutics Perspective
LIU Hong-bo
(Chinese Department,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Chu Ci Bu Zhu is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of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books whichs named“BuZhu”.It is inevitable that Hong-Xingzu created and selected the“Buzhu”style to interpret Chu Ci.It is the result of Chu Ci's nature and Lyric features,with Hong Xingzu's purposes of complementing previous disadvantage and expressing his thoughts and emotions,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Hermeneutics about the style of interpretation.
Hong Xingzu;Chu Ci;Interpretation;the“Buzhu”style
I207.223
A
1001-6201(2012)05-0133-04
2012-05-22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315)。
刘洪波(1974-),女,吉林通榆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
——王逸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