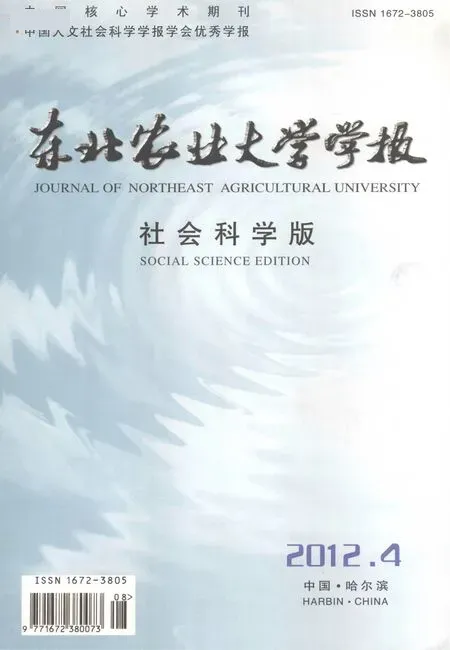论隐喻——修辞与认知的辩证关系
葛向宇 孙跃鹏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识与否,我们一直都在使用隐喻。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对隐喻的研究从未停止。作为一个令人惊奇的研究学科,隐喻既是语言构建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人类建立并扩展自己思维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表现了对隐喻研究的狂热,被称为“隐喻热”。而1980年莱克夫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针对隐喻的文章层出不穷,这在语言学的研究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本文在对比和评述的基础上将隐喻理论分为修辞派和认知派,指出隐喻的修辞性和认知性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隐喻应被视为一种转换生成的动态过程。
一、隐喻的修辞性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很久以来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各个领域的学者一直对这一现象进行着不断的思索和探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隐喻的理论研究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各个不同的研究流派相继形成,导致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的隐喻研究出现热潮。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隐喻研究的重点已从修辞性转向了认知性,这种转变开阔了人们对隐喻的认识。但修辞性作为隐喻的一大特性,自柏拉图开始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了,对它的忽视,甚至摒弃是完全错误的,它的合理成分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与继承。
众所周知,把隐喻纳入修辞学范畴的第一人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著《修辞学》中指出,隐喻是一种隐含的类比,或者说是两个事物相似性的比较,这就是隐喻理论中的“比较论”。“比较论”把隐喻归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修饰话语的手段,一门说话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人们使用隐喻时既能从中获得学习的愉悦,又能借此展示自己的博学。此种观点使得隐喻成为欧洲雄辩术和文体学中备受关注的修辞格之一。一般来说,要想在日常交流中使自己的话语具有“不同寻常”的风格,就要借助修辞性话语,因为修辞性话语可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而隐喻以其新颖、精炼及委婉的特征为增强话语的修辞效果提供了可能性。对于隐喻修辞功能的研究,使人们在进行话语构建的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应用隐喻,从而让所使用的语言更有说服力,更具创造性,在美化自己语言的同时,还能和对方达成一种亲近感。
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修辞观点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比较论”建立在两种事物相似性的基础上,而这种相似性是很难界定的,因为它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相似关系,又受复杂的语境因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对隐喻机制进行解释是不够严谨的。除此以外,亚里士多德仅仅把隐喻研究局限在隐喻的修饰性上,视其为语言润色的工具,认为隐喻仅仅是对常规语言的一种偏离,隐喻功能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由于时代历史的局限性,他并没有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加以进一步的研究,而是止步于文体特征的层面。“比较论”对隐喻的研究之所以只局限在辞格层次,主要是因为其研究的层面不是句子,而是词汇。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不能见到隐喻作为人类认知手段的论述。换言之,“比较论”对隐喻的研究是以逻辑类比为基础,从指称之间的相互性入手,偏重于对隐喻现象本身的研究,在修辞性的研究方面功不可没,但并没有全面地解释隐喻的机制和实质问题。
二、隐喻的认知性
人们对隐喻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狭到宽的发展阶段。在隐喻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无疑是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此书由莱克夫和约翰逊共同编著,它摆脱了以文体学和修辞学为基础的隐喻理论的束缚,隐喻不再是语言内部的修辞手段,而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把隐喻和人类的认识过程联系在一起,让人们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认识隐喻。
对于隐喻,莱克夫更多的是深层次地研究其认知机制,不再把隐喻视为语言的表面现象,隐喻可以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断,使语言结构化,从而获得巨大的语言生成力。莱克夫和约翰逊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莱克夫等人不再把隐喻视为单一的语言现象,因为语言只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换言之,两种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被放在同一语言结构中相提并论,是因为在认知领域中人类对它们的相似性产生了联想,继而利用这两种事物的相似相通来评述、解释、表达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这被视为隐喻的认知基础。莱克夫等人从认知的角度较前人更加系统地对隐喻的本质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概念隐喻的观点,全面开启了人们对隐喻的认知研究。如果把莱克夫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两种观点存在着些许联系,都是借助一个事物来谈论另一个事物,但莱克夫等人对隐喻的定义则更加宽泛。不可否认,概念隐喻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隐喻观的一个重大突破,为隐喻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不仅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人类认知的发展也同样意义重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其实在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这也就是莱克夫所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为它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基础。人类在语言的最初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词汇大多是用来表示具体的事物的,对于抽象概念的表达,人类往往是借助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当人类从这些具体概念之中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也就构成了人类的隐喻思维体系。
从对语言变异形式的研究,到对人类认知规律的研究,莱克夫等人的隐喻理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的认知也不再局限于对单个事物的孤立认识,而是要从众多的事物中发现共同点,这就要求人类具有创造性和联想性。隐喻思维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力,它是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从认知的角度来说,隐喻既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构建对已知世界的了解,又可以帮助人们利用已知的世界来了解未知的世界。
三、隐喻的修辞性和认知性的辩证关系
人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一件事情看懂了,一篇文章读明白了,但却表述不出来,尤其是英语学习者经常会遇到这样问题,犹如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嘴里却说不出来,这就如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思维想到了,但是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述出来。难以言表、难以名状的感觉,就是人们在思维的内核下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外衣。当你无法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便无法与他人分享,无法交流、沟通,所以我们要注意语言的修饰加工,让形式与内容有机地融合到一起,相辅相成,合二为一,更大限度地发挥隐喻的作用。
隐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对它的兴趣和关注由来已久,各个领域的学者一直对这一现象进行着思索和探讨。传统的隐喻理论把其视为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研究其如何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表达,注重语言层面的分析,反映了隐喻语言运作的特征,认为隐喻仅仅是附属于语言的一种修饰性成分。当代理论,尤其是认知学派,则把隐喻扩大为语言乃至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不可或缺的特征,揭示了隐喻的概念性本质,关注人们是如何借助隐喻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两种观点分别阐释了隐喻某一方面的特点和性质,都对隐喻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肯定的,但孤立地来看,他们并不能对隐喻的机制问题给予较为全面的解释,前者未触及隐喻是如何形成的,而后者则忽视了隐喻在修辞方面的重要性。事实上,隐喻是具体语境条件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隐喻的修辞性与认知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而非截然对立的,因而对隐喻机制及特点的分析不应孤立于某一方面,而应是全面的、多视角的。把隐喻视为一个有机体、生命体,其必然有内外,过去只看到外部语言现象,现在只顾究其本质。只有内外兼收,才能真正认识其全貌。修辞性与认知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是隐喻这个生命体中两种共存的力量,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隐喻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同时又可以把对世界的感受有效生动地表达出来。在交流过程中,这两方面处在一个不断交替,不断循环的状态下。语言与思维同源同生,互相转化,语言是思维的起点和归宿,思维为语言提供更新和再生的动力。人们理解事物是从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这其中隐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隐喻不管是进行修辞性的研究还是认知性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隐喻的操作特征,因而两者之间是互补的而不应该是截然对立的。笔者认为修辞性与认知性地位平等,不可顾此失彼。正因如此,本文试从修辞、认知两方面对隐喻展开讨论和探索,力图辩证地看待隐喻的双重身份,博采两家之长,贬抑其短,指出隐喻应被视为一种转换生成的动态过程。修辞性和认知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互为表里的,缺失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无法解释隐喻的巨大生命力,更无法推动隐喻的发展。统而言之,修辞性和认知性分别代表语言与思维两个不同的层面,虽然各自独立,分属不同机制层面,但两者却统一于隐喻,并不断地相互作用,推动语言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发展,而隐喻则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
本论文对隐喻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目的,是试图说明隐喻不仅表现在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人类语言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思维支配语言,语言表现思维。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把隐喻的两方面研究结合起来,把隐喻的修辞性与认知性同时纳入视野,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探索隐喻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有利于丰富和完善隐喻的语言学阐释理论,推动隐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Aristotle.Rhetoric and Poetics[M].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54:227 -229.
[2]Lakoff,G.,Johnson,M.Metaphor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41 -44.
[3]曹务堂.隐喻的认知性立体透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3):49-53.
[4]束定芳.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外国语,1998(6):10-19.
[5]王萍.隐喻的修辞性及认知性[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3(1):54-60.
[6]李勇忠.认知语境与概念隐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26-28.
[7]刘振前.日常英语中隐喻的普遍性及其与认知的关系[J].外语教学,2002(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