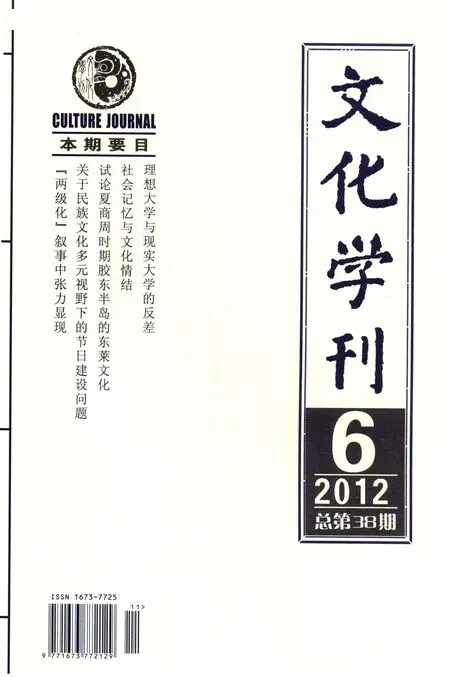天人交合中的神圣与敬畏——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的技术观
梁 海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00)
创世神话是对世界起源作出解释的神话。著名神话学家珍妮·佳利和汉森·米沙在其合编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中的原型和母题》中对创世神话作了如下界定:“作为一种最初的原型,创世神话解释宇宙的起源,描述世界及其有生命和无生命是如何被创造的,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是如何出现的。它还解释整个宇宙,包括天地原初的状态、天地间的一切存在物,人类和诸神的起源和等级制度的来源。”[1]实际上,创世神话折射出的技术观,往往反映出远古先民对技术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些技术观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走向和本质属性。本文通过对创世神话的爬梳和解读,挖掘其中蕴含的技术观,以此从一个新视角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同时,这些技术观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 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
一
创世神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技术观。在中国古人的眼中,世界在出现之前是一片混沌,这是宇宙诞生前的状态,即所谓的前宇宙状态。“关于世界最初的状态,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混沌’。”[2]有关混沌的神话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下母。”在老子看来,宇宙的最初状态是“混成”,亦即是混沌。继《老子》之后,《易传》继承了老子道家的宇宙论哲学并给与了新的阐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阐释了宇宙生成的过程。“太极”指的就是天地混沌未分的原始统一体。
那么是什么力量劈开混沌,创立了宇宙呢?创世神话中告诉我们是技术。这一点在著名的盘古开天辟地创世神话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3]
盘古使用技术的力量分开了天地。“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在斧与凿的这些物性工具的打造中,天与地分离了,结束了混沌,诞生了宇宙。显然,盘古斧凿印记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实际上,技术不仅“斧凿”出了宇宙,也开启了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产生于技术开始的地方。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同样讲述了神灵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人类的故事。这些神话中的主角女娲,是人类缔造者。最早有关女娲的记载当属屈原的《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认为“有”为“育”的讹误,“育体”即培育人的身体,“盖南楚有女娲化生万物之说。”[4]王逸《楚辞章句》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中“化”为化育化生之意。所以许慎《说文解字》对女娲的解释是:“古之圣女,化万物者。”对女娲造人记载最为详尽的当属《太平御览》: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绳亘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智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亘人也。
在这则神话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则与技术相关的信息。第一,女娲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了人类。“抟”在《说文》中的解释是:“抟,以手圜之也。”也就是团捏制作的意思。显然,“抟”这项技术操作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工艺,由此,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对待技术操作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人类的高低贵贱之分。或者说,技术不仅打造了人类本体,而且也打造了人类的等级。第二,制造人类所使用的工具材料是泥土。泥土松软可塑,在我国古代一直是制陶技术最重要的原材料。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古代原始的技术观念中带着浓郁的农耕民族文化意识。
可以想象,在人类诞生初期的艰苦年代,还在茹毛饮血的先民已经感受到了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将技术设想为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自身的神圣工具。但是,就在人们享受到技术福祉的同时也对这种足以改造自然的巨大威力敬畏而恐惧。这种情感在另一则著名的创世神话“浑沌开七窍”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篇》)
这则寓言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倏和忽出于好心,希望能为浑沌凿出七窍,结果却意外地导致了浑沌的死亡。七窍是人的特征,也明显地成为人后天心智的隐喻。浑沌是神的原型,也是宇宙的初始状态,在那样的状态中是没有人类的心智的。于是,已经由神向人蜕变的倏和忽 (显然他们已经有人的七窍),强行为浑沌打凿七窍。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凿”这一技术活动再一次出现。“凿”所代表的技术话语言说着人类不可避免的技术命运,正是因为“凿”才结束了充满神性的永恒的“浑沌”,在“倏忽”的瞬间开启了人类的技术时代。浑沌的死意味深长,它是神性时代结束的标志,也是人本时代的开始。从此,由人类心智掌控的技术开始大刀阔斧,凿出了智慧,凿出了财富,也凿出了死亡。如果和盘古神话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惊人相似,那就是两者都强调了技术创世,都使用了相同的工具——凿子。凿子在它本己层面只是单纯的技术工具,然而在神话的叙事层面里,凿子却远远超越了作为技术工具的存在,言说了创造世界的伟大技术事件,凝聚了中国古人对于技术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前一把凿子在盘古手里虎虎生风,创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而后一把凿子凿出的却是浑沌之死。这是出于对技术的恐惧和敬畏。“凿”这一冰冷的技术性动作硬生生地作用于血肉之躯浑沌身上,让人感觉不寒而栗。技术,犹如我们所说的双刃剑,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这些技艺工具和手段,正是这些工具式的劳动才实现了人的创造;但在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生存的必然命运,技术性的生活和经验又与恐惧、焦虑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创世神话用生存哲学的语言诠释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本原意义和价值。
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以共工为例,先秦神话传说中,共工总体上是以危害人类生存的反面形象出现的。他撞断了不周之山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大洪水,闻一多先生曾说:“共工在历史上的声誉,可算坏极了。他的罪名,除了招致洪水以害天下之外,还有‘作乱’和‘自贤’两项。……许多有盛德的帝王都曾有过诛讨共工的功。”[5]《韩非子·五蠹》云:“共工之战,铁铣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可见,共工几乎成为暴戾血腥的化身。然而,共工本身的原始面目,却是以技术神的神格出现的。“共”在古汉语中为“大”之意。所以,“共工”亦即大匠。古人将工匠神视为祸害人类的大敌,表现出了对技术双刃剑效应的畏惧。中国古人对于这种失控的间接工具性价值表现出焦虑和担忧,即使在今天都有警世的作用。
二
基于对技术双刃剑的认识,人们自然期望能够完全控制技术,避免间接工具性价值所带来的危害。然而,中国古人选择的“控制”方式并非是将技术视为与自身对立的异己,而是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人与技术、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甚至是诗意的平衡状态。这样,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人们采取了“顺应自然”的方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达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对 “人”、“地”、“天”、“道”、“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解。人类的生产实践取法于地,适应地面上万物变化的规律;地上万物变化取法于天,适应天时气象的变化;天地万物变化遵循内在的“道”,创生和孕育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而这种最优的途径要符合事物自在的固有的本性。
这种“顺应自然”的技术观在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获得了形象的诠释。创世神话中有很多关于造物的神话,讲述技术神性主体发明创造某种技术器物的故事。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创世神话中的技术主体作一研究,可以发现,影响技术主体发明创造最关键的自然因素往往被凸现出来。这一点,在神圣技术主体的名字中可以管窥一斑。列维·布留尔曾说:“中国人有一种把名字与其拥有者等同起来的倾向。”[6]比如,木车的发明神称为“吉光”。从文字的构型上看,“吉”本指长矛之类的兵器,这类兵器闲置时为直立状,所以“吉”的引申义为直木。“光”字在甲骨文和小篆中都是在火下增一人,也可以理解为在火光下忙碌的人。从木制车辆的工艺上看,其难度最大的部分是车轮的制作,需要通过烘烤将直木制成圆形,这是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工艺,所以,木车创制者命名为“吉光”,显然出于对烘烤车轮工艺中“火”这一技术要素的重视,也表达出对于能够掌握“火候”自然要素的强烈愿望。还有,铸鼎的神匠叫蜚廉,《墨子·耕柱》中有关于他的记载:
昔者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
这位铸鼎的蜚廉是一位风神,行走速度极快,所以蜚廉也叫飞廉。《楚辞·离骚》有“后飞廉使奔属”的句子,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其解释是“飞廉,风伯也。”铸鼎是一项需要高超冶炼工艺的技术活动,温度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完成。因此,鼓风就成为铸鼎技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艺环节,也是铸鼎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由风神来担当铸鼎的工匠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彰显出古人希望充分利用自然力为技术服务的强烈渴望。[7]
这种“顺应自然”的技术观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制器尚象”。所谓“制器尚象”指的是 “创制人造器物要崇尚 ‘象’,以‘象’为根据,符合‘象’的机理。 ”[8]《周易·系辞下》中很详尽地描述了远古技术造物时的制器尚象: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揖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析,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仵,掘地为臼,杆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棒,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9]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器物制作都是圣人根据卦象而制。其实,无论是从现实经验技术还是从理性逻辑推理来看,制器尚象似乎都是不成立的。否则,中华几千年技术成果就都要归功于卦象了。那么,制器尚象是不是荒诞的臆造?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制器尚象呢?实际上,制器尚象并非是针对现实技术而言的,它是一种有关中国古代技术起源的学说。“象”也并非仅仅指卦象,而是泛指一切自然之“象”。所以,“《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10]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
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
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11]
女娲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娲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12]
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娲所制的笙簧是一于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 “绵绵瓜瓞”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蠡(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伟器尚象,师之以利用”[13]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
“顺应自然”的技术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表现出来。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14]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观,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三
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观中还蕴含了一种生命意识。技术不再是一种人类改造自然的纯粹物性手段,而是融入了人的智慧、情感乃至生命本身。它是富有灵性的,是能够与人进行情感沟通和生命对接的有机体。
在具体的神话文本中,这些原创性技术的发生往往源自神灵的神性或圣人先天的智慧。《神异经》中一则神话这些写道: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长一丈,其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凭青龙,右手凭白虎,知河海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知百草木盐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无不达。凡人见拜者,令人神知。(《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人事部十八·长绝域人)
神话中的大神有四个名字 “圣”、“哲”、“先通”、“无不达”,这些命名都是和智慧相关的。正是因为智慧才具备应对自然的力量,开启了技术的时代。而这种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充满了神性的色彩,与大神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技术是充满灵性和生命意识的,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这种原创性的技术及其传承,都是通过生命的洗礼来完成的。《山海经·海内经》写道: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
相传祝融是南方的火神。虽然我们在文本中捕捉不到他与技术相关的信息,但是他的儿子共工却是制造金属器具的工匠神。古代冶炼技术中最重要的就是因素就是火和水,共工承继了火神的遗传基因,又诞生在水边,可见,共工生来就是一位发明冶炼技术的带有神性的工匠。他的技术天赋是在 “父生子”的生命传承中造就的,为技术的起源编码了感性而直观的神圣形式。同时,共工用他的技术天赋直接创造了“术器”。术器是上部呈方形的,治理水土用的铁锹类金属工具,即所谓“共工生术器”。值得注意的是,“共工生术器”本身是一项具体的原创性的技术实践,指共工冶炼金属铸造疏导性的治理水土的铁锹类工具,但是文本没有提起任何的锻铸方式和细节,只是用一“生”字来描述共工的技术原创。可见,不仅技术主体的技术禀赋是在生命活动中的完成的,就连具体物性的技术实践也被赋予了生命的内涵和色彩。中国古代神话把技术发明与创造等同于生命诞生,使技术本身也赋有了神圣的充满灵性光辉。此类“神生技术”的神话还有很多,诸如“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天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禹号,禹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能工巧匠的始祖倕,还有舟船的发明者番禺、木车的发明者吉光,都在神话系统中以“生”的方式成就了天与人的沟通。完成了由天工之技向人工之技的神圣仪式。
技术中的这种生命意识在古代铸剑神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铸剑名匠是干将、莫邪,他们是一对夫妻,也是他们所铸造的雌雄剑名称。关于干将、莫邪铸剑的神话有很多,主要的篇章如下:
雨师扫洒,雷公出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
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庄子·大宗师》)
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侯天伺地,阴阳同光。干将曰:“昔无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知成物。今吾作剑不变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师知烁身以成物,吾何难哉!”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刀濡,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综合上述三则神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干将、莫邪造剑得到了天助,包括雨师、雷公、蛟龙在内的各路神仙都纷纷参与,就连天帝也不例外。第二,铸剑活动必须顺应自然,就像庄子说:让天地作大熔炉,自然造化作工匠,这样打造出的才是集自然之天成的“宇宙之剑”。第三,干将、莫邪将自身的肉体投入炉中,与金属合而为一,以一种最壮烈的形式完成生命与技术的对接。“干将、莫邪这对宝剑是莫邪投入炉中后冶炼、铸造出来的,是以人的生命与天神相感应、相配合,最终获得成功。在这类接触型天人感应传说中,感应的生成物都带有灵异的性质。”[15]
总之,这类铸剑神话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天人交感,将自然、生命的元素投置到技术活动中,用生命的灵性铸造技术产品。工匠的品格与其所造器物的品格相重合。所以,作为夫妻的干将、莫邪也就将自身的生命形态投射到所造的雌雄双剑上,言说着最为原始也是最为神圣的阴阳交合的缔造过程。就具体字义而言,古汉语中“干”有进攻之意,“将”的意思是“强壮”,所以,“干将”意味着强壮有力的进攻,属阳刚之象。《管子·制分》曰:“屠牛坦朝解九牛,用刀而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莫铁”也即削铁之意。邪字形从牙,意即尖锐。由此,“莫邪”也就是削锐,把对方显露的锐器削折。[16]“在干将、莫邪的传说中,阴阳学说又恢复了它的原型,男和女分别作为阴阳的代表出现,阴阳渗透就是阴阳两性的结合。至于对阴阳剑具体形态的描绘,也是取象于男女两性生殖器的特征,不过所用语言比较含蓄。”[17]干将、莫邪神话将最为神圣原始的生命仪式赋予了技术。
创世神话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意识,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起源于技术、技术工具的发明、技术创造者的神化,等等。创始神话凭着超越现实的生动想象,在现实技术与幻想技术的交融中,完成了人类对技术缘起最深奥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在今天“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海德格尔语)的文化语境中,重温中国古代技术观必然是有益处的。其中,对技术双重工具性价值的理解,技术有机自然主义以及技术中的生命意识,都使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中存在着的精神超越向度,这一点,对于遏制当下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嬗越,重建诗意栖居的人类家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转引自李滟波.中国创世神话元素及其文化意[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2]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42.
[3][11][12][14]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80.181.148.
[4]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2)[M].北京:三联书店,1982.49.
[6]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16]沈瑞侠.中国古代早期工匠神话解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8]王前.中国技术思想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5.
[9][10]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439.319.
[13]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成都:四川大学,2004.
[15]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6.
[17]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