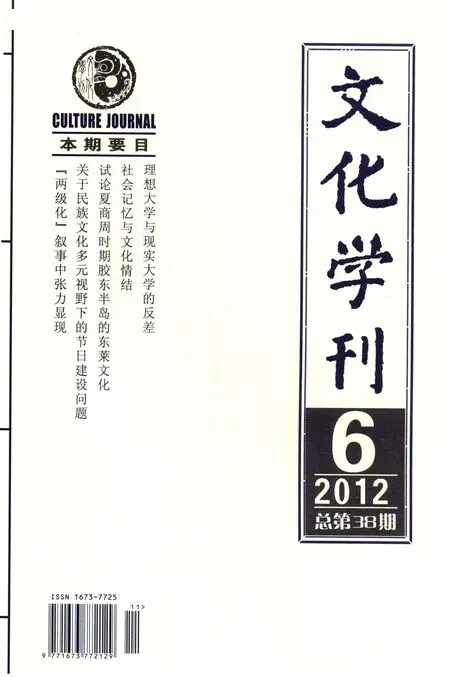倚声:宋代文人对言语的救赎
韩立平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一、天生好言语
“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陈眉公《小窗幽记》)
此无他故,天然是也。天然即道家所谓“大美不言”;儒家所谓“大道不器”;禅家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皆可相通相证。
然禅意若不凭借偈语,诗意若不表诸文字,一任其油然而生、悄然而灭,春梦似的了无痕迹,寒日一般无言西落,岂非愧对了造物主的无尽藏?虽达观者自可视之以烟云过眼、百鸟感耳,失去后不复丝毫挂牵,但古往今来,熙熙攘攘,皆是情之所钟,未能免俗,对人说梦,说听皆痴耳。操持文字之辈,遂欲尽己所能,转暂为恒,多拯赎一份诗意,多凝铸一句好言语。在中国文化造极的宋代文人那里,倚声填词,便担负了这样的功能。
庄子告诫我们:“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可是在倚声的境遇里,必须首先听之以耳,因为感官愉悦拒绝奥涩。当竹肉相发之时,灯酒流连之际,诉诸听觉而辅以视觉、嗅觉的宋词,不比诗文可窗下案头寻绎,须立地成佛似的动人;须解衣盘礴似的沉醉;须如秦少游《满庭芳》那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即使唱给“不识字人”听,“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侯鲭录》卷八)。
天生好言语,非书斋苦思冥想就能批量生产,故文人并不享有专属权。天生好言语往往由白丁口中道出,一经文人点染,自然凑泊,便触手生春,千古传唱,谁都有可能迸出天生好言语:妻儿奴仆、贩夫走卒、酒徒琴侣、樵叟钓童,乃至名妓、闲僧、尼姑、无名氏、女鬼……
二、妻奴
中国古典文学大抵是男性的文学,偶尔出现一二才女,也会招来非议。如词中第一圣手李清照,当时就被人指责其词多“闾巷荒淫之语”,“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王灼《碧鸡漫志》)。不过表面上的辱骂,掩饰不住暗地里的喜爱,王灼仍不得不承认易安“姿态百出”、“本朝第一”。宋人倚声以拾掇好言语,最多的例子即是女子语:
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云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苏轼《减字木兰花》)
元祐七年(1092)正月夜半,东坡先生正在汝阴州堂前赏梅。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更何况有佳人相伴!王弗看着月色下梅花绽放,忽对先生道:“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道:“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苏东坡的敏慧通脱,千载以下仍是令人欣羡,他竟能在这平平之语中听出诗意来,遂袭用王弗语中简单的机杼,化为《减字木兰花》中的最后两句(事见《侯鯖录》卷四)。
元祐元年(1086)二月,王鞏由岭外赦归,遇东坡于京师。鞏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贬海上五年,连失二子。鞏有一家妓,名叫柔奴,又名寓娘,一直跟随他南迁北归。东坡见柔奴归来,笑问道:“广南风土好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是吾乡。”柔奴实在说出了东坡的心理,东坡自己的诗句尝云:“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一个歌儿竟有如此的见识!东坡欣遇知己,感而作《定风波》,以柔奴语为歇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赵翼说苏东坡“遇成语佳对,必不肯放过”,实则遇天生好言语,更不肯放过也。
夜来深雪前村路,应是早梅初绽。故人赠我,江头春信,南枝向暖。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月明溪浅。向亭边驿畔,行人立马,频回首、空肠断。别有玉溪仙馆。寿阳人、初匀妆面。天教占了,百花头上,和羹未晚。最是关情处,高楼上、一声羌管。仗谁人向道,何如留取,倚朱栏看。(晁端礼《水龙吟》)
晁端礼此词也化用一位夫人语,她是刘元载的妻子,原诗题作《早梅》,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礼部郎中孙冕尝刊刻《三英诗》,刘元载妻是三英之一,另二英为詹茂光妻、赵晟之母,可惜她们的真实姓名,已无从知晓矣(事见《诗话总龟》卷十)。
三、尼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苏轼《洞仙歌》)
苏轼七岁的时候(1043),曾经遇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尼,姓朱,自言曾跟随其师父入蜀主孟昶(919-965)的皇宫。时孟昶正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纳凉,孟昶作《洞仙歌》令。老尼虽年老健忘,但能歌唱出完整的《洞仙歌》。40年后,物是人非,东坡只依稀记得开头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遂以己语将其补足(事见词序)。罗大经《鹤林玉露》里也记载了一位悟道老尼的七绝:“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后来,辛稼轩《青玉案》词将老尼之语点化得天衣无缝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四、女鬼
金风淡荡,渐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气,轻烟乍敛,皓月当轩练净。对千里寒光,念幽期阻、当残景。早是多情多病。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最苦碧云信断,仙乡路杳,归鸿难倩。每高歌、强遣离怀,惨咽、翻成心耿耿。漏残露冷。空赢得、悄悄无言,愁绪终难整。又是立尽,梧桐碎影。(柳永《倾杯》)
一个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落魄才子,寓居京城景德寺,见僧房壁上有一残诗,不知谁作,亦未尝听人吟诵:“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因觉末句妙极,随即填了一阕《倾杯》,化此诗句为歇拍。是夜,柳永梦见一妇人,对其言曰:“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诗,数百年无人称道,公能用之。”(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八)盖感永之恩情,故托梦于焉。既为数百年,则已然唐代或更远古的女鬼了。而柳永生前也未曾料到,自己为鬼后,每年春风骀荡之时,诸名妓便会不约而同上坟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冢”。
宋词中的妙句,不少都带有鬼气。晏几道《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道学家程颐就说是“鬼语也!”(《邵氏闻见后录》)当法云秀指责黄庭坚词多淫艳之语时,黄庭坚竟以“鬼语”来搪塞:“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冷斋夜话》)所谓“空中语”,即神仙鬼怪之语,原来不是自己的写作,山谷只是借其语倚声耳。
五、叛逆与救赎
宋代文人倚声填词,不仅拾掇了散落一地的好言语,救活了他物;也赎回了自己,赎回了人之天性。
宋代文人相较唐代,更多表现为知识化、学者化、思想化,故宋代诗学有一根本祈向,就是在个体一己的创作中追求融贯经典、点化前贤,强调个人才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然而宋词却表现出相反的艺术祈向,这可以用宋徽宗的话来证明。身为皇帝,一言一行应具有官方正统性。宋徽宗曾经对一位太学官宋齐愈说道:“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词进呈,须是不经人道语。”(《宣和遗事》)“不经人道语”恰与宋代诗学讲究的“无一字无来处”针锋相对。
可即便皇帝如此说,许多宋人硬是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白乐天的原创(《能改斋漫录》卷八,白《吾土》诗:“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秦观那首《满庭芳》,也硬要说成是隋炀帝的原创(《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隋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可见,诗学思想对于宋代文艺的影响之深。
宋代文人的心态,应是中国古代最佳的一个朝代。因为他们有自我调剂、发泄乃至叛逆的窗口。据说,北宋翰林学士韩维,早晨与门客吃饭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俨然正经,可一到了晚上,“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清波杂志》卷十)。如此劳逸结合,是怎么也不会得抑郁症的。倚声填词,便是宋代文人的一个调剂品,他们可以在这里抛却诗文中仁义道德、思想学识的枷锁,暂且赎回“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本性,以避免人性在过度文明化、人文化过程中可能遭致的压抑、扭曲。
吴冠中先生有句名言 “笔墨等于零”,不过有个小前提,是“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
明人唐顺之嘲笑南朝沈约:“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能道出一两句好话”(《与茅鹿门主事论文书》)。
我想借用吴先生的话,接着唐顺之说,在词里,“声律、思想、情感都等于零”,如果它们一旦脱离了好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