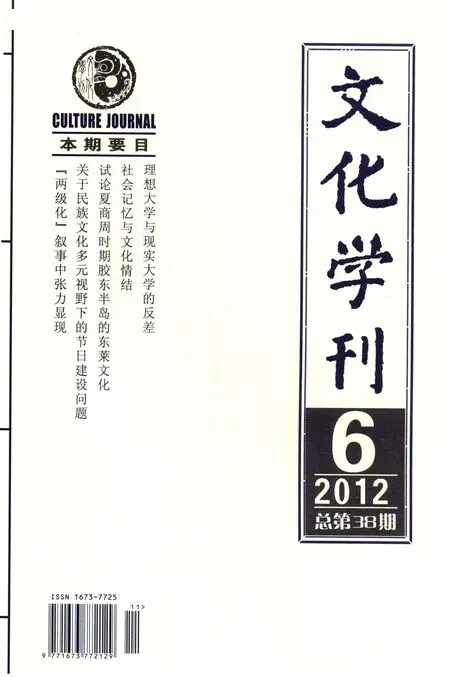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的核心价值观
高日晖 聂雯雯
(大连大学宣传统战部;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古代小说价值观概说
小说处于萌芽时期便被系附正史之末,这不仅因为小说创作本身确实有一些是从史传而来,而且,小说家为了抬高自己创作的价值,也愿意把小说与正史比附。所谓“刍荛狂夫之议”,所谓“治身理家”,都是指小说有辅助经史的认识教化功能,可以补经史之所阙,因此才有可取之处。魏晋时期,葛洪的《西京杂记跋》中明确指出“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 ”[1]干宝谓《搜神记》“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2];王嘉说张华《博物志》乃“捃采天下遗逸”[3],而他自己的书名则干脆名之曰“拾遗记”;郭宪谓《洞冥记》“藉旧史所不载者”[4],这些都说明小说拾遗补缺的功能在魏晋时期已经被普遍认识到了。进入唐代,这一观念被继承下来并且又有所发展。刘知几云:“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是知史文有缺,其来尚矣。”[5]有缺则有补,小说便充当了“补正史不足”的角色。同时,他也指出小说有实广见闻的社会作用。“补史”之论的最终目的是攀附经史,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中国人尚实,尊崇正史,藐视野史,小说不向正史靠拢便难以取信于人。有些小说家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把历史小说视为正史的附庸,并力图将小说的功能纳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轨道。例如,熊大木认为“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6],林瀚《隋唐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7]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羽翼正史”说,[8]吉衣主人袁于令《隋史遗文序》说:“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9]如此之类,均可见他们眼中正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家还认识到小说应该具有消遣功能。其实,中国古代小说最早起源于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一件事之所以被街谈巷语,则必定是因其具有新、奇、怪之类的故事、新闻、消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遣。对于小说的娱乐审美作用,魏晋小说家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有“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主张。“游心寓目”是干宝对《搜神记》以及同类小说娱乐作用的准确概括。萧绮的“爱广尚奇”说进一步表明了小说的娱乐功能。[10]爱广、尚奇是萧绮对《拾遗记》的评价,但同时也是对当时小说审美意识的总结。自觉的虚构意识和美学追求的结合,正是小说观念觉醒的标志。鲁迅先生云:“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1]鲁迅指出了志人志怪小说娱乐的价值。唐代的古文运动,推动了文言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张籍与韩愈讨论“驳杂之说”的书信往来是当时的重大事件。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引用《诗经》上的“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来为自己辩护,强调了小说的创作所以为戏是并不有害于道的。柳宗元为《毛颖传》辩护中提出“异味”和“以文为戏”的主张,对小说更多地从审美角度进行观照。而“以文为戏”观念的出现,是唐人对文学本质认识提高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对“文以载道”的一次反拨。沈既济在小说《任氏传》将小说的审美功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12]明朝谢肇淛的 《五杂俎》中:“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伴,方为游戏三昧之笔。”[13]他认为小说如果像史传那样讲究实,就会无味。古代小说的娱乐功能还体现在作者在创作时常常也自觉地认识到小说创作乃 “自娱以娱人”,将创作当作是游戏笔墨,抒写烦郁之情怀。特别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创作,更能体现出创作上的消遣目的。总之,消遣功能不仅是古代小说作家创作小说的原因、目的之一,同时也是小说能实现其他功能的必要手段。
二、小说理论史上的核心价值观
小说除了补史、博物、审美娱乐的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的功能,这是小说批评家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古代小说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一开始就被纳入政治的范畴之内成为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孔子较早提出诗歌“兴观群怨”的功能,和“事君”、“事父”的价值和作用,《诗大序》更加强调诗歌风教的价值,认为古代帝王用诗歌来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方面的用途。曹丕把文学说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代柳宗元提出“为文明道”的主张,宋理学家周敦颐正式提出“文以载道”说。这些文学理论观点,都是针对于经史诗文等文体的,小说的地位不同于经史,乃九流之外第十家。所以,小说要攀附正史,只能是补史之阙,毕竟它不是正史,而经史最终也还是要辅助王化实现政教,小说自然也是如此,“补史”并不是小说的终极价值,小说的根本和最终的价值与经史一样,也是教化。古人把小说的教化价值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观念承继“文以载道”的传统,自小说产生之日起,不管它是属于诸子还是属于文学类,对它的教化价值的认识和追求一直不变。小说理论和创作发端期的桓谭说小说“有可观之辞”,是因为小说能“治身理家”,再推而广之,就是有利于实现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汉书·艺文志》虽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摒弃于“可观者”之外,但他同时又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4]这种观念被后人不断加以深化、发展。静恬主人的理论可作为这种教化作用说的代表,他在《金石缘序》中说:“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15]因此,批评家对小说作品都明确提出要具有教育功能,否则就称之为“诲盗侮淫”之作而加以批评。在古代小说批评家眼中,只有让读者读了有所观感戒惧,达到劝善惩恶之目的的作品才能算是优秀作品。这种教育功能不仅作用于下层平民读者,而且对上层统治者也有借鉴意义。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16]这种观点,又恰恰与最初的小说功能观相近。因为古代之所以有稗官之设,就是搜集街谈巷语之说,以供天子知晓民风民情,有助政教。可见,这种教育功能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确实是一以贯之的主张。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部分,直到唐宋时期也没有取得和诗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小说要改变长期受人歧视的尴尬地位,似乎也只有在政治、道德的教化作用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来。唐代传奇作家李公佐在《谢小娥》后表明自己的创作目的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相信自己的故事“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17]《春秋》之义,也就是记述君臣父子之道,存亡绝续之道,善恶是非之道。李公佐认为创作小说应该本着《春秋》之义,而传奇知善而录,颇能起到《春秋》之义的教育作用。唐长孙无忌也认为小说与《传》、《书》一样同样具有箴谏规诲和观知风俗的作用。南宋批评家曾慥将小说功能总结为四个方面:“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 ”[18]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人对小说功能的认识。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指出小说的教育作用:“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19]
明代小说家更加倡导小说传道教化的价值,这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小说创作实际情形密切相关。明代不仅政治严酷,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思想箝制也十分严酷。晚明手工业、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队伍不断壮大,社会上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价值,在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这些通俗文学中表现得更多一些。新文艺、新思想对传统的封建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统治阶级自然对那些与统治思想相悖的小说严令禁止,从晚明开始,《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一直被禁毁。同时,面对通俗小说已然成为流行的趋势,又没有办法阻止,于是便想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用儒家思想来占领通俗文学的阵地,使小说戏剧为统治者的儒家思想教化服务。
明代小说批评中充满了肯定小说忠孝节义、裨益风教、劝善惩恶的传道教化理论,强化了小说的教化价值,使之成为小说的核心价值观。署名“庸愚子”的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云:“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20]由此看来,历史小说的“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的功能就显而易见了。历史小说的社会效果远过于史书正是因为小说的通俗性,更能通乎众人。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指出“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21]他认识到小说有一定的教育价值,但仍把小说归为“正史之补”,却又可见其仍未摆脱重史籍轻小说的观念。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则云:“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22]修髯子的“羽翼正史”除了使读者获得历史知识外,更注意历史小说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明代通俗小说大家冯梦龙更看重小说在儒家传统道义教化普及大众中的作用,署名无碍居士的《警世通言序》认为,小说可以“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23]。
明代小说批评家重视传道教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小说的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所认识。明代批评家开始认识到新小说通俗性、生动性的审美特点,十分有利于“传道”目的的实现。经史传道,哲理玄奥,枯燥无味,而小说通俗易懂,容易引人入胜,更便于传道。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无不能悉数颠末……及举 《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24]汤显祖在《点校虞出志序》中谈到了小说的审美功能:“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可神释,骨飞眉舞。”[25]所以这些高明的读者认为,借小说传道,诗文所不及也。与戏曲比较也有优势,因为戏曲毕竟还要受空间、时间等条件限制,不能反复欣赏,过眼易忘,而小说则可反复捧玩。与统治者不同的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小说理论批评家抓住小说大众审美这一突出特点而充分肯定小说,进而倡导以小说为载道的文体,这是明代更加重视小说教化价值观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近代小说理论的新变与小说核心价值观
近代小说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小说与政治紧紧连在一起,把小说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看待,认为小说可以作为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载体,从而表现了功利主义的小说观,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小说教化价值观的新变和发展。当然,随着小说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另一部分理论批评家则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纠正片面的实用主张,从而体现了反功利的小说观。
我国近代小说戏曲的新局面,是随着维新派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而出现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号召小说家以小说形式宣扬救国的思想,以期唤醒民众,参加改良运动。梁启超及其响应者完全突破了小说补史之不足或小说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小说观,充分认识了小说的特殊功能和审美价值。不过,他们为了服务于思想政治运动而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切实际地拔高,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潭。梁启超在纲领性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论述小说的社会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26]梁启超竭力夸张小说的社会作用,从文学观看,唯心地认为小说的艺术功能具有改造社会的力量,甚至是拯救社会惟一的灵丹妙药,这是错误的。同时,过分强调了小说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不少弊端,这首先往往表现在以政治性取代艺术性。在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前后,社会上一时出现的大量的政治小说,大都缺乏艺术生命。然而,这也恐怕是一种规律,只要时局出现激变,国家处在存亡关头,政权面临易主,这一规律就会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产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晚清影响很大,但晚清另一部分小说批评家很快认识到梁氏的实用理论的不足。他们更多的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理论,表现了反攻利的小说观。徐念慈和黄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评家,他们从小说的艺术价值出发,提出了反功利的小说价值观。徐念慈认为小说是带有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产生小说,而不是小说能挽救社会,小说只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指出改良派的小说主张:“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27]他强调小说的审美功能,指出小说的价值在于鼓舞和感觉,这表现出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徐念慈的观点也得到了诸如他的同乡好友黄人等的赞同附和。从小说的理论发展来看,他们纠正了“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偏颇,正确揭示了小说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四、结论
小说的价值是历代小说批评家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宋元及以前的理论批评家,大都把小说看作是正史之补,认为其价值主要在于补正史之未赅和广识博闻。明代以后把小说抬高到与《六经》正史相平等的地位,认为小说通俗、生动,能够传道,有益于世,因而与经史典籍有着相同的地位。偶尔有一些理论批评家推崇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就会遭到排斥或耻笑。直到晚清阶段,才真正从小说本身角度考察,揭示小说的文学功能。然而,近代一部分批评家也把小说当作救国的良药,带有严重的功利性。这些都说明,以往一些批评家大都没有从文学的特点,特别是小说的特点去认识小说的价值。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认为是“稗官野史”,而白话小说更是市民文化的产物。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文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而小说批评家为了为小说争得一席之地,也从史的角度去评判小说,肯定这一文体的教化作用。由此可见,小说的教化功能一直贯穿着古代小说价值的始终,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的核心价值观。
[1]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
[2][3][4][6][7][8][9][10][13][15][18][19][20][21][22][24][25][27]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20.25.23.121.113.115.274.29.167.436.63.91.109.113.115.184.187.298.
[5]刘知几,刘占召.史通评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33.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0.
[12][17]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6.71.
[14][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5.
[16]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9.
[23]冯梦龙.警世通言影印本(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10.
[26]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