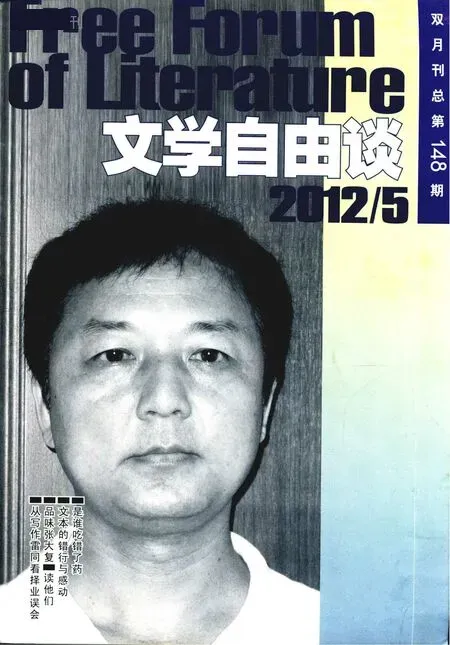不会忘记的名 字
●文/庄伟杰
旧话重提。记得新世纪之初,大陆有学者撰文质疑“余光中神话”,并因此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引发争议。其实,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史,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常常都是有争议的人物,余光中也不例外。因为他是大诗人名作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要求自然会比常人来得更加严格,甚至苛刻,这是可以理解的。追根究源,引发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对他在“陈映真事件”和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一些个人表现。至于李敖2004年曾于凤凰卫视中,以极端、偏激甚至可以说带有攻击性的言辞,抛出对余光中几乎不屑的批评,相信凡是听过如此狂妄口气或读过李敖这种以偏概全和乱扣帽子的文字,会保持足够清醒的警惕。限于篇幅,暂且不表。
一湾浅浅的海峡,除了是余光中的“乡愁”,竟导致了海峡两岸因为信息不通的认知误差。说明我们对台湾文学史的复杂性和其中许多恩怨纠结的真相欠缺足够的了解,对余光中“乡愁”背后的“中国想象”的真实内容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和认知。余光中到底怎么啦?素来热衷于纠缠历史事件和恩怨的国人,动辄就翻出点滴旧账,或抓住一点所谓“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却常常陷入肤浅的阐释和片面的理解。倘若只是抓住那些本身带有争议的所谓“历史问题”来否定余光中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要么是不幸地落入一叶蔽目的可能,要么是给人小题大作、有意挑弄的嫌疑。诚然,余光中在漫长的创作生涯和探索历程中,难免对一些问题曾经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只要我们以包容、宽容和开放的姿态去接纳,甚至允许人(不是神)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正如爱情双方,爱一个人的同时也得接纳其缺点,否则,就永远不会有爱的结合之存在。对此,余光中曾说过,一个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的观点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的那一小段历史和曾发表过的观点是不可回避的,然而,盘根错节的是非曲直,在特定的语境和背景下,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况且,站在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时间段看问题,结果往往是不尽相同的,甚至相去甚远。
至于把大陆曾掀起的“余光中热”与某些人所披露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那就很有些牵强附会之嫌了。只要我们随手点击百度“余光中”词条,那数百万(非数万数十万)条的信息映入眼帘,谁能说这种热是偶然的,谁能说他浪得虚名?在笔者看来,“余光中热”本身说明诗人在大陆的知名度和普及度与国内读者对诗人形成的独特的阅读心理是同构的。换句话,“余光中热”是凭借其个人的“文气”、“才气”和“人气”而形成的。这种现象与大陆风靡一时的“金庸热”、“三毛热”、“琼瑶热”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明显区别。本文恕不展开。至于所谓“余光中神话”,总比“王文华神话”、“几米神话”要好(钱虹语),因为余光中对于“美丽的中文”的感情比他们要深得多。余光中在《五行无阻》后记中有着自谦式的感言:“一位诗人到了七十多岁还在出版新作诗集,无论生花与否,都证明他尚未放笔。”这种精神姿态和创作状态,两岸诗人确实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据香港学者黄维梁观察分析,余光中的诗歌大概每五年就在时间里自焚”一次,换得一身新的羽毛。《蓝色的羽毛》于1954年出版六年后是《钟乳石》和《万圣节》,四年后是《莲的联想》,五年后是《敲打乐》和《在冷战的年代》,又五年是《白玉苦瓜》,再五年则为《与永恒拔河》……每一册新诗集的出版,他都表示了要超越自己的努力和信心。
在物化而浮躁的时代,笔者素来对那些在艺海不断航行穿越,在诗山执著攀援的追寻者心存敬意。尽管峰顶或彼岸笼罩着神秘的雾岚,哪怕大部分可能将距之遥遥,将路之漫漫,但他们依然躬身喘息着穿行其中,始终心无旁骛。尤其是在一个需要用生命体验、用灵魂认知、用文化涵养的“贫乏”的时代,倾诉与倾听,注定诗人无法摒弃个体的声音与世界与万物对话。可以说,一个民族在每个历史阶段如果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极其不幸和悲哀的。由是令人恍然醒悟,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的确需要多一些“余光中式”的诗人。一个从少年时期就确立文学信仰的人,用其一生营求一项“有意味”的事业,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感佩了。
我们可以断言,余光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个案”存在,是当代华文世界无法轻易替代的景观。他的全部著作所营造的深邃而独特的话语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就笔者个人而言,如果自己也算得上是一名文学(诗歌)的钟情者和实践者的话,那么,余光中笔下对母语文字的弹性把握,对中文内质的伸张,对中文诗性因素的采掘,对现代新诗的创造性转换及其对散文文体的革命性创新等等,绝对是启发良深,受益匪浅的。于是,我突然想起卡尔维诺的观点:“我仍然纯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不会告诉你真实。”《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富有艺术成就的作家,卡尔维诺是十分清醒和明智的。他是文本细读的主张者,在他那里,不愿意看到的是,读者把作品和作家混为一谈,更不愿意让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家的行状、好恶和名声互为因果。这种纯粹的文本细读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下)文论的所谓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批评观是相抵牾的,却自有其道理,即把作品从作家那里剥离出来,让它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现在很多文艺评奖和论文课题的评审之所以采用“匿名”的方式,大概亦然)。当然,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批评方法其实都是优劣互见的。是故,其缺点常常造成诸多的误读,或与作者原来的意旨大相径庭,甚或可能有悖于传统的道德伦理,乃至于可能把人格上有缺憾的作家推到台前,反之亦然。
其实,对于那些始终走在永远的路上企冀复活所有的美,像在寻找屈原的五月舟,像在怀抱荷马的七弦琴去确认属于生命和文学(艺术)价值与尊严的诗人作家,面对他们创造的文本世界,有时必要的“误读”反而能为我们再造或敞开一片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更加接近作品企望传达出来的意志和情感真实,而这恰恰是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文本呈现出来的最大价值化。况且,任何艺术形式自有其自身的艺术道德、良知和境界,用世俗(道德)的眼光是无法领会和洞穿的。如果一个诗人作家在创作时勇于摆脱世俗道德规范的束缚,自觉自由地听任来自灵魂深处的本真律动,呼应比现实世界具有更高意义的庄严艺术召唤,那么,这应是一种伟大的写作抱负,因为他直面的不是显而易见的真理,而是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秘密。这正是每一个诗人都渴望企及却并非每一个诗人都能臻达的境界。相信诗人余光中包括明智的读者自有一番体会和感悟。
朱光潜曾说过:“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现也生生不息。”如果说,《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连同那些余音萦绕的“乡愁”诗篇,作为优秀作品成就了“曾经沧海”的余光中,也创造了乡愁般又深又浓的“余光中热”,同时造就了当代华文世界一位具有独立艺术个性的大诗人,那么,时至今日,余光中敞开的诗文大门还没有关闭,我们尚不能过早地急于定论或用预设的框架来解读这位世纪诗人。文学靠自身的魅力征服读者,惟有作品和时间最有发言权。我们已经看到,余光中的诗性智慧颇具智性特质,其特色是融思入物,在精雕细刻中呈现出珍珠项链般的质地。他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诗艺,也是智性和生命精神不息的自然延伸。从这位把“永恒”两个闪光字眼写进诗中的诗人身上,我们同样看到,诗歌和历史的大门一直为他敞开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来者,都将从文学教科书中记住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