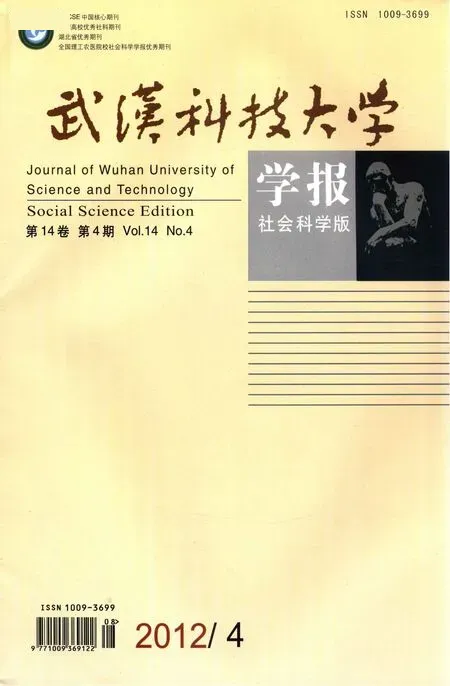康德义务论的自律性及其来源
姚 云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从伦理学上看,康德提出了行为的规范性问题——义务。义务作为行为规范,既要对行为主体具有约束力,又要具有动机激发性。那么,义务在康德那里如何能同时具有约束性与动机性的统一呢?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科斯嘎德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明白义务如何具有约束性或规范性,其次要澄清义务的动机激发性的来源。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其欲实现的意图或目的,而在于行为必依之而行的准则,准则的标准是道德法则,所以说,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寻求法则,行为本身就具有价值。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你的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必须具有合乎法则性的形式,这就是你的义务。所以,义务无疑具有规范性与约束性。而准则和法则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解决义务规范性问题的关键。义务对行为如何具有动机激发性?在康德那里,这种激发性来源于义务本身。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性是行为的理由,等于说义务就是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行为的动机。那么,为什么义务具有正当性的特征呢?答案依然在于它所依据的准则具有可普遍化的法则的形式。如此一来,这种法则的来源就成了问题。如果法则来源于上帝的意志,它也是可普遍化的,对人同样具有规范性,这种法则是否具有动机激发性呢?像奥古斯汀所认为的那样,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如果你严格地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你的行为就是善的,而恶是你的自由意志对于上帝旨意的偏离,所以恶是善的缺失。这就表明在意志论那里,义务的约束性和动机性是不能统一的。法则不能来源于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之外,只能来自于它本身。康德的自律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
一、义务具有规范性的理由
你对于自己的善是你的权利,你对于他人的善是你的义务。要弄清义务如何具有规范性,得澄清义务的具体内容,以及由它的三个命题所引发的准则和法则的关系问题,义务的规范性就潜存于它们之中。
(一)义务的三个命题
义务的规范性体现在义务的概念中。“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这个义务的命题表明了义务本身具有规范性,即义务是道德价值判断的依据。那么,什么样的义务才具有道德价值呢?这就要对义务本身做一个词义上的分析了。
我们知道,康德的哲学具有反神学的特征,但他又要确保有道德的人能够配享幸福,为此他不得不为信仰留下地盘。但在他那里,上帝的存在只是一种预设,只是确保德福一致的可能性的前提。意志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摆脱自然法则的约束,具有自主性,它才能去行动。而自由意志又受到主观的干扰和限制,如果不受理性的约束,它则可以作恶,或者说使一切本身可以成为善的品质成为恶的。康德说:“苦乐适度,不骄不躁,深思熟虑等,不仅从各方面看是善的,甚至似乎构成了人的内在价值的一部分;它们虽然被古人无保留地称颂,然而远不能被说成是无条件的善。因为,假如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这些特性就可能变成最大的恶。一个恶棍的沉着会使他更加危险,并且在人们眼里,比起没有这一特性更为可憎。”[1]9意志必然是善的,绝不会是恶,恶只是自由意志有时受到偏好的影响,并不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的准则而产生的,“意志是彻头彻尾善良的,绝不会是恶,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的准则变成普遍规律,是永远不会自相冲突(Widerstreiten)的。从而,你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照那些你也想把其普遍性变成规律的准则而行动。这一原则就是善良意志的最高规律”[1]57。“恶必须存在于准则背离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主观根据中,而且如果可以把这种倾向设想为普遍地属于人的(因而被设想为属于人的族类的特性),那么,这种恶就将被称做人的一种趋恶的自然倾向。——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从自然倾向中产生的任性把道德法则接纳或不接纳入自己的准则的能力或无能,将被称做是善良之心或者恶劣之心”[2]。可见,按照符合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事,就是出于善良意志的行为,该行为就是道德的。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它仅仅由于意愿而善,是自在的善,虽然不是唯一的完全的善,但一定是最高的善,它是由被先天赋予人的理性的实践应用产生出来的,“我们终究被赋予了理性,作为实践能力,亦即作为一种能够给与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1]11-12。善良意志为理智本身所具有,而不需要教导,但它需要显现出来,因此,就需要义务这个概念。义务就是善良意志的显现,就是夹杂着一些主观限制和障碍的善良意志,即不纯粹的善良意志,就是善良意志对人的理性提出的要求,因为人不像上帝一样仅仅只有善良意志,他还有感性欲望和偏好,这些会影响他的意志去按照满足它的偏好的准则去行动。所以出于义务的行为也就是出于善良意志的行为,同时也就是自觉地把自己的准则变成普遍法则的行为。法则是用来规定意志的行为准则的,如果意志不依据合乎法则的准则去行动,虽然它的行为中有道德的成份(如同情中就含有帮助他人的义务的成份),但却只能是合乎义务而不是出于义务的,因此,不会具有道德价值,就不具有规范性。
这就进入了义务的另外两个命题。“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仅依赖该行为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欲的原则”[3]406;“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3]407。在这里,准则和法则的关系问题成了义务是否具有规范性的关键。
(二)义务成为规范性的关键:准则和法则的关系
准则就是意志的主观原则,作为主观原则的准则要具有规范性,就必须变成类似于法则的客观原则。客观原则就是道德法则。康德的道德法则不等同于绝对命令。道德法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最高的理念和法则,它是最为神圣的,是为有德性的人所遵守的,如果有上帝,那么为最完满的上帝本身中就具有的。人作为一个不完满的存在,会有自己的欲望,会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他的准则会和道德法则相冲突,因此,就需要定言命令,以摒弃他的理性中夹杂的各种欲念,从而规定他的意志严格地按照道德法则去行事。绝对命令就是道德法则的体现,是道德法则被应用到有限的存在者——人身上的方式。“绝对命令,作为一个命令,惟一地指向这样一些合理的存在者,由于他们是具有各种需要的有限的存在者,他们把道德法则作为一个限制来经验。像这些存在者一样,我们以那种方式来经验道德法则,所以,绝对命令规定了那个道德法则将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方式”[4]。
绝对命令的形式公式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3]428准则和法则的关系就明确了。你的行为必须依据这样的准则才具有规范性,才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即它所依据的准则必须具有内在的合乎法则的形式,必须是可普遍化的准则。换句话说,你的准则必须在同时应用到其他所有人身上时也具有普遍有效性,并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所接受,而他们也能自觉地按照此准则去行动。这实际上是你和所有的人在订契约,并自觉地去遵守它。道德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就蕴含于这种准则的一致达成之中。义务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寻求法则,并按照它所寻求到的法则去行动。这种寻求法则的途径就是所有人的意欲的主观原则即准则的同一性。法则和准则的关系就类似于正当和善的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在康德那里正当是优先于善的。每个人意欲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善,这就类似于准则。而你的行为对于他人是善的,这就是你的行为的正当性,也就是你的义务,所以正当性就类似于法则。你的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必须具有法则的形式,才具有义务性,才是正当的,因而对于他人才是善的。所以正当优先于善。
二、义务的动机性:准则和法则的一致
关于义务的动机性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意志论者的观点,它来源于上帝的意志。情感论者如休谟,则认为义务来源于建立在人的苦乐感、同情原则基础之上的人的赞成和谴责的情感,即义务来源于反思性的情感。而在康德那里,这种从外部引入动机性力量的外部主义的设想是不必要的,义务对行为所具有的动机性就存在于义务内部。要证明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义务做内在主义的分析,说明义务的规范性来自于义务本身而不是义务之外。
行为的动机不能是出于偏好或同情,如果那样,每个人的行为就会只具有自己的准则,行为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具有约束性,也就没有对行为可以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即没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其结果只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主观主义。因此,行为的动机只能是出于义务,义务本身对行为具有动机激发性。这就涉及到和义务规范性同样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义务才具有动机性。义务所依据的准则必须具有普遍法则的形式,它才能作为所有人行为的动机。如何自觉地按照法则去行事也就是义务的来源。义务既然来源于人对于普遍法则的尊重,它的实践也依赖于对绝对命令的遵守。义务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你必须要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依据普遍法则做出来的。如不自杀是你的义务。比如,在一个人患了癌症的情况下,如果被医生告知只能活几个月,而在这几个月中要经历极度痛苦的化疗,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萌生自杀的念头,因为化疗后也可能会活不了多久,他想如此受罪早晚都是死,还不如痛快地早点死掉。可依据康德的义务论,他不应该选择自杀,而应该积极地与痛苦做斗争,这种选择就是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反之自杀不可普遍化,否则人人都死了,世上就没有自杀的事件了,它会造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康德说过,只有自由而又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自身才有绝对的价值,人的价值就是人格,每一个有道德能力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所以,“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48。不自杀显然包含着人对于他自身的人格的尊重。这个例子表明了为什么人的行为只有可普遍化才是出于义务的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但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一个具有善良意志的人一定会按照绝对命令去行动。这里实际上就要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能力做出分析了。这就涉及到自律。
三、义务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自律
康德认为人是一个双重存在,既有感性存在的一面,生活在自然界受到自然因果律——幸福原则的制约,因此具有他律的一面;又有理智的一面,生活在理智世界中,受具有像自然法则一样约束力而又独立于经验的人的理性法则的支配。而这个法则是人的意志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1]51,即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并同时自觉地去遵守那个法则。自律在康德那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法则的意思,即它具有制定法则的功能,这回答了约束性问题;二是我的意愿,我愿意去遵法而行,这回答了动机激发性问题。而之所以我们会遵法而行,不仅仅因为法则的外在强迫性,而更在于法则包含着人是目的这样一个实质的内容。在给出了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的质料的公式后,康德说人性作为目的,这个法则不是来源于经验。一方面,这是由法则的普遍性决定的,它的应用对象是所有的理性存在者。经验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必然的东西;另一方面,在这里人性是客观目的,而不是被别人当成人们的主观目的或工具,这个客观目的是人们的一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条件。“因此,这一原则必须源自纯粹的理性。也就是说,一切实践立法的根据客观上在于规则和(按照第一条原则)使规则能够成为法则(必要时成为自然法则)的普遍性的形式,但主观上则在于目的;然而,一切目的的主体就是每一个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3]439。可见康德将在自律公式中实现了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的同一与结合,即自律原则作为第三条实践原则,使意志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一致成为可能。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在他的行为中都自觉地把自己和他人人身中的人性当成客观目的,每个人都具有自主性,自由、自觉、自愿地去以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性为目的而立法,自己作为法则的主人,而不是这法则来源于自我之外的他人或上帝等意志的强制,这样的立法作为你的义务,你应该会乐于接受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别人的意志或权威之下。另一方面,你自己订立的可普遍化的准则,你也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它,它对你具有动机激发性,是你的实践的动力和根源,即只有通过理性的反思,你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则才能成为你的义务的来源,并激发你自觉地依照该法则去履行你的义务。而这样的法则是对每个人都行之有效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换言之,康德通过自律原则实现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任务,人在理智世界受到了实践法则的制约,而该法则是由人的实践理性自己制定的,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自由。
自由是康德整个哲学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人的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写道: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提出了“人是什么?”这个哲学的根本目的。但“康德哲学并不是‘人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并不是张三、李四等‘人类本质’的问题,而是普遍的人性问题,是人的意义问题,是主体的主体性问题。”[5]这个问题不能在经验领域解答,因为它超出了经验的领域,而只能在人类的实践领域进行。实践领域在康德那里就是道德领域,康德伦理学就是要解答理性主体如何成为道德主体这个问题。而解决的途径就是自律。通过自律,人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指意志在起作用时不受外来因果性的制约。从这种消极概念中产生了自由的积极概念。积极的自由即为自律。“除了自律之外,亦即除了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的那种属性之外,意志的自由还能够是什么东西呢?”[3]454自由被赋予每一个意志的理性存在者。自律证明了人的理性能力。一是理论理性能力,即我可以将我的行为准则变成普遍法则,亦即我可以在思维中将准则与法则一致起来。但这仅凭思维的结合,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法则。因此,就需要实践理性,即实践理性把这种思维的结合变成现实的道德法则。此外,实践理性还有另一个功能,即作为动机激发性,促使行为者去自觉地按照这个法则而行动。即实践理性能力就是我具有能够并愿意按照法则的要求去行动的能力。这样,“自律的概念与自由的理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道德的普遍原则又与自律的概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道德的普遍原则在理念中是理性存在者的一切行为的根据,正如自然法则是一切显象的根据一样”[3]461。所以,只有义务才能作为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和理由,它只能来源于自律。因为自律实现了准则与法则的统一,也实现了义务的规范性与动机性的统一。
[1]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
[3]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26.
[5]李蜀人.道德王国的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