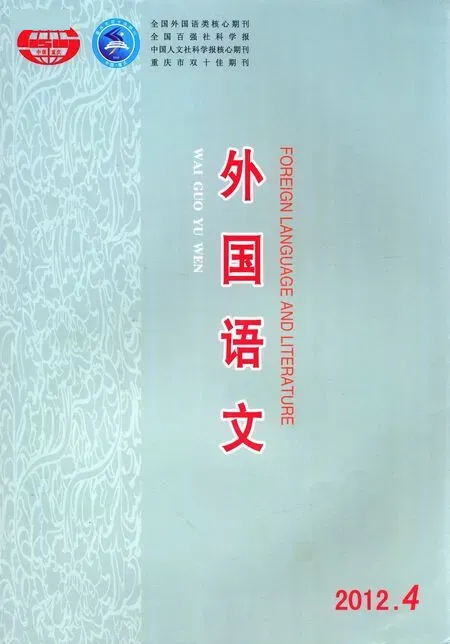轻逸·快速·复杂——卡尔维诺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
杨晓莲 姚 诚
(1.四川外语学院 中文系,重庆 400031;2.四川外语学院 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是20世纪举世闻名的小说家,是当代意大利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以自己富有活力的形式创新、卓尔不群的个性风范和深邃宽广的思想内涵,为小说创作、文学、作家开辟了一个相当另类的艺术空间。
集中反映卡尔维诺文学观的是他的《美国讲稿》(又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美国讲稿》是卡尔维诺为主讲哈佛大学诺顿诗论而写的讲稿合集,包括“轻逸”、“速度”、“精确”、“形象鲜明”、“内容多样”五篇演讲稿。在这些讲稿中,卡尔维诺提出了他认为未来文学应该保存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在“轻逸”、“速度”、“内容多样”这三篇讲稿中,卡尔维诺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文学应怎样认清世界?第二,文学应该如何表现世界?第三,文学要表现什么样的世界?从卡尔维诺对这三个问题的阐释,可以看出卡尔维诺对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独到性见解。
一、从轻逸的角度观察世界
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1]在世界这个大背景之下,作家、作品、读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文学这个整体。作家、作品、读者的共同在世性,无可辩驳地决定了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世界的关系。
作家的职责在于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客观世界,引起人们对现实世界各种弊端的思考,从而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以便使人类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卡尔维诺极为重视这种职责,他说:“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表现我们的时代曾是每一位青年作家必须履行的责任。”[2]3可见,在卡尔维诺看来,表现世界是作家的使命,他自己也努力肩负起这一使命。然而,卡尔维诺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正在变成石头”[2]3的世界。
1.沉重的现实世界
卡尔维诺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物质享受,并且渐渐被自己生产创造的物质所奴役。在卡尔维诺眼中,色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其实就是死亡的场所。“那些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东西,诸如喧闹、寻衅、夹马刺、马蹄嗒嗒,等等,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死亡的王国就像一个堆放破旧汽车的垃圾场。”[2]12卡尔维诺从各个方面表现了现实世界人类的生存困境:人口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失衡、人类内在尊严的缺失、道德沦丧等问题。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生活在人口拥挤、污秽不堪、欲望横流的现代城市里;在《命运交叉的城堡》中,人们愿意用灵魂与魔鬼作交易来追求黄金;在《阿根廷蚂蚁》里,负责灭蚁重任的政府机构竟然就是蚂蚁的大本营;在《烟云》里,正是那些贼喊捉贼的环保机构让城市上空烟云密布,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的十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处在一种茫然的心理状态——疏离、彷徨、困惑、焦虑、疑惧、紧张和虚无之中。在卡尔维诺笔下,整个世界已经混乱无序,人们灵魂空虚,生活没有意义,忙忙碌碌却毫无目标,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在追逐经济利益中迷失了自我。
不仅如此,统治阶级还以一种伪善的方式将人们变成奴隶,而人们对这种奴役不仅不自知,而且还满心欢喜。正如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所表现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宣传导向制度等,暗示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人们渐渐认同,并甘心服从他们的统治,丧失了自主性的人们正在成为统治者的奴隶,并且心甘情愿、满心欢喜地接受其奴役。
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没能摆脱商品化的漩涡。文学的商品化导致人们只关心外在的经济利益,只考虑文学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使文学变成了商品,使高雅、严肃的文化消费形式转化为一味迎合消费者趣味的消费形式,于是,文学艺术“不要沉重严肃的话题,不要深度,不要引人思考,不要确定的阐释,要的是满足人的本能需要的官能刺激,要的是虚幻的游戏,要的是休闲娱乐后的良好感觉”[3]。文学的醒世价值正在丧失,人们只是追求文学带来的消遣式的享受,而对文学价值的拷问趋于停滞,人们已经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正在变成一种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因此,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努力为其疗治。卡尔维诺正是这样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他觉得自己肩负着一种为世人敲响警钟、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使命,他说:“我认为,凡是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证人和当事人的人,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对我来说,这种责任最后让我觉得这个命题太严肃太沉重了。正是为了避免它的约束,我决定面对它,但不是正面,而是由侧面切入。”[4]
2.以轻逸的方法看待世界
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观察这个世界,如果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它本来的面目,那么,如何认清世界就极为简单了,如可以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直面客观世界。但是,当今世界正在“变成石头”,沉重的现实遮蔽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直接去观察它,就会被其复杂繁乱的遮蔽所迷惑,无法窥见它的本来面目。因此,当世界笼罩上一层虚假的外衣时,要想达到认清世界的目的,就不能对其进行直接观察,而需要采取另一种方法。
卡尔维诺用了一个隐喻式的形象来阐释他对如何处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柏尔修斯是成功地砍下美杜莎脑袋的惟一英雄,他穿着飞行鞋,不直视那个戈耳工女妖的面孔,而是通过铜盾的反射看着她的形象。”[2]3显然,柏尔修斯战胜可怕的美杜莎面孔的方法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来看它”[2]5。其实,关于“镜像”的一个经典说法是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作家对自然的模仿不过像“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5]。他的意思是作家无法认识真理,因为作家的叙事不过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但卡尔维诺给我们的启示正好相反:要想看清可怕的美杜莎的真面目,我们只能通过这虚幻的“镜像”。同样,要想看清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或许我们也只有换一种方式——正如“柏尔修斯的力量在于,始终拒绝正面观察,而不是拒绝与妖魔相处”[2]5。也就是说,在面对人类世界不可避免地变得沉重时,我们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2]7这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用“轻逸”的方法来观察世界。
卡尔维诺之所以选择以“轻逸”的方法来观察世界,是因为他在研究前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在他看来,世界就是由没有重量的原子构成的,笨重的硬件必须服从没有重量的软件的指挥。卡尔维诺还对科学史、文学史和其他知识中有关轻逸的例子进行了旁征博引。比如: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将空虚和实在一同归为具体,消解了世界的实体性,注重对轻微的、细小的元素的感知;奥维德的《变形记》通过神话故事把“轻”看作观察世界的方法;卡瓦尔坎蒂作品中的极度轻微、不断运动的形象消解了物质的沉重感;蒙塔莱在诗句中喜欢表现那些微弱的、似乎注定消亡的事物;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以轻写重;昔拉诺力图逃避重力,运用他的想像力设想抵达月球的方式;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也刺激了诗人们的幻想。文学中也充满了这种在空中漂浮的想像,如《天方夜谭》中的飞毯、有翅膀的马等。还有萨满教徒在对待威胁部落生存的灾难—干旱、疾病和其他不幸时,所采用的办法是:“减轻自己的体重,飞到另一个世界去,依靠另一种直觉去寻找战胜灾难的力量。”[2]29当农村妇女承受着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时,“那里便有女巫骑在扫帚上或骑在更轻的麦秸、麦穗上夜晚出来飞行”[2]29。如此等等,都表明了人们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时,极度向往轻松生活的思想。
可见,卡尔维诺想表述的是:当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变得沉重时,我们要想脱离现实生活的困境,就只有从沉重的大地上轻巧地跃起。而且,对待痛苦的方法,就是选择让自己轻盈起来,让自己飞起来,远离这个沉重的大地。而文学不停寻找的正是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正是人类渴望摆脱痛苦的需求让“轻逸”文学得以产生。
二、以轻、快的方式来表现世界
现实世界变得十分沉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文学表现的客体就只有一个,即沉重的现实世界。然而,作家通过文学表现世界的手段却可以分为两种:沉重与轻逸。即表现世界时,作家可以“以重写重”,也可以“以轻写重”。卡尔维诺选择的就是“以轻写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是由没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与没有范围和边界的空间组成的聚合体,人类想要在有限的生命里认识广阔无边的世界,就只有通过自身的加速,才可能更多地认识无限的世界。因此,卡尔维诺推崇以轻逸和快速的方式来表现世界。
1.“轻”、“快”结合,对抗世界的沉重
首先,在卡尔维诺看来,轻逸,就是一种对抗沉重的价值观。当其作品中描绘的世界异常沉重时,卡尔维诺并不去增加这种沉重的分量,而是通过一系列轻盈的形象,如独特的视角、独特的人或物的形象,来与世界的沉重相对立。并且还用“轻逸”来超越一切使现实生活变得沉重的东西。
卡尔维诺用他的全部创作实践证明了他对“轻”的器重和喜爱。在创作中,卡尔维诺不仅喜欢用“一”、“半”等词来减轻词语的重量,而且还创作出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蜘蛛网、半边人、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等,同时他还对人物的微妙感觉进行了精确的捕捉和细腻的描写。
从其作品本身看,无论是早期的《通向蜘蛛巢的小径》、《阿根廷蚂蚁》、《烟云》等,还是后期的作品都表现出童话般的语言和梦幻般的叙述。如《看不见的城市》是海市蜃楼般地漂浮在空中的幻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是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交错交融,《命运交叉的城堡》是在森林里交叉的一个个童话故事,《帕洛马尔》是哈姆雷特般的个人独白和梦中呓语。卡尔维诺的作品亦真亦幻,总是给人一种模糊飘渺、若即若离的感觉,然而正是这种轻逸的书写,体现着作者对沉重现实世界的反抗。所以,卡尔维诺指出:“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2]29换言之,面对生活的沉重,轻逸的文学能够给予人们在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感受,使人们的精神轻松化。
其次,卡尔维诺认为速度和轻逸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卡瓦尔坎蒂的诗就是轻和快的统一:“卡瓦尔坎蒂诗中的各种形象一闪而过,我们甚至看不清它们,只是感觉它们存在。”[2]15在这里,“快”成了表现“轻”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卡尔维诺十分注重时代的快速发展与读者的感受,他说:“在未来更加繁忙的时代,文学应该像诗歌或思想那样高度浓缩。”[2]51因此,卡尔维诺在思考文学的过程中,加了一个“快”字,他所指的“快”并不是浅薄直露的“快”,而是一种厚重的“快”,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轻”。在连续不断的“轻”、“快”刺激之后,却还能绕梁三日,回味犹新。
卡尔维诺所说的“快”就是“速度”,这个速度是指思想上的速度,即在最短的篇幅内融入最大量的信息和思想,是一种高度的浓缩。他说:“我希望写有关宇宙的传说与故事,篇幅只有短诗那么长。”[2]51这种希望将有关宇宙的宏大叙事装载在短诗般的篇幅之内的理想,让卡尔维诺成为一个喜欢短篇小说的作家,而他创作的长篇也都是由一篇篇短篇故事累积起来、组合起来的。可见,卡尔维诺正是以“轻”、“快”的方式,对抗着世界的沉重。
2.速度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追求
卡尔维诺之所以选择“轻”、“快”的方式来表现世界,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作家的智慧,也是他站在读者的角度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卡尔维诺本身既是一位多产作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读者。他清楚地知道,顺应和满足读者的需求是作家创作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读者与作家的共同在世性,决定了读者具有按照自己独立的生活经验和意识结构对作品进行再创造的权利。正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也创造出游戏的意义来。”[6]德国文学理论家伊塞尔也在《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中写道:“由于未言部分在读者想像中成活,所言部分也就‘扩大’,比原先具有较多的含义。”[7]英国当代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在总结接受理论的观点时也提到,接受理论认为“读者连接断裂,填补空白,进行推测,验证预感”[8]。可见,很多文论家都对读者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卡尔维诺与他们一样,重视速度的意义正在于此:即留下更多的空白让读者去发挥。短小的篇章只给出故事的梗概,其他的细节全部交给读者去想像。
从作家方面看,创作时的高度紧张感,也让卡尔维诺青睐短小的形式;“从开始创作生涯那一天起,我就把写作看成是紧张地跟随大脑那闪电般的动作,在相距遥远的时间与地点之间捕捉并建立联系。”[2]48因为“写长篇时很难保持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2]49。从这可以看出,作为作家,卡尔维诺喜欢闪电般的速度,作为读者,卡尔维诺也喜欢短小的、流畅的、不断运动、快速变化的故事。
为了说明对速度的喜爱,卡尔维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查理大帝爱上一个年轻姑娘,姑娘死后,查理大帝对她的尸体爱恋不止,主教发现并取出了死者舌头下的一枚戒指,查理大帝立即对这名同性男子产生爱慕,主教将戒指扔入湖中,查理大帝便爱上了这个湖。文学史上其他关于这则故事的记载,加入了很多中间的细节。而卡尔维诺认为仅有这条只记其梗概的故事最引人注目。这条故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通过连续不断的变化,迅速到达故事的终点,中间的细节全部留给读者自己想像,作者不置一词。也就是说,作家一旦点燃读者内心的火花,作者就应该及时退场,从而让读者通过思考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别样的空间。
在卡尔维诺看来,速度使人感到兴奋,感到快活,感到充满精力和力量,感到朝气蓬勃。文笔敏捷和简练能得到读者喜欢,因为这种文笔能给人们的心灵提供许许多多几乎同时一闪而过的思想,能使人们的心情在众多思想、形象与感觉之中沉浮,让你既不能全部抓住它们,也不能完全抓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又让你不能漠然视之或毫无感受。速度留下了很多空白,又把剩下的一切都留给读者去想像。速度拒绝了作家的过度阐释,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创造空间。
三、文学应表现复杂多样的世界
卡尔维诺宣称:“文学生存的条件,就是提出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超出一切可能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只有当诗人与作家提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时,文学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能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2]107在这里,卡尔维诺把文学看作是一幅世界的地图、认知的地图,文学不仅要表现复杂多样的世界,而且还要成为百科全书。
1.文学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舞台
卡尔维诺希望传给21世纪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文学不仅要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爱好,而且要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2]113文学传达的内容应该是各种知识的聚合体,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大文化”。理想的文学应该是一个舞台,一个可以容纳任何可能性的舞台。文学还应是各门学科乐于交汇的场所,文学不仅要容纳各门学科——科学、哲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而且还应将过去的与未来的、现实的与可能的、无穷无尽的、各式各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完备的“关系网”。
巴赫金认为,文学文本是其他文本的交汇场所。在这一点上,卡尔维诺与巴赫金不谋而合,卡尔维诺明确提出,“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的关系网。”[2]101卡尔维诺理想的文学文本是一种内涵更深、涉及范围更广的文本,是社会的文本、文化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比巴赫金走得更远。
卡尔维诺一直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同一的,一切形式都平等存在。文学的作用就是在不同物质、不同事物之间进行传递与交流。他说:“但愿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2]119可见,卡尔维诺总想在小说中努力寻求一种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智慧和策略。同时,卡尔维诺也否定作者的权威,但又不像罗兰·巴特那样宣称“作者死了”。在卡尔维诺看来,作者只是一个参与者,作者有自己的声音,但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作者的声音与其他声音平等地进行交流、对话,形成一个真正的众声喧哗的、狂欢节式的场面。
卡尔维诺希望文学为各种声音、各种思想的交互提供一个场所,他指出:“那些最受我们欢迎的现代书籍,却是由各式各样的相反相成的理解、思维与表述通过相互撞击与融合而产生的。”[2]111文学表达多样性的思想在他的小说中有深刻的表现,如在《命运交叉的城堡》中,每一个人都在用一副纸牌讲述自己的故事,面对同样的纸牌,不同的人都认为:不是他说的那样的,而是我说的这样的,他们在用自己的故事进行“争吵”,真正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面。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卡尔维诺让不同的读者、人物、文本都和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争论,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氛围。可见,“文学的作用就是在不同之间进行传递,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为了更加突出差异。”[2]45为了让世界的复杂多样能够在文学中展现出来,文学就应该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提供展示的舞台。
2.文学应成为一部百科全书
卡尔维诺指出:“20世纪伟大小说表现的思想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2]111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打破了,新事物、新思想、新方法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大脑神经,如今的世界已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文学也应该与之相适应,打开怀抱,容纳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学的宏伟愿望就是刻画现在的与未来的各式各样的关系。”[2]107文学要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复杂而多样的面貌。
卡尔维诺为了说明他对百科全书型小说的重视,他列举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作为例子,如:但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创作了百科全书式的、具有宇宙派的作品,他用书面文字建造了有关世界和认知的一张地图,书中所写涉及了神学、玄思、想像、百科全书甚至被视为自然科学或者被视为对变形、梦幻的考察;卡尔洛·埃米里奥·加达“终生不渝地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线团、一个线球或一团乱麻,从不忽视它的复杂性。即从来不忽视同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互相区别的因素”[2]101;穆西尔“把所知道的或想知道的都写进一本百科辞典型的书中,而且极力赋予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2]105,使这本书的结构不断地变化;福楼拜为创作《布瓦尔和佩居谢》花了十年时间,读了1500多本书,他为了创作两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自己也“变成了百科全书”[2]11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所包含的思想至今还是各式各样思想的源泉;乔治·佩雷克创作的《生活的使用说明》用一种精确的数学模式容纳了客观世界的百科知识;还有歌德、利希滕贝格、诺瓦利斯、洪堡、马拉美等都试图创作百科辞典型的作品。
卡尔维诺极力推崇博尔赫斯,因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宇宙模式或宇宙的某一特性的模式,如无限、无数、永恒、同时、循环,等等;他的文章都很短小,是语言简练的典范;他写的故事都采用民间文学的某种形式,这些形式经受过实践的长期考验,堪与神话故事的形式相媲美”[2]114。卡尔维诺还举例说明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一篇间谍故事,里面包括一个抽象推理的故事,后者又包含对一本中国巨型长篇小说的描述,所有这一切都压缩在12页的篇幅里。
对百科全书型小说的喜爱,充分体现了卡尔维诺对内容多样和高度浓缩的追求,对宇宙和速度的追求;文学不提供答案,只告诉人们各种可能性,文学只是一种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网。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信息、知识和幻想的一种组合。“每个人都是一本百科辞典、一个图书馆、一份物品清单、一本包括了各种风格的集锦。在他的一生中这一切都在不停地相互混合,再按各种可能的方式重新组合。”[2]119因此,作品内容的多样化,才是真正的作者个性、真挚和诚实的统一。
综上所述,在处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时,卡尔维诺主张以轻逸的方法来观察世界,以轻逸、快速的手段来表现世界,并且要求文学最终表现一个全面的、复杂多样的世界。卡尔维诺对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并为未来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6.
[2]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Z].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70.
[4]伊塔洛·卡尔维诺.通向蜘蛛巢的小径[Z].王焕宝、王恺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9-10.
[5]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5.
[6]罗兰·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3.
[7]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511.
[8]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