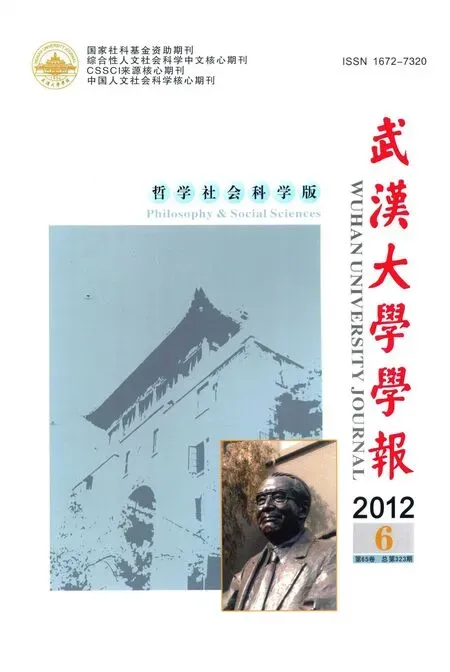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以迪亚洛案为例
万鄂湘 黄赟琴
1998年12月28日,几内亚政府以提交请求书的方式向国际法院起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声称刚果对几内亚国民迪亚洛(Diallo)的一系列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在确定几内亚部分诉请的可接受性之后①在双方都已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情况下,刚果为阻止国际法院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于2002年10月3日对该案的可诉性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2007年5月24日,法院作出关于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认定几内亚提出的三类权利主张中的两类具有可诉性,即几内亚有权对其国民迪亚洛的个人权利及作为股东的直接权利进行外交保护。但是,法院驳回了几内亚提出的,其有权为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对该国民作为股东的公司行使替代保护的主张。Case Concerning Ahmadou Sadio Diallo,Preliminary objection.,国际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最终判决②几内亚公民艾哈迈迪·萨迪奥·迪亚洛自1964起在刚果定居。由于试图追讨刚果以及几家石油公司对迪亚洛所拥有的公司Africom-Zaire和Africontainers-Zaire欠下的债务,他多次遭到该国当局的逮捕及拘禁,并最终于1996年1月31日被驱逐出境。1998年12月28日,几内亚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方式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声称刚果的行为侵犯了其国民迪亚洛在国际法保护下的多项权利。2010年11月30日国际法院对迪亚洛案作出最终判决。。该案审理历时10余年,并涉及外交保护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投资法等诸多重要领域,整个审理过程都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数量颇丰的论著从不同角度对该案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国际公法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也出现了相关词条,但鲜见从人权条约解释方法的角度研究该案。然而,该案虽是几内亚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方式提起,却是国际法院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处理人权问题③在迪亚洛案中,针对迪亚洛的个人权利问题,几内亚提出刚果政府驱逐迪亚洛的决定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3条以及《非洲人权及民族权宪章》(以下简称《非洲宪章》)第12条第4款;1995年至1996年期间对迪亚洛的多次逮捕及监禁违反了《公约》第9条第1款、第2款,以及《非洲宪章》第6条;在拘禁期间迪亚洛所遭受的非人道及侮辱性待遇使其受《公约》第7条,第10条第1款以及《非洲宪章》第5条保护的权利受到侵害;在两次逮捕期间,刚果当局都没有迅速告知其有请求领事协助的权利,这违反了《维亚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第1款b项。法院的判决正是围绕着对这些条款的解释而展开。在该案之前,国际法院在许多案件中,在处理其他问题时也常常附带涉及到人权问题,这些案件对人权法在各方面的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Shiv R S Bedi.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by the Jud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Portland:Hart Publishing,2007.。并且,尽管刚果和几内亚都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的当事国,但国际法院在该案中对有关人权条约的解释并未援引被公认为是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至第32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在国际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中也得到了肯定。如,Territorial Dispute(Libya v.Chad),para.41;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1995,para.33;1996,para.23;Oil Platforms,Preliminary Exception(Iran v.United States),para.23;Kasikili/Sedudu Island(Botswana v.Namibia),para.18;LaGrand Case(Germany v.United States),para.99;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tigan and Pulau Sipadan(Indonesia v.Malaysia),para.37;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para.94.,其解释实践有可能使该案成为国际人权条约解释方法演进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因此,本文拟以2010年国际法院迪亚洛案最终判决为例,试图就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一、人权条约模糊抽象的特点为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在《条约法公约》起草之前,学理上对于条约的解释的探讨,大致分为三个学派:主观学派、客观学派及目的学派。其中,主观解释学派认为解释条约应将重点放在探求缔约国在缔约时的共同意思上;约文解释学派反对过分强调探求缔约各方的真正意思,认为仲裁或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应在于对一个条约中的某一词语,按其上下文,确定其自然的和通常的意义;目的解释学派则强调一个条约应符合该条约的目的②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39~347页;万鄂湘:《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216页。。国际法委会在起草第31至32条时,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以避免教条主义③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国际法委会强调在解释条约时应对条约文本、上下文、通常含义、条约目的与宗旨、当事方意图等诸多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拒绝给予某一种特别的因素以更多的重视的观点④Commentary on the 1969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pp.415~449.。然而,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解释结果。因此,第31至32条所采之折衷式方法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满足解释不同类型条约的需要,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使得条约解释规则在确定性方面有所损抑。在实践中,《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解释规则只是对解释过程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最终仍无法解决条约含义模糊不清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依据这些解释规则也难以从多种可能的含义中选择一个较为确切的意思⑤Joseph Weiler,“Prolegomena to a Meso-theory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draft unpublished presentation,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Colloquium: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available at http://iilj.org/courses/documents/2008Colloquium.Session5.Weiler.pdf,2012-5-5;Myres McDougal,“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Draft Articles Upon Interpretation:Textuality Redivivu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7(61).。
如果说一般国际法中的条约解释已经是一项难题,那么有关人权条约的解释则是最难以解决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⑥M.Fitzmaurice.“Dynamic(Evolutive)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Part I”,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21).。这首先与人权条约相较其他条约更为模糊抽象的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国际人权条约是世界各国为促进人权的发展与保护而在人权领域进行国际或区域层面合作的产物。人权条约谈判国数目众多,且在不同文化传统及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对于人权概念的理解分歧较大。为了弥合这些分歧,在人权条约的起草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一些宽泛的措辞以使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另外,基本权利大多以宽泛的原则运作,而不是精确的规则。因此人权条约所保障的人权,其含义总是模糊不清的⑦Henry J.Steiner,Philip Alston & Ryan Goodma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Law,Politics,Morals,3d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80~294;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三联书店2008年,第9页。。人权条约在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必然会遇到大量的解释问题。不同的解释者受各自信仰、偏好、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对这些抽象的人权概念作出了各异的解释,有时甚至先有结论,然后再为这个结论寻找法理支持。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就此批判道,由于鼓励草率的人道主张以及对不清晰且无拘束力的原文表述过于形式的依赖,人权运动降低了法律的专业性⑧David Kennedy.“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vement:Part of the Problem?”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2002(15).。
二、非互惠性的特点使人权条约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其目的与宗旨
为限制解释过程中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许多学者认为人权条约的解释应适用特殊的解释规则,并将解释方法上的特殊性归因于人权条约的非互惠性①R.Bernhardt.“Though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rights Treaties”,in Franz Matscher & Herbert Petzold(eds.),Protecting Human Rights:The European Dimension:Studies in honour of Ggrard J.Wiarda,Koln:Carl Heymanns,1988,pp.65~71;Mark Toufayan,“Human Rights Treaty Interpretation:A Postmodern Account of its Claim to‘Specialty’”,NYU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Justice Working Paper,2005.。早在1951年,国际法院就注意到人权条约的这一特殊性。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问题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就指出,在这样一类条约中,缔约国不具有任何它们自身的利益,它们所具有的唯一的和全部的是一项共同利益,即实现作为公约存在之理由的崇高目的。因此,在这样一类公约中,我们不能谈论各国单独的有利或不利或者对约定的权利义务之间完美平衡的维持。美洲人权法院认为,人权条约区别于传统类型的多边条约,不是为了缔约国相互间的利益,完成权利的互惠交换而缔结;人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是不论国籍,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包括其母国在内的所有缔约国的侵害②Restrictions to the Death Penalty(Arts.4.2and 4.4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Advisory Opinion OC-3/83,September 8,1983,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50.。同样,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强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不是国家间义务组成的网络,它们关注的是赋予个人以权利,在这种条约中,国家间的互惠原则是没有位置的③General Comment No.24,UN Doc.CCPR/C/21/Rev.1/Add.6,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17.。因此,人权条约虽由国家参与制定,但人权条约所保障的权利直接由个人所享有,缔约国负有尊重、实现和保护条约所列人权的义务,并且这一义务不因互惠性的承诺而有所减损。
人权条约的非互惠性特点使得人权条约在解释与适用时特别强调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因素,并且较为排斥探寻缔约方意图的解释方法。欧洲人权机构认为,解释《欧洲人权公约》中的人权条款必须是能最恰当地实现条约的宗旨与目的,而不是最大程度地限制当事方应承担的义务④Case of Wemhoff v.Germany,Application no 2122/64,Judgment of 27June 1968,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8.。为了实现条约的目的与宗旨,人权条约应当考虑社会及法律的变迁,在当前的环境下予以解释,而不应拘泥于公约在批准当时的缔约方的理解。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许多场合下也采取了以上相类似的解释方法⑤例如,在约翰斯顿诉牙买加(Johnston v.Jamaica)一案中,人权委员会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7条、第10条以及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第6条必须根据公约的目的与宗旨予以解释。Johnston v.Jamaica,Communication No.588/1994,22March 1996,UN Doc.CCPR/C/56/D/588/1994,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8.2(c);又如在尹和崔诉韩国案(Yoon and Choi v.Korea)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根据公约第18条的文本及目的,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对公约其他保障的理解一同发生变化的。Communications Nos.1321/2004and 1322/2004:Republic of Korea.2007-01-23.UN Doc.CCPR/C/88/D/1321-1322/2004,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8.2.。这些解释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解释者的自由裁量范围。然而,条约的目的与宗旨也是空泛概括的。究竟何谓条约的目的与宗旨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判断一项行为是否符合保护人权的宗旨并非易事。如在德国共产党一案中⑥1956年8月17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裁决中宣布,德国共产党违反宪法,应予以解散并没收其财产。之后德国共产党向欧洲人权委员会申诉,指控上述裁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言论、思想和结社自由。,欧洲人权委员会以解散德国共产党是为了保护《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为由驳回了德国共产党的申诉。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根据德国共产党所发表的宣言,该党的目的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与《欧洲人权公约》背道而驰,将压制若干《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⑦Council of Europe,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The Hague:Mar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57,pp.222~225.。一般而言,很难说限制人权保护的解释仍然与人权条约整体的目的和宗旨是一致的⑧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在该案中,目的与宗旨却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同的解释者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各取所需,而标准的确定则最终取决于实质上的有权解释者。
不可否认,由人权条约的非互惠性特点所决定,目的解释方法在人权条约的解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解释方法仍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权条款模糊性的问题,“条约的宗旨与目的”概念本身尚有待厘清。国际法院在迪亚洛一案中并未抽象地谈论《公约》及《非洲宪章》整体或有关条款的目的与宗旨,也没有提及《条约法公约》其它的解释规则。
三、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人权条约难以形成特定的解释
人权条约具有非互惠性的特点,考虑到人权条约的遵守不是依靠对等原则获得保障,因此不得不引入集体监督和实施机制①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第35页。。几乎所有的人权条约都存在监督机构。除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建立以外,联合国其他八个核心人权条约②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及《残疾人权利公约》。都根据条约本身设立了相应的条约监督机构用以监督条约的执行情况。它们的职责一般包括:接受并审议由缔约国定期提交的报告,详细说明条约条款在其本国的执行情况;发出准则协助各国编写其报告,制定一般性评论解释条约条款,并就与条约相关的专题组织讨论;在缔约国明确承认的基础上,审议个人声称其权利被缔约国侵犯的投诉或来文;在接到可靠和充分的信息,认为可能出现了严重或者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时,依职权启动调查程序等。在区域人权机制中,还建有人权法院等司法机构对区域人权条约中规定的权利进行有约束力的管辖和解释。国际机构在履行上述监督职能时,无可避免地对有关人权条约的条款予以解释。因此,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主体虽然主要是主权国家,但解释权却不只属于国家。
有些学者认为由当事国解释国际人权条约会产生许多问题。在他们看来,由于人权条约具有非互惠性的特点,国家极易对人权条约进行限制性解释以减缓所承担的义务,并在国内政策制定上保持更大的自由,这将破坏人权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并有损于人权条约的有效实施。而由相对独立、中立的国际机构进行解释则可避免解释结果过度地遵从国家利益,从而更能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③Kerstin Mechlem.“Treaty Bodi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ights”,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09(42);John Tobin.“Seeking to Persuade: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Treaty Interpretation”,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2010(23);Kristen M.Hessler.A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01,pp.85~107;James Hathaway.The Rights Of Refuge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71.。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沙赫特(Schachter)教授所指出的,国家虽常受自身利益驱动,但这并不表明国家不能为其所期望结果的产生提出公正的法律基础。利益与正当性在分析时是被区别对待的。不论政府的行为目的为何,为了使它们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各国必须将正当性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而不是它们自身的利益或愿望。况且,有时国家的主张只是关乎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事项,并没有法律上的要求排斥这样的主张,换句话说,法律将该事项的决定权留给了国家④Oscar Schachter.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Hague:Mar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p.35.。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了国家“承担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以便……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之义务。仅从文字表述即可看出该条只能由缔约国根据各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加以解释。又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家庭”(family)一词的含义。即使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对个人申诉具有强制管辖权的欧洲人权法院也不得不承认该词的含义取决于各国历史文化上的差异⑤Pieter van Dijk.“A Common Standard of Achievement.about Universal Validity and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1995(13).。但是,部分甚至是个别的缔约国的解释不产生约束全体缔约国的法律效力,只能约束本国或有关各国,因为国家在其条约关系中不可能不经其同意而受拘束。全体缔约国对一种解释达成协议,是该解释在缔约国间产生效力的必要条件,个别缔约国或少数缔约国的解释只有经全体接收后才产生上述效果⑥万鄂湘:《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同样,条约机构在履行其监督职能时对有关条约所作的解释,在未经全体当事国明确接受或通过嗣后一致的实践默示地表明接受时,这些解释只产生建议的效果,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国际法院及区域人权法院在案件审理当中对有关人权条约所做的解释虽是有权解释,但它们对案件的审理需以当事国的授权为前提⑦欧洲人权法院除外。,且其对条约的解释仅仅约束该案当事国。
由于国际法所建立的不是一种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超于当事者的最高权威⑧梁 西:《国际法》(修订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因此,在这样一种横向的“平行式”社会中,若无国家授权就不可能有一个处于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来解释法律。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对条约的解释都是独立进行的,不存在一方超越于另一方的权威。在国际机构的实践中,它们往往对人权条约中界定特定权利适用范围的术语进行自主解释,而不用缔约国国内法中这些术语或者其国内法院的权限来解释。例如,在阿瓦斯庭尼诉尼加拉瓜(Mayagna(Sumo)AwasTingniCommunityv.Nicaragua)一案中,美洲人权法院强调,“国际人权条约中的用语具有自主的意思(autonomous meaning),因而不能等同于这些词语在国内法上的含义。”①C ase of the Mayagna(Sumo)Awas Tingni Community v.Nicaragua,Judgment of August 31,2001(Merits,Reparations and Costs),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146.欧洲人权法院在恩格尔诉荷兰(Engelv.TheNetherlands)案中也认为,如果当事国能够任意地将“违反”(offence)归类为“违纪”(disciplinary)而不是“犯罪”(criminal),或者以违纪而不是犯罪为由起诉具有各种犯罪的行为人,那么《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及第七条(该两条规定了被起诉犯罪的行为人的最低权利)的实施将会从属于主权意志②E ngel et al.v.The Netherlands,Application Nos.5100/71,5101/71,5102/71,5354/72,5370/72,Judgment of 8June 1976,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81.。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这方面与以上两区域人权法院也有着基本一致的实践。在凡杜森诉加拿大(Van Duzen v.Canada)一案中,当事国曾广泛援引各自国内法上的概念以解释规定在《公约》第15条中“刑罚”一词的含义。人权事务委员会否认了这种解释方法,原因是:“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公约的术语及概念独立于任何国内制度或法律的原则之上。尽管公约的用语的确来源于许多国家长期的习惯,但是委员会现在必须将它们视为具有自主的意思。”③Communication No.50/1979:Canada.1982-04-07,UN Doc.CCPR/C/15/D/50/1979,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10.2.在2008年的赛亚迪和万克诉比利时(Sayadi and Vinck v.Belgium)一案中,这种观点再次得到重申④Communication No.1472/2006:Belgium.2008-12-29,UN Doc.CCPR/C/94/D/1472/2006,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10.11.。人权条约中大部分的术语或表达,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及政治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其涵义在各国之间不尽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国际机构对它们加以自主性解释。另外,对于一些限制条款⑤即 规定缔约国可以采取措施克减特定条约义务的条款,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及《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等。,由于只有缔约国最了解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国际机构也不能取代国家判断社会紧急状态是否存在以及哪些措施是为防止这种状态所绝对必要的。但是,为了避免国家滥用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利来逃避其根据条约所应承担的义务,欧洲人权机构在实践中发展出“自由判断余地原则”,即承认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有自由判断和裁量的余地,但国际机构保留对国家采取的限制措施是否符合条约之要求的审查监督权⑥孙世彦:《欧洲人权制度中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美洲人权法院曾在建议修正案(ProposedAmendments)咨询意见中给予该原则以重要考虑,认为“国籍取得的条件,以及是否符合该条件的决定权属于国家,但是法院的结论不应被看成是赞成这样一种实践,即在某些区域将限制入籍人的政治权利夸大至不正义的程度。”⑦P r 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Naturalization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osta Rica,Advisory Opinion OC-4/84of January 19,1984,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62.人权事务委员会虽未明确采用“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但实际上在这方面也遵循了欧洲人权机构的方法⑧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三联书店2008年,第90~112页。。诺瓦克(Nowak)认为,这是国际法在承认主权国家为保护其宪法和民主秩序而具有的合法权力和禁止只为了维持其事实上的权力地位而滥用紧急状态的权力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⑨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89页。。
本案中,几内亚曾提出迪亚洛受《公约》第13条所保障的被驱逐的外侨有权“提出反对驱逐出境的理由和使他的案件得到合格当局复审”的权利没有得到刚果的尊重。刚果则辩称,当存在“国家安全的紧迫原因”时,该条有例外规定,而该案正是出现了这样的“紧迫原因”。国际法院否认了刚果的主张。除刚果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的紧迫原因”外,法院还特别指出:“原则上,毫无疑问应由国内机构考虑是否出现了有必要采取某项警察措施的公共秩序方面的原因。但是,当这涉及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重要的程序保障被搁置时,就不能简单地由国家断定排斥这种保障的情形是否存在。”⑩以上表明,国际法院虽未明确提到“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但其推理与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实践并无二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证驱逐令由总统签发是否符合刚果国内法这一问题时,法院甚至认为,“国内法应首先由国家进行解释,国际法院原则上无权取代该国国内有权机构,
⑩判决第74段。尤其是该国最高法院对该国法律的解释。然而,当一国对其国内法的解释明显不正确,特别是为了在待决案件中谋得利益时,法院将采用它所认为的合适的解释。”①判决第70段。一般来说,国家虽负有善意履行国际义务,不使其国内法与所加入的条约相冲突的义务,而至于该国如何解释其国内法,则完全是一国主权管辖下的事项,国际机构本无权置喙。但倘若一国有权机构作出驱逐决定所依据的法与《公约》并不相冲突,是否仍有可能出现违背《公约》第13条的情形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国际机构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审查这一决定与国内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在马鲁菲多诉瑞典一案(Maroufidouv.Sweden)中,人权事务委员是这样认定的,“对国内法的解释在实质上是缔约国的法院和行政机构的事情。委员会没有在其根据《任择议定书》审理的案件中评估缔约国的合格当局是否正确地解释和适用了国内法的权力和职能,除非它可以证实这些法院或行政当局没有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国内法律或者明显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②Communication No.58/1979:Sweden.1981-04-08,U.N.Doc.CCPR/C/12/D/58/1979,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 10.1.很明显,国际法院在迪亚洛案中遵从了这种“马鲁菲多模式”(Maroufidou formula)的中间路线。
四、人权条约在内容上的重合为各解释主体相互引证提供了客观基础
人权条约在内容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其中有些重合的规定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习惯法规则,如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动等③龚刃韧:《不可克减的权利与习惯法规则》,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在迪亚洛一案中,法院肯定了禁止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属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拘束国家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即使在无条约承诺的情形下也对国家具有拘束力④判决第87段。。还有一些权利,尽管在各人权条约均有相同的规定,但其是否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习惯法规则尚不能完全确定。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13条,《非洲人民和人民权利宪章》第12条第4款、《欧洲人权公约》第7号议定书第1条及《美洲人权公约》第22条第6款都规定了外国人免受任意驱逐的权利。这些条款在措辞上极其近似,但是由于诸多法定例外情况的存在使得这一规则能否确立为习惯国际法规则仍存在疑问。然而,这些共同的规定却为国际法院在解释这一规则时广泛借鉴参考其他国际机构的裁决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
在本案中,针对几内亚提出的刚果驱逐迪亚洛的行为违反了刚果在《公约》第13条及《非洲宪章》第12条第4项下义务的主张,国际法院首先对有关条款进行了解释。国际法院认为,“根据这两项规定的措辞,只有当缔约国驱逐合法处于其领土内的外侨的决定是根据国内法作出的时候,该国的驱逐行为才符合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在这里,是否遵守国际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守国内法。然而,很明显,‘依法’仅是遵守这两项条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首先,可适用的国内法其本身必须符合《公约》及《非洲宪章》的其他要求;其次,驱逐必须在本质上不是任意的,因为保护不受任意对待处于人权保护国际规则所保障的权利的核心。”⑤判决第65段。法院在作出以上解释时,并未依据《条约法公约》第31条及32条的规定,也未参考其他有关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这使得法院的解释主观性较强。为了增强判决的说服力,法院分别引用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案例、一般评论,非洲人权委员会的案例,甚至是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的有关案例来证明其所作解释为共同接受的标准。对于人权事务委员会和非洲人权委员会的解释,法院认为它并没有义务照搬,但应给予着重考虑。其目的是“实现国际法必要的清晰、基本的一致,以及法律安全”⑥判决第66~67段。。人权事务委员会及非洲人权委员会都是为了监督条约的正确适用而创设的独立的专家机构及准司法机构,所作裁决及一般评论皆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国际法院当然没有义务采纳它们对相关条款所作的解释。但是,这些一般评论及裁决往往构成《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b项的“确证该条约各当事国对该条约的解释一致的该条约适用上的嗣后惯例”的证据。在各条约机构的解释实践中,其曾经作出的一般评论及裁决经常被引用,其数量之多甚至可认为这种解释方法已成为人权机构解释人权条约的主要方法①Helen Keller,G.Ulfstein.UN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Law and Legit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3。如果说国际法院借鉴参考人权事务委员会及非洲人权委员会的解释体现了国际法院对人权机构嗣后惯例中所蕴含的当事国共同意志的尊重,那么国际法院以欧洲人权法院及美洲人权法院这两个与本案当事国毫无关系的区域司法机构的判例为例证,其理由是这四个人权条约有关驱逐外国人的条款“在本质上是接近的”②判决第68段。。这种相互参考的解释方法在国际法院中是第一次应用,但绝不意味着在其他国际机构中不存在先例。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曾在1989年的贝拉斯克斯·罗德里格斯诉洪都拉斯案中参考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系列相关实践以证明其对违反人权的赔偿案件具有管辖权③Case of Velásquez-Rodríguezv.Honduras,Judgment of July 21,1989 (Reparations and Costs),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28.。次年,又引用欧洲人权法院林盖森一案(RingeisenCase)以考虑其解释判决的权力④Case of Velásquez-Rodríguezv.Honduras,Judgment of August 17,1990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Reparations and Costs),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26.。在建议修正案咨询意见中,美洲人权法院采用了欧洲人权法院比利时语言案(BelgianLinguistic)中的论证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差异都构成歧视⑤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Naturalization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osta Rica,Advisory Opinion OC-4/84of January 19,1984,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56.。在新闻审查案(LicensingofJournalism)中,美洲人权法院明确写道,欧洲人权法院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案(TheSundayTimes)中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的分析结论同样适用于对美洲人权公约相应条款的解释⑥Compulsory Membership in an Association Prescribed by Law for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Arts.13and 29American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Advisory Opinion OC-5/85of November 13,1985,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para.46.。相较于美洲人权法院,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在借鉴其他机构案例方面则显得较为保守。只是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一份裁决中,该委员会明确援引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及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解释⑦Communication No.30/2003:Norway.2005-08-22,U.N.Doc.CERD/C/67/D/30/2003,CERD Committee,para.7.3.。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条款内容上的一致性不可过分强调,有时即使相同的措辞在实际适用时也不排除对标准的不同解读。例如,对规定在《公约》第9条第1款及《非洲宪章》第6条“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拘禁”中“任意”一词的解释,就不可能为任何时候、所有地区划定一条界限。国际法院最终根据影响迪亚洛遭拘禁的不正当行为的数量及严重性等具体情况判定刚果逮捕拘禁迪亚洛的行为构成对《公约》第9条第1款及《非洲宪章》第6条义务的违反。
五、结 论
从迪亚洛一案,我们可以看出,《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只是对解释过程加以了一定的限制,但最终仍无法解决条约含义模糊不清的问题。对人权条约来说,尤其如是。首先,国际人权公约中大量使用模糊语言从而为解释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其次,人权条约解释中尤为重要的目的与宗旨解释方法,由于“目的与宗旨”概念本身相当宽泛,因而仍难以解决实践中有关解释的争议。这一矛盾由于人权条约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和缺乏权威的解释主体而更加突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由全体当事国就某种解释达成一致的协议才构成正式的、有权的解释,但对于多边条约而言,要想每一当事国对于条约某一解释都予以同意,一般来讲,是不太现实的⑧万鄂湘:《国际条约法》,第242~243页。。司法机构作为最后的补充手段,也属于有权解释,但它们的解释权通常以当事国的授权为前提。条约机构对各自条约的解释并未被赋予法律地位,而只有道德权威。由于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法律体系那样的司法等级制度,人权条约的各解释主体在解释人权条约时都是分别独立进行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际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机构之间它们极有可能产生冲突。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其基础都应源于条约当事国之间的共同意志。国际机构在取得当事国的授权对有关人权条款进行解释时,不能偏离主权国家的意志。相较于国家,国际机构似乎更加以保护人权为圭臬,但它们也只能在国际人权保护和国家主权之间颇有难度地走钢丝①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第57页。,否则其所作解释无法为主权国家所接受而最终有损其权威。同时,国家也不能单凭某个或某些国家的意志对人权条约加以解释,不能简单地将同一术语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含义套用到对国际人权条约的解释上,而必须遵从体现在条约中的各当事国的“共同意志”,且这种“共同意志”并不限于缔约当时各国的意志,而是在当前环境下各国在条约适用上相一致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意志②Communication No.829/1998:Canada.20/10/2003,U.N.Doc.CCPR/C/78/D/829/1998,Human Rights Committee,para.10.3.。缔约国间的某些实践实际上可能偏离了条约原来所设计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缔约国间的实践是一致的,在不违反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就成为有效的实践解释③万鄂湘:《国际条约法》,第240页。。当这种共同意志尚不明确、难以证明,或只是具有某种趋势而未最终形成时,国际法院却不能因为当事国对争议条款理解的不一致而拒绝司法,而只能根据条款本身判定当事国有无违反其根据条约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院在迪亚洛一案中所采取的方法是,先由国际法院构建出有关解释的“共同意志”,再通过其他国际机构的相关解释来佐证其所作解释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正如王铁崖先生所指出的,不少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仅单纯适用国际法,而且在适用中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国际法原则和规则④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这种由国际法院所创造的“法”在经过国家的默许之后,并随着国家及国际机构一致实践的增多,便有可能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法。其拘束力来源于国家及国际机构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国家共同意志。对于人权条约的解释也是如此。其他国际人权法院及人权条约机构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对各自条约所作解释经多次相互引证,特别是被国际法院引证后,也能对人权条约某项条款意思的确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国际机构构建出的国家“共同意志”必须以主权国家的意志为基础,若将毫无国家意志基础的解释强加给国家,则不仅超越了解释者的权限,而且还会遭到国际社会真正的“立法者”── 主权国家的反对。如欧洲人权法院在许多案件中不顾国家意志,将公约义务看成是具有客观性质的义务而擅作解释的做法就遭到了许多政府及学者们的严厉批评⑤Malgosia Fitzmaurice.“The Tale of Two Judges Sir Hersch Lauterpacht and Sir Gerald Fitzmaurice: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Revue Helle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8(1).。迪亚洛案中,国际法院在充分尊重当事国意志的前提下,通过参考借鉴其他国际机构的案例对有关条款进行了解释,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受到法官在异议意见中的质疑,而且其对迪亚洛根据《公约》第13条、《非洲宪章》第12条第4款及根据《公约》第9条第1款、第2款及《非洲宪章》第6条所享权利遭到侵犯的判定得到法官们的一致认可。
必须强调的是,国际机构虽在推动形成人权条约具体实施标准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但由于主权国家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国际机构的解释若没有适应主权国家的意志则有可能被后来的实践所推翻。因此,我们应重视各国及国际机构的实践,有必要收集、编辑并出版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及有关国际机构践行人权条约的实践材料,并加以研究。通过此举,不仅向外充分表明我国的立场和意见,同时把握最新实践发展动态,以为将来在我国人权问题遭受挑战时能够更加及时和有力地作出回应。同时,由于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传统上被认为是国内管辖的事项,规定在公约中的权利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极其相似,因此国际人权法庭的裁决不仅在彼此间,而且在国内法院,特别是一国宪法法院中也经常被引用⑥安妮—玛丽·斯劳特:《世界新秩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72页。。国际人权机构的推理和经验同样可为我国司法机关在重大判决中所学习和借鉴。它们的裁决对我国法院虽不具有约束力,但在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前提下,国际机构对有关权利的论证推理可为我国法院在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中审理有关个人权利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