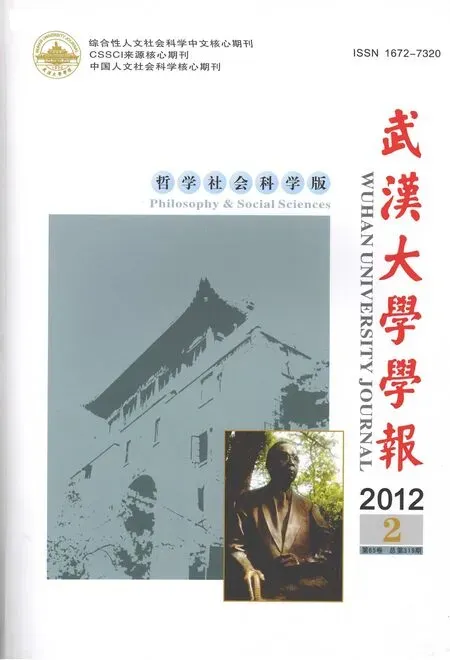刑法文化解释问题研究
徐光华
刑法文化解释问题研究
徐光华
刑法解释是将纸面上的刑法付诸实践的重要一环,是刑法解释学的本体。我国现阶段的刑法解释学过于注重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使得刑法与社会生活面临不同程度的脱节。对于刑法立法、刑法解释而言,进行经验积累式的解说,实际上是让刑法回归生活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在对刑法进行文化的解释,是对刑法经验积累的重新回顾。刑法解释必须结合本土文化展开,才能使刑法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刑法解释;社会文化;礼法结合
一、刑法解释脱离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刑法解释学是刑法的基础,我国刑法学者近些年来在刑法解释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赌的,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股刑法解释学之“热风”。虽然关于刑法解释学方面的著述已经非常丰富,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并不理想。从1997年刑法出台后,我国连续出台了一部单行刑法、八个刑法修正案,说明我国刑法学领域更多的是批判立法。并且,每一次刑法修改之后,对于相关内容的批判性的文章便不断出现,这也反映了刑法学的研究不是尽量地解释刑法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生活,而是过多地批判立法。“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应该通过发达的刑法文化解释学来更好地适用刑法。
就我国目前关于刑法解释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关于刑法解释技术、方法的研究较为深入。如对于各种解释方法的来缘、意义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刑法学界给予了过多的关注。传统解释学将解释视为“避免误解的艺术”,因此,非常重视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宏观层面的关于刑法解释的研究也在逐步开展。刑法解释学不仅仅是具体解释方法的研究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而且如何指导具体方法的运用,刑法解释的立场、原则等宏观层面的研究显得必不可少。拘泥于具体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研究将无助于提升刑法解释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我们的刑法解释研究注重方法和技巧,但犯了法律解释上功能主义的错误。法律解释上的功能主义,是法律解释上的这样一种立场和方法,即观念上仅把法律简单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忽视法律作为文化符号的体现价值之一面,因此只从功能层面解释法律,而看不到表面上功能相近的制度之内之后可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依据①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第54页。。现今关于刑法解释学的学者寄希望于制定出一套一劳永逸的解释方案,以期能够解决刑法适用中的所有难题。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性决定了,稳定的刑法不可能通过一劳永逸的解释方案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刑法解释学在联系刑法与实践中的任务是持续的。如何解释刑法,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必然要求对刑法进行实质合理的解释。
二、刑法文化解释的必要性
在法律的生成模式上,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两种主要途径:一是理性建构,一是经验积累。但是,近代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第二种模式,无论是在刑事立法还是刑法解释领域,过分强调理性建构的意义,这一教训在其他部门法领域是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定的大量民商事、经济立法,如破产法,虽然基于理性建构,但却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如果缺乏对社会现实经验的审视,刑法将难以符合现实,即使对于理性建构而言,也绝非空中楼阁,而应奠基于经验积累之上。因此,对于刑法立法、刑法解释而言,进行经验积累式的解说,实际上是让刑法回归生活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在对刑法进行文化的解释,是对刑法经验积累的重新回顾。毕竟,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诸多内容是人类在与自然、外敌的斗争中多次试错行为的结果,是人类对付外界威胁和维持内部秩序的最优抉择的结果。
刑法解释学不仅仅是刑法学者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必须面向中国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使刑法解释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刑法规范的形成和解释,既要尊重生活事实、发现生活原型,又要发挥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和主观性构建。刑法既不是一种生活事实和秩序的简单模拟,也不是一种脱离生活、异想天开的纯粹发明。刑法只能是一种建立在发现基础上的对生活事实的再创制和再构建”①杜 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笔者认为,刑法解释学再也不应该局限于刑法解释方法的深究,不应拘泥于空洞的概念的理解,而应该面向中国的本土文化这一实际。法律文本本身的文字含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必须进行文化解释。刑法解释应贯彻非法学解释方法,而非法学解释方法虽然指向刑法条文,但更注重的是对刑法条文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效果以及对可能性效果的预测和检验。这样的情形决定了在使用非法学方法时所选择和运用的材料也不同于法理解释方法,前者尽量遴选刑法条文实现的现实情形和可能情形,这样的材料必须尽可能的全面,能够进行归纳和抽象,而后者则用的是刑法理性认识的基本结论,虽然这些结论也来源于经验和实践的积累,但主要是理性分析和理性推理的成分②赵秉志:《刑法解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3页。。
三、我国刑法解释脱离本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目前刑法解释并没有很好地结合本土文化展开,导致刑法适用中的诸多困惑,例如,对于亲属之间的窝藏、包庇行为如何定性,我们面临情、理、法的艰难抉择;对于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司法解释,对于偷拿自己家里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但对于亲属间的抢劫、诈骗或者其他犯罪,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也同样面临亲情与刑法的协调。刑法解释必须结合本土文化展开,才能使刑法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在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如果在立法大量出台之后,实践中有法不依的现象又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对于法制权威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四川省凉山县的彝族地区,民间权威依习惯法处理的案件是法院法官的十倍甚至数十倍③陈金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述论》(上),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藏族地区赔命价的习惯虽然国家已经多次出台规定予以禁止,但仍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不可否认,这些处理方式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绝大多数的案件通过习惯法来处理,民众对刑法的认同感会逐步降低,影响刑法的权威。如果刑法解释实践中能重视本土的具体文化背景,如在国家制定法的领域引入习惯法等因素,既可以提高刑法的威信,又能使案件的处理得到较好的效果,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如果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司法也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将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在国家倡导建立法制社会的同时,我们对于法律包括刑法在内寄予了太大的期望,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法律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忽略了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尤其是土生土长于我们实际的办法。即使制定法出台之后,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些曾经长期、反复适用的有效的办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坚持。中国乡土社会的平民阶层很少有能够通晓国家法律的,但他们大多数都能够不触犯法律,这无疑是因为教化使得宗法观念和意识深入人心,而国家的法律又是依照宗法制度来制定的,因此,在中国古代法律和宗法观念是相统一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宗法意识成为连接国家法律与乡土社会的纽带①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背景的考察》,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地方官在上任伊始往往派员或亲自赴乡里调查民俗。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地方法官则通过一种“向居民进行习惯法调查”的方式,发现管辖区域内的习惯法②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其奉行的是一种以实用主义为至归的生活哲学。法律,包括刑法,如果与民众的习俗、生活习惯、解决问题的方式等不符合,必将在短期内遭到淘汰。在刑法学界,赶学德日、英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口号。由此也造成了一种局面:对刑法文化的关注很少,我们的刑法学研究言必称英美、德日。殊不知,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是具有地域性的,必须结合本土文化适用。法律既是一种规范、规则与制度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理念、思想与文化的范畴。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现时的,因此,对于刑法进行文化解释是永远都存在的。法理学研究者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法律,往往偏重于对国家制定法的实证操作,相对地缺乏对法律的文化分析,缺乏对法律所由产生的生活本身的关注。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是以方法论为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的,这只是法解释学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层面。我国过去的法学研究是只注重法律汇集的核心地带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分散着的诸多习惯法的周边地区的研究,这种“以点代面”的研究是无法关照中国这一复杂文化整体的全局的。法律、道德、习惯和风俗本身是一种文化,或者说,它们是文化的构件。例如,习惯法的每一个运行过程:议定、实施、适用、解释等,无不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而其仪式、语言、动作、精神等,又无不是文化的真实表征③李 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从刑法适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诸多问题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甚至可能加深了刑法与民众的冲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刑法解释学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解释技术、方法的问题,而必须基于文化的立场加以实质的考察。在进行刑事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也不是必须固守所谓的法律逻辑和推理,盲目机械地维护所谓法律的内在价值。相反,我们应当更为强调对刑法制度的一种宽松和开放式理解,尽量复归到“民意”、“情理”、“习惯”这些更为本源的所谓法律外在价值。尽管我们仍然不能无视刑事制定法上的现行规定和制度,但绝不能将其奉为不可动摇的根本基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规定和制度背后更为基础的价值,并在刑法解释中去全面贯彻和竭力表达这些理念。这便是在刑法解释中开掘和释放一种大众话语,并谋求法律适用真正的价值回归④杜 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四、刑法文化解释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通过对我国刑法文化解释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刑法的文化解释并非一个创新的概念,而是长期以来就客观存在的。刑法文化解释的历史考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能够为现实社会如何在刑法领域尊重习惯提供指引。“事实上,法治秩序的建构,从来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体将法治观念加以实践的过程”⑤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546页。。
(一)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刑法文化解释概说
以礼入刑,刑法与道德相辅相成,触犯礼以犯罪论处,是中国传统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又一大特征,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在中国古代,礼最初是一种祭祀程序和规则,后来它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发展分化出一些不同团体中的礼,例如,国礼、家礼、社礼。在民间社会中,礼的代表者主要是“士”这么一个阶层。与此相对,习俗的代表者或承载者则是农、工、商三个阶层。其中,存在于农民和小手工业阶层中的礼主要是一种家礼。家礼是联结国礼,沟通国家与民间社会、士与农工商之间的一个中介。正是依靠家礼和一些类似家礼的封建礼仪,中国传统社会才得以维持一种严密的等级体系①李 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第83页。。中国古代的刑事立法之所以能够使“引礼入法、礼法融合”一以贯之,其重要理由是尊重社会文化,强调法律与社会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古代的刑法解释学是相当发达的。从秦律的“法律答问”到西汉的“引经解释”,再到东汉与魏晋的章句注释,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伴随着法律发达一路高歌猛进,至唐代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②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3页。。《唐律疏议》是法律解释高度发达的典型代表。“为了统一法律适用,解决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以后,而与以秦律为渊源的制定法之间的矛盾,从汉武帝时起便推行以儒家经义注释制定法。通过引经注律,为引礼入法开辟了捷径,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逐渐渗透于现行法中”③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从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实践来看,到处可见刑法文化立法、解释的实践。例如,《唐律疏议》关于化外人犯罪的解释:“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根据这一解释,在对域外的人适用刑法时,应考虑其文化差异。唐代距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已数百年,如果说,汉、晋律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发端,那么唐律的儒家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儒家推崇的礼,合于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因此礼的基本规范入律,取得了法律的形式,礼法关系被确认为本用关系,所谓“德以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二者被比喻为“昏晓阳秋”的自然现象,以示其永恒性。于礼以为入,既是法律的指导思想,也是注律的基本精神④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189页。。
(二)我国古代刑法文化解释的积极意义及启示
不可否认,任何年代的刑法解释都必须服务于当时的时代文化。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集中反映为大一统的皇权统治,律学所追求的统一适用法律是服务于大一统的皇权统治的。基于此,以礼释法是具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的。
从中国古代刑法文化解释的实践出发,刑法文化解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刑法的文化解释能够具有如此广大的市场,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尊重文化、尊重礼仪的社会。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冲击,这是否意味着刑法文化荡然无存呢?笔者认为,文化与人类社会是共存的。在当今社会并不是不存在法律文化,而是文化的形式予以了适度的变更。法律,包括刑法在内,均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进行刑法的文化解释,在当今社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面对我国处于文化转型时期这样一个特点,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都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协调文化的变迁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在维持法律的稳定性的同时,尤其是刑法领域,进行刑法的文化解释,其意义是积极的。经济领域的变迁对法律的冲击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法律体系难以跟上步伐,我们注重了立法应该紧跟经济发生的步伐,紧跟经济模式的变更,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大量立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但是,对文化的变迁似乎我们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文化的变更同样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域外的立法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并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效仿西方社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均发现,这些法律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结合中国的文化土壤,必将失去其生命力。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华法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法系,这与当时发达的立法技术、结合社会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客观地说,中国目前的法律地位还远不能达到盛唐时期的法律在当时世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较好地契合文化进行解释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徐光华,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江西 南昌3300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0YJC820126)
车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