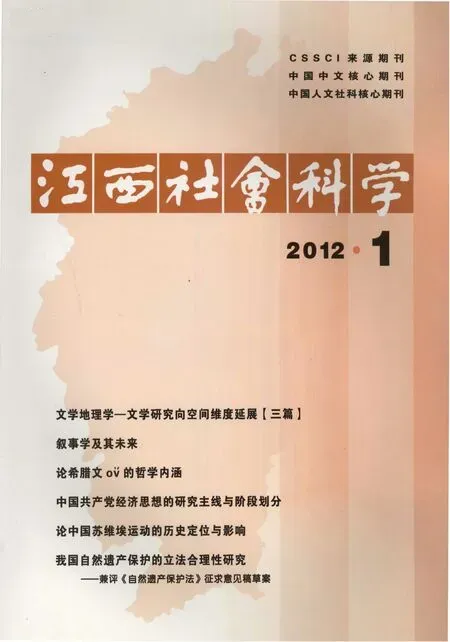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后现代创作策略刍议
■武 娜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后现代创作策略刍议
■武 娜
库切;他者;后现代;历史
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在2003年9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他在现今世界文坛上毋庸置疑的地位。尽管各种各样的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作家形象在库切的作品中被塑造成不同类型的人物反复出现,对于评论家来说,他们更希望能够把库切归类于某一传统。但对库切来说,这种希望似乎只能是徒劳。通过对其创作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库切一直都在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抗拒着各种形式的划分与归类。
一、切入后现代历史观照下的文本真实
在《双重视角》中,库切曾这样界定他对“身份”的理解:“所谓身份,首先是个集合名称,往往是某一群体声称其自身为其会员的一个标志。”[1](P200)对于“身份”二字,库切通过其小说创作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与反感,读者通过阅读也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这种抵制情绪。这种对传统的反抗在带给库切具有独特写作风格褒奖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种种非议。有评论家批评库切缺乏明确、坚定、负责任的政治立场,心安理得地认为南非长久以来所承受的不平等压迫只是南非历史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谈及有关历史与小说的关系问题时,库切曾说过:
我今天要谈一下南非的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创作其实只是一种对历史事实充满想象性的调查研究;但以现今很多学者的眼光来看,如果小说创作不履行这种功能,那么这样的创作就是缺乏所谓的“严肃性”。[1](P200)
产生以上两种理解偏差的根源在于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理解不同,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无外乎是相互独立与互为补充。当然,这两者绝不可能共存。如果小说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在特定历史时段可引发共鸣的第一手生命体验,展示奋力拼搏人物的某种生存状态,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充盈厚重,那么,小说创作与历史模式间显然只是从属关系。
如果小说只是简单地陈述某具体历史事件,那小说的地位则被消减为简单的历史补充,而不能称其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众所周知,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历史的地位作为一个较高等级的系统在本质上优越于任何文学形式,能够凌驾于任何批评风格与趋势之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注重于描写南非种族歧视与有色人种苦难经历的文学文本自然大受褒扬;相比之下,库切的作品就显得十分的扎眼另类——反对的声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在1986年库切出版《福》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年,麦克·查普曼曾这样尖锐地讽刺过这部作品:
据我们所知,在我们的自家门口有成千上万的被拘禁者企图寻求法律的支援而被当局拒之门外,而这一切以《福》的角度看来,似乎只是一次充满欢愉之情的激情释放——这无疑是知识分子圈内人被欧陆思想洗脑后的产物。[2](P335)
在20世纪80年代,库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似乎招致了南非文学圈众多批评家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会比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来得更加紧要迫切。库切的创作令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作为一名南非当时在世界文学创作圈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在南非政治局势突变的时刻,不去行使自己应尽的政治使命呼吁世界关注南非民生,而返回到18世纪的故纸堆里做文章,从这些批评家的角度看来,库切不仅缺乏敏锐的政治觉悟,更缺乏基本的伦理责任感——从作品他们似乎觉得库切总是试图卸下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与历史责任,完全置自己同胞的苦难于不顾。从根子上讲,顺着这条思维走下去,读者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库切对他者的“他性”熟视无睹,全无丝毫的敬畏与尊重——缺乏政治敏锐性就这样很自然地“被发展”为缺乏伦理责任感。
二、于竞对式创作中重构文学伦理观
面对如此这般的指责与非难,库切选择用写作进行辩驳与回击——他在《今日小说》中一篇名为《走进黑暗的房间》的文评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库切明确阐释并辨析了依附于既定的历史模式、担当历史补充剂的“补充式写作”与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竞争的“竞对式写作”的异同。读过库切作品的人很容易看出,他比较倾向于后者。库切这样说道:“‘竞对式写作’在作者须根据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与计划按步骤进行,在依次所要进行的步骤中,写作本身自能呈现出历史的独特与神秘之处。”[3](P23)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详细论述了他对两种文学创作形式的感悟与理解——对库切而言,在作品中一味地着重再现时代的暴力,如虚构各种极端痛苦与死亡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在为“暴力”建立某种不可一世的权威性。在一篇谈到依拉斯默斯《傻人颂》的文章中,库切畅谈了他所理解的作家在创作中应处的立场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援引了依拉斯默斯有关“立场”的理论。依拉斯默斯认为: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么,他就必须站在一个完全超然的角度,处在一种存于其中、飘忽其外的近乎“疯癫”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换言之,库切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依拉斯默斯“立场”论的目的在于厘清“疯癫”境界与文学立场的一致性关系,在库切看来,无论是文学立场还是“疯癫”境界与政治都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个观点在库切的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库切就用自己的文学实践来质疑因循守旧的创作模式,颠覆了历史事实与文学创作间的必然关联性,坚决捍卫了一名自主型文学创作者的伦理责任感。在库切的小说中,读者能清晰地感到他者的“他性”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至高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者甚至能够俯瞰历史。这不由使笔者想到了莫里斯·布朗绍所说的:“任何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来讲都是构筑于‘他性’基础之上的——这和任何具体的主体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4](P211-20)如果布朗绍的论断成立,我们就不难理解库切的创作伦理观了。正是基于此,库切决然不愿仅仅担任一名历史事件的报道者。在一篇名为《闭目写作:论库切小说中的策略与问题》的文章中,迈克尔·马雷通过详细探讨库切小说中所表现的政治与伦理关系问题得出结论:库切正是通过作品中潜移默化所渗透出的伦理意识在影响着读者。马雷主张:“文学文本可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历史,通过文本间接地影响读者是个不错的介入途径。”[4](P43)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质疑,从根基上动摇了“作家必须用直接介入的手段正面积极地参与到历史活动中去”[5](P74)的传统理念。但如今大行其道、涉及诸多政治性“他者”问题的后殖民理论,常把给予“他者”声音作为一场展开反话语的行为来对待;而库切则拒绝赋予“他者”某一具体的声音,因为他更倾向于“在超越历史的时间、空间内构建人物关系”[6](P65)。作为一名有着超强独立情节的作家,库切不断质疑各种具体类型的表征形式,尤其是和视觉直接相关的表现,库切认为这样的表征其实就是在试图把“他者”同化为“同一”;库切其实是在有意厘清政治与伦理的界限,用列维纳斯的理论来讲,也就是不想使“整体”溶于“无限”之中。
三、库切的坚守:探寻“他者”行将湮灭的声音
现今对库切所进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有从美学角度展开的,有从情感塑造方面展开的,也有从分析作品的历史、政治意义角度入手的。库切通过作品中对人性残酷、隐忍、贪欲、爱恨的刻画来表现人类最本真的特质与动力,尤其当人已处于濒临崩溃绝望边缘时,如何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动力,是其作品中反复关注的主题之一。当然,库切作品的非凡之处绝不仅限于此,对伦理与政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也构成了库切作品主题涉及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可构成切入库切文学创作的主线之一。库切在创作中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他者责任问题,这种责任包括个人责任、伦理责任、社会责任等众多领域。学者们对有关库切作品中所渗透的责任问题如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大卫·阿特韦尔的《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和罗斯玛丽·乔丽的《论白色南非写作中的殖民、暴力与叙事》都探讨了库切如何运用叙事策略来表现他者问题。本研究的立足点与创新之处在于从伦理的角度在纵深层次上扩展了对库切作品中“他者”以及“他性”的研究范畴,通过分析库切的系列作品对“他性”进行了深入浅出开放性的定义与阐释。
笔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伽达默尔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对历史相对的、实验性的理解是可能为人们所企及的,人自身的视阈由于历史观、人生观的拓宽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库切创作的最大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物与历史关系的独特认识,在创作中他甚至不惜把一个可能“非真实”、“被异位”的历史情境加诸于其笔端人物之上——因为他坚信,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绝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具体主观描述或某利益集团权利意志的体现,它更应包括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甚至被湮灭的“他者”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些被遗忘、被湮灭的声音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如实地体现这些声音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作家需要完成的任务。
库切的作品不像以往那些被打上“后殖民”类标记的创作一样,老生常谈式地呈现给读者西方列强是如何实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与压迫——剥削与压迫是客观存在的,是应暗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为读者所体会、感知的,但这绝不应是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库切没有选择人们所期待他走的创作之路:从不同角度描述南非所经历的沧桑与不幸,白人如何惨无人道地实施对有色人种的剥削与压迫,给别人包括他们自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等等。库切认为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完全毋庸赘述的东西。相反,那些事实的成因与人们在这场浩劫中所承受的种种才是真正需要呈现给读者的:“他者”是如何被历史隔离、疏远、直至湮灭,如何用不确定的指称于残缺的叙事中淋漓尽致地再现这些,如何在叙述这些的同时建立起作家的权威性与责任感,才是真正重要的。
库切创作的最大特质之一莫过于他对权威性主导伦理观的持续排斥,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读者远离各种预设性观念,着力给予长期被忽视的“他者”自己的声音、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那困惑复杂的人道主义情节,《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迈克尔·K的遁世策略,《福》中苏珊·巴顿的迂回曲折的创作磨炼历程,《耻》中大卫·卢里令人费解的人生选择……这些无疑都给读者留下了最大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1]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David Attwel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Blanchot, Maurice.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Trans.Susan Hans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3]Blanchot, Maurice.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of Art.In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Ann Smock,211 -20.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4]Marais,Micheal.After the Death of a Certain God:A Case for L vinasian Ethics.Scrutiny 2:issues in English Studies in South Africa.Vol.8,no.1,2003.
[5](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本文对库切在国内外批评界所引起的喝彩与争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库切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他者“他性”的关注是造成其作品争议的焦点所在。库切使文本与他者的关系不拘泥于所谓的历史真实,并始终在创作中坚持文学应以体现“他性”为前提,后结构主义看似绝对的怀疑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伦理观的坚守,因此,库切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他者“他性”的关注,在实质上拓展了主体对自我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I106
A
1004-518X(2012)01-0119-03
武 娜 (1978—),女,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河南郑州450001)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后现代阐释学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KL-2011-1495)、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库切边界诗学创作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0BS06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