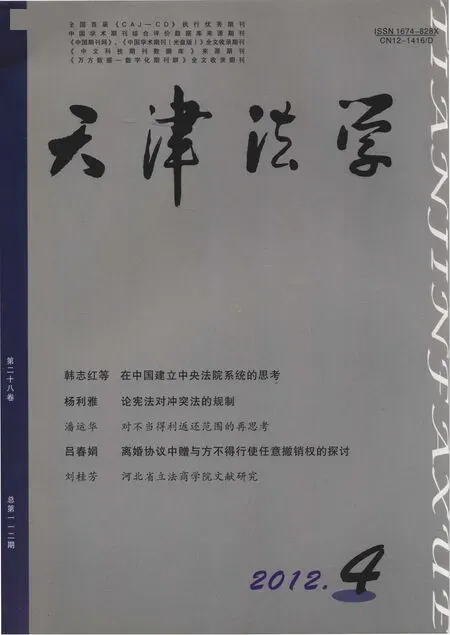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与作用的反思——一种刑事政策学意义上的观察
张曙光
(井冈山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引 言
1988年1月,为了惩治我国社会日渐严重的腐败现象,我国立法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国情,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法中创制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最初,人们称其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对其寄于厚望[1]。1997年新刑法将该罪名略作修改后作为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第395条第1款规定①。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又对该罪做了重要改动,除了对罪状的表述进行修订外,主要在原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法定刑基础上,增加了“差额特别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规定。现在,该罪已成为我国反腐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常用罪名,与贪污罪、受贿罪等罪名一起频繁出现在人民法院惩治贪污贿赂分子的刑事判决中。
然而,随着该罪在实务中适用的常态化,该罪“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的美誉渐少有人提。相反,20余年来人们对该罪的质疑非议、呼吁修改完善乃至废除的意见屡见诸报刊文章,甚至许多人一度称其为贪官的“保护伞”、“安全岛”、“避风港”等。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对该罪法定刑的提高其实就是对上述舆情民意的回应,但似乎并没有使人们要求对该罪进行变革的议论平息多少。
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不能止息的人们关于该罪的种种非议和持久焦虑,反映出该罪在现实中的实效与人们的期待仍有较大距离。这可能不仅仅是该罪罪状如何完善和法定刑是否提高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到该罪在整个反腐斗争中的基本作用问题乃至该罪在整个反腐斗争中的基本地位问题;不仅是其在刑事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其在整个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该罪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为该罪未来可能的立法改革提供参考,我们有必要对该罪在我国现行反腐制度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检讨,必要的话提出调整建议。
一、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和作用的立法描述
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事政策目的(或立法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对此,原立法机关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做过清楚的说明:“近几年②,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个别财产来源不明的‘暴发户’,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不是几千元,而是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更多,本人又不能说明财产的合法来源,……对这种情况,首先应当查清是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或者其他犯罪所得,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罚。但有的很难查清具体犯罪的事实,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不好处理,使罪犯逍遥法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属于犯罪。因此,草案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说明,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本规定只是对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才要求说明来源”③。根据这一说明,我们不难确定在立法目的意义上该罪在我国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
首先,该罪是我国刑法反腐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立法者为了弥补传统反腐制度体系的缺陷和功能不足,借鉴国际经验,在刑法中创立的一个“新”罪名,具有我国制度特色。从各国经验来看,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要依据财产申报制度而确立,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是财产申报制度在刑事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延伸。我国迄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该罪主要依据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确立,它根源于刑法反腐制度体系,属于刑法反腐制度体系,并立足于此发挥其特殊的反腐作用,是对我国刑法反腐制度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
其次,该罪的基本政策作用在于避免放纵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些贪腐犯罪行为(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等),解决一些上述犯罪司法证明难的问题,最终起到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2]。这是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第二个特色。在该罪确立之前,我国司法上常因难以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差额巨大”财产的具体来源而无法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的情形,要么可能放纵犯罪,要么使案件久拖不决。有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上再遇到难以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部分具体来源的情形,就可以以该罪进行折中惩治,避免使犯罪逍遥法外或司法上因证明困难而使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形,并提高司法效率。
其三,在刑法反腐制度体系中,相对于其他贪腐犯罪(如贪污、贿赂罪),该罪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发挥着补漏性、堵截性的作用。这应是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第三个特色。如前文所引,实务中有时难以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差额巨大”财产的具体来源,以致无法按传统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使罪犯逍遥法外”,为了避免此情形出现,立法机关确立该罪进行补漏、堵截。这使得该罪与关联犯罪之间存在着地位上的主次关系和适用上的从属关系。具体而言,在刑法反腐制度体系中,贪污、贿赂犯罪仍发挥着主要的反腐作用和功能,处于主要的体系地位,该罪只是起到次要的作用,处于次要的体系地位。在适用时应考虑优先适用其关联犯罪,如果不能适用关联犯罪才适用本罪:“首先应当查清是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或者其他犯罪所得,依照刑法规定处理,”对于不能或难以查清具体来源的,不得已才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在笔者看来,该罪没有自己独立的诉讼程序,在程序意义上它是司法机关在追究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以及其他非法取得财产犯罪的诉讼中“副产品”,是追究其关联犯罪同一诉讼的“半成品”[3]。该罪的这种实体地位、功能和程序上的从属性,是由该罪的刑事政策目的所决定的。
最后,尽管同其他国家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该罪采用较低的法定刑,但是该罪的刑罚目的或者说其直接作用主要是为了惩治,即为了避免放纵犯罪,“防止罪犯逍遥法外”,而不是预防。在这点上,与其他各国财产申报制度中的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功能作用明显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预防,通过保障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来避免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
可见,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根据我国特定国情、出于特殊的政策目的而确立的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罪名,它在我国刑法反腐制度体系处于特殊的政策地位,担负特殊的政策作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存在,显然有其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也有其合理的立法背景。但是,随着该罪在现实中常态化的适用和我国社会的变迁,这种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罪名能否适合我国反腐斗争的整体需要呢?
二、我国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和作用的实务检讨
前文已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目前已成为我国刑事反腐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常态化罪名。一方面,笔者认为,20余年的司法实践能够确证该罪在我国反腐斗争中具有上述特殊政策地位和作用:一是许多案件典型地表明设置该特殊罪名的必要性、合理性。如原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啜文对300万元存款拒不说明来源,人民法院审了一年多也不能查清其具体来源,最后一审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在该案中,如果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像本案的结果很可能对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这就可能完全放纵了犯罪。而有了该罪,犯罪人就受到一定的惩治。在本案中,该罪起到了防止放纵犯罪、解决证明困难的作用。再如,海南省原东方市市长戚火贵,家里现金几千万都粘在一起了,因为他不用,也不去数,根本无法记起具体的受贿情节、人员、数额,除了部分查明外,尚有大部分“不能说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那么,司法机关就会因无法查明这些非法财产的具体来源放弃对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然而,因为有了该罪,司法机关就能够对其不能说明部分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二是“这一罪名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单独使用过,而基本依附于贪污、贿赂罪等主罪”[4]。这充分表明该罪在刑法反腐制度体系中的从属性、次要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少数案件虽仅判处某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是在追究其关联犯罪未果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结果,如山西“啜文案”。三是司法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的效率明显提高,像过去那样因难以查证财产的具体来源而使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不存在了,这说明该罪确实在实务中发挥着其提高司法效率的政策作用。所以,就立法者确立该罪的政策初衷来看,该罪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与刑事政策对其的地位和作用期待基本吻合的。
但是,另一方面,该罪在适用中也暴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现象或问题,这些现象或问题引起许多人对该罪的反腐实效乃至其在反腐斗争中基本地位的质疑:
第一,该罪在实践中被“异常”频繁地适用。立法机关确立该罪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贪污、受贿等关联犯罪的一种补漏性、堵截性的罪名,使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贪腐行为在证明困难以按关联犯罪进行追究的情况下,亦能给予一定惩治,并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是不得已补充性的罪名,而不是主要适用罪名。另外,由于该罪的实质和较低的司法证明要求决定了该罪只能规定较轻的法定刑,通过该罪惩治贪腐行为的力度有限,其惩治不能不说是象征性的。这两方面决定了,在整个反腐斗争中,按贪污、受贿等贪腐犯罪追究比例越高,说明反腐效果越好,相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越多,反腐效果越差,人们乐见其少量的偶然适用,最理想的状态是无须适用。但是,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该罪的适用已是一种惯常的情况,适用之频繁为各国罕见[5]。特别在一些案件标的较大的案子里,该罪基本伴随贪污、贿赂等犯罪一同出现。该罪在司法实务中作为一种“常见”的、被大量适用的犯罪,实际是对司法现实的一种“嘲讽”——这意味着大量的贪腐犯罪得不到应有的、真正的刑事惩治,只能退而求其次按该罪来进行象征性的处理,在案件标的异常巨大的情况下,该罪的惩治效果微乎其微。
第二,该罪在一些案件中“异化”为贪官的“保护伞”、“避风港”等。同国外的财产来源不明罪相比,同样是规定了较低的法定刑,但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求“来源不明财产”数额巨大的条件才可能入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这一标准是30万元以上)。而在司法实务中,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财产”数额往往又远超出这个最低标准,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相对于此,该罪较低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前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其惩治未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又由于该罪与贪污、受贿等罪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一些贪官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进入诉讼程序后通常都“有意识地”患上“健忘症”,“不能说明来源,”实际是把该罪作为自己逃避更为严厉惩罚的“避风港”、“安全岛”或“免死牌”。例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因贪污、贿赂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5年有期徒刑等。其中,夫妇俩共同受贿折合人民币120余万元,另有1200余万元无法说明来源。尽管“不明财产”数额是受贿数额的十倍,但只能判处5年的最高刑期,且被受贿罪、贪污罪的量刑吸收,对实际刑罚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犯罪人说明了来源,依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相形之下该罪无疑成了“安全岛”。
其三,现行该罪的特殊地位、作用和适用机制,给司法惰性甚至司法腐败“预留”了可能的发生空间。该罪是一种从属于其关联犯罪的补漏性、堵截性的轻罪,在司法实务中要优先追究其关联犯罪,在司法机关不能查明“差额巨大财产”具体来源的情况下,才适用该罪。从追究其关联犯罪“转处”追究该罪依赖于司法机关的程序操作。实务中存在个别司法工作人员因为司法惰性不去积极追究关联犯罪的情况,甚至在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明了具体来源情况下,也不去认真核实,直接按照该罪处理,完全背离了确立该罪的政策初衷。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转处”机制给了一些“法官、检察官乃至公安、纪检等调查机构”一定的“勾兑空间”[6],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借机进行权力“寻租”,这种现实无疑进一步促使了该罪沦为贪官的“保护伞”、“避风港”,加剧了人们对该罪适用的批评。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认识上分化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罪未能令人满意地起到预期的遏制犯罪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异化”为贪官的“保护伞”、“避风港”,主要原因在于该罪法定刑过低、惩治力度过小,应该提高该罪法定刑幅度,从而使贪官们得到有效惩治,并消除其侥幸心理。这种观点在专家学者、实务部门中有较大市场,也反映了一定舆情,导致了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的修改。但是,这并仍未能彻底平息这种意见,许多人认为该罪应当继续提升量刑幅度,“直至死刑”。第二种意见认为该罪自被确立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在现实中也未起到预期的遏制腐败犯罪的作用,反而自身沦为贪官的“保护伞”,甚至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某种“契机”,因此不如取消或废除该罪[7],或是建议“以贪污、受贿论处”[8]。第三种意见认为该罪未能发挥人们所预期其作用、目前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根本上与缺乏相配套的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有关,如果我国确立了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需要该罪来防堵,剩下的贪官也可能没有拥有那么多财产,也不会因为财产的数额超大与量刑有限形成的强烈反差。因此,认为确立被誉为“阳光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治本之策[9]。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意见承认该罪的实际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认为该罪法定刑过低是导致其该罪适用效果不彰、试图通过再提高法定刑幅度来解决问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反腐利器”声誉的获得,不在于各国立法规定的法定刑多么严厉,而在于该类罪名因为其成立条件、证明内容简单而具有涵盖性、防堵性,使那些即使逃避了传统罪名(如贪污、贿赂)追究的贪腐分子最终还是难以通过最后一关,在于该类罪名既能事前打消一些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又能事后对其进行一定惩治。其次,各国(地区)立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规定来看,法定刑一般都是较低的,重者一般不超过10年(如新加坡),轻者只有1年(如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各国立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普遍采取较轻的法定刑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在于该罪的严重性是有别于贪污、受贿等犯罪,因为不明的财产来源可能是多样的,既有可能是贪污、受贿得到的,也有可能是其他非法(如盗窃、走私等)渠道得来的,也有可能是合法获取的而确实难以记清的,在处理上应当有别于贪污、贿赂罪等;二是各国确立该类罪的价值抉择上都存在强调打击犯罪的功利需要而牺牲一定的实体和程序的公正性,典型的如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该罪是在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或拥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的抽象、推定意义上确立的,它省略了进一步查清具体非法来源的证明要求,是以丧失实体和程序上某些正当性来满足司法上打击犯罪的功利要求,可能导致伤及无辜,在这种情况下,对此类犯罪规定严厉的法定刑是不适当的;三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虽然号称“反腐利器”,但是从整个反腐斗争制度体系来考虑,不能过于期待这种罪名发挥多大效果,在根本意义上它只是一种次要的、补漏性罪名。所以,那种认为该罪法定刑过低并呼吁进一步提高该罪法定刑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意见看到该罪立法规定本身的问题引发人们长期争议,看到该罪在实务中也出现诸多问题,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因此完全否定该罪存在的必要性,则是以偏概全的片面立场。事实上,刑法分则中没有争议的罪名是罕见的,而且本罪的许多争议问题来源于本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规定,存在如何从理论上合理解释的问题,没有必要夸大其争议性;而对于该罪在实务中产生的许多“特色”问题,完全将其归结于该罪本身是不公正的,许多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罪特殊的制度适用环境导致,如由于缺乏财产申报制度导致实务中过多贪腐犯罪(下文将具体说明)。而且,该罪在实践中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因为法定刑幅度的限制,对一些犯罪处罚较轻,但是毕竟是进行了一定的惩治,这比完全放任不管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设立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各国刑法制度反腐的重要经验和潮流,是“阳光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节,我国虽然未能确立财产申报制度,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该罪存在的必要性,相反,应当肯定其存在的意义并针对其问题进行完善。
笔者基本赞成第三种意见。从各国反腐经验和立法做法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种犯罪类型本来就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内容[10],该罪也依赖财产申报制度的行政义务内容作为立法和司法适用的前提,这种财产来源不明罪不是追究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走私等非法获取财物犯罪的“副产品”,不从属于这些罪名,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并与它们并列。由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存在,国家公职人员(或其家属子女)的财产、支出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这就能规范公职人员的日常行为,防范公职人员涉嫌贪腐行为,或涉嫌贪腐行为后防止任其发展,大大减少公职人员贪腐犯罪的数量和严重程度。此外,在司法实务上,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助于提供追究贪腐行为的事实证据、查明非法所得的具体来源,因而能够按照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处理。在上述情况下,需要以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理的只是少数,难以出现大量频繁适用的情况,由于犯罪行为能够及早发现也难以出现涉案金额巨大的案子,也避免该罪沦为贪官的“保护伞”、“避风港”。
与此相对照,我国因为缺乏财产申报制度,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变化情况得不到及时的监控,任其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必然加重刑事制度反腐的压力,而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犯罪行为通常具有私密性质、过程复杂,发案时又往往时过境迁,难以查证,这就不得不依赖该罪进行防堵,而该罪的法定刑幅度较低,面对汹涌而来的腐败犯罪浪潮,该罪的防堵“效果不彰”是显而易见的。在立法层面,缺乏财产申报制度必然使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功能定位于作为追究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替补性、补漏性罪名,而不能作为一种常态的财产监控和申报制度的保障性罪名,在其实际发生机制(即刑事诉讼)上,也不能不从属于追究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诉讼程序,成为其“副产品”,所以,由于财产申报制度或类似制度的缺乏,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反腐功能定位和作用是天生就是有局限。
可见,我国特色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现实反腐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是需要肯定的,因为其达致了立法确立该罪的基本目的,即在司法实务中发挥了严密刑事法网、防止放纵犯罪、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尽管其作用效果没有如人们所愿,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该罪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该罪自身的存在和设计的问题,而是整个反腐制度体系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缺乏财产申报制度的支撑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废该罪,不在于是否加大该罪的刑罚量,而在于尽可能早日确立财产申报制度,以促使该罪在整个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归位”。
三、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和作用的重塑
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八五”立法规划。1995年4月30日、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的行政规范文件。此外,个别地区还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等等[11]。虽然这些党纪政纪文件仍属于政策性文件性质,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律制度,这种制度的创建也显得有些缓慢,但是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落户将是迟早或晚的事情,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创建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④将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有利于建立科学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将极大促进反腐倡廉事业走向胜利。就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言,将使立法机关重新确定该罪在刑事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甚至罪名本身也因此做相应调整。本文这里也略加探讨:
首先,应重新确定该罪的政策地位和作用。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前提,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刑法中追究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关联犯罪的从属性、堵漏性罪名,即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因为国家工作工作人员对其拥有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实际是司法机关不能查清来源)而无法追究贪污贿赂等关联犯罪的情况下,才能够以该罪论处[12]。其作用价值在于一定程度上严密刑事法网、防止放纵犯罪、提高司法效率。而确立严格意义的财产申报制度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能够“摆脱”上述关联犯罪的“束缚”回归本位,直接与财产申报制度发生关联,也可以成为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法体系中成为与贪污、贿赂等反腐罪名并列的独立罪名。这样一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作用不仅仅发挥堵漏性的作用,也有相当的惩治意味,而且还为财产申报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用“财产来源不明罪”取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成立,必须事先存在“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的前提条件——非此不能称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有权机关”才能责令其说明来源,如果“不能说明来源”,“差额部分”就以“非法所得论”,最终在“持有非法巨额财产”或“非法持有巨额财产”的意义上成立犯罪。这里要求“巨额”是为了增加该罪确立的法理基础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制约,行为人无法说明或不愿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对其惩治可能伤及无辜,而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的财产,那么,这种伤及无辜的可能性将会减少。但是,这样一来,就提高了该罪成立的“门槛”,也束缚了该罪充分发挥反腐作用。确立了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常规的日常监控和审核,如果一旦财产有所异动且不能说明来源,那么就其来源非法性是确定的,可以设立“财产来源不明罪”以追究刑事责任,该罪立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坚实的。“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治范围显然远远超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范围,更具有适用效能和威慑力。
再次,应当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确立了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就能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避免“出现像今天这么多的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尴尬现象”,能够避免出现越来越多的贪官一到刑事诉讼中就得了“健忘症”而使该罪“沦为”贪官的“避风港”、“安全岛”的“奇特景观”,立法机关也不必面临着提升该罪法定刑的压力。相反,由于案件减少、不能说明财产数额低,立法者可以考虑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特别是确立“财产来源不明罪”取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情况下,更应当根据该罪的新政策定位和作用降低其法定刑幅度。
最后,从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分解出拒不申报(包括拖延申报)财产罪、申报不实罪。根据司法解释,现行刑法395条第1款中的“不能说明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治行为条件,包括拒不说明、虚假说明、无法说明、说明不具体等的四种情况⑤,是个小“口袋罪”。“拒不说明”、“说明不实”的行为方式应是有别于“不能说明”这种情况的,但是由于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因而,不能在违背申报义务的意义上予以定罪,而也建立在推论的非法持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意义予以定罪。这不仅存在法理正当性的瑕疵,而且也因为巨额的条件限制,不能有效防范犯罪。有了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对拒不说明、说明不实行为的追究,就可以建立在违反申报义务意义上,即单独确立拒不申报财产(包含拖延申报)罪、申报财产不实罪的罪名,这样做法理正当性更为坚实,更具有威慑力,反腐效能也大,也能对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效保障。
总之,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原来在反腐斗争中具有探索意义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应当不断进行嬗变,以适应时代需要。其中,最为可行的是,在财产申报制度确立后,该罪应进行全面的变革。
注 释:
①该罪量刑部分由原来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修改为“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②这里指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即上世纪80年代。
③这是1987年11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惩治走私罪和惩治贪污罪贿赂罪两个补充规定(草案)的说明》发言的部分内容。在该发言中,王汉斌同志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背景、立法原理、立法目的、条文实质等做了较清楚的说明。
④一般而言,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应按照申报公开、强制申报和如实申报三大原则确立。
⑤详情可见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法(2003)167号《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于当日正式生效。
[1]储槐植.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 [N].法制日报,1989-12-15,(3).
[2][9]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线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张曙光.持有论:行为、犯罪和诉讼[D].北京: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EB/OL],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32132.htm,2012-08-13.
[5][13]杨兴培.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J].政治与法律,2005,(5):2.
[6]童大焕.刑法应废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N].东方早报,2008-08-26(A22).
[7]李乔.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废除[J].法制与社会,2011,(10):24.
[8]王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如取消 [N].信息时报,2008-08-26,(A13).
[10]赵秉志,赫兴旺.论中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完善[J].政法论坛,1995,(5):19.
[11]卢乐云.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制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8):146.
[12]张曙光.持有的本质——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的分析[J].刑事法评论,2010,(26):438-442.